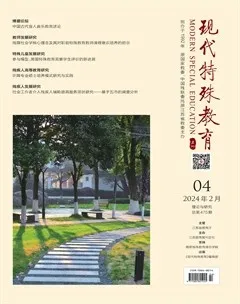殘障社會學核心理念及其對職前特殊教育教師課程意識培養的啟示
劉修豪 曾雅茹

【基金項目】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大學生對殘疾人社會的越界理解研究”(20YJ880032)研究成果。
【摘要】 殘障社會學發展經歷了傳統的殘障社會學、批判的殘障社會學、后現代殘障社會學的演變。借鑒殘障社會學核心理念分析其對特殊教育的影響,有利于增進職前特殊教育教師對課程的理解,有助于職前特殊教育教師培養“遭逢”的課程意識、“跨越”的課程意識、“處境”的課程意識。
【關鍵詞】 殘障社會學;課程意識;職前特殊教育教師
【中圖分類號】 G760
【作者簡介】 劉修豪,教授,泉州師范學院特殊教育系(liu15260786300@qq.com,福建泉州,362000);曾雅茹,教授,泉州師范學院特殊教育系(福建泉州,362000)。
一、前言
特殊教育關注殘障學生的特殊需要,廣泛運用醫學、心理學、教育學、康復訓練等學科理論來指導特殊教育實踐。這深刻影響到職前特殊教育教師(以下簡稱“職前教師”)的培養,導致職前教師課程認知視角較狹獈。特別是容易導致對殘障學生“弱勢”“低能”等污名化與歧視。因此,職前教師培養亟待開拓新的視野。
課程意識支配著教師在教育中的行為方式、存在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課程意識的形成能塑造教師的課程觀,以及反思性的實踐能力,進而深化其對殘障的理解。殘障是一種復雜的、多維的現象[1]。然而殘障社會學因理解殘障的范式不同而有不同的立場及理念,范式轉換也表明殘障社會學有著不同的歷史內涵,這可以為職前教師培養特別是對其課程意識的多元理解提供有益的啟示。
二、殘障社會學發展脈絡及其核心理念
國內對殘障社會學理論的探討,始于1989年續西發、1990年馬才華、1992年奚從清等人以個人經驗總結探討中國殘疾人社會學的內涵[2-4]。2005年于松梅及孫琪等人以社會生態系統為理論基礎,轉向新的殘障認識[5];2009年陳璇從融合教育背景轉向對殘障社會學的理解;2015年楊柳概述了理論模式,但并未深入理解殘障社會學的核心[6]。直至2018年李學會從社會學角度系統地探討殘障研究的演變[7],殘障社會學研究再次被重視,并走向深入。2019年陳昫引介了國外對殘障文化的多元解讀[8];2021年《殘疾人研究》也于第3期開設殘障觀點辨析的專欄,討論個人模式與社會模式[9],以及介紹新一代殘障觀點[10]。
上述研究多以自身專業視角強調殘障意義的一個側面,不易反映該學科演變的全貌及重要人物的核心理論,且解釋議題不盡相同,較少能與特殊教育交相輝映。本文擬透過西方文獻梳理殘障社會學的發展脈絡,分析比較殘障社會學所討論的核心理念(見表1),及其對特殊教育的影響。
(一)傳統的殘障社會學:從本質論轉向社會建構論
1.發展脈絡
殘障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可以追溯到涂爾干(?mile Durkheim)。涂爾干將“殘障者”相對于“正常”和“病態”來看待。后來,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關注“病態角色”,首次提出“疾病的社會”和“病人的社會角色”概念。他認為醫學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整合和控制機制,而疾病的發生就像是一種脫離社會規范的偏差行為(越軌行為),使得病人暫時脫離其原來的社會角色。然而,這個社會角色必須接受醫療的建議,并盡快脫離[11]。
20世紀50年代開始,傳統的殘障社會學家受到結構功能論觀點影響,通過醫學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的狹隘視角(偏差視角)來研究殘障問題。這些視角傾向于將殘障者病理化,以身心傷殘的個人或以殘障者遭遇障礙的社會制度作為分析單位,謀求醫學或社會的干預方法[12]。代表人物納吉(Saad Z. Nagi)提出“殘障者功能限制”觀念,運用“角色理論”解釋殘障者遭受限制的原因:主要由于其各種身心條件限制,讓他們在不同人生階段,無法獲得社會對他們角色期待的滿足。此種差距可以在各種文學作品、劇作、詩集等中看到負面、悲慘、可憐、凄苦的生活經驗描述。因此,大眾對殘障者的社會理解,就容易陷入這種刻板的印象中[13]。
這些社會學家往往從本質論角度解釋殘障,將殘障定義為一個特定個體或團體所具有的先天的、固有的或不可或缺的核心屬性,這些屬性被用于與其他團體進行區分(如健全與殘障)[14]。
直至60年代,戈夫曼(Erving Goffman)進一步討論殘障意涵的社會建構過程,以“符號互動論”反省偏差視角的社會。戈夫曼認為“污名化”是屬性和定型觀念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因為在人與人之間產生的差異標簽通過互動成為污名,最終導致被污名化的社會建構。污名化使殘障成為社會學的話題,殘障對個體而言是帶有污名色彩的“異常”身份,是社會對“身體憎惡”(abominations of the body)的反應。以殘障者為例,由于殘障身體的疾病或畸形威脅了人類對于完整性、健全性的一致追求,致使人們經常將此類對象視為不完整的個人。因此,身體傷殘者的污名化是一種社會分類的手段,也是一種社會認同的形成過程[15]。
2.核心理念
傳統的殘障社會學蘊含了從早期的本質論轉向社會建構論的理念。本質論把殘障解釋為由于先天的身體功能或結構傷殘而導致個人缺陷、異常的現象,把殘障與疾病(病態)混為一談。社會建構論則強調殘障是社會結構強加在傷殘者身上的一種差異所造成的歧視。醫學社會學者或醫師等人擁有殘障的知識話語權。他們對殘障側重于處理特殊的病理問題以及個人差異和社會環境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障礙問題,如采取診斷、分類、干預或隔離等方法解決個人及社會問題。然而當傷殘的身體標識為“殘障”的社會身份時,是否表示所有殘障者將前仆后繼、心甘情愿地走上這個社會位置?事實上,這游移在成為或不成為殘障身份之間,還有各種異議的紛擾。
(二)批判的殘障社會學:從殘障行動主義轉向唯物論
1.發展脈絡
20世紀70年代,出現一股對殘障重新定義的聲浪。1972年美國肢障人士羅伯茨(Edward Roberts)發起的獨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最終演變成殘障者權利運動。該運動挑戰殘障者面臨的教育障礙,支持其自主決定獨立生活,反對傳統侵犯性和剝奪式的治療方法,呼吁立法保護殘障者免受歧視待遇,在美國民權理論中形成了一個平等機會的新理念[16]。與此同時,英國的“肢體傷殘者反隔離聯盟”(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簡稱UPIAS)首先區分殘障和傷殘的概念,并提出了殘障的社會模式,英國政府在該模式挑戰傳統殘障觀點的沖擊下,于1978年召開著名的沃諾克會議,提出“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取代“教育遲緩”(educationally subnormal)的概念,質疑特殊教育的醫學、心理理論框架的合法性,反映社會、教育環境與官僚體制所帶來的不平等。
殘障行動主義的興起,使得特殊教育不再僅是醫學、心理學領域的專利,但因其隱含的政治色彩遭致許多社會學家的批評,造成80年代特殊教育學界出現風起云涌的社會學觀點,殘障研究也成為社會學的一個獨特子領域[17]。如1986年美國殘障研究學會(The 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成立,出現諸多社會政治背景下的殘障研究,其中佐拉(Irving Zola)大膽敘述自身的殘障問題,并進一步探討助長殘障者被隔離、被邊緣化的社會背景。這些研究作了殘障的政治分析,揭示殘障者的不平等待遇。1990年《美國殘障者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即在此氛圍下通過,掀起新一輪殘障研究學術浪潮,擴大了批判的力量及范圍[18]。
唯物論的英國代表人物奧利弗(Mike Oliver)認為,殘障不能僅歸因于個人,而是源自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因素,所以殘障者面對的壓抑也反映出社會階級地位的不平等[19]。其在著作《殘障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中指出,殘障在社會結構中作為一個病態的類別,正是因為殘障者無法滿足資本主義對個人勞動的要求而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話語受到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和殘障者不如健全人的文化形象所制約,“修復問題”成為特殊教育專業的重點[20]。
巴頓(Len Barton)對殘障研究和特殊教育領域有開創性的見解,其著作《特殊教育需要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觀點。在這場殘障政治和融合教育的斗爭中,政治分析極為重要[21]。巴頓認為殘障是由于能力主義所造成的社會排斥,疾病和殘障問題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他認為,批判“特殊需要”這樣的辭令貌似反映人道關懷,實則是一種與既得利益相關的控制措施,已成為那群能夠定義和形塑特殊教育系統的掌權者掌控的一種合理化過程。
湯姆林森(Sally Tomlinson)首次將新馬克思主義的沖突論、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引進特殊教育領域,其在著作《特殊教育的社會學》(A Sociology of Special Education)中表達了一個極具批判性的理解,她說“國家特殊教育的社會起源絕對可以追溯到普通學校想將那些缺陷以及會造成問題的殘障者進行隔離的需求因素,因此特殊教育被視為一個讓普通教育更順利發展的安全價值”[22]。換言之,在資本主義持續發展過程中,將學生分類后,特殊學生被隔離出普通教育系統,普通教育的運作即可更加順暢,并經由教育系統的資源分配控制,達到整體社會控制的最終目標。
2.核心理念
批判的殘障社會學蘊含了從殘障行動主義轉向唯物論的理念。隨著殘障運動興起與關注焦點的轉變,這種范式被殘障者權利組織引入英國和美國,提供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強調了對殘障和權力的物質關系的政治分析。批判的殘障社會學基本上暗示了三個假設。首先,殘障是社會不平等的一種表現,殘障者是受歧視和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的少數群體。第二,傷殘和殘障需要區分,不存在因果關系;導致殘障的不是傷殘本身,而是“障礙”的社會。第三,消除殘障者面臨的障礙是社會的責任。因此,殘障知識的話語權來自殘障運動倡導者及批判社會學者,對殘障關注的要點在于解決由制度形成的排斥,以及嵌入社會實踐的文化態度所導致的壓迫和歧視問題,最終目的在于揭示不平等的現象。批判的殘障社會學更直接挑戰特殊教育范式,批判專注于個人缺陷和補救措施的合理性及融合教育的內在矛盾。
(三)后現代殘障社會學:從多元文化主義轉向文化認同
1.發展脈絡
20世紀90年代,殘障社會學領域越來越接受多樣性、交叉性和跨學科的研究范式。殘障社會學受到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的影響,挑戰著現有的理論。從早期醫學社會學對殘障的本質主義論述,歷經批判殘障社會學的唯物主義反省,再到近年來后現代主義關于身體“體現”的討論,憑借殘障經驗為中心的文化分析及話語分析方法,以凸顯殘障者的聲音,使得殘障群體文化、殘障美學也逐漸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英國利物浦大學《文學與文化殘疾研究雜志》(Journal of Literary & Cultural DisabilityStudies)在2016年慶祝創刊十周年,見證了殘障研究的“文化轉向”。殘障觀點的擴散引領殘障社會學開始對殘障問題進行多元的反思,并開展“新的殘障研究” [23] 。
穆拉利(Bob Mullaly)在其著作《挑戰壓迫和對抗特權》(Challenging Oppression and Confronting Privilege)中認為,文化政治研究有助于挑戰主流文化,促進殘障文化變革與理解。文中提到歧視是個人、文化和社會結構層面上相互關聯的運作。其中,文化層面的壓迫來自集體的價值觀、規范、思維和行為模式,它們共同支持優越文化的信仰。因此,為了克服文化帝國主義,受壓迫的群體必須定義自己的身份,積極維護群體差異感[24]。穆拉利以“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作為克服壓迫的手段,避免本質主義的分類。缺乏對差異的認識只會讓強勢群體的觀點和規范更顯普遍,從而使文化帝國主義長期存在,將被壓迫的群體視為具有特殊性的“他者”。顯然,差異政治方法作為發展殘障群體的聲音、語言和觀點的工具,可支持殘障者的自我組織,從而挑戰主流機構。
受女權主義及后殖民主義啟發的莎士比亞(Tom Shakespeare)認為,殘障者已被戲劇、文學、繪畫、電影和媒體等文化表征所“物化”,成為一種文化特質,勾畫出殘障者和健全者之間如同殖民者(幫助者)和被殖民者(受助者)的照護關系[25]。莎士比亞質疑“他者”作為殘障的另一種形式,在文化中以何種方式(再)產生。要回答這些問題,應該將文化作為分析工具充分地融入殘障研究。另一位后結構女權主義者加蘭·湯姆森(Rosemarie Garland Thomson)通過解構現代主義所描繪的殘障敘事中的正常/異常二元關系,認為殘障是身體在空間和期望中不協調時導致的變化,產生殘障身份的“凝視”(gaze)[26]。此種凝視涉及凝視者與被凝視者之間的權力關系,更是一種雙重體驗,即一方面觀看影像中展現的客觀世界,另一方面又把這影像轉化為我們對這世界的認知。這說明殘障者主動凝視影像并根據自身的認同來建構影像,同時又根據影像重新評估自我的身分認同。
身體的文化表征與人們經歷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影響殘障者生活條件以及社會的差異建構至關重要。希伯斯(Tobin Siebers)基于“殘障美學”(disability aesthetics)的認識論,拒絕承認健全身體的表現,以及它對和諧、完美的唯一定義。相反地,有別于傳統審美標準的“破壞之美”也是一種平凡(unexceptional)的藝術,一種不能達到理想卻姿態尚存的藝術[27]。古德利和科爾(Daniel Goodley & Katherine Runswick Cole)以后人文主義視角提出“殘障/人類”(dis/human)概念,一方面承認殘障所帶來的不便,以及對人的價值的否定;另一方面基于殘障者的人性渴望,重塑人類的可能性,企圖發展出“后人類”(a post-human condition)的理解。換句話說,殘障是一種能照亮人性與殘疾的現象[28]。
2.核心理念
后現代殘障社會學蘊含從多元文化主義轉向文化認同的理念,此種理念完全不同于前述傳統的及批判的殘障社會學,二者一致視殘障為“與問題有關”,因此傳統的殘障社會學欲解決因自身缺陷帶給社會的“個人問題”,以及與社會環境互動所呈現偏差的“障礙問題”。批判的殘障社會學則企圖解決牽涉各式權力斗爭中所引起的壓迫和歧視的“社會控制”。然而后現代殘障社會學并不是試圖“修復”殘障問題,而是通過殘障者對自身經歷采取的行動及反思,呈現與主流文化的對話與抗衡。基本上,殘障的概念來自于“官方文本生產者”(official text producers),這些生產者擁有更多的資源、機構支持和話語權威,加強了已在文化傳播中的意識形態結構[29]。后現代殘障社會學認為,每個殘障者的經驗都是獨特的,殘障者不應該被視為社會排除或救濟的對象,而是作為社會多樣性的一種,屬于多元文化的一環,透過尊重差異及文化認同的建立可提供一個殘障社群的溝通機會。殘障的知識話語權必須來自殘障者本身,因為圍繞殘障的社會話語可能被解讀(confirmed),但并不被理解(interpreted)。特殊教育需要通過多元視角及文化思考殘障者如何透過自己的身體回應社會對他的詮釋與作用,并將這種反應體現在特殊教育實踐中。
三、殘障社會學對職前特殊教育教師課程意識培養的啟示
隨著我國對殘障權利的重視,越來越多的高校都開設了特殊教育專業,但長期以來主要以醫學、心理學思維的培養模式認識特殊教育專業人才培養,仍然充斥著能力主義的歧視 [30]。在職前教師的課程意識中往往充斥著主流教育話語中的假設,缺乏殘障經驗,限制了職前教師的態度、知識和教學實踐。職前教師除了接受特殊教育的醫學、心理學觀念,也要豐富對殘障社會學的理解。殘障社會學可以為職前教師提供殘障的歷史視角、批判視角及多元視角 [31]。
(一)傳統的殘障社會學價值:作為“遭逢”的課程意識,培養基于經驗的認識能力
傳統的殘障社會學貢獻在于提供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理解,也就是對殘障的認知及如何看待殘障。許多職前教師對將來的工作熱情很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對殘障者的身心狀況卻知之甚少,甚至只看到表面或片面的現象,特別是在與殘障者的溝通交流方面往往存在著障礙。傳統的殘障社會學可以引導職前教師跨越自己的“安適界限”(comfort zone),明確地審視一系列二分視野價值體系的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善良與邪惡、有價值與無價值、美麗與丑陋。殘障一詞是一個歷史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術語,沒有公認的方法來識別、定義和衡量。職前教師缺乏關于殘障的經驗性知識。接觸傳統的殘障社會學所提供的傷殘與殘障的歷史視角,正是職前教師首度“遭逢”(encounter)的課程意識。這可以幫助職前教師深入理解特殊教育的社會正義,促使他們以新的方式看待殘障與社會的聯系,擺脫傳統認知的束縛。
(二)批判的殘障社會學價值:作為“跨越”的課程意識,培養基于批判的思辨能力
批判的殘障社會學的貢獻是為霸權文化意識形態假設提供了批判的視角。殘障的概念是一系列法律、行政程序、醫療診治、福利制度、專業分工,以及蘊含各種經濟利益考慮的文化產物,是法律、醫學、教育等各式團體力量凝聚交織的反映。然而,批判的殘障社會學可以漸次思索不同的專業論述如何看待與定義殘障的問題,檢視各種的意識形態如何透過專業論述或實踐管道運作其中。諸如:這是誰的特殊需要?家長還是殘障學生本身抑或機構部門因維持和控制教育穩定性的需要?在融合教育的擴展下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結構? 普特二者之間存在什么樣的沖突?當今特殊教育學校的職業訓練課程中是否隱含著資本主義的消費生產價值意識?“殘而不廢”“廢而有用”等觀點已證明其對社會有所貢獻,卻視為理所當然?這一連串的省思,很顯然地將職前教師帶到“跨越”(straddle)的課程意識中,意味著需要培養批判的思辨能力。這種跨越提醒職前教師在努力實現融合教育的過程中要避免陷入“浪漫天真的實用主義”。
(三)后現代殘障社會學價值:作為“處境”的課程意識,培養基于多元視角的文化能力
后現代殘障社會學的貢獻可補足課程實踐中文化認同不足的弊端,即不將殘障視為既定的實體或事實,而是描述為一種話語、一種過程經驗或事件,視殘障的身體為一個知識領域,透析其中隱含的力量糾葛。職前教師與其只會繼續“盯著”殘障者,詢問他們面臨什么樣的問題以及社會應該如何支持他們,不如去了解殘障者身份和新的主體性形式如何被形塑。因此,后現代殘障社會學意味著職前教師培養不是把殘障類別問題化,而是要轉變為多元視角的文化能力,理解“正常”與“殘障”之間的相互作用。殘障者長期被社會化為“無聲的依賴者”。特殊教育在鼓勵殘障者發聲的同時,要有關于殘障認識的自主覺醒過程,而不是僅僅復制主流社會的“殘補式”慈善觀點。職前教師進入“處境”(situated)的課程意識,不斷修正所學的理論,更新自己的學生觀、教育觀。這雖然給課程實踐留下了不確定性,但促進了職前教師對殘障者的理解,有利于形成更加尊重殘障者的課程意識。
四、結論
殘障社會學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殘障的社會結構性因素,為人們重新理解殘障創造了新的可能性。殘障社會學理念對職前教師更新課程意識,增進對融合、公平等問題的理解具有重要價值。正如戴維斯(Lennard J. Davis)所言,“雖然大多數正常人和學者們認為他們了解殘障問題,并且擁有殘障知識的話語權,但事實上并沒有,拋棄先前的知識似乎是進入殘疾/能力世界的新旅程的良好出發點”[32]。
【參考文獻】
[1][25]Shakespeare T. Debating disability[J].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08(34):11-14.
[2]續西發.對新疆殘疾人的社會學研究[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3):4-9.
[3]馬才華.建立中國殘疾人社會學的思考[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3):92-93.
[4]奚從清.殘疾人社會學:對象·任務·功能[J].社會學研究,1992(6):105-109.
[5]于松梅,孫琪.透視殘障理論的社會學觀點[J].中國特殊教育,2005(7):16-20.
[6]楊柳.西方特殊教育研究范式及其發展走向[J].教師教育學報,2015(4):8-12.
[7][14][20]李學會.社會學中的殘障研究:強弱范式及歷史發展[J].殘障權利研究,2018(5):44-67.
[8]陳昫.國外學術界對殘疾文化的多元化解讀及啟示[J].殘疾人研究,2019(2):3-11.
[9]趙森,易紅郡.從個人到社會:殘疾模式的理念更新與范式轉換[J].殘疾人研究,2019(3):12-22.
[10]龐文.殘障模式的代際演替與整合——兼論邁向人類發展模型的殘障觀[J].殘疾人研究,2019(3):3-11.
[11][29][30]Tanya T. Disability studies:the old and the New[J].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25):197-224.
[12][17][23]Allison C C,Cheryl N S. Constructing the sociology of disability:an analysis of syllabi[J].Teaching Sociology,2021(49):17-31.
[13]Nagi S Z. Some conceptional issues in disability and rehabiliation[M].Washington,DC:American Socioloigcal Association,1965:110-113.
[15]Goffman E.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M].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3:14-16.
[16]Romel W M,Richard O 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social work: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J].Sociology Work,1996(41):7-14.
[18]Sari A,Cristibal S. Early American disability studies[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2017(52):1-27.
[19]Oliver M.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M].London:Macmillan,1990:13-31.
[21]Barton L. The politics of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J].Disability,Handicap & Society,1986(1):273-290.
[22]Tomlinson S. A Sociology of special education[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2:13-29.
[24]Mullaly R P,Juliana W.Challenging oppression and confronting privilege:a critical approach to anti-oppressive and anti-privilege theory and practice[M].Canada,Ontari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27-129.
[26]Garland-Thomson R.Integrating disability,transforming feminist theory[J].The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Journal,2002(14):1-32.
[27]Siebers T. Disability Theory[M].Michiga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8:83-90.
[28]Goodley D,Runswick-Cole K.Becoming dishum-an: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through dis/ability[J].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2016(37):1-15.
[31]Marilyn D. Disability culture and cultural comp-etency in social work[J]. Social Work Education,2012(31):168-183.
[32]Lennard J 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Routledg,2006:16.
The Core Concept of Sociology of Disabil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ultivation of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in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LIU Xiuhao? ?ZENG Yaru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logy of disability has evolved through traditional sociology of disability,critical sociology of disability,and postmodern sociology of disability.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core concept of sociology of disability to analyze its impact on special education,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on curriculum.The main purpose is to help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develop a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of “encounter”,“straddle”,and “situated”.
Key words: sociology of disability;curriculum consciousness;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uthors: LIU Xiuhao,professor,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liu15260786300@qq.com,Quanzhou,Fujian,362000);ZENG Yaru,professor,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Fujian,362000)
(責任編校:王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