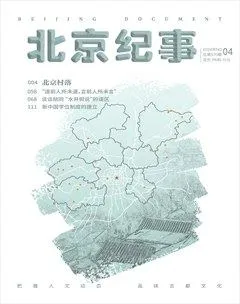山青海闊 風生水起
孫晶巖
煙臺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春天很長,桃花和梨花趕著趟兒地盛開。該冷的時候就冷,該暖的時候就暖。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除卻人與景,便是煙臺毓璜頂公園楹聯的考究。
擇一個晴朗的好日子,我獨自來到毓璜頂公園,細品楹聯。
正看得入迷,一位公園的工作人員認出我來。見我詫異不已,他告訴我,幾年前,你們幾個作家來我們這里采風,還留下了墨寶,公園出了本雜志,把當年你們的合影及墨寶都刊登出來啦。
他喚醒了我的記憶:那是一個金色的秋天,煙臺市委宣傳部曾邀請作家到煙臺采風。
特別記得那副橫批是“毓璜頂”的對聯,位于玉皇廟山門的右便門上,上聯是:毓秀鐘靈地不愛寶;下聯是:璜琮璞玉山自生輝。
——我們曾經一起琢磨過這幅楹聯。
那一次,陳建功、魯光、麥家、陳昭在,韓作榮也在。
文人墨客相聚港城
那一次,在毓璜頂公園,我們飽覽了美景。
煙臺電視臺的記者采訪了陳建功——建功是我所尊敬的領導,文章寫得好,人品更好。汶川地震發生后,他身先士卒,帶頭為災區捐款,又冒著生命危險奔赴災區,創作了一批膾炙人口的抗震作品。擔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他對煙臺建立冰心紀念館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
公園請我們賜墨寶,大家一時想不出來好詞,韓作榮打算用毓璜頂公園的楹聯“毓秀鐘靈地不愛寶,璜琮璞玉山自生輝”來題字。我覺得不過癮,用激將法對陳建功說:“建功,您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古典文學底子好,快點想個好詞。”
建功眉頭微皺,脫口而出:“要有點現代意識,叫山高海闊風生水起如何?”
我說:“好啊,煙臺山高海闊,麥家剛憑《暗算》奪冠,他的新小說叫作《風聲》,風生水起里還暗含這部小說的諧音。”麥家真名叫作蔣本滸,和我都是軍藝文學系第三屆學員,戲稱“黃埔三期”。我們同學大多來自基層,入學時起點并不高,但現在文壇上鼎鼎大名的閻連科、麥家、徐貴祥、趙琪、岳南、陳懷國、石鐘山、王久辛、衣向東、曹宇翔,都是我們班同學。這些當年的無名小輩在文學的羊腸小道上艱難地攀登了三十多年,把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等國家級大獎都拿遍了。“黃埔一期”師兄莫言更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記得那一次,不知是煙臺的風水好還是什么原因,就在麥家定下去煙臺后,喜從天降,他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只見韓作榮攥著毛筆說:“這里到處都是綠樹,還是叫山青海闊好。”
我暗暗佩服他的觀察力,韓作榮大筆一揮,寫下了“山青海闊風聲水起”八個大字。大家一致叫好,我突然覺得不對勁,問建功:“您說的風生水起的生是生活的生還是聲音的聲?”
建功眨著眼睛說:“當然是生活的生了。”
我對作榮兄說:“剛才都賴我,扯麥家的《風聲》把您繞暈了,您還得重新寫一張。”
主人有點舍不得,說風聲水起也行啊。建功較真地說:“不行,一字之差意思滿擰。”
好脾氣的韓作榮說:“沒事,我再寫一張。”
他揮舞毛筆,一會兒工夫又寫好一張條幅,這一張比剛才那張更棒。我不由得對他刮目相看。若干年前浙江筆會見過韓作榮的書法,不想苦練經年,竟然大有長進。
銘心刻骨鐵云藏龜
在煙臺市委宣傳部部長朱秀香的陪同下,我們來到福山區采風。
雖然福山現在是煙臺的一個區,可老煙臺人都曉得先有福山,后有煙臺。福山山清水秀,古稱“福地”。福山地靈人杰,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哺育了無數仁人志士。僅明清兩代就曾考取進士67人。
我們來到了位于福山區的王懿榮故居。王懿榮是福山區古現鎮人,清朝光緒年間進士,曾任國子監祭酒,掌管全國的高等教育,兩次擔任欽命團練大臣。
那次去煙臺,恰逢新的王懿榮紀念館奠基。
王懿榮故居位于福山區城里大街路北,大門兩邊的柱子上,鐫刻著一副隸書楹聯。上聯是:“探驪得珠彪炳新學發夏史”;下聯是“釋生取義輝煌大節振民魂。”
王懿榮是19世紀重要的金石文字專家,有“甲骨之父”的美譽。1899年秋天,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病倒了,中堂翁同龢帶著太醫前往王府探望,太醫診斷為傷寒,開方用中藥調理。王懿榮急忙讓家人到藥房抓藥,家人很快為他煎好中藥。喝藥時他發現藥有一股怪味,便叫家人把沒有煎的藥拿來觀看。他是個有心人,發現有一味叫作龍骨的中藥上刻著朦朦朧朧的圖案,便讓家人到中藥店把這味中藥全部買來。
把龍骨攤在桌子上,用放大鏡仔細觀看龍骨上的刻畫,組拼成了形態各異的符號,發現這些符號是一種從未發現過的文字。他從拼湊的龍骨上認出了“日”“月”“山”“水”等字,在北京首先發現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公元前16世紀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漢文文字。在甲骨文發現之前,人們所見到的最古老的文字只有鑄或刻在古代銅器上的文字,人們稱之為金文。王懿榮這一轟動中外學術界的重大發現,為中國文字和古代史的研究開拓了新領域,將漢字的歷史提前到公元前16世紀。
王懿榮不僅是一位學者,還是一位愛國志士。1900年,八國聯軍以出兵鎮壓義和團為借口,在天津大沽口登陸后,一路燒殺搶掠入侵北京。王懿榮出任京師團練大臣,率領軍民浴血奮戰,終因敵強我弱兵敗城破。為了向入侵的八國聯軍表示反抗,不做俘虜,他率領全家投井以身殉國。顯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高尚民族氣節。
參觀完畢,王懿榮紀念館的主人讓我們題字,館里的匾額和楹聯,都出自國內書法家之手,我是不敢班門弄斧的,便把球踢給了陳建功和韓作榮兩位才子。建功說:“寫一代宗師百世流芳吧。”
韓作榮說:“我剛才在展覽中看到有藏龜兩個字。”
我說:“藏龜的意境很棒,再想幾句和建功的那句對仗就行。”
大家一琢磨,最后由韓作榮題寫了“刻骨銘心鐵云藏龜,一代宗師百世流芳。”
《鐵云藏龜》是世界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1903年,劉鶚向王懿榮家族購買了大量殷商甲骨,從他所收藏的五千余片甲骨中精選了1058片,編成《鐵云藏龜》六冊。
事后細品“藏龜”兩個字,我越發覺得貼切、雋永。
君子之交淡如水
韓作榮上世紀70年代崛起于詩壇,在《詩刊》《人民文學》《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500多首詩歌,僅出版的詩集就有十余本。江南筆會與當地文學愛好者對話時,有個小伙子說:“我覺得發表作品還是要認識人,現在著名刊物上仍然有平庸之作,肯定是關系稿。我條件不好,不認識編輯,再好的作品也上不了好刊物。”
話音剛落,當過《人民文學》雜志主編的韓作榮搶過話筒說:“條件固然重要,只要你真有本事,在哪兒也埋沒不了。我們《人民文學》雜志有個新浪潮欄目,每期都要隆重推出沒有發表過作品的人的稿子。退一步講,你寫了平庸之作,即使托關系發表在大刊物上,也未必是好文章,人家仍然不買你的賬。歌德說:‘真正的詩是超我的,要達到一種極致。看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陳毅,有幾個人不會寫詩?現在有些領導講話盡是空話、套話、假話,如果能把詩意的東西融進去,講話會很有味道。真正的生存是一種詩意的生存,只知道物質享受是沒有生活趣味的。為什么現在這么多大學生跳樓,就是有挫折感。小地方怎么了?小地方的人有靈氣、有水準。我們這些編輯還是認真的,所有的來稿都看。我看作品是看才氣,而不是看作者活動能力有多強,多會炒作。我喜歡勤奮耕耘的人,青年人要讀點哲學、經濟學、法學和詩學,要堅持本真,堅持文學創作,立功、立德、立言。”
韓作榮講的是肺腑之言,我是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時認識韓作榮的,那時候他是《人民文學》雜志的編輯,來系里和我們聯歡。我們班有一個來自西藏的同學給《人民文學》投稿,韓作榮根本不認識他,但還是幫助他反復修改作品,在頭條發了他兩篇報告文學。對于一個地域偏遠的人,這是很高的榮譽。有的省就規定在《人民文學》和《當代》《十月》這樣的雜志發表兩篇作品就可以加入省作協。
我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是韓作榮當的責任編輯。那是在十多年前畫家韓美林走背字的時候,他畫的畫被人貶低,搞的雕塑被人坑蒙拐騙,談戀愛被人卷走錢財。望著身無分文的美林,我覺得作家應該雪中送炭,便滿腔熱情地采訪。
韓美林的畫室靜得出奇,他的身邊依偎著一只叫作二鍋頭的狗。在錄音機的旋轉聲中,在我的筆尖的沙沙聲中,韓美林毫無保留地向我傾訴了他遭遇的磨難。
作品完成后我沒有立即投稿,想再沉淀一段,好好修改一下。幾天后的一個文學聚會中我見到了韓作榮,他問我最近在寫什么?我如實稟報,他說你把剛寫完的這篇給我看看。當我把作品寄給韓作榮時,他以極快的速度看完了稿子,當即拍板刊登。他還給我的拙作改了題目叫作《生命的雕塑》,我覺得改得很有詩意。后來,《人民文學》雜志又重點推介發表了我的報告文學《中國金融黑洞》和《用夢想跨越障礙》。
有一天,編輯通知我說拙作《假如給我三刻光明》榮獲《人民文學》《民族文學》雜志舉辦的“象山杯”散文獎,讓我到人民大會堂領獎。我急匆匆趕到人民大會堂,發現韓作榮也在現場。我前幾天剛跟他通過電話,可他對我獲獎的事情只字未提,他知道我從來不去跑獎,壓根兒不曉得自己能獲獎,他也不在電話中向我透露只言片語。后來我才知道,我的獲獎離不開作榮兄和葉梅姐對我的提攜。
那次煙臺筆會,經常要即興賦詩,主辦方天南海北地點題,作榮兄文思泉涌,出口成章,寫的詩總是高人一籌,這與他熱愛讀書有很大關系。無論是坐飛機還是坐火車,他都要隨手拿一本書翻閱。有一次我們一群作家一道參加筆會,我恰好和他坐在一個軟臥車廂里,他一直在讀書。參觀酒文化博物館時,我的注意力在酒、酒具和工藝品上,而他卻捧著兩本介紹葡萄酒的書滿載而歸。原來,他想寫點關于葡萄酒的文字,專門到酒博物館的小賣部買書去了。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滋養了韓作榮的靈魂,激發了他的靈感。
之前的一次筆會期間,同行的韓作榮、趙麗宏、楊匡滿等人都是在全國頗有影響的詩人,受他們傳染我也利用等車的間隙開始諏詩,并把自己信手涂鴉的詩句拿給韓作榮看。他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毛病,并且在極短的時間里幫我選出恰當的句子。他對我說:“詩首先是語言的鮮活可感,有動人心魄的力量,能喚起讀者內心的經驗并產生共鳴。好詩是那種心靈細微處的把握,具有本源性的真實感覺。你不要看到什么寫什么,而是詩人寫出什么才讓讀者看到什么。”
君子之交淡如水,韓作榮對作家不是誰給我送禮我就發誰的稿子,而是誰的稿過硬我就扶持誰。我覺得他有獨立見解,總是按質量選擇稿件。
友直友諒友多聞
韓作榮1978年在《詩刊》當編輯時,從自然來稿中發現一封來自青海的信。打開一看,是一個叫昌耀的人寫來的詩《致友人》。作者名不見經傳,可韓作榮卻認定這個作者前途無量。他編發了《致友人》,昌耀又寄來一個厚厚的信封,里面裝著幾百行的長詩《大山的囚徒》。韓作榮覺得里面有很多叫人心動的句子,便給昌耀寫了一封信,歡迎他來北京改稿。
在北京虎坊橋甲15號《詩刊》社九平方米的小平房里,韓作榮第一次見到了昌耀—— 一個矮個子、方臉盤、身材瘦削的男人,鼻梁上架著一副白色的眼鏡,頭發凌亂,穿戴普通,不修邊幅。他說一口流利的湖南話,顯得有些木訥。但韓作榮還是敏銳地窺探出他痛苦的人生經歷、深刻的人生體驗以及超群的詩歌才華。
乍一見面,就很投緣,韓作榮對詩歌的真知灼見令昌耀打心眼兒里佩服,韓作榮敢講真話的個性又讓昌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韓作榮不客氣地講了《大山的囚徒》的不足,昌耀覺得句句在理,逐字逐句推敲,終于改好了這首長達八百行的長詩,韓作榮把它全文刊登在《詩刊》雜志。后來,韓作榮調到《人民文學》雜志,昌耀也把自己詩歌的投稿方向鎖定在《人民文學》。昌耀寫了好詩,必定首先寄給韓作榮;韓作榮每年都要給他發表一些詩歌作品。由于韓作榮的推舉,昌耀的詩在中國打響了!很多大學生都可以大段背誦他的詩歌。大學畢業時,我的同學吳國平就用昌耀的詩句“前方灶頭,有你的黃銅茶炊”作為送給我的臨別贈言,可見昌耀的詩歌影響力之大。
1996年初,昌耀又給韓作榮寄來了二十二首詩,說這是三年來的作品。韓作榮一看驚呆了,篇篇都是精品。力排眾議,韓作榮把這二十二首詩以目錄頭條、正文二條的醒目位置,排單欄,一股腦兒發表在1996年第六期《人民文學》雜志上。以二十多頁的篇幅一次推出一個作家的詩作,這在《人民文學》雜志社是史無前例的。昌耀的詩給沉寂的詩壇吹來了一股旋風。
韓作榮才華橫溢,在多年的編輯生涯中,一旦碰到超越自己才華的作者,他打心眼兒里敬佩愛戴人家。昌耀就是其中之一。韓作榮佩服他心胸博大,以多繭的手拼讀大河砰然的轟鳴、從胸腔呼喚起搖撼的風濤。
為了鼓勵勤奮創作的詩人,韓作榮煞費苦心拉過企業贊助,搞詩歌評獎。可有的企業當初談得好好的,到發獎時就不認賬了,一分錢也不出。雜志社沒錢發獎,韓作榮只好自掏腰包。得知昌耀非常清貧后,本就不富裕、上有老下有小的韓作榮,便用發獎金的形式來資助他。而這一切,昌耀并不知曉內情。他寫詩并不在乎是否獲獎,當韓作榮給他寄來“獎金”時,書呆子氣的昌耀竟然毫不懷疑。有些名氣很大的人仰慕昌耀的詩才,想見他,他卻避而不見;但對韓作榮,他卻說:“士為知己者死。”
第五屆全國作代會開幕那天,恰巧是韓作榮的生日。晚上,好多朋友跑到韓作榮的房間喝酒,向他表示祝賀。一向不言不語的昌耀居然破天荒唱了一首湖南情歌,讓在場的朋友非常驚訝。
1999年,中國詩歌學會評選“中國詩人獎”,昌耀以高票獲獎。作為評委,韓作榮受中國詩歌學會的委托給昌耀撰寫了授獎詞:“昌耀對于詩壇而言,是個獨特的現象。當諸多的詩人在詩潮中隨波逐流,他卻卓然獨立于高原之上,以雄奇、高邈、博大、精微,塑造了自己的詩歌品格。”“他的多數詩章,都在苦難的摧折與生命的強勁、盛大中,形成了藝術的深度表達與完善;他讓我們領略了什么是詩歌意義上的高原。在他的詩中,大地與大地所繁衍的一切,那些原生性的品屬已與語言、心靈融于一體。他,是大西北無數生命的靈魂,讓我們感知精神的能量、傾聽穿透時空的聲音,以及經驗與超驗。”發獎會上,韓作榮熱切盼望見到昌耀的身影,卻意外地接到詩人肖黛給自己捎來的話:“作榮,昌耀快不行了。在告別這個世界前,他想見到你!”
韓作榮聽后潸然淚下。春節快到了,他也想與家人團聚,可那一年不能,他要用春節假期專程去西寧看望病重的昌耀——他的作者、他的摯友、他的兄長。
他找出中國詩歌學會首屆年度詩歌獎發給昌耀的獎狀和五千元獎金,裝在一個皮包里。另一位獲獎詩人朱增泉得知韓作榮要到西寧,特意把自己的五千元獎金托韓作榮一并轉交給昌耀。朱增泉是一位“將軍詩人”,曾經在西部工作了大半輩子,他深深地理解另一位西部詩人昌耀。
大年初二,韓作榮登上了開往西寧的列車。初三一下火車,他拎著包就直奔西寧人民醫院。此時的昌耀,身子像紙一樣單薄,腿上的皮膚用手一捏便能合攏;原來方闊的臉已經被病魔削成了三角形,鼻子上插著一個塑料吸氧管,臉色蒼白,氣若游絲。韓作榮輕輕地喚了一聲“昌耀”,昏睡的昌耀突然睜開了眼睛,硬撐著坐了起來。他把獎狀和裝有一萬元錢的信封鄭重其事地遞到昌耀手里,告訴他這里有朱增泉將軍轉贈的五千元錢,我們這些詩友都特別想你。
面對榮譽和友情,昌耀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哽咽著。他有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的錢都用在了前妻和孩子身上。他早就感覺胸部不舒服,可他咬牙挺著,實在太痛了,就用雙膝頂著胸部痛苦地號叫。他已經身無分文,韓作榮送來的一萬元是他的救命錢啊!
昌耀說:“作榮,從你上了火車,我就開始盼你。我害怕自己昏睡過去,就定了鬧鈴提醒自己。鬧鐘六點十分響了一次,那是你下火車的時間;這次響,是你應該到賓館的時間,可你卻站在我面前,說明你一下火車就直奔了醫院。”
在韓作榮面前,昌耀如數家珍地回憶往事。看著瘦得皮包骨頭的昌耀,韓作榮心如刀絞,他一再叮囑昌耀:“這一萬元獎金一定要用來治病,錢不夠盡管說,朋友們來湊,不要為錢而擔憂。”
昌耀一字一頓地說:“作榮,我要死了,癌癥在我的體內正突飛猛進。”
韓作榮喝斥道:“昌耀,還記得里爾克的詩嗎?頂住就是一切!只要你堅持治療,說不定會有奇跡發生。”
昌耀的臉上掠過一絲苦笑:“作榮,死也沒關系,我不是對你說過‘士為知己者死嗎?”
韓作榮的眼睛里噙滿淚花,這是四年前昌耀在信中寫給自己的話。他緊緊地握住昌耀的手,半晌沒說出一句話來。
新春佳節,韓作榮寸步不離地陪伴著昌耀。可千里相見,終有一別,大年初八,韓作榮來到昌耀的病床前,緊緊地擁抱昌耀。他轉過臉用手輕輕地拍打著昌耀的背部,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昌耀像孩子似的哭出了聲,韓作榮鼻子一酸,淚水奪眶而出,轉身向門外走去。他知道這一走就是永別,可他不敢回頭,他害怕自己的淚水會擊垮孱弱的昌耀。離開病房,韓作榮的眼前一片模糊。這個從不輕易流淚的男子漢,每下一層樓梯,淚珠就砸濕一層臺階。
——韓作榮對作者的深情厚誼,不止這一種。
第七屆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我和韓作榮正說著話,軍旅詩人周濤向我們走來。周濤是實力派詩人,可韓作榮在《詩刊》雜志當編輯時,卻曾經退了周濤五年的稿子,而周濤在《詩刊》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恰恰又是經韓作榮的手發表的。給一個退自己五年稿的編輯繼續投稿,認死理連續五年退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的稿子,都只有對文學真誠的人能做到。后來,倆人成為了朋友。
周濤非常信任比自己年幼的韓作榮,有一次到北京出差,他和詩人李曉樺一道去看望韓作榮。韓作榮的書房叫半醺齋,醺是醉醺醺的醺,意思是人在微醉的狀態下寫的詩最有味道。三個男子漢邊喝茶邊抽煙邊聊天,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三桿煙槍一直燃到午夜兩點,半醺齋里早已云遮霧障,可他們仍然意猶未盡。書房的木鐘敲了三下,周濤才猛然醒過味兒來:“曉樺,趕緊撤,作榮明天還得編稿呢!”
半夜三點的北京街頭公共汽車早就無影無蹤,那時候還沒有出租車,周濤和李曉樺居然從韓作榮家所在的和平里,沿著北三環往西一直走到他們在北太平莊的住處。后來,周濤把自己作品的刪改權僅授予韓作榮一個人,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
那次作代會上,韓作榮正和周濤聊天,李存葆走了過來。
李存葆是軍藝文學系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但韓作榮就敢一口咬定他和王光明合寫的一篇報告文學不如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在一次由其推薦參加評獎的作品中只能列在第二位。開始李存葆不服,非要找韓作榮理論理論:怎么就不如別人?后來韓作榮向李存葆直言,誰料李存葆聽了竟然大為感動。
上世紀90年代初期,韓作榮向李存葆約報告文學稿,李存葆和王光明合作完成了《沂蒙九章》。韓作榮趕到青島看了稿子后對李存葆說:“存葆,正因為你是全國有影響的作家,所以我要對你嚴格要求。你們的稿子有兩章寫得不行,必須推倒重來。”
李存葆虛心聽取韓作榮的意見,老老實實地改起了稿子。為了讓稿件更加真實生動,韓作榮又和李存葆一道來到山東臨沂,聽取沂蒙山人對稿子的意見。在韓作榮的點撥下,李存葆筆下生花。稿子改好后,韓作榮非常高興,編稿時還加了一段《編者的話》。稿子寫得長,韓作榮刪稿有點不落忍,便去征求劉白羽的意見。劉白羽看后說:“這么好的稿子別刪了,都給他發表了吧。”于是,建國以來《人民文學》雜志破天荒首次用一本雜志刊登一部報告文學。在“1990——1991”年度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評獎中,《沂蒙九章》以高票獲獎。
孔子說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諍言逆耳,韓作榮敢于對作家講真話。如果天下的作家和編輯之間都是這樣的諍友,大家都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那世界該有多美。
后來我到新疆采訪,想找周濤聊天,經韓作榮引見,周濤在家欣然接待,同我聊了好幾個鐘頭。如今,我寫新疆的長篇報告文學《西望胡楊》出版了,反響不錯,我多想給作榮兄送一本請他指教啊!可是,酷愛讀書的作榮兄卻在2013年11月永遠地睡著了。
昌耀走了,是肺癌奪去了他的生命;
如今,作榮也走了,又是肺癌奪去了他的生命。昌耀說士為知己者死,作榮兄:你不是曾經用里爾克的詩鼓勵昌耀嗎?“頂住就是一切!只要你堅持治療,說不定會有奇跡發生。”
你心里那么明白,可你為什么不頂住呢?我知道你是為了《李白傳》的創作延誤了治療。
如今,我們參與奠基的新的王懿榮紀念館已經在煙臺落成,可是作榮兄不能來參觀了。天堂里多了一位純粹的詩人,作榮,在天堂里,你可以和普希金、昌耀、周濤、海子等人一邊品茶一邊吟詩了。
中國文壇依然山青海闊,中國文學必將風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