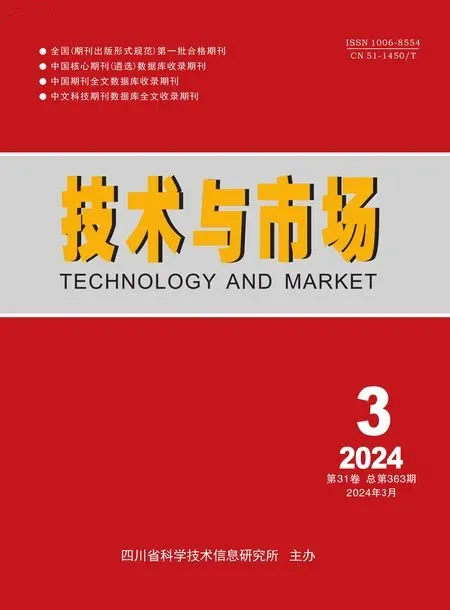高管在職消費對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基于內部控制調節視角的實證研究
陳麗霞,陳昱良
長春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0 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家不斷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企業是進行創新的重要市場主體。高新技術企業是經認定在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內持續進行研發與技術成果轉化并形成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享受相關政策優惠,承擔著科技創新的重任。在兩權分離的現代企業中,高管是進行創新決策的重要主體,而創新活動具有高投入、回報周期長、高風險的特點,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可能會減少創新活動投入。高管激勵機制的設置則可能減少高管的代理成本,促使高管進行創新活動。其中,高管在職消費的作用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在職消費是企業管理者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所獲取的非直接貨幣性收益,在職消費可能與職責有關也可能無關[1]。高管在職消費與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研究為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管理提供理論參考。企業任何制度的制定、實施以及監督均受到企業的內部環境影響,因此,研究內部控制對兩者間關系的影響可為公司治理及企業提升創新活動績效提供一定參考。
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績效或研發投入的影響,而關于高管在職消費對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較少。相關研究結論主要為以下2種。支持“效率觀”的學者認為高管在職消費能夠提高高管工作積極性并提升其管理效率[2],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高管在職消費能夠正向促進企業研發投入及產出[3]。出于“代理觀”考慮,Jensen et al.[4]在1976年首次提出在職消費的概念并認為高管在職消費給公司帶來代理成本,不利于企業發展,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高管在職消費會抑制研發投入[5]。將高管在職消費、內部控制與創新績效三者納入同一體系的研究同樣較少。相關學者研究指出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可降低管理者的在職消費水平[6-7],而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卻表明應加強對高管在職消費的監督才能更好發揮其對企業創新產出的積極作用[8]。
基于此,以我國2018—2022年滬深 A 股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樣本,研究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豐富了高管激勵對于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研究;進一步,引入內部控制,研究其對高管在職消費與企業創新績效的調節作用,為企業內部治理提供一定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高管在職消費與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
現有研究結果表明,高管在職消費具有補充性貨幣薪酬、職務性正常消費以及自娛性消費三重性質[9]。在職消費的貨幣薪酬補充性質體現了高管的身份與地位,滿足其自我實現需求,從而提升高管職業忠誠度與個人成就感,不斷增強高管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正常的職務性消費包括公務用車費、通訊費、辦公費用及國(境)外考察培訓費等,保障了高管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工作體驗,滿足其工作中的職務需要以及關系需要,同時,也為高管提供專業化的培訓,提高其綜合能力。正常職務性在職消費能夠提升高管工作積極性以及工作效率,進而促進企業創新活動的投資與決策,但由于現代企業兩權分離會造成信息不對稱問題,高管可能利用在職消費進行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創新活動投入受到抑制。
國家出臺的一系列高管在職消費規范政策有利于促使在職消費的組成結構更加合理,使得對創新活動具有正向作用的貨幣薪酬補充和職務性正常消費占據主導成分,而抑制創新活動的自娛性消費比例減少。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1:高管在職消費正向促進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
1.2 內部控制對兩者關系的調節作用
薪酬管制等一系列措施使在職消費更多地發揮其貨幣薪酬的補充與替代作用,發揮其合理正面作用,從而更多地表現出對高管薪酬激勵的替代性激勵作用[10],而內部控制的加強則會限制高管在職消費作用的發揮。首先,公司對于高管進行研發投入決策的審批流程會隨著公司內部控制增強變得更加嚴格,給高管無形之中增加工作壓力,使高管對于工作的滿意度削弱,工作的積極性降低,從而導致創新活動受阻;其次,隨著內部控制的增強,高管預期水平的在職消費可能難以得到滿足,進而可能導致高管對創新活動投入減少;最后,創新活動具有高風險、高不確定性、長回報周期,在更加注重實質性創新的高新技術企業時,這些特點更加明顯,更需要對高管進行創新活動風險承擔補償,而在職消費水平會隨著內部控制的增強而降低,對于貨幣薪酬的補充減少,導致對高管進行創新活動的風險補償減少,最終可能導致高管進行創新活動的意愿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內部控制負向調節高管在職消費與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關系。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選取2018—2022年我國滬深 A 股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為初始樣本,并進行以下篩選。①剔除樣本期間ST、*ST及PT公司。②剔除缺失值及異常值。為消除極端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對連續變量進行1%、99%的雙邊縮尾處理,最終得到5 485個有效樣本,所使用的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調節變量數據來自于迪博數據庫。
2.2 變量定義
2.2.1 被解釋變量
使用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直接成果產出代表企業創新績效(A),專利指標由于具有通用性、一致性,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可與使用。一部分學者使用專利申請數衡量企業創新績效的指標[11],而一部分學者指出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科技含量較低,發明專利相較于前兩者科技含量較高[12],使用發明專利申請數衡量企業創新績效。
在主檢驗中,選取企業當年申請發明專利數量加1后取對數衡量創新績效(Α);在穩健性檢驗中,用當年授權發明專利數量加1后取對數(A1)來對被解釋變量進行替代研究,并進行滯后1期取數。
2.2.2 解釋變量
采用陳冬華 等[10]的方法,使用財務報表附注“支付的與其他經營活動相關的現金流”項目所披露的辦公費、差旅費、業務招待費、通訊費、出國培訓費、董事會費、小車費和會議費共8類費用之和來衡量高管在職消費(Z)。
2.2.3 調節變量
內部控制(O)采用迪博數據庫“內控指數”的數據來衡量,并將內部控制指數均除以100,得到內部控制新數值用來表示內部控制水平。
2.2.4 控制變量
借鑒已有研究,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M)、股權性質(X)、兩職合一(E)、董事會獨立性(Φ)、股權集中度(K)、市場評價(T)、發展能力(Γ)、現金流水平(Ψ)、行業虛擬變量(I)、年度虛擬變量(Y)。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2.3 模型構建
為驗證H1,以高管在職消費為解釋變量,創新績效為被解釋變量,控制行業及年度效應,在主檢驗中構建如下模型。
Ai,t=β0+β1Zi,t+β2Mi,t+β3Xi,t+β4Ei,t+β5Φi,t+β6Ki,t+β7Ti,t+β8Γi,t+β9Ψi,t+ΣΙ+ΣY+ε
(1)
式中:i表示相應的公司個體,t表示對應年份,ΣY表示年份固定效應,ε表示隨機誤差項。
為驗證H2,引入內部控制(O)及其與高管在職消費(Z)的交乘項(Z×O),控制行業及年度效應,構建如下模型。
Ai,t=β0+β1Zi,t+β2Oi,t+β3Ζi,t*Oi,t+β4Χi,t+β5Ei,t+β6Φi,t+β7Ki,t+β8Ti,t+β9Γi,t+β10Ψi,t+
ΣΙ+ΣY+ε
(2)
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當年授權發明專利數量來對被解釋變量進行替代研究,同時考慮到專利授權需要較長時間,對變量進行滯后。即模型(1)(2)中被解釋變量替換為A1,解釋變量取t-1期的數據。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文章使用Stata軟件先對樣本主要研究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分析其均值、標準差、中位數和極值。經過處理后共得到5 485個有效樣本觀測值,通過對樣本的整體統計分析,對樣本中各主要變量的情況有了初步了解,有利于后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樣本變量描述性分析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由表2可知,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量最小值0,最大值5.823,均值2.355,中位數2.398,標準差1.324。說明在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創新水平差異較大,樣本內部分企業并未實質性創新產出成果,其中,均值小于中位數,說明在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實質性創新成果產出較高的企業相對較少。高管在職消費均值為16.57,中位數16.61,說明樣本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高管在職消費數據分布相對集中,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13.37、19.39,標準差1.106,這表明樣本企業當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差異較大。從內部控制數據來看,均值為6.355,中位數6.548,最大值7.608,標準差0.972。這說明樣本企業內部控制變量整體偏離程度相對較低,最小值為0,說明存在少數企業內部控制水平極低,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3.2 相關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分析法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初步把握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相關性分析結果以相關系數矩陣展示,如表3所示。多數相關性系數的絕對值均小于0.5,說明所研究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且高管在職消費與企業創新績效相關系數為正,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高管在職消費正向促進企業創新績效,這與前述假設結論相同,初步驗證了H1。

表3 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
3.3 回歸分析
多元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表4中的2、3列分別顯示了H1、H2的檢驗結果。從第2列的結果來看,樣本中高管在職消費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181,在1%水平上顯著且為正。這表明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創新績效起到正向促進作用。高管在職消費不僅具有經濟效益的性質,也具有代理成本的性質。我國出臺了相關政策進行管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管在職消費的代理成本,使其更多地發揮相應的經濟效益,即發揮其貨幣薪酬補充以及正常在職消費的作用,更多地補償高管在進行創新活動中承擔的風險,并為高管履行工作職務提供更多支持,從而提升高管在創新活動中的工作積極性以及工作效率,進而促進企業整體創新績效。從第3列的結果來看,高管在職消費與內部控制的交乘項系數為-0.026,在5%的水平上顯著且為負,表明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內部控制對高管在職消費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起到負向作用,驗證了H2。高管在職消費在我國實施薪酬管制的情況下更多地表現出經濟效益而非代理成本,此時內部控制的加強會使得流程繁雜,并使高管工作受到各方限制增多。高管在職消費難以發揮其預期的激勵效果,對高管在創新活動中承擔風險的補償作用減少,將抑制高管對于創新活動的投入,降低其創新積極性,從而對創新績效產生負向影響。

表4 多元回歸結果
3.4 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上述結果的可靠性,進行穩健性檢驗,即被解釋變量采用企業發明專利授權專利數量衡量,并進行滯后,即模型(1)、(2)中被解釋變量替換為A1,解釋變量取t-1期的數據,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在對創新績效數據進行變量替換與滯后,回歸結果與上述結論一致,即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內部控制在兩者關系中呈現負向調節作用。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5 穩健性回歸結果
4 結束語
本文根據相關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發現上市高新技術企業中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即高管在職消費更多的是發揮本身的經濟效益而非產生代理成本;總體來講高管在職消費能夠提升企業創新績效;同時,內部控制的加強對兩者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即過于嚴格的內部控制制度抑制高管在職消費積極正向作用的發揮,不利于創新績效的提升。
基于以上的研究結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上市高新技術企業應重視高管在職消費這一隱性激勵對于創新績效的積極作用。一方面發揮高管在職消費對貨幣薪酬的補充作用,提高高管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發揮其非貨幣性福利性質,促使高管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同時給予高管的正常職務消費也使高管在履行工作職責的過程中彰顯自身身份與地位,工作更加便捷高效,從而更加積極高效地進行創新活動,提升企業創新績效。
第二,合理完善內部控制機制,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由研究結論可知,內部控制對于高管在職消費與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上市高新技術企業應意識到過于嚴格的內部控制會使高管在職消費對于創新績效的積極作用受到削弱。企業應結合自身內外部環境與實際情況,建立合理完善的內部控制機制,與高管在職消費的實施形成良好的配合,從而使高管更加積極、高效率地進行創新活動,提升企業創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