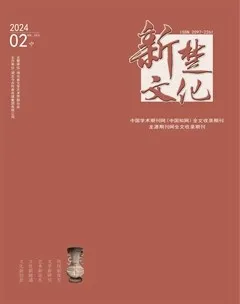基于卡倫?霍尼理論解析辛格的悲劇
【摘要】本文基于卡倫·霍尼的神經癥理論,對《心是孤獨的獵手》中主人公辛格的種種神經癥表現特征進行分析,進而探析其產生焦慮的深層原因及其對抗焦慮的種種努力,以期揭示辛格令眾人困惑無助的悲劇結局,并剖析作者卡森·麥卡勒斯創作該小說的意圖——反映美國人所面臨的各種精神困擾。本研究對美國文化中越來越普遍的神經官能癥進行反思,警示我們重視經濟的同時,更要重視社會普遍存在的焦慮,以避免更多像辛格一樣的神經官能癥者的悲劇。
【關鍵詞】《心是孤獨的獵手》;卡倫·霍尼神經癥理論;辛格的悲劇
【中圖分類號】I106.4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05-0038-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5.012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1年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項目編號:2021SJA2246);江蘇省現代教育技術研究2022年度課題(2022-R-101489)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課程思政”示范課程建設項目(項目編號:202035)階段性成果。
繼威廉·福克納之后,美國南方再出天才作家——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22歲完成了代表作《心是孤獨的獵手》,1940年出版時,小說引起了文學轟動,迅速登上暢銷書榜首。該書在美國現代文庫所評出的“20世紀百佳英文小說”中列第17位。學界研究熱度持續增長,對該小說的研究角度也推陳出新,從精神孤獨、雌雄同體到馬克思主義角度的饑餓敘述、疾病書寫等。但無論何種形式的解讀和研究,都未解答一個問題:辛格的悲劇結局——是因為孤獨嗎?本文將基于卡倫·霍尼神經癥理論,層層剖析,以期解開此謎底。
一、卡倫·霍尼神經癥理論
卡倫·霍尼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是新弗洛伊德主義代表人。她發展了自己的神經癥理論,該理論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觀點不同。霍尼將其描述為:神經癥乃是一種由恐懼,由對抗這些恐懼的防御措施,由為了緩和內在沖突而尋求妥協解決的種種努力所導致的心理紊亂。當這種心理紊亂偏離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被稱為神經癥。
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從其診斷手冊中刪除了“神經癥”一詞,作為精神疾病標準化改革的一部分。如今,神經癥不再是一種獨立的精神疾病。相反,醫生通常將其癥狀與焦慮癥歸為同一類,換句話說,過去所謂的神經癥現在屬于焦慮癥的范疇。
二、辛格悲劇命運的表征
被小鎮上形形色色的人奉為神一般存在的辛格,為什么最終命運卻是悲劇?聾啞人辛格是美國南方小鎮一家珠寶店的銀雕師,十年來他與另一位聾啞人斯皮羅斯·安東納帕羅斯一起生活。辛格似乎從未意識到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愛都放在了與安東尼帕羅斯的關系上,辛格與安東尼帕羅斯的關系對了解這個問題以及他的性格大有裨益。辛格唯一充滿活力的時刻是和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時,問題是他完全把這個人理想化了。安東尼帕羅斯雖然溫和友善,但卻軟弱無力。在辛格看來,他平和而睿智。
霍尼認為:“愛的吸引力不僅表現在對滿足、和平與統一的渴求中,而且通過愛他能夠實現理想化的自我。在愛中,理想化自我的美好品質可以得到升華。”[1]198。對神經癥者而言,對愛和贊賞不加分辨,辛格在給予愛的時候,并不期待對方積極的回應,這種給予和獲得愛的態度是其悲劇命運的第一種表征。
內在的不安全感正是悲劇命運的第二個特點。“手”是辛格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重要媒介[2]37,在與安東尼帕羅斯相依相伴時,辛格會用手語不停地比畫,后來,離開了安東尼帕羅斯,辛格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敢表達真實的自我,他緊緊克制自己的雙手。
再者,他對小鎮人們的事情,保持疏離,點頭微笑。他缺乏自發的自我肯定,其不可避免會有一種軟弱感和缺乏自我保護能力感,不能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霍尼指出:“精神的寧靜對于這種需求來說非常重要。要想變得可愛,就要抑制夸張的行為”[1]198。此為辛格悲劇命運的第三種表征:缺乏自我肯定或者肯定自己主張的行動。此方面,辛格表現出大量的抑制傾向。
三、辛格悲劇的成因
神經癥患者的驅動力與正常人的努力之間存在差別,主要表現為兩者的推動力不同。前者主要為焦慮驅動,以及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御機制。
霍尼將神經癥分為性格神經癥和情境神經癥,“性格神經癥的癥狀可能與情境神經癥完全一樣,但主要的紊亂卻在于性格的變態。它們乃是潛伏的慢性過程的結果,通常形成與童年時代”[3]15。辛格童年坎坷,淪為孤兒,被送到收留聾兒的慈善機構。當辛格遭遇大量不幸經驗,但他不能駕馭這些苦難,由此,產生了基本焦慮。
霍尼指出:性格神經癥由基本焦慮(basic anxiety)導致,并將之描述為“一種自覺渺小、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被拋棄、受威脅的感覺,一種仿佛置身在一個一心要對自己進行謾罵、欺騙、攻擊、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覺”[3]67。雖然幼年辛格聾而不啞,但當他說話時,“他能感覺到自己的聲音聽上去想必就像動物的聲音,或者自己的言語中有某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對他來說,努力用嘴說話是痛苦的”[4]11。無能感和自我厭惡的心理由基本焦慮引起。在遇到安東尼帕羅斯后,辛格完全放棄了語言表達,但基本焦慮仍在,辛格暫時在與安東尼帕羅斯的關系中找到了安全感,所以可以坦然接受自己。
辛格獨處時,小鎮上的四個人成了他的聊天常客:假小子米克、杰克·布朗特、杰克黑人醫生科普蘭、咖啡店老板。無論面對誰,辛格總以溫和的微笑來回應。而他們認為只有辛格如上帝般理解、贊同甚至支持他們。對神經癥者而言,“一方面,他希望依賴他人,另一方面,由于他對他人深深的不信任和敵意,他又不可能依賴他人”[3]70。辛格并不全然理解他們,但看似全盤接受的外面下,是一種因為焦慮而作出的妥協。
除基本焦慮外,一般性焦慮主要是由對受到壓抑的沖動的恐懼而產生。辛格想要和安東尼帕羅斯在一起的愿望被現實殘酷地壓抑之后,辛格看起來溫和、親切,但他的焦慮體現在與其他人相處時,總保持沉默。“引起怕遭反感的恐懼的主要原因,是神經癥病人顯示給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facade),即榮格所說的‘人格面具(persona),與隱藏在這面孔后面的所有一切受到壓抑的傾向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3]190他必須隱藏的東西構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懼的基礎——辛格須掩藏他和安東尼帕羅斯的同性關系,20世紀40年代同性戀不為美國主流社會所接受。“盡管神經癥病人因為不能與自己成為一體,因為不得不始終保持所有這一切偽裝而備受痛苦——他自己并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保護這些偽裝,因為它們是保護他不受自己潛在的焦慮襲擊的屏障。”[3]190
在基本焦慮和一般性焦慮的雙重影響下,辛格從最初失去戀人的歇斯底里,到沉默絕望,內心不斷增長的孤獨感,以及無能為力的絕望感,他也努力在自我拯救。
四、辛格抗爭悲劇命運的方式
霍尼認為,神經癥源于基本的焦慮,這是由孩子的早期經歷(主要是與父母相處)引起的。她確定了個人可能發展神經質行為或防御機制來應對這種焦慮的三種主要方式:
走向他人:這是一種個人尋求他人的感情、愛和認可以減少焦慮的策略。他們可能會符合社會期望,變得過度依賴他人,并且過度需要接受和保證。這種策略是出于對被遺棄的恐懼和對安全的渴望。
與人為敵:在這種策略中,個人可能會采取攻擊性和控制性行為來保護自己免受感知到的威脅。他們可能會做出競爭或敵對行為,爭奪權力和統治地位,并對他人產生敵對態度。這種策略是出于對脆弱的恐懼和維護控制權的需要。
遠離人群:采取這種策略的人往往會退出人際關系并孤立自己。他們可能會變得社交疏離、避免沖突并壓抑自己的情緒。這一策略的驅動因素是對被拒絕的恐懼以及對自給自足和自主的渴望。
首先,辛格嘗試走向他人,過分依賴愛的作用,他接受小鎮上各種人的傾訴,以此來對抗焦慮,以及由此引起的神經癥。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3]70。辛格總有四個常客:第一個是熱愛音樂的米克,把他當作與自己靈魂契合的朋友,他耐心溫柔地傾聽,即便自己耳聾,也為她分期支付購買了收音機;第二個是杰克——流浪者,帶著對社會主義起義的混亂而充滿激情的計劃來到鎮上,杰克性情暴躁且酗酒,有激進改革的想法,卻從未付諸實踐的行動力,每次他躁動不安時,他都渴望找辛格,因為辛格給人平靜的力量;第三個是科普蘭醫生,他是小鎮上懷有偉大理想和情懷的黑人。但眾人并不理解他。而他信賴白人辛格,辛格總是謙遜、溫和而有禮。他煩悶不安的時候,在辛格這個平和如神的人身上找到內心安寧的力量;最后是比夫·布蘭農,和辛格一樣,他保持距離、觀察力和安靜,所以他和所有人都是疏離的。如霍尼所言:“有的神經癥患者會感覺自己生活在迷蒙之中,對所處環境十分陌生,既不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也不明白別人的感情和想法。”[1]127這一階段的辛格實在處在這樣一種“迷蒙”狀態中,生活沒有活力和目標。
另一方面,辛格害怕失去這些“朋友”,所以他采取順從的態度。霍尼指出順從“表現為順從一切人的潛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敵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可能壓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壓抑他對別人的批評……并且隨時準備不分好壞地幫助一切人。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放棄自我,我就不會受到傷害”[3]70-71。辛格周到體貼地照顧每個來訪者,無論他們多么激動,他都溫文爾雅,微笑沉默。他放棄表達自己情感的愿望是為了順從他人的愿望,以便能獲得安全感。順從是辛格為了對抗基本焦慮的第二個措施。這也恰恰加重了辛格自我感的喪失,為他最后孤獨死去的結局埋下伏筆。這解釋了辛格對四位訪客的體貼和關心的深層心理機制。如果個人的抑制狀態符合文化所贊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現存的意識形態,那么,個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識不到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3]36。辛格的緘默符合了文化潛意識中人們對沉默而包容的上帝的期待。久而久之,小鎮上的眾人將之視為上帝一般的存在。但沒有人理解辛格擔心別人對他產生敵對情緒,因此他選擇了退讓,他對自己持續加壓,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蜷縮起來。正如霍尼提到他們“往往會在早期借助‘親和力來解決人際沖突”[1]183。在內在壓力下,人們可能表現出真實的自我完全脫節,他們會將主要精力用于聽從“內心的指引”,盡其所能塑造一個完美的自我。
第三種自我保護的方式為:不參與。不讓他人對自己的內外需要發生影響,即缺乏奮斗意志,沒有理想和追求。放棄者最突出的表現就在這里。他是在無意識中放棄了奮斗。霍尼有言“由于很早就遭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以致他們的自覺態度已變得對任何愛都深感懷疑。他們的內在焦慮是如此深刻,以致他們只要不遭到任何正面的傷害,就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3]98。所以,神經癥者對愛的需求體現在:不遭到任何正面的傷害——這是對安全感的需要。因此,辛格對他人的情感回應沒有期待。孤獨時,辛格給安東尼帕羅斯寫信,但從未寄出,盡管他的來訪者從與他交談中得到了安慰和解脫,但他放棄了從與他們交談中得到平等的交流,此為辛格的無奈退縮舉動。
辛格——作為神經癥者逃離了自己內心的戰場。他成了自己的旁觀者,也是生活的旁觀者。這是他緩解內心緊張的一種方法。做自己的旁觀者,意味著對生活的消極態度,但在潛意識中對這種做法有非常抵觸。此類不可調和的沖突構成了神經癥最常見的動力核心。“從神經癥病人的感覺和行為來看,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幸福和安全仿佛都要取決于他們是否能被人喜愛似的。”[3]88愛人離開后,辛格嚴重輕視現實,生活在想象中,此時,焦慮也會加重。但他并不是個例,學者田穎分析道:“啞巴辛格的境遇極具代表性,是整個小鎮居民生存狀態的縮影。”[5]30霍尼認為,這些策略是為了抵御焦慮,但它們最終會變得適應不良,并導致神經癥癥狀的發展。霍尼相信,個人可以通過發展更健康的自我形象、培養真正的人際關系、擁抱自己真正的愿望和抱負來克服神經癥。值得注意的是,霍尼認為神經癥是社會和文化因素的產物,她強調社會和文化期望對神經癥行為發展的影響。她還強調了解決這些社會影響以實現個人成長和福祉的重要性。
五、研究啟示
美國文化中的矛盾構成了典型的神經癥沖突的社會文化,這些矛盾存在于人們生活中,長期積累,就可能導致神經癥。首先,美國文化一方面強調競爭和成功,另一方面極力倡導友愛和謙卑。其次,在美國消費主義文化影響下,人們所受到的欲望刺激和為了這些欲望實際受到的挫折,而美國文化提倡追求愛和贊賞來解決此難題,這往往難以實現。最后,所謂的個人自由和他實際所受到的局限之間矛盾。辛格無法保護他的同性愛人,對方的死訊都沒有通知他,這成了辛格的神經癥永遠無法得到緩解,最終悲劇的直接原因。這些深藏在文化中的矛盾,轉化成神經癥患者難以調和的內心沖突,研究這部小說可以促使我們正視美國文化中的相關問題,以此警示身處東方文化中的我們。
我國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群受到焦慮的影響,從幼童到耄耋老者都能感受到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尤其是中年人群。據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數據,全球精神障礙疾病負擔更加沉重,重度抑郁癥和焦慮癥的病例分別增加了28%和26%,抑郁癥患者激增5300萬,增幅高達27.6%。現實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給抑郁癥的診斷及治療帶來了更大的挑戰。與社會上實際的神經癥的普遍性相比,人們對該癥的認識仍非常狹隘。因此,期望通過本文的探討,有更多的人關注像辛格一樣的神經癥,以避免類似的悲劇。
參考文獻:
[1]霍尼·K.自我的掙扎——神經官能癥與人性的發展[M].崔文智,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
[2]趙藝.基于語料庫的《心是孤獨的獵手》檢索分析[J].大學,2021(33):36-39.
[3]霍尼·K.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M].馮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4]卡森·麥卡勒斯.心是孤獨的獵手[M].秦傳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5]田穎.論《心是孤獨的獵手》中的空間與權力[J].當代外國文學,2015,36(04):27-33.
作者簡介:
王蘇雷(1983-),女,漢族,江蘇南通人,碩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