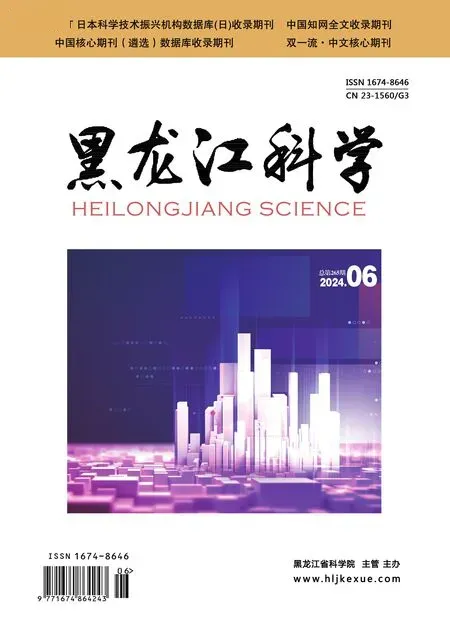抑郁焦慮導致心肌梗死的危險因素
劉澤巖
(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合肥 230601)
0 引言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由于一根或多根冠狀動脈供血不足或中斷而導致心肌缺氧或壞死[1],此病有極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長期在此高壓狀態下會對患者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有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 MI)病史患者焦慮、抑郁的患病率會顯著增加[2-3]。由于治療過程的不確定性,這種壓力可能會給患者造成焦慮,使其擔心再次發生MI[4-6]。然而,并非所有患有MI病史的患者都表現出相似的心理反應。患者過去的創傷經歷、社會關系、經濟和環境因素、人格特征以及應對和防御機制都會發揮重要作用[7-8]。MI會增加出現抑郁、焦慮和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等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多項研究表明,MI后抑郁和焦慮與較高的心血管事件和死亡風險相關,但人們對更廣泛的心理健康指標的影響知之甚少,MI的患者通常會有消極的心理狀態出現。美國在2001—2011年間,未經任何干預的患者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后的院內死亡率有所增加,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患者沒有變化,而接受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患者則有所下降[9],因此有必要探討影響 STEMI 患者死亡率和發病率的生理和心理因素。MI后患者最常見的心理表現是抑郁和焦慮。MI后抑郁癥的發生率可高達80%。有研究發現,抑郁癥與 MI 后的長、短期并發癥有關。短期內,MI發生后的20 min,MI復發性缺血、再梗塞、室性心動過速、心室顫動、心源性休克、肺水腫等是并發癥的獨立預測因素,可造成心內膜炎、左心室附壁血栓和院內死亡。此外,高度的抑郁癥與較高水平的疲勞和較長的住院時間,尤其是在重癥監護室以及較低水平的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有關,說明MI的發病率持續上升與抑郁和焦慮有很大關系[10]。與吸煙和高脂血癥等傳統危險因素相比,抑郁癥是MI后造成不良后果的重要預測因素。抑郁與再次梗死、再入院和缺血性心肌病的風險增加相關。此外,抑郁癥會增加MI后的發病率和死亡率。2014年,美國心臟協會根據對11項研究的分析,在一份科學聲明中評估了抑郁癥對MI后死亡率的影響,8項研究報告了其顯著的關系。根據分析結果,美國心臟協會加強了對抑郁癥作為MI后并發癥和死亡危險因素的評估。MI后患者的應對、心理狀態的恢復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取決于心理(即抑郁),而不是生理因素。研究表明,個人控制和社會支持對預防抑郁癥有很好的保護作用,并能改善不同心臟病人群的生活質量,因此,如果對MI患者的抑郁癥狀進行良好的評估和管理,會改善他們的預后并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對于沒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來說,焦慮也有可能導致其心血管疾病。焦慮與其他因素融合會使心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增加 26%[11]。此外,健康成年人患有抑郁癥也可能導致心血管疾病[12]。
盡管總體研究結果證明焦慮抑郁顯著影響心血管疾病的發展,但在多變量分析中,20 項研究中只有10項報告焦慮與心血管疾病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意味著心理健康問題和MI之間可能存在聯系[13]。故此,本研究對抑郁和焦慮如何導致MI的危險因素進行深入探討。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9 年 1 月 1 日—2021年 12 月 30 日在我院住院治療的300名MI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120例,占40%,女性180例,占60%,平均年齡為(49.1±5.8)歲。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同意,所有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
納入標準:心肌酶譜或心電圖檢查確診為MI;入選患者符合MI的臨床診斷標準。排除標準:無法配合測評的患者;不同意參與臨床試驗者。
1.2 觀察指標
對所有研究對象進行住院焦慮和抑郁量表(HADS)測量,由14個項目組成,分為焦慮和抑郁兩個21分的量表,得分≥8分被認為焦慮或抑郁異常。根據抑郁嚴重程度分為正常 (0~7分)、輕度 (8~10分)、中度 (11~14分) 和重度(15~21分)。觀察患者的性別、年齡、吸煙情況、入院時的生命體征和胸部疼痛嚴重程度以及糖尿病、高血壓、左心室射血分數 (LVEF) 和患MI的經歷。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MI患者的并發癥發生情況
MI常見以下并發癥:急性復發性缺血、肺水腫、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再梗塞、心源性休克、心室顫動。并發癥發生人數及比率詳見表1。

表1 MI患者的并發癥發生人數及比率
2.2 抑郁癥的發生率和治療用藥情況
高度抑郁者中的并發癥患者有59例,占30.3%,低度抑郁者中并發癥患者有48例,占18.8%,說明抑郁評分高的患者 (8~21分)比抑郁評分低的患者 (0~7分)更容易出現并發癥 (χ2= 34.15,P<0.001)。抑郁癥的發生率及治療藥物見表2。

表2 不同程度的抑郁癥發生率及治療藥物
2.3 MI類型與HADS評分
表3結果顯示,從MI類型看,STEMI更為常見。

表3 MI類型與HADS評分情況
3 討論
焦慮與心血管疾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性。據Van der Kooy 等報道,抑郁癥導致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了46%[14]。Roest 等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的心源性死亡風險增加了 55%,與焦慮癥的影響相當[15]。既往研究中,焦慮與動脈粥樣硬化和室性心律失常的風險有關[16-17]。
焦慮是AMI最早的心理反應。有證據表明,患者罹患MI后會增加焦慮癥和抑郁癥的風險,而MI后焦慮癥與MI復發的風險相關[18]。一項研究結果對MI患者住院2個月和12個月后的焦慮癥狀進行了評估,分別有38%和33%的患者出現焦慮癥狀,說明抑郁/焦慮史、女性、年輕、吸煙和心臟病史與MI后焦慮密切相關[19]。Roest 等研究表明,焦慮人群心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增加26%[20]。由于焦慮造成心臟疾病死亡的風險會增加 48%,證明焦慮與非致命性MI之間也存在著關聯性[20]。
除了心理、社會和功能障礙外,MI后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與新發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的風險增加相關[21],該結果強調優先考慮MI后患者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要性。研究結果發現,MI后心理健康狀況不佳是預后不良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獨立于臨床、社會人口、行為和其他心理危險因素[22],心理健康狀況對于識別不良結果風險較高的患者具有增量價值,在目前的危險因素庫中添加心理健康狀況測量可以幫助臨床醫生區分出不良結果風險非常低和非常高的患者群體,從而幫助其識別需要優化護理的弱勢患者。然而,心理健康狀況的測量和預后知識的提高是否會為患者帶來更好的結果是該領域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焦點。
本研究證實了之前調查發現的MI后院內并發癥發生率相對較高的結果。在這項研究中,HADS 用于測量抑郁癥,以區分身體疾病患者的抑郁癥,從而消除了可能掩蓋心臟病因素但可能削弱抑郁癥檢測的跡象。
在行為方面,抑郁癥與鍛煉和健康飲食的減少以及吸煙和其他不健康行為的增加有關。
據Meng等人報道,除了肥胖、吸煙、糖尿病、久坐等生活方式等傳統危險因素外,抑郁癥是心血管病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23-24]。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表明抑郁和焦慮與MI風險增加顯著相關。由于焦慮、抑郁可嚴重影響MI的發展,因此預防和治療抑郁及焦慮可減少MI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