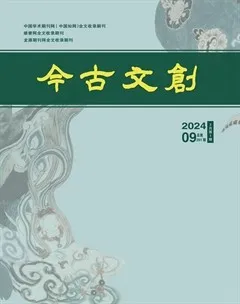精神分析視角下的屈原及其作品
【摘要】弗洛伊德、榮格等人的精神分析方法雖然在病理學的層面上遭到質疑,但其仍不失為一種進入文本的有效批評工具。本文將結合屈原生平和《楚辭》具體文本,探究屈原作品背后的潛意識,進而抽象出屈原在本文、自我、超我等不同階段的形象。
【關鍵詞】弗洛伊德;榮格;精神分析;屈原;《楚辭》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4)09-002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9.008
一、隱含于《楚辭》文本之中的潛意識
(一)個人潛意識
個人潛意識是影響屈原創作的重要因素。弗洛伊德提出:“心理過程自身是潛意識的,并且整個心理生活只有某些個別的活動和部分才是意識的。”[1]他將人的心理結構劃分成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外界環境與意識的關系可以用“刺激——反應”模式概括,屬于表層。例如,長期被疏、遭人陷害和流放造成的政治地位、身份認同的雙重危機,無疑是外界環境對屈原精神的打擊與刺激。《楚辭》中的部分內容指涉了外界刺激在文本維度的展開,折射了精神層面上屈子的個體意志與這種沖擊的抵抗與入侵的關系。如《離騷》中有:“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2]10
對自身高潔品質的再確認、對小人形象的矮化處理對和對自身命運的嗟嘆展現出屈子沉郁的“黑色”意識,與后世《野草》中魯迅作為孤獨啟蒙者的掙扎與迷惘有契合之處。
前意識是可以被喚醒、激活的過往經驗。在三個層次中處于中間層。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指出:“激發夢的真實欲望以及夢所表現的欲望滿足都來自童年。”[3]與之類似的是,屈原的家庭出身及童年經歷是其前意識的重要來源。譬如《卜居》寫道:“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2]182又據《楚勝蹟志》記載:“歸州三間鄉有玉米田,相傳屈原耕此,產玉米,似玉三間鄉一名歸鄉。”[4]
此外,屈原在《離騷》中說:“朕皇考曰伯庸。”[2]73此處的伯庸指屈原父親的可能性較大。而他的父親名未傳世,只在其子的作品中出現。可見屈父并不是高級官員,應是中下層的胥吏。屈原是楚武王的遠孫,屈姓也是來自封地的名稱。他的祖先屈瑕曾任莫敖(集軍事指揮和外交權力于一身的高官),我們可以推測屈原的祖輩是楚國高級貴族,而至其父輩已家道中落。
在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古代社會,作為家長的父親的收入水平、社會威望決定著家庭的政治、經濟地位。故屈原的原生家庭并不能為屈原的發展提供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物欲的被壓抑與體力勞動的辛勞投射到幼年屈原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勞心且勞力的撕裂。這種經驗通過屈原的文學創作得以被喚醒。對貧賤出身和寒士身份的強調成為《楚辭》文本中重要的敘述聲音。截取記憶橫斷面對幼年貧困生活的抒寫與莫言在《紅高粱》中的“恨鄉”心態有相似之處。鄉野——廟堂——重回鄉野的宿命閉環導致的心理落差參與了屈子前意識的質料收集與加工。
潛意識是人類行為的內驅力,包括人的各種原始沖動和本能(以性本能為主),是人生命蠻力的內化。性本能對屈原創作活動的介入可分為兩個方面。
首先,屈原在許多作品中流露出對愛情的贊美和對女性美的肯定。如《湘君》寫道:“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2]45
對愛情的書寫是《九歌》眾多篇目的重要主題。屈子突入人物的心靈世界,通過紛繁的意象聯結男女主人公陷入愛情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煎熬心境。潛入文本之中,大家可以領略《楚辭》中人神交雜、光怪陸離的審美世界。這組詩歌的主人公雖大多是神怪,但他們的感情奔放率性,與沈從文在文學場域構建的“湘西世界”中真淳的男女之情遙相呼應,實乃與古希臘神祇類似的神性與人性的復合體。
其次,大家不能單純地從情欲的角度解構屈原創作的源動力。人是社會人與自然人的統一,社會責任是大共同體(如國家、集體等)對個體的約束。屈原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儒家淑世情懷的影響。在《離騷》中,他集中表現了自己的“美政”思想。“美政”是明君與賢臣共榮共生、雙向互動的政治綜合體。屈原筆下的賢臣范式,具有清高氣節,執著于理想,兼有憂民情懷,在道德上達臻完美,是儒家話語體系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的道成肉身。可見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或干涉了《楚辭》的文本生產,因而其成為屈子之外的隱含作者。“美政”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便是明君。屈原還寫道:“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2]6
正如董仲舒希望用天人感應等學說將君王的行為納入天人合一、君臣協和的軌道,屈原在文學創作中以楚國昔日的君主作為道德標桿,往日君王的賢明與今日懷王的昏聵形成強烈反差,強化了藝術張力。同時,屈子“今不如古”的價值判斷也指向了古代農業社會循環封閉的思維方式。在文本中,《楚辭》中的君臣關系被置換成戀人關系。《離騷》中的“香草美人”的理想和《思美人》的“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2]141的情感流露都屬于政治隱喻的范疇,而其本體便為君臣關系。從文學層面看,這種處理方式進一步激活了傳統詩歌“興觀群怨”功能中“怨”的維度。
此外,正如李澤厚在《華夏美學》中所指出的:“既然集中把情感引向現實人際的方向,便不是人與神的關系……而是……這種種人際關懷。”[5]58這種處理方式展現出屈子的文學世界和現世生活存在的大面積交集,折射出中華民族著眼現實的價值選擇。從情感層面上看,作為臣子懷才不遇的郁憤、對國君的憂與怨的復雜情感可以抽象出超越時空界限的人類普遍、共通的悲情,與少年維特求愛情而不得的苦悶遙相呼應,也與《沉淪》中主人公承載民族恥辱和個人困境的雙重痛苦相契合。
綜上所述,屈原文學創作背后的“性本能”具有形而下與形而上的二重性,從形而下的層面上看,他為美好愛情立傳、放歌,以人性解構神性,又不將愛情異化為肉體之愛,在靈與肉的二律背反中實現了超越。從形而上的層面上看,傳統意義上的性本能以屈原為中介,得到了升華與迭代。君臣關系和家國憂思本質上已躍出了性欲的范疇,但屈原思慮之深,感情之強烈,與熱戀中的情人對待自己的愛侶有相似之處。屈原通過文學創作,推動形成了一種更為完善的“性本能”范式,即情欲、文才、社會責任的復合體。屈原的文學實踐張揚了人類豐沛的情感和鮮明的、固有的社會屬性,這對弗洛伊德等人建構的精神分析理論形成了有益的補充,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其“泛性論”的弊端。
(二)集體潛意識
榮格繼承了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又有所突破。他提出了“集體潛意識”理論,認為個人潛意識中包括祖先的經驗的沉淀和濃縮。此外,榮格還認為,全人類的群體意識被濃縮、加工至個體的大腦結構中時,便形成了不同種類的原型(archetype)。再以屈原的出身為例,屈原的祖先中還有一位屈完。魯僖公四年,齊國率諸侯欲討伐楚國,他臨危受命前去交涉。面對齊國國君的耀武揚威,他有勇有謀,以楚國的強大實力作為背書,使齊國不戰而退,展現出卓越的外交家風范。
同時,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夏歷正月初七,即寅年、寅月、寅日。屈父認為屈原生辰不凡,為其取名“平”,意為期望他將來為人公平正直;又字“原”,有希望他不忘記養育自己土地之意。結合上述內容和屈原沒落貴族的出身,可以推斷出屈原的家族具有光輝的歷史和輔佐楚君的傳統。雖然屈原家族的政治、經濟地位可能自屈完等先祖后進入了波動下滑的通道,但是忠君愛國等價值觀念卻可在家庭這一場域中自上而下垂直傳遞,這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屈原對楚國的政權認同。因而屈原在集體潛意識的影響下,創作也具有祖輩價值觀念的烙印。如在《離騷》中,屈原以“帝高陽之苗裔兮”追溯自己高貴的出身,此時文本中的敘事聲音來源已被置換為屈氏先祖。同時屈子在此篇極言服裝配飾之華美、行為之卓爾不群。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作為貴族的屈原先祖的生活經驗滲入了《楚辭》文本之中。
此外,屈原在創作中,進入了一種類似催眠的狀態,獲得了某種超經驗的體驗,即與承載中華民族群體記憶的“原型”同頻共振。如在哀悼秦楚戰爭中犧牲的楚國士兵的《國殤》中寫道:“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2]75
屈原想象了戰場廝殺之慘烈,渲染了戰爭的殘酷,實現了楚國將士犧牲的崇高化。屈子在詩篇中極言不同方位環境的惡劣、可怖,似但丁在《神曲》中對地獄、煉獄的描摹。他又在文末呼喚英魂回歸、贊美將士勇武,或是遵循了一定的體例。朱光潛在《詩論》中指出:“詩歌與音樂舞蹈同源。”[6]8《國殤》具有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二重性,即具有祭歌的功能。屈原得以成此《國殤》一篇,與積淀著中華民族先民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價值觀和祭祀經驗的原型的介入密不可分。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在15世紀的文學和哲學領域里,瘋癲經驗一般都表現為道德諷喻的形式。”[7]28屈原在“催眠”階段的創作體驗雖然具有噴射式抒情的鮮明特征,與“瘋癲”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屈原的情感抒寫仍然被限定于某種理性場域(即作為原型的倫理道德、國家觀念等)之中,這也區別于酒神精神式的無節制迷狂。李澤厚在《美學四講》中將人類的審美層次分為著眼于感官刺激的“悅耳悅目”、走向人類心靈的“悅心悅意”和象征人類最高審美能力的“悅智悅神”。[8]146在個體生命律動與先民經驗積淀、自然規律的水乳交融中,屈子將作品的時空維度無限擴展,達臻了“悅智悅神”的境界。
二、屈原的本我、自我和超我
(一)本我
在弗洛伊德的理論體系中,“本我”是人格結構最原始的無意識的部分。筆者將屈原青壯年時得到君主賞識、仕途順利的時期類比為“本我”。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9]127
這時的屈原身居左徒高位,對楚國的政權認同感應達到了頂峰。他又出使齊國,加強了齊楚聯盟,壯大了楚國的威望。此時的屈原堅定地認為“賢臣——明主——強國”三位一體的楚國盛世將會實現。可見屈原在這一時期的人格形象是賢臣與愛國者,較為單純。
(二)自我
而“自我”往往會結合現實因素滿足自己的需求。屈原的所作所為觸怒了楚國的既得利益者。先是尚官大夫靳尚欲奪取屈原所定法條的文稿,遭到屈原拒絕后,他便向懷王進讒言,挑撥楚王和屈原的關系。此后又有指責屈原淫亂等誹謗。楚王聽信讒言,逐漸疏遠屈原,屈原從左徒降為三閭大夫,逐步遠離楚國的權力中心。
此后屈原又因反對與秦國聯合、勸諫懷王、《離騷》詩禍、為懷王招魂觸怒新王等風波屢遭貶黜,直至流放漢北、放逐江南。遭遇個體價值與家國理想雙重危機的屈子感受到知識分子失去權力庇護的痛苦與無力,對人生的意義以及楚國的命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文本的層次內短暫地隔離外界痛苦,排解情緒。此時的屈原已經進入了“自我”狀態。但是“自我”狀態下屈原的人格并不是完善的,自戀與戀君、入世與出世、生存與死亡三對矛盾束縛著屈原。
首先,再以《離騷》為例,屈原將自身形象塑造得極端完美,側面反映出一種自戀情結。然而,他又極言受到懷王疏遠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對小人態度的關注似乎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們得到楚王寵信的嫉恨。自戀和戀君的矛盾讓屈原在追求自我和等待重新受用中掙扎。
與莊子對現實的冷眼旁觀不同的是,屈原在審美世界中“生活在樹上”,卻又在現實世界中“心系大地”。他在《天問》中追憶堯舜禹的賢德,以提問的方式加以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在樹立道德標桿以自勉。這也展現出屈原人格中存在相當的溫柔敦厚、兼濟天下的士人成分。
屈原雖最終選擇自沉江中,但對生的留戀和對死的恐懼困擾著屈原。例如在《懷沙》中,屈原寫道:“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陲不斵兮,孰察其揆正?”[2]136
屈原仍在不斷強調自己的懷才不遇,似乎對人世還有所留戀。但是他在行文過程中逐步克服恐懼,擁抱死亡。他在文末寫道:“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2]139這種坦然的態度與拜倫臨終前的義無反顧若合一契。
整體上說,這三對矛盾貫穿屈原“自我”狀態的始終,但并沒有影響屈原人格的進一步升華。
(三)超我
屈原達臻“超我”境界的標志是他的投江自殺,途徑是通過死本能這一破壞性本能的釋放。“超我”狀態下的屈原,肉體已死,精神猶存。屈原的“超我”形象是一種抽象化的人格,不但是屈原個人精神的結晶,而且更是中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品質群體意識的集合。這已經超出了作為詩人或是文化符號的“屈原”的范疇。
歷史上不乏一些文人是以為理想或名節獻身的殉道者的身份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種宗教犧牲式的人格超越如同屈子自沉大江的千年后的余響。李澤厚認為:“中國人很少真正徹底的悲觀主義,他們總愿意樂觀地眺望未來。”[10]265促使屈子選擇自決的直接原因來自外界,即家國歸屬的幻滅,而不是屈子對未來信心的喪失。對此在世界中楚國國運和民生疾苦的關照也包含了相信發展進步將要發生的價值判斷,蘊藏著寶貴的現代性思維。這又使得屈原實現了對農業社會思維的超越。屈原“超我”境界的實現使得“我”這一個體的能指溶解至群體話語之中,令“超我”的內涵擴展至一類人的群像,這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論。
三、余論
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共同驅動著屈原的文學創作。他的個人經歷、思想嬗變以及時勢的變化推動著屈原人格“本我——自我——超我”的迭代與升華,雖有矛盾阻礙,但他最終以死本能突破了自我,用自沉江中締造了不朽的“超我”人格。精神分析只是進入屈子心靈世界和《楚辭》文本的方法之一,而若要動態地把握作為某種文化符號的屈原及《楚辭》二合一的文本、美學、歷史等全維度的開放系統,仍需要來自文化人類學、美學、歷史學等不同領域的分析方法的引入。
參考文獻:
[1]劉宏宇.弗洛伊德與榮格精神分析文學批評觀比較[J].湖北社會科學,2014,(08):144-147.
[2]屈原,宋玉等.楚辭[M].北京:中華書局,2010.
[3]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孫名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4]高學棟.舉世混濁我獨清 眾人皆醉我獨醒——論屈原的生平及其創作[J].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5,(06):95.
[5]李澤厚.華夏美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
[6]朱光潛.詩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7]福柯.瘋癲與文明[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2019.
[8]李澤厚.美學四講[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
[9]羅宗強,陳洪.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10]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作者簡介:
侯家琦,男,漢族,天津人,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