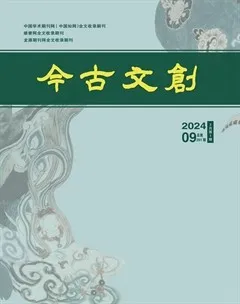幻想的劇場
楊金萍
【摘要】圖米納斯的戲劇作品有著空靈、怪誕又結合輕柔、優雅的風格特色,他導演的作品充分發揮了戲劇美的張力,體現著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他的作品中有設置的“第三視角”的角色以及怪誕風格的元素,幫助戲劇舞臺達到“間離”和充滿游戲化的效果,進而使觀眾能夠獲得“游戲性”的體驗。但是圖米納斯的作品又不同于令人眼花繚亂的秀場,不能僅僅將其看作是一出大型的游戲,他是在通過凸顯戲劇的即時效果,來引導觀眾進入更加崇高的境界,走向一種永恒的美。這一切是繼承了蘇聯戲劇家瓦赫坦戈夫的“幻想現實主義”戲劇流派,在不斷地探索和實踐中構成了他自己的“新幻想現實主義”創作風格。
【關鍵詞】圖米納斯;新幻想現實主義;導演手段;反再現戲劇
【中圖分類號】J80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9-007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9.022
一、前言
里馬斯·圖米納斯于1952年出生于立陶宛的一個小鎮里,他的童年生活是輕快美好的,在童年時期他就受到了當地不少宗教戲劇演出的影響。長大后,他先后考入立陶宛音樂學院和俄羅斯戲劇學院,1979年到1990年,圖米納斯在立陶宛國家戲劇院擔任導演,1994年到1999年,他升為了首席導演。1990年,圖米納斯創立了自己的劇院,名為“維爾紐斯·馬利劇院”。2007年,他來到瓦赫坦戈夫劇院擔任藝術總監一職,并在此開啟了更為精彩的戲劇創作生涯,期間他導演了諸多知名的作品,有《假面舞會》《葉甫蓋尼·奧涅金》《俄狄浦斯王》《萬尼亞舅舅》《戰爭與和平》《最后的月亮》等。
瓦赫坦戈夫劇院是由蘇聯戲劇家瓦赫坦戈夫在1913年創辦的,1926年,劇院從“戲劇講習所”被更名為“瓦赫坦戈夫劇院”,并始終由瓦赫坦戈夫的繼承人經營管理。瓦赫坦戈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一批學生中的一位,被斯坦尼認定為“斯氏體系的權威認證者”,曾經態度堅決地執著于莫斯科藝術劇院的現實主義戲劇創作。但是在十月革命后,瓦赫坦戈夫的戲劇觀產生了極大的轉變,他對當時總體的創作風格提出了質疑,對戲劇進行了大膽的革新,徹底反叛了斯坦尼體系,提出了“幻想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式。
圖米納斯的創作風格與瓦赫坦戈夫的創作理念極為相似,在瓦赫坦戈夫“幻想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圖米納斯提出了“新幻想現實主義”的觀點。“幻想現實主義”強調劇場性、表演呈現上進行表現和體驗的結合,并要求舞臺要對劇本進行現代化的再創作。“新幻想現實主義”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了戲劇舞臺上的有機夸張,強調舞臺要給觀眾帶來幻想的希望。正如他自己對“幻想現實主義”的理解:“現實就是鄉下牛棚里難聞的糞便,然而它揮發后會在棚頂,就成星星一樣的水滴。夜晚時看在眼里很美,當它落在嘴里已經純凈,這一滴水就是‘幻想現實主義”[1]
本文以圖米納斯導演的《葉甫蓋尼·奧涅金》 《萬尼亞舅舅》 《假面舞會》 《俄狄浦斯王》等戲劇作品,通過對具體舞臺呈現的具體分析,描繪圖米納斯的創作特色,并以此了解他的“新幻想現實主義”創作理念。
二、新幻想現實主義中的“第三視角”
圖米納斯的舞臺上常常存在一個“第三視角”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在舞臺上大部分時候處于游離的狀態,人物的行動脫離于整個故事的劇情,他們在舞臺上漫無目的地游移或是自顧自地蜷縮在舞臺的角落。他們是舞臺上的“邊緣人”,有著在舞臺上隱形的能力,但是當劇情出現轉折或是達到高潮時,這些“第三視角”又會出現在事件的中心,打破人物紐結的關系,打斷觀眾的視野重心。
在圖米納斯導演的《俄狄浦斯王》中,有三個“第三視角”的角色:頭上綁滿了白色繃帶的人,身穿黑色連衣長裙的女人,還有一個是手執長矛身著鎧甲的男人。繃帶人時而像是一個在舞臺上游走的人體細胞,漫無目的地緩慢行動著,構成獨屬于自己的風景。有些時候他出現在劇中人物陷入了靈魂探究的情境之中,當歌隊集體轉身開始向天神祈禱,希望俄狄浦斯能夠早日找到這場瘟疫的源頭,希望這場瘟疫能夠早日離開忒拜。此時繃帶人在歌隊身后佝僂著身子緩慢走動,就好像那令人沮喪的瘟疫,他穿行在舞臺之上,模樣與舞臺上的其他人事物十分不和諧。他又像是一種冥冥的宿命、一粒游走在舞臺上的訊息,預示著這場瘟疫最終的結局。當先知對著俄狄浦斯大聲喊出:“你雖有眼,看不見你的磨難”之時,繃帶人和俄狄浦斯一起站在舞臺中間巨大的滾輪上,面對生命的質詢,二人急躁地邁步,那一刻繃帶人像極了已經自戳雙目的俄狄浦斯,像極了已經自我流放的俄狄浦斯,像極了冥冥之中已經達成了神諭的俄狄浦斯,他與還未被悲劇降臨的俄狄浦斯形成了跨越時空的互文。轉身他又拿走俄狄浦斯脫下的衣服,成為一個制造間離效果的“撿場人”,沉痛裹挾著詼諧,這也是圖米納斯創作特色的一部分。在劇目的收尾,像是殘破的命運一般,繃帶人緩緩走向舞臺中央,給眾人帶來伊俄卡斯忒已死的消息,他大聲疾呼著形容俄狄浦斯怎樣用伊俄卡斯忒袍子上摘下的金別針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嘶吼著:“你們再也看不見我所受的災難,你們看夠了你們不應當看的人,不認識我想認識的人。你們從此黑暗無光。”他將所有對命運的質詢化作呼號,此時,他是俄狄浦斯生命悲劇徹頭徹尾的見證人。
相比于繃帶人,身著鎧甲的男人在舞臺上的動作步伐更加矯健,表演節奏更加靈動,他經常揮舞著長矛出現在人物關系劍拔弩張之時。當俄狄浦斯質問克瑞翁是否由于他的罪行導致了城邦的瘟疫時,身著鎧甲的男人拿著長矛不斷變換動作,他的身體成為背景的一部分,行動的同時打破了干枯的人物對話。像繃帶人也做“撿場人”一樣,鎧甲人做了舞臺上的“物造型”。舞臺上,當伊俄卡斯忒問俄狄浦斯究竟是什么令他如此憤怒,身著黑色長裙的女人手持圓盤,身披鎧甲的男人手持長矛站定在舞臺上,兩個人的動作靜止,貼近對話的中心,形成一幅凝固的圖景。俄狄浦斯此刻憤怒的情緒像是一種自我問責,他用憤怒來掩飾自己的不安以及不愿面對的苦痛。此刻的兩個“第三視角”人物更像是兩人情緒的外化,精神的演繹。
在《葉甫蓋尼·奧涅金》的開場,奏樂人和塔季揚娜、奧涅金一起出現在舞臺上。作為這部劇中的“第三視角”,她始終靜靜地待在舞臺的角落,常常在奧涅金久坐的椅子旁彈奏自己的樂器,有時她會抬起奧涅金的手放在自己亂蓬蓬的頭發上,在毫無疑義的動作中充當一個“道具”。看見年輕帥氣的連斯基和奧涅金登場,她也會不由得露出欣賞美貌的傻笑。雖然她時常隱形,但是奏樂人始終在完成對“第三視角”的塑造,她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舞臺上的各個主角,并隨時以手勢和眼神做出微妙的回應,不斷打破戲劇嚴肅的狀態,以詼諧回應整場演出。圖米納斯戲劇中“第三視角”的角色形象完成了一種“間離”的效果,他們的走動將觀眾從沉浸式的劇情中拉出來,讓觀眾能夠走出被敘演劇情帶動情緒的狀態。但是又與布萊希特的“間離”不同,布萊希特的“間離”使觀眾從感性的狀態中走出來,走向理性的思考,從而達到戲劇的教育目的。但是圖米納斯的“第三視角”,是為了給觀眾提供一個審視的方向,并且這些審視者的突然出現能夠形成打斷的態勢,達成一種令觀眾恍然的效果。這種恍惚也是促成“游戲感”的重要方式,是“新幻想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圖米納斯的創作區別于其他戲劇能夠帶給觀眾的獨特感受之一。
三、新幻想現實主義與“游戲”
談及圖米納斯認為演員需要最后以什么樣的狀態進行演出,他說道:“沒有固定的,這完全看你每天不同的心情。因為這場戲就是要有極強的游戲感,而固定的方式只會讓它變得無聊。”[2]圖米納斯的戲劇極大程度地發揮了戲劇的即時性,在他的創作理念中戲劇不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復上一次或是理想的范本,而是每一次的演出都是唯一一次,都是嶄新的創造。哲學家德勒茲在自己的哲學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對戲劇創作的見解,即反再現戲劇。德勒茲思想是一種后結構主義思想,強調在同一性之外進行建構,強調差異、生成、感知與感受。于是,在他看來,值得認可的戲劇藝術應當是對現實生活的權力的顛覆,應當是在同一性之外的。而再現戲劇始終用生活本身的語言回應生活,萬變都沒有能夠跳出同一性進行建構,這樣的戲劇始終是被生活的權力支配的。關于戲劇創作,德勒茲的表述與圖米納斯的發言出奇一致,認為戲劇應當是“特定觀眾的獨特性和一個戲劇事件的某些特征,而不是表演一個熟悉的和精心排練的行為模式的完美重復。”[3]
圖米納斯對于戲劇“反再現”的追求具體表現在,他創作的戲劇作品尋求一種強烈的游戲感,這是一種內在的精神追求,深刻的樂觀主義,強調每一次的“在場”。這與對于外在形式化的“游藝”的追求不同,呼應著戲劇即時性的特點,游戲感給圖米納斯的創作帶來了特別的活力。
圖米納斯戲劇中的怪誕元素是通往游戲感的重要方式。例如,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大幕拉開出現在舞臺上的便是老年的奧涅金和連斯基,早已去世的連斯基以不可能的形態站在那里,使一切變得怪誕而荒謬,他的出現打破了時空間的存在,打破了故事的順序進程,生命變得無解,敘事的意義也便不復存在,圖米納斯的舞臺時刻在進行著打破與解構。劇中塔季揚娜離開久居的鄉村趕往城市,路上突然出現一只兔子,這只兔子扭動著肥胖的身軀卻穿著芭蕾舞的服裝,士兵舉槍對準兔子,眼看著槍口朝自己舉起,這只兔子卻扭動身體跳起了妖嬈的舞蹈,在詼諧的音樂中,舉槍的士兵暈頭轉向。在《萬尼亞舅舅》中,葉蓮娜映著怪異的音樂拿著一個呼啦圈緩緩地走上舞臺,在把呼啦圈遞給萬尼亞舅舅之后,自己便躺在地上,她的生活充滿了厭倦和煩悶。沉悶與怪誕交織,契訶夫作品透露出無限的隱秘感,但也能夠用非常規的語言在舞臺上呈現。其中,萬尼亞舅舅的舉槍是劇作情節的精彩瞬間,但是在舞臺上卻出現了滑稽的“失誤”,巧妙的設計引得觀眾哄堂大笑,詼諧的氛圍與后來萬尼亞舅舅沉痛的憤恨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驚心動魄的一瞬間,圖米納斯選擇了用詼諧搞笑的方式來呈現,差異化是帶來怪誕感受的重要表現方式。再說《俄狄浦斯王》的創作,原劇本基調本是古典、深沉的,這無可非議是一部經典的悲劇作品。圖米納斯一方面選擇了以部分現代著裝對其進行詮釋,穿白色西裝的俄狄浦斯,集體穿黑色西裝的歌隊,卻有另外的角色仍然穿著古典,時刻帶給觀眾割裂的感受。另一方面,圖米納斯還在創作中加入了許多詼諧的音樂,克瑞翁的登場伴隨著滑稽搞怪的音響聲,上場時同歌隊打招呼的愉悅與后來面對俄狄浦斯責難時的哀聲形成強烈的反差。圖米納斯擅長于打破舞臺上“應該有的”,創造出“不該有的”現場,時刻提醒觀眾,舞臺上的一切都是區別于現實生活的一場狂歡。正是通過打破規則樹立起了舞臺上的游戲感,圖米納斯巧妙運用反差、夸張以及打破時空間等導演手段完成了每一次作品的敘事。
關于游戲,在《游戲的人》中荷蘭學者約翰·赫伊津哈指出:“游戲可以求助于嚴肅性而嚴肅性也求助于游戲。游戲可以升到優美和崇高的高度。而嚴肅性與這高度遠不相稱。”[4]這里游戲與嚴肅性的相互求助局限于狹義的游戲,指的是動物通常的娛樂項目,而后面游戲和嚴肅性產生了是否能夠形成優美與崇高的分野。圖米納斯創作追求的就是一種反嚴肅性的游戲,將嚴肅的規則剔除,拒絕重復,發揮戲劇即時的效果。圖米納斯創作的內核就是一種破壞,一種對傳統敘事模式的破壞與解構,正是破壞了真實生活的權力結構,創造了嶄新的舞臺話語體系,強調了即時的、在場的、反再現的戲劇。
在許多書有關圖米納斯作品的劇評中,評論人常常強調圖米納斯的作品如何制造了浪漫且極具藝術氛圍的作品,講述他的舞臺如何與曼妙的音樂、優美的舞蹈結合形成了空靈之感,但是都沒能最終達到對他戲劇作品強調游戲感的思考,而更多的是局限在其浪漫化的表象上。圖米納斯作品的唯美屬性追求的并不是一種淺表的類似于浪漫主義的舞臺呈現,而是更深刻地通往了精神的層面,通向了他“新幻想現實主義”的戲劇觀,通向了“在場”,通向了戲劇藝術的即時性本質。
四、戲劇舞臺不是秀場
圖米納斯明確提出“戲劇”和“秀”是有區別的,他曾表示:“讓演員在舞臺上脫衣服并不難,難的是點燃觀眾心中的火焰。什么是戲劇,什么是秀,這是應該區分清楚的。”[2]
圖米納斯導演的一些作品在劇情上其實算不上精彩,比如《葉甫蓋尼·奧涅金》講述一個俄國“多余人”形象的男子在年輕時辜負了一位姑娘的愛意,到了自己年老之時,姑娘嫁作人婦才感到追悔莫及。但就是這樣簡單的劇情,在圖米納斯的舞臺上卻那樣深刻而動人,作品仿佛擁有了新鮮的生命活力。這些活力是由圖米納斯的導演手段帶來的。例如在《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結尾,伴隨著激昂的鼓點與優美的樂聲,塔季揚娜穿著飄逸的長裙與一只巨大的仿真熊共舞。這時的塔季揚娜已經經歷了人生的許多跌宕起伏,她已經從當初的少女變成了而今的貴族夫人,在前一幕她的臉上儼然寫滿了退去了理想主義的疲憊,呈現在舞臺上的是另一個的她。原本已經失去了靈巧與活潑,但是當音樂聲響起,仿佛時間再次流動一般,舞臺的時空再一次變得模糊而難以言說。人們的視線跟隨著那只巨大的仿真熊,跟隨著塔季揚娜流淌著的舞步,這不禁讓人想起在她的青年時代,翻滾而過的她與奧涅金的故事,翻滾而過的一個少女熱烈的心,仿佛時間靜止了幾分鐘,熱情、悔恨、悲哀同時在那一刻滑過,最終又歸于巨大的平靜之中。
在圖米納斯構思的舞臺上,演員并非是單純地敘演一則故事,更是在傳達一種有著永恒力量的思維和機制。他十分擅長在舞臺上展現人永恒的情感,而非一時的情緒,如果把《葉甫蓋尼·奧涅金》一劇簡單地形容是在展示人成長中的懊悔,那么圖米納斯的重新構建則是在向觀眾傳達一種渴望,一種模糊了時空間的精神世界的構建。當老年連斯基和老年奧涅金、青年奧涅金同時出現在舞臺上時,觀眾看到的不再只是人無法抓住的時間的流逝與無盡的懊悔,赤裸著呈現在眼前的是關于生命的存在與人生的體驗。這種體驗支持著人從悲哀的情緒走向希望,絕望是作品呈現出的一部分內容,但在這里是更重要的是希望。也正是在這些瞬間,即時的戲劇成了永恒的藝術作品。“新幻想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支持著在圖米納斯的戲劇舞臺上出現的這些精心的設計,這是區別于生活與技巧的呈現,是有據可循的來自靈魂深處的信念,是圖米納斯傳達自己信仰的通道,而不是毫無情感的元素的堆砌,不是無限的教化與空吼,在圖米納斯的創作中沒有為了取悅觀眾而存在的多余的賣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戲并不是為了排給觀眾的,而是排給天使看的。天使就在舞臺的燈架上。戲劇應該是讓觀眾通過演出和上帝進行溝通,但不是扮演上帝給觀眾傳道。”[2]
在現代科技發達的今天,有太多作品借助于各類設備、多媒體來實現劇目的創作,確實給戲劇舞臺帶來了巨大的生機,但是也帶來了湮滅。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急于求成地在作品中放置了太多無端的堆砌,作品中堆滿了冗余的感官刺激。現代觀眾感知了太多人造的煽情、人造的興奮、肉體的沉溺,許多作品無法說是需要觀眾去感知,而是在主動“投喂”。
20世紀50年代開始,戲劇被質疑:移情的傳統造成了自身危機。傳統的亞里士多德式戲劇被懷疑,模仿生活的“再現戲劇”被質疑總結了太多的戲劇技巧。于是“后現代主義戲劇”開始尋求變革,它們開始主張戲劇空間的語言,強調以運動和身體來喚醒觀眾,這通常被看作是一種與原始主義息息相關的“復歸”運動,是一種潛意識的面向儀式的追尋。從一些角度來講,圖米納斯的創作也可以說是一種是一種“復歸”,拋卻了對于“再現戲劇”的追求,也剝掉了“秀”的外殼,而選擇了探尋內在的真實。
談及悲劇與現代創作的關系,有種觀點指出:“在當今這個人人都可以自稱是‘多余人或是‘局外人的時代,這些概念業已失效,越來越成為景觀式的存在。”[5]悲劇在當下的位置越來越值得思考。圖米納斯戲劇帶給觀眾的有關希望的感受似乎正可以填補悲劇的空缺,這種樸實的渴望可能實現新時代的劇場性的繁榮。
五、結束語
圖米納斯的導演創作無疑給當下的戲劇舞臺帶來了巨大的生命力,他的“新幻想現實主義”透露出他創作的活力所在。對此,直接的借鑒并不適合所有的創作環境,而且“模仿”一詞也本就有悖于圖米納斯的創作思路。但是創作者也許可以從他的“新幻想現實主義”理念中找到更多的創作靈感,窺見更多舞臺上的可能性,發掘更多現時應當被拋棄與應當被創造的東西。
參考文獻:
[1]楊申.幻想現實之間相差的不僅是主義[N].北京青年報,2016-9-6.
[2]楊申.里馬斯·圖米納斯與“新幻想現實主義”[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學報),2020,(01):58-71.
[3]Krasner,David,and David Z.Saltz,eds.StagingPhilosophy:Intersections of Theater,Performance and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2006,122.
[4]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38.
[5]費洛凡.“美”是方法,又是目的——評VMT國立劇院《假面舞會》[J].戲劇與影視評論,2018,(04):28-37.
[6]陳世雄.現代歐美戲劇史[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7]劉桂誠.“再現”的終結:德勒茲的戲劇思想探究[J].四川戲劇,2021,(11):33-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