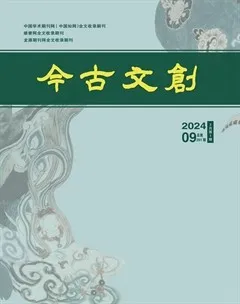嚴復《天演論》中的譯者主體性
楊欣三
【摘要】作為語言轉換和文化傳播的橋梁,翻譯在不同的文明交往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作用同樣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在傳統的翻譯理論與實踐中,譯者往往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人們往往忽略了他的主體地位,及其在翻譯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從嚴復譯《天演論》出發,結合翻譯活動所處的時代背景來分析譯者主觀能動性對翻譯活動,包括翻譯策略以及翻譯方法的選擇所產生的作用與影響。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天演論》;嚴復
【中圖分類號】H31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9-009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9.029
一、譯者主體性
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其在翻譯過程中為達翻譯目的而發揮的自身主觀能動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根據自身的語言能力、文化背景、審美觀念等因素,對原文進行理解和解讀,從而創造性地進行語言轉換的過程。可以說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對翻譯結果有很大影響。雖然翻譯的目標是盡可能準確地傳達原文的意思,但由于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異以及個人理解的不同,譯者在翻譯時難免會加入個人主觀色彩。縱觀西方翻譯史,譯者主體性的發展并非一蹴而就。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指出,翻譯的實質就是要使信息適應接收者的語言需求和文化期望,從而實現完美、自然的表達。可以看出此時翻譯活動已經開始關注到譯者本身,譯者不再是被動的。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提出譯學中的文化轉向后,譯者成了翻譯過程中文本操縱的操縱者,意識形態、贊助人以及詩學都會對其產生影響。隨著翻譯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翻譯學已不再單純局限于文本的研究,社會、歷史和文化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也已被納入翻譯學的研究范圍。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體,譯者的角色得到了明確的肯定,進而他們的主體地位也得到了確立。到20世紀后半葉,解構主義翻譯思想日益擴大,其代表人物本雅明認為,只有從原作中找到所隱含的特殊意義,才能與原作產生共鳴,翻譯中也會有譯者本身對作品的理解和創造性的闡釋。因此,好的譯文必然是原作與譯作共同創造的結果,離不開任何一方的努力。至此,譯者主體性得到充分發揚。到20世紀30年代起,在國內,譯者的主體地位也開始慢慢得到譯界的認可。
本文通過對嚴復《天演論》譯文的分析,力求探索譯者主體性對翻譯活動的影響,通過研究可以將影響譯者主體性的因素分為兩類:一是譯者自身個體因素,即譯者的語言風格、翻譯策略等;二是社會因素,即從翻譯的角度來考察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和社會環境對翻譯的影響。另一方面,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往往繞不開翻譯活動的目的。因此,在探討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同時,就必然要分析其翻譯目的,進而探討其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
二、嚴復譯《天演論》中譯者主體性的制約因素
(一)嚴復的個體意識形態
在探討嚴復個體意識形態對其翻譯策略以及翻譯思想的影響時,就必然要先對嚴復個人情況進行研究。嚴復(1854—1921),清末著名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他被譽為中國翻譯界的先驅和奠基人之一,對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光緒年間,嚴復被派遣留學英法。在此期間,嚴復逐漸開始研究英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達爾文關于進化論的學說。在國家與民族危機面前,嚴復深刻意識到,中國之所以貧困和衰敗,其根源不在器具,而在制度。在其發表的一系列政治言論中,對封建專制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他提倡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以及新學,并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啟蒙思想,從而為維新運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嚴復及其同代人對進化論的研究,其研究重點并非是對進化論的研究,而是對生物進化原則與社會演化法則的研究,但二者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嚴復在了解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思想之后,深刻領會到這種在弱肉強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則同樣適用于人類社會。
嚴復在接受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受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因此,可以說嚴復的個人意識形態是中西方不同思想的摻雜與貫通。這一創造性的個體意識為當時的中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資產階級社會文化,從根本上撼動了封建專制的思想根基。而其具有先進性的個體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對《天演論》的譯介。
(二)社會性因素對譯者主體性的制約
探討社會性因素對嚴復譯者主體性的影響就必須將時間倒回到那個風雨飄搖的時期。甲午一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彼時沉醉于天朝上國迷夢中的中國人民被猛然驚醒,他們從未想過如彈丸之日本也能將自己當時最先進、最強大的北洋水師徹底擊敗。社會意識的“覺醒”正慢慢發芽。正是處于當時這樣一種社會大背景之下,嚴復想借翻譯《天演論》來達到一種“啟民智”的效果。《天演論》的基本思想是: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是在競爭中不斷演化而來,也就是所說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道理。人們通常只是從生物學層面去研究“進化論”的思想,而嚴復卻看到了進化論中“叢林法則”的社會學意義。當中國正面臨著西方列強與日本的雙重威脅時,進化論所具有的社會學含義,對那些還沉浸在“天朝上國”幻想之中的中國封建文人來說,無疑是一次振聾發聵的警示。
因此,生于當時中國之社會,而又作為具有獨特視角的先進知識分子,嚴復自然而然地卷入了這場社會變革。而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筆與文章就是他們戰斗的武器。他們要面對的是當時落后的社會制度與迂腐的人民大眾思想,他們要達到的目的是“啟迪民智,警醒世民”。所以,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就是帶著這樣一種目的,同樣,翻譯目的論對嚴復譯文的分析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無論是個體意識形態還是社會因素的制約,在分析嚴復譯《天演論》時,其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并不少見,這也是嚴復翻譯過程中值得探討的一大特點。
三、文化語境下譯者主體性的探析
(一)嚴復翻譯策略的選擇
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已然被中國譯壇所認可。然而,《天演論》的問世,也使得許多學者認為嚴復的翻譯并未達到他所要達到的“信”的境界。但仔細研究可以發現,這里的“不信”是嚴復有意為之。嚴復在翻譯時對原文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有意識的增減、創造,對此,黃忠廉先生認為,當嚴復翻譯《天演論》時,他注意到了其中的不足之處,并加以改進;同時,對于其中的亮點,能夠與國內外的作品進行比較,并愿意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
1.省譯法
在嚴復譯文中,刪減策略的使用很是常見。為了滿足特定的翻譯要求,有時候需要在翻譯的過程中有意地刪減某些信息。在《天演論》中,嚴復為實現自己啟迪民智、警醒世人的翻譯目的,對原文信息的選擇、刪減隨處可見。
赫胥黎起初書名為Evolution and Ethics,即《進化與倫理》。而嚴復卻將其翻譯為《天演論》,嚴復取名為天演論其實是與原題目中“進化”部分對應的,“倫理”部分則省略不談。而嚴復此舉是考慮到自己翻譯該著作的目的,是為了喚醒世人,救亡圖存。同時,這也是嚴復自我意識的覺醒影響了其翻譯策略的選擇。
2.增譯法
赫胥黎在其原作中對自然界生存環境與生存法則的描寫頗多,而對于這部分內容嚴復在處理時并不僅僅是對原文的翻譯,因為要考慮到該譯著所要達到的社會影響及其文化意義,就必須要做出延伸與補充。這一點在《導言一:察變》中就有所體現:
原文:“They filled up,as they best might, the gaps made in their ranks by all sorts of underground and overground animal ravagers.”此句嚴譯為: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嚙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這句話用白話文的解釋為:上有鳥獸的踐踏啄食,下有螞蟻幼蝗的啃咬傷害,枝葉枯萎殘缺,生死短暫,從茂盛到枯死只是一會兒的事,不能詳細深究。看原文與譯文的對應會發現,似乎彼此之間并不能很好的對應,“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是嚴復基于原作語境引申創造而來的,用意何為?原文描寫的就是被鳥獸蟲蟻啃食的植物瀕臨死亡的畫面,嚴復將這種場面境況轉嫁到當時的清政府身上,是為了再次讓世人看清風雨飄搖的清政府正面臨的真實境況。因內部、外部兩種社會因素的制約使得其譯文歷史作用更加突出,進而增強了讀者的歷史使命感。
3.對原作內容的再創造
在分析嚴復的譯文時會發現,很多時候其譯文與原文并不能達成很好的對應。原文:“...not merely the world of plants,but that of animals,not merely living things,but the whole fabric of the earth...and has endured through boundless time,are all working out their predestined courses of evolution...”該部分嚴復翻譯為:凡茲運行之理,乃化機所以不息之精,茍能靜觀,隨在可察;小之極于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隱之則神思知識之所以圣狂,顯之則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原文內容主要闡釋了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在處于不斷變化中,強調的是自然演化的結果。嚴復在他的翻譯中,把話題轉移到了人類的社會上,在原文的基礎上進行了延伸與再創造,指出時代的更替變革是符合進化論原理的。在這里,嚴復再一次暗示當時中國之社會亟須順應社會發展變革之規律,自強保種、救亡圖存。若不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社會環境,或許嚴復再譯時也不會這樣去操作。因此,在討論翻譯文本和譯者問題時,必須把它們放在特定的文化環境和時代背景中去考慮,并尊重譯者的主體地位。
4.變譯
嚴復在翻譯時很多時候并不是按照原文基本意義直接轉換來的,其在翻譯過程中更多時候是在原文基本意義基礎上有所改變,并加以選擇。這種案例在文章中并不少見,在《導言一》中,嚴復將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 soil譯為“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原作中表達的意思為“植物在稀缺的表層土壤上爭奪著有限的生存空間”這層意思,但嚴復在翻譯時并不只是淺顯地將這層自然界中植物的生存競爭譯出來,一“爭”,一“相雄”,一“據”,無不讓人聯想到一幅各方征戰,互相爭奪的場面。因此,這里嚴復就將原文自然界的一種生存情況變譯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演化競爭。在他的視角下,無時無刻不注視著國家的生死存亡。后面接著一句“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同樣也能看出嚴復的別有用心,此句譯自now from the Atlantic,and now from the North Sea,Atlantic本意是地理名詞“大西洋”,而在嚴復筆下卻譯為“西洋”,這不禁又讓人們聯想到他這么做的目的,誓要敲醒國人,國家正面臨來自西方國家的蠶食侵略,睜眼看清現實已刻不容緩。正是通過這種有意識的改變原文,以達譯文服務社會的需求。
(二)嚴復《天演論》的文化意義
翻譯活動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最終目的還是要服務于社會文化的需要。而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在文化構建中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嚴復《天演論》的文化意義在于引領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化,促進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得當時的中國學者能夠及時了解和掌握西方科學的最新發展,為中國科學領域的興起提供了基礎。此外,嚴復的翻譯還開啟了中國翻譯史上的新篇章。他以自己對西方科學的了解和中文表達能力,翻譯出了較為通俗易懂的版本,并加入了適合中國文化的注釋與闡釋。嚴復的翻譯方法不僅在當時受到了廣泛贊譽,也影響了中國后來的翻譯流派和理論,對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結語
翻譯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是人類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隨著社會的更迭發展,時代背景的變化不同,譯者在進行文學作品的翻譯時不免會刻上時代的烙印。而翻譯又是一種“人”的活動,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摻雜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主體意識的發揮。從文化視角看譯者主體性的發揮繞不開對翻譯目的論的探討。翻譯目的主導翻譯行為,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同樣也是依據翻譯目的來開展。因此,由于翻譯目的的不同就會形成不同的個體意識形態,而大家在進行翻譯活動或者進行翻譯研究時,就不得不將不同的譯者主體性考慮進去。嚴復作為思想家和翻譯家,他以學術翻譯之手段,達思想啟蒙之目的。本文主要從個體意識、社會因素兩個方面入手,分析嚴復譯著《天演論》中譯者主體性的體現,并對作品背后的文化意義進行了探析。
參考文獻:
[1]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8.
[2]陳琳琳.從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看嚴復《天演論》中的變譯現象[D].湖北大學,2011.
[3]崔娟,劉軍顯.論個體意識形態對翻譯策略的決定作用——以嚴譯《天演論》為例[J].外語研究,2016,33(06):
81-85.
[4]鄧雋.從目的論管窺嚴復譯《天演論》[J].上海翻譯,2010,(02):73-75.
[5]高方武.德國功能理論與中國傳統譯論之對比略論[J].外語教育,2008,8(00):140-145.
[6]韓江洪.嚴復話語系統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7]黃苗.權力話語視域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D].長沙理工大學,2010.
[8]黃忠廉,郎需靜.嚴復“達旨術”研究之《天演論》譯評考察[J].語言文化研究輯刊,2014,(01):77-85.
[9]黃忠廉,倪璐璐.變譯之刪減策略研究——以嚴譯《天演論》為例[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5,38(03):
105-111.
[10]黃忠廉.變譯之“加寫”功能研究——以嚴復譯《天演論》為例[J].外語與翻譯,2015,22(03):1-4+99
[11]蔣小燕,羅曉洪.論嚴復《天演論》的文化觀[J].求索,2006,(05):158-160.
[12]焦衛紅.嚴復譯著《天演論》的生態翻譯學解讀[J].上海翻譯,2010,(04):6-10.
[13]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4]劉明.論成功的翻譯——再讀林紓、嚴復作品有感[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0,30(06):103-107.
[15]劉文娟.嚴復與《天演論》的翻譯[J].蘭臺世界,
2013,(10):54-55.
[16]榮利穎.解構主義視野下看嚴復的《天演論》 [D].天津理工大學,2006.
[17]王東風.一只看不見的手論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操縱[J].中國翻譯,2003,(5):16-23.
[18]王東風.《天演論》譯文片段賞析[J].中國翻譯,
2010,31(05):74-79.
[19]王克非.論嚴復《天演論》的翻譯[J].中國翻譯,
1992,(03):6-10.
[20]王少娣.跨文化視角下的林語堂翻譯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225.
[21]王姝婧.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看文學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問題[D].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04.
[22]王燕.論社會歷史語境下的嚴譯《天演論》[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04):41-42.
[23]徐蕾,李里峰.嚴復譯著與“翻譯的政治”[J].廣東社會科學,2006,(02):107-114.
[24]葉慶芳.從文化語境看譯者主體性——以嚴復譯本《天演論》為例[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9,6(05):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