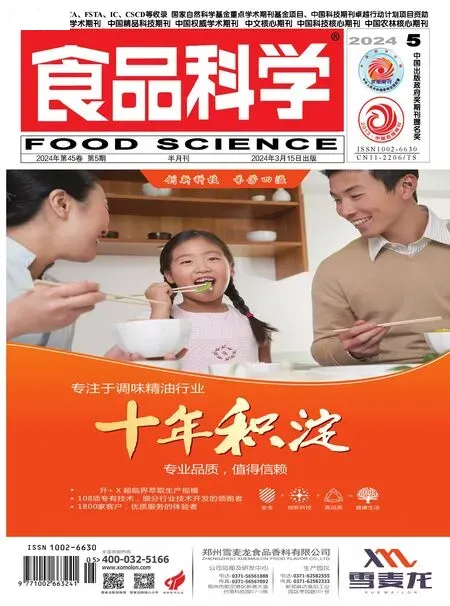根據Vrentas-Vrentas理論模擬小麥粉的水分吸附滯后:模型參數χ及k表示為Fermi函數的形式
楊 毅,趙學偉,2,*,魏笑笑,王宏偉,2,張 華,2,*
(1.鄭州輕工業大學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河南省冷鏈食品質量安全控制重點實驗室,河南 鄭州 450001)
水分吸附及其滯后現象在食品加工及儲藏過程中廣泛存在并具有重要意義[1-3]。人們試圖從微觀結構[2,4]乃至分子水平[5]上解釋滯后現象。該現象的存在說明平衡水分與物料某種特性的溫濕度經歷有關,已提出多種理論用以解釋該現象[6-7]。可歸結為兩大類,一類是基于介質的多孔性假設,如基于毛細管吸附理論的凝結-蒸發理論、不完全濕潤理論、瓶頸理論、開孔理論等,以及吸附位點可用性理論[6]。另一類是基于玻璃態大分子的結構松弛假設,滯后的原因在于解吸進入了玻璃態,及玻璃態材料的緩慢結構松弛[7]。玻璃態時的黏彈性松弛時間比實驗時間要長得多,導致體系內產生應力,應力的黏彈性松弛導致水分解吸滯后[8-9]。
食品的水分等溫吸附模型有很多,可以參考文獻[6]。基于Flory-Huggins(FH)理論的等溫吸附模型在該文獻中沒有提及,而在合成高分子領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其良好的理論基礎,該模型被Van Der Sman研究團隊廣泛應用于食品體系[9-11],這里對此作重點介紹。FH理論用于描述大分子的水分吸附時要解決兩個問題:如何考慮玻璃態帶來的影響,如何考慮玻璃態時性質的歷程依賴性。關于前者,由于玻璃態為熱力學非平衡狀態,問題就歸結為如何考慮玻璃態引起的額外自由能以校正FH方程。Vrentas &Vrentas(VV)方程[12]通常被稱為FVFH(Free Volume Flory-Huggins)方程[13],實際上是考慮玻璃化轉變對比熱從而對自由能的影響[14],該理論僅考慮大分子的玻璃化轉變對額外自由能的貢獻,最近Kocherbito等[14]還考慮了水分玻璃化轉變的貢獻。Leibler等[15]將玻璃態時的混合體系看作彈性體,由滲透模量計算滲透壓,以校正FH方程。Rosenbaum[16]根據可壓縮性計算水分吸濕引起的體積變化,計算額外自由能。關于后者,Vrentas等[17]認為解吸實驗過程中玻璃態相對于平衡態的自由能偏離程度與吸濕實驗時的相對偏離程度呈正比。Doumenc等[18]拓展了Leibler &Sekimoto模型[17],認為滲透模量是隨時間衰減的,如果其在解吸過程中的衰減特性已知,則可用于模擬解吸。從吸附動力學的角度研究吸附過程是吸附滯后模擬的另一個方法,Yang等[19]認為水分吸濕過程中的相變導致溫度梯度從而引起熱量傳遞,傳熱速率反過來又影響相變和傳質,從而導致水分的再分布,最終導致吸附滯后現象,并用數學方程表示這些耦合關系。有研究者在以化學勢差為動力的水分擴散方程中以不同方式考慮黏彈性引起的額外自由能[8-9]。
根據VV理論,玻璃化轉變溫度和水-大分子相互作用參數χ是決定吸濕曲線走勢的兩個關鍵因素。玻璃化轉變溫度的測定方法有很多,動態吸附法測定平衡水分近年來也被用于確定一定溫度下的玻璃化轉變水分[20-21]。干物質的玻璃化轉變溫度是決定混合體系玻璃化轉變溫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溶液體系,可以根據相平衡測定結果由FH方程反演算出χ,也可以根據溶解性參數計算出χ[22]。對于中高水分食品體系,可以通過溶脹特性測定[23]或相變溫度測定[11,13,24],然后根據Flory-Reher方程或其Hoffman近似式確定χ;對于低水分體系,更多的是通過水分等溫吸附測定,然后根據FVFH理論[8,25]反演確定χ。對于大分子-水混合體系,χ具有組分依賴性,前人用分段函數表示其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13,26]。
前人對小麥粉的吸濕、解吸平衡水分進行了測定并基于經驗或半經驗等溫吸附模型進行了分析[27-29]。動態水蒸氣吸附(dynamic vapor sorption,DVS)法具有用樣量少、時間短、溫濕度控制準確等優點,近年來在食品的水分吸附特性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3,25,30]。本研究以小麥粉為原料,采用DVS測定其在3 個溫度條件下的吸濕、解吸平衡水分,然后基于吸濕-解吸曲線估算其發生玻璃化轉變時的水分含量并進一步建立其與溫度的關系;在采用VV理論模擬等溫吸濕時,用Fermi分布函數的Peleg改進形式表示χ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在根據吸濕數據預測解吸時,認為VV模型中的參數k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遵循Fermi函數。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試劑
小麥粉,金苑特一粉(水分質量分數12.2%、粗蛋白質量分數11.4%),購自當地超市。
1.2 儀器與設備
Intrinsic型DVS分析儀 英國Surface Measurement Systems公司。
1.3 方法
1.3.1 DVS測定
自制直徑9 mm的不銹鋼圓盤,用毛筆蘸取少量的小麥粉,輕彈毛筆的尾端,讓小麥粉自由散落在圓盤上,形成均勻的粉層,如此可在增加樣品量的同時保證樣品層厚度均勻。然后將圓盤小心放置在DVS的樣品盤上,再整體放入DVS樣品室。DVS采用高純N2為氣源,通過調整N2與100%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RH)空氣的體積比得到不同相對濕度的混合氣體,總氣流量為200 mL/min。先0% RH干燥樣品,隨后RH從0%以5%的步幅增大到15%,然后以10% RH的步幅增大到85%,再以5%的步幅增大到95%;最后降低RH,步幅設定與吸濕過程相對應。分別在20、30、40 ℃條件下測定,吸附平衡標準:連續5 min內樣品質量的變化速率低于0.0001 %/min。每個實驗進行3 次,根據平均值計算平衡水分。
1.3.2 VV理論模擬
對于由大分子(設每個大分子含有N個鏈段)與溶劑小分子的混合溶液,根據FH的均勻場晶格假設,每個溶劑分子、每個鏈段各占據一個晶格。由n1mol溶劑分子(本研究中指水)與n2mol大分子均勻混合達到熱力平衡時,混合前后整個體系的Gibbs自由能(ΔGm)的變化為[31]:
式中:R為氣體常數(8.314 J/(mol?K));T為溫度/K;?1=n1/(n1+Nn2)、?2=Nn2/(n1+Nn2)分別為溶劑、大分子在混合體系內所占據的體積分數;χ12為溶劑-大分子相互作用系數。根據Gibbs-Duhem方程可推導出式(2),式(1)對?1求導并帶入式(2)得式(3),其中,μ1為混合溶液中水的化學勢/(J/mol),為純水的化學勢。
水分吸濕過程是由水蒸氣到液態水的相變過程以及水與固態物質的混合過程。對于處于橡膠態的混合體系,在等溫等壓條件下水分吸附過程達到熱力學平衡時,水在液相中的化學勢與其在氣相中的化學勢相等,即μ1=,進一步轉變為:
又由于對于理想氣體有式(5)[32],其中aw為水分活度,下標FH表示該aw是基于FH假設得到的。
根據式(3)~(5),同時考慮到對于大分子1/N→0,則有FH方程:
如果吸附過程中混合體系處于玻璃態,由于玻璃態為熱力非平衡狀態,水在混合體系中的化學勢除上述根據熱力學平衡假設計算得到的化學勢μ1,FH外,還應包括額外的化學勢,該部分主要是由于玻璃體的結構松弛引起的,用μ1,rel表示,這時式(4)應轉變為式(7):
根據VV理論[12],μ1,rel由式(8)計算,其中,M1為水分子的摩爾質量/(g/mol);ω1、ω2為水、大分子的質量分數;cpg、cp2為大分子在玻璃態、橡膠態時的定壓比熱;Tgm為混合體系的玻璃化轉變溫度。由于cpg<cp2,玻璃態時T<Tgm,又dTgm/dω1<0,則μ1,rel為負值。由于式(8)的推導過程中并未用到自由體積的概念[14],以下在論及FVFH理論時將其稱為VV理論。
將式(3)、(5)、(8)帶入式(7)得式(9)。很顯然,在T=Tgm時F=0,式(9)還原為式(6)。式(6)和(9)可由通式(10)和(11)表示:
大分子處于不同狀態時其水分活度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示意見圖1。藍線以下為玻璃態,吸濕-解吸曲線的分叉點為玻璃化轉變點。根據前言中的論述,相同水分體積分數時,平衡態的水分活度最高而解吸過程中的最低。從數學的角度看,玻璃態的aw,ad是橡膠態的aw,FH乘以校正因子expF的結果,由于玻璃態的aw較低,F應當是負值才能保證expF<1。在數值上,F實際上為相同水分體積分數時兩狀態下的aw對數差。解吸的aw更低,則應對F乘以一個大于1的校正因子k(式(12)),其定義為k=(μde-μFH)/(μad-μFH),Vrentas和Vrentas[17]進一步推導出其表達式(13),下標D表示解吸。吸濕過程中的樣品在TD溫度時的熱力學結構與解吸過程中樣品在T溫度時的相同。

圖1 不同狀態時水分活度數學表達式的含義Fig.1 Explaining the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of water activity at different states
1.4 數據處理與分析
根據測得的DVS數據,由0% RH條件下達到平衡時的樣品質量計算干基水分含量以及水分質量分數。考慮到蛋白、碳水化合物的密度分別為1330、1550 kg/m3[10],本研究中按面粉中固形物的密度為1500 kg/m3、水的密度為1000 kg/m3計算水體積分數。
采用1stOpt 8.0軟件(七維高科,中國)進行參數擬合,采用Excel軟件進行試錯計算求FH相互作用參數。
2 結果與分析
2.1 小麥粉水分吸附滯后的直觀觀察
圖2顯示,小麥粉存在解吸滯后現象,且隨溫度升高,滯后程度降低。吸濕曲線與解吸曲線在高水分時幾乎重合,Babbitt[33]關于小麥的水分吸附研究中明顯觀察到這種現象,Julio等[27]在小麥全粉中觀察到的這種現象較輕微,對于面筋尤其是奶粉這種現象更明顯[7]。一些研究中沒有觀察到這種現象[28-29],可能是由于吸附沒有達到充分平衡或實驗觀察的aw范圍不夠寬。本研究采用DVS,由于用樣量很少且吸附平衡充分,得以觀察到這種現象。根據VV理論,橡膠態時不存在解吸滯后現象,則分叉點對應于小麥粉在水分吸附過程中的玻璃化轉變點。至于該點的確定方法及玻璃化轉變水分的具體值,將在后面論及。本實驗將基于VV理論對小麥粉的水分吸附滯后現象進行模擬分析。

圖2 小麥粉在20(A)、30(B)、40℃(C)的吸附等溫線及其Park模型擬合Fig.2 Water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isotherms of wheat flour at 20 (A),30 (B) and 40℃ (C) and their fitting to the Park model
2.2 根據吸濕-解吸等溫線求玻璃化轉變水分
式(11)顯示dTgm/dω1是決定玻璃態時水分吸附曲線走勢的關鍵因素,因此要先確定混合體系的玻璃化轉變溫度與水分含量之間的關系。通常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符合Couchman-Karasz(C-K)方程(式(14))或Gorden-Taylor(G-T)方程;在水分變化范圍較窄時,可采用線性關系[12]。C-K方程基于在玻璃化轉變溫度時體系的熵、體積都是連續變化的,本研究采用該方程:
式中:ω2、ω1為大分子、水分的質量分數;Tg1、Tg2為純水、干物質的玻璃化轉變溫度;Δcp1、Δcp2為玻璃化轉變前后水、干物質的比熱變化,如Δcp2=cp2-cpg。關于水分的參數,各文獻中的差異不大,本研究采用Tg1=136 K[34-35],Δcp1=1.94 J/(kg·K)[25];對于蔗糖[35]、多糖[17]和蛋白質[36],Δcp2=0.42 J/(kg·K),根據VV理論擬合出淀粉、面筋的Δcp2分別為0.49、0.32 J/(kg·K)[25],本研究取Δcp2=0.42 J/(kg·K)。關于Tg2,由于高溫時材料的熱降解而不能通過實驗測定,通常是基于一定的模型由實驗數據外推求出。
前人采用動態露點等溫線(dynamic dewpoint isotherm,DDI)確定玻璃化轉變水分[20],該法可以測得很多數據點;也有研究者采用DVS相對濕度掃描確定玻璃化轉變水分[21],但該方法會受到R H掃描速率的影響。本實驗采用DVS測定平衡水分,數據點有限,提出如下方法估算玻璃化轉變水分。式(12)與式(10)相除得式(15):
根據VV理論,在橡膠態時吸濕、解吸曲線重合,也就是ln(aw,ad/aw,de)=0,這與橡膠態時F=0、k=1是一致的。ln(aw,ad/aw,de)中采用的是相等水分體積分數的水分活度之比,而實驗測定時采用的是相同水分活度。為得到相同水分含量時吸濕、解吸的水分活度對應值,采用Park模型(式(16))擬合等溫吸附數據,式中:M為平衡水分含量;ML、kL分別為Langmuir吸附水分含量、平衡常數;kH為Henry常數;kc為成簇反應的平衡常數;n為平均每個水分子簇中水分子的個數。結果如圖1中曲線所示,模型參數見表1,可以看出Park模型能很好擬合等溫吸附平衡水分。

表1 Park模型參數值Table 1 Parameter values of the Park model
采用1stOpt軟件,在水分含量0.02~0.36 kg/kg范圍內,步幅為0.01 kg/kg,對式(16)作圖求出35 組吸濕-解吸水分活度對應數據,然后計算ln(aw,ad/aw,de)值,圖3舉例了20 ℃的結果。從圖中確定ln(aw,ad/aw,de)=0時所對應的玻璃化轉變水分含量,為0.223 kg/kg。30、40 ℃時分別為0.177、0.166 kg/kg,換算成體積分數分別為0.251、0.210、0.199。前人根據VV方程求得20 ℃時淀粉膜、面筋膜發生玻璃化轉變時的水分體積分數分別為0.20、0.15[25],而采用考慮應力松弛的FH改進模型時,求得的值分別為0.23、0.16[8]。根據對面筋、奶粉在20 ℃的DVS測定結果,分別在aw=0.8、0.35時解吸與吸濕等溫線重合,對應的水分含量大約分別為0.18、0.055 kg/kg[7]。綜合比較[7,8,25]可以看出蛋白的玻璃化轉變溫度較低,另外,本研究的結果與前人[8,25]的基本一致。

圖3 根據VV理論確定20℃時的玻璃化轉變水分Fig.3 Determination of glass transition water content at 20℃according to the VV theory
根據式(14),干物質的Tg是決定Tgm的關鍵參數。將上述確定的玻璃化轉變水分與溫度(就是實驗測定溫度)的對應值,以及前人采用差示掃描量熱儀(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測定杜倫麥粗粉[37]、動態機械熱分析[38]以及DSC[39]測定小麥粉得到的玻璃化轉變溫度匯總于圖4,可見,采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所確定的玻璃化轉變溫度與前人的基本在同一范圍。

圖4 文獻報道及本研究測定的玻璃化轉變溫度及其C-K模型擬合Fig.4 C-K model fitting and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s reported in literature and measured in this study
以Tg2為擬合參數,采用式(14)擬合圖4中的數據得Tg2=464 K。前人根據Fox-Flory方程推算出無水淀粉的Tg2為520[40]、500 K[13]或475 K[11],根據C-K方程計算出無水淀粉的Tg2=545 K[25],根據G-T方程[7]、C-K方程[25]求得干面筋的Tg2分別為404、413 K。這里取干面筋的Tg2=410 K,干淀粉的Tg2=500 K,小麥粉中蛋白的質量分數為0.1318,淀粉的為0.8682,根據Fox公式(式(17),下標p、s分別代表面筋、淀粉)計算出無水面筋與淀粉混合體系的Tg2=485.9 K。考慮到小麥粉中還含有玻璃化轉變溫度更低的低分子質量成分,干面粉的Tg2=464 K是比較合理的。
2.3 小麥粉等溫吸濕的VV擬合
盡管一些文獻[8,25]在采用VV理論擬合水分等溫吸附時采用恒定的χ值,實際上,對于小分子碳水化合物χ是定值,而對于高分子物質,χ具有組分依賴性,Van Der Sman團隊[10,11,13]提出式(18),式中χ0、χ1分別表示稀、濃狀態時的χ。需要說明的是,文獻[13]中的表達式與式(18)有差異,但該團隊在后續發表的論文中多引用為式(18)的形式,在一定?值范圍內兩種表達式的計算結果差異不大。Argatov和 Kocherbitov[26]提出式(19)表達χ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其中χ*為χ的最大值,χ*、?*、α、β、ν皆為待定參數。
式(18)中:χ0=0.5,具有普適性,對于多糖-水混合體系,χ1=0.8[13],對于蛋白-水混合體系,χ1=0.8~1.4,隨溫度而變化[37]。但對于小麥粉的水分吸濕,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恒定的χ、式(18)(χ1設定為待定參數)或式(19)時,式(12)都不能很好地擬合實驗數據,圖5舉例給出了30 ℃的結果。由于VV理論體系中水的體積分數為自變量,與通常的吸附等溫線圖示方式不同,這里以x軸表示水體積分數。可以看出,采用定χ時對中高水分段的擬合不好;式(18)對低水分段的擬合偏高,而式(19)對高水分段的擬合不好。

圖5 采用恒定χ、式(18)和(19)表達的χ根據VV理論模擬小麥粉30℃的水分吸濕Fig.5 Modeling water sorption isotherms of wheat flour at 30℃ using the VV theory with constant χ or χ obtained from Eqs (18) and (19)
在Excel中對式(10)、(11)、(14)實施運算,Tgm采用式(14)時dTgm/dω1由式(20)計算。由于其他參數已知,可以通過調整χ的大小使aw的計算值與實驗值一致(精確到小數點后3位數),如此試錯求得的χ值如圖6所示。可以看出χ明顯不是定值,另外,在高水分時,χ既不像式(17)認為的是定值,也不像式(19)認為的是直線。本實驗提出采用Fermi分布函數的Peleg改進形式(式(21))表示圖6所示的χ變化趨勢,其中χ0、χr、?*、a、b可看作是擬合參數:

圖6 根據VV理論采用試錯法確定的吸濕過程中的χ值及其根據式(21)的擬合Fig.6 Fitting to Eq (21) of water sorption χ values determined by the trial-and-error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VV theory
Fermi分布函數原本是量子力學中用于描述一個電子處于能級E的概率,其原始形式為f=1/(1+exp((E-Ef)/kBT)),其中Ef為費米能,kB為Boltzmann常數[41]。Peleg[42]最先改進該函數用于描述食品的彈性模量及楊氏模量在玻璃化轉變前后隨溫度的變化,Zhao Xuewei等[43]進一步改進后用于描述食品在臨界水分活度前后質構特性的變化。式(10)結合式(21)擬合小麥粉的等溫吸濕數據,得到式(21)中的最佳參數值,見表2。然后由式(21)計算χ,結果如圖6所示,采用式(21)能夠很好地擬合高水分區域χ的非線性變化。對小麥粉的等溫吸濕擬合結果見圖7。

表2 式(21)中各參數的值Table 2 Parameter values of Eq (21)
圖6顯示,對于小麥粉來說,χ在?1約為0.15時達到最大值,溫度的影響較小。前人的結果顯示χ隨溫度的變化很小[10]或基本不變[13]。有文獻指出,χ<0.5意味著大分子-溶質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較強,而χ>0.5意味著大分子-大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較強[44]。根據表面吸附理論,低水分時形成單分子吸附層,大分子-水之間的作用強;圖6顯示,水分含量很高時,大分子-水分的作用減弱,可理解為水分子間發生成簇反應造成的[45]。
根據水分吸附等溫線由FH方程求得的凍干糊化馬鈴薯淀粉的χ在干基水分約為0.35時達到最大值(約為0.7),但在水分低于0.1時為負值[44],酸水解淀粉及交聯淀粉微球在低水分時χ也為負值[26],這兩個文獻中的χ都是基于FH方程計算出的,實際上在低水分時由于體系處于玻璃態,FH方程不再適用。FH理論結合Clausius-Clapeyron方程,根據糊化溫度求得不同淀粉-水分子的χ在0.55左右,采用Hoffman近似方程求得的要高一些,約為0.75[24]。這里的χ值低于本研究的結果,原因在于糊化體系的水分含量比吸濕的高很多,圖6顯示在高水分時χ開始下降,也正說明了高水分時χ值較低。淀粉膜、面筋膜的χ分別在0.9、1.0左右[8,25]。根據式(18),采用Van Der Sman團隊普遍采用的參數取值χ0=0.5、χ1=0.8,計算本研究中小麥粉的χ,結果明顯低于圖6中的值。綜合比較發現,上述文獻中的χ比本研究的結果要低,原因在于這些研究中的樣品都經過了熟化處理,使得大分子-水相互作用強于水-水相互作用,表現為χ較低[44]。但基于糊化淀粉的χ函數(式(18),χ0=0.5、χ1=0.8)卻能成功用于描述西蘭花[10]、蘑菇[46]的水分吸濕,可能由于樣品中存在可與水有強相互作用的水溶性纖維素和小分子糖,樣品的漂燙處理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2.4 根據吸濕預測解吸
盡管式(10)也可以模擬解吸,但在采用式(12)模擬解吸時應當采用吸濕的χ參數。食品研究文獻中幾乎沒有采用由吸濕擬合求得的χ參數來擬合解吸的嘗試。西藍花的水分吸附滯后效應很弱,仍采用式(10)擬合解吸[10]。其他領域的研究中有這樣的嘗試[47],但一篇關于木材的研究中,在采用吸濕的χ參數(定值)模擬解吸時,發現僅調整k還不夠,又將水分的Tg1作為擬合參數[48]。
根據VV理論,在擬合解吸過程時應當采用吸濕過程中的χ參數,需要調整的僅是參數k。本實驗采用吸濕過程中的χ,發現式(12)中的k為定值時擬合效果不好,圖8舉例給出了20 ℃時的結果。可以看出,在玻璃化轉變點前后,預測值低于測定值。根據VV理論,由玻璃態到橡膠態時,k值一步降為1。說明k值的變化可能是一個漸進過程,故此提出用Fermi分布函數形式表示k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k值由k0降為1,轉變區域的中間點為?′,b′值決定?轉變區間的寬窄或k值降低的速率。

圖8 根據VV理論采用k定值模擬小麥粉20℃的等溫解吸Fig.8 Modeling water desorption isotherm at 20℃ according to the VV theory with a constant k value
應用吸濕過程中的χ參數,采用式(10)結合式(22)擬合解吸數據,結果如圖9所示,最佳參數見表3。可以看出,采用式(22)能夠很好擬合玻璃化轉變前后的數據。根據式(12),如果k為定值,也就意味著TD為定值,實際上,根據VV理論[17],大分子在玻璃態、橡膠態時的熱膨脹系是影響TD的重要因素。熱膨脹系數在玻璃化轉變時的變化并非躍變[49],因此,認為k在玻璃化轉變時有個漸變過程是一個合理的假設。

表3 式(22)中的參數值Table 3 Parameter value of Eq (22)

圖9 根據VV理論結合式(22)模擬3 個溫度條件下的等溫解吸Fig.9 Modeling water desorption isotherms at three temperatures according to the VV theory combined with Eq (22)
3 結論
在水分吸附充分平衡的條件下,小麥粉的吸濕和解吸曲線在高水分區域基本重合,說明發生了玻璃化轉變,可以根據文中提出的方法基于吸濕-解吸曲線確定玻璃化轉變點。FH相互作用參數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可以采用Fermi函數的Peleg改進形式表示,如此VV理論能夠很好地描述小麥粉的等溫吸濕。采用吸濕過程的χ參數基于VV理論模型擬合小麥粉的等溫解吸時,其中的參數k不是一步變化的,可以采用Fermi函數表示k值隨水分體積分數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