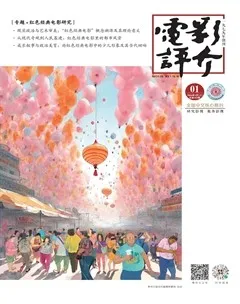現(xiàn)實(shí)政治與藝術(shù)審美: “紅色經(jīng)典電影”概念溯源及其理論意義



陳濤史小說,包括《平原槍聲》《暴風(fēng)驟雨》《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野火春風(fēng)斗古城》等作品,尤其是被稱為“三紅一創(chuàng)”的《紅巖》《紅日》《紅旗譜》《創(chuàng)業(yè)史》和“青山保林”的《青春之歌》《山鄉(xiāng)巨變》《保衛(wèi)延安》《林海雪原》。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作品在此之前一直隸屬于“革命文藝”或“工農(nóng)兵文藝”的范疇,其創(chuàng)作源頭可以追溯到“延安文藝”時(shí)期。[3]
1942年,毛澤東發(fā)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厘清“文藝工作”與“一般革命工作”的關(guān)系,認(rèn)為文藝工作應(yīng)當(dāng)服務(wù)和參與現(xiàn)實(shí)的革命運(yùn)動(dòng),成為“革命機(jī)器的齒輪和螺絲釘”;首次明確了“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文藝為大眾服務(wù),文藝為無產(chǎn)階級(jí)政治服務(wù)”的文藝創(chuàng)作原則。[4]此后,延安文壇涌現(xiàn)出以《小二黑結(jié)婚》《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呂梁英雄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代表的一大批反映解放區(qū)革命事業(yè)和人民生活的作品,成為“紅色經(jīng)典”的發(fā)軔。
誠如學(xué)者黃子平所見,這些被稱為“紅色經(jīng)典”的“革命歷史小說”特殊之處在于,它們“承擔(dān)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jīng)典化的功能,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并且通過大量的印刷傳播和電影改編,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最終“建構(gòu)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shí)”[5]。然而與“革命歷史小說”這一概念相比,“紅色經(jīng)典”的外延更寬泛:一是“紅色經(jīng)典”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shí)間”不局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二是作品講述的“革命歷史”也可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事件,例如,周立波創(chuàng)作于20世紀(jì)40年代《暴風(fēng)驟雨》、柳青講述農(nóng)村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創(chuàng)業(yè)史》是“紅色經(jīng)典”代表作,但很少被稱為“革命歷史小說”。
從文學(xué)史的角度來說,將“革命歷史”作為一種題材的討論在20世紀(jì)50年代便已出現(xiàn)。茅盾在1960年中國作協(xié)第三次理事會(huì)(擴(kuò)大)會(huì)議作報(bào)告時(shí),用它指1956年至1960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戲劇、詩歌、電影劇本等不同體裁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革命歷史”包括鴉片戰(zhàn)爭和辛亥革命。20世紀(jì)50至70年代,“革命歷史”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指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斗爭,而在80年代后則專門用于講述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的起源,和這一‘革命經(jīng)歷曲折過程之后最終走向勝利的故事”[6]。具體而言,“這個(gè)概念中的歷史特指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到1949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執(zhí)政黨這個(gè)歷史區(qū)間”“革命特指在這個(gè)歷史區(qū)間中以中國共產(chǎn)黨為主體從事的各種各樣改變社會(huì)、改變?nèi)四酥粮淖儦v史的活動(dòng)”[7]。
從這個(gè)角度看,如果說延安文壇上的革命歷史小說構(gòu)成“紅色經(jīng)典”小說之開端的話,那么與這些“紅色經(jīng)典”小說同一時(shí)期的戰(zhàn)后進(jìn)步電影實(shí)際上也同樣肩負(fù)著“革命機(jī)器”的使命,具備將革命歷史經(jīng)典化的政治向度,因此可以被視為“紅色經(jīng)典”電影的雛形。由此可見,“紅色經(jīng)典”這一概念最初在媒介層面上僅指小說;時(shí)間維度上也只涵蓋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依其源流則最早可以追溯至1942年之后,遵照延安文藝精神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或文藝作品。正如學(xué)者孟繁華所見,“紅色經(jīng)典”這一概念實(shí)際上包括1942年以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指導(dǎo)下,“以革命歷史為主要題材,以歌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為主要內(nèi)容”[8]的各類文藝作品。
誠如學(xué)者侯洪、張斌所見,在“紅色經(jīng)典”這個(gè)組合式概念中,“紅色”與“經(jīng)典”彼此限定,打開了一個(gè)復(fù)雜的價(jià)值和情感維度:一方面,“紅色”指向“革命”含義,“在諸多被歸入‘紅色經(jīng)典的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中,廣泛意義上的‘革命(包括新中國成立后所進(jìn)行的社會(huì)主義革命改造和建設(shè))題材是‘紅色經(jīng)典創(chuàng)作第一,也許是唯一的選擇”;另一方面,“經(jīng)典”則是一定時(shí)代認(rèn)為重要的、有指導(dǎo)作用的著作,是主流政治話語對(duì)文藝作品權(quán)威性、示范性地位的認(rèn)可。由此可見,“紅色經(jīng)典”本質(zhì)上是政治概念與藝術(shù)概念的結(jié)合,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文藝作品與人民政治緊密相連的典范”或“約定俗成的、歲月久遠(yuǎn)的、描寫英雄人物和革命歷史的經(jīng)典作品”[9]。
因此,作為“紅色經(jīng)典”這一概念的源頭,延安文藝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直接指引和領(lǐng)導(dǎo)下發(fā)生的,其根本屬性是人民文藝——換句話說,“紅色經(jīng)典”植根于人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土壤,以人民大眾為立場,其本質(zhì)的審美特征與最高審美理想是人民性。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15日文藝座談會(huì)上講話所指出的:“社會(huì)主義文藝,從本質(zhì)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工作者要“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dǎo)向”“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jiān)持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這個(gè)根本方向”。[10]作為延安文藝的本質(zhì)特征,人民性正是“紅色經(jīng)典”的精神內(nèi)核所在。
二、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與“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
自1997年以后,“紅色經(jīng)典”的說法逐漸得到文化市場認(rèn)可,其概念邊界也得以不斷拓寬。21世紀(jì)初,一大批由革命歷史小說改編而來的同名電視劇開始出現(xiàn),引發(fā)一場“紅色經(jīng)典”影視創(chuàng)作熱潮。隨之而來的則是關(guān)于“紅色經(jīng)典”改編的爭議。以上映于2003年的《林海雪原》為例,部分觀眾和學(xué)者并不認(rèn)可電視劇對(duì)原著小說的改編,認(rèn)為“電視劇移用了原著中的人物線索,拋棄了原著中的線性結(jié)構(gòu),重新編織起一個(gè)全新、立體式的故事,大大加重了情色因素,使一部充滿了陽剛氣和戰(zhàn)斗智慧的‘紅色經(jīng)典,成為一部大俗片”。[11]因此,為了進(jìn)一步規(guī)范同類影視作品的生產(chǎn),國家廣電總局于2004年向各級(jí)有關(guān)單位發(fā)出《關(guān)于認(rèn)真對(duì)待“紅色經(jīng)典”改編電視劇有關(guān)問題的通知》,這也是“紅色經(jīng)典”的概念首見于官方文件。[12]該《通知》指出,“紅色經(jīng)典”改編電視劇存在著“誤讀原著、誤導(dǎo)觀眾、誤解市場”的問題,相關(guān)作品“沒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沒有理解原著所表現(xiàn)的時(shí)代背景和社會(huì)本質(zhì),片面追求收視率和娛樂性”,最終“影響了原著的完整性、嚴(yán)肅性和經(jīng)典性”。因此廣電總局要求各省級(jí)廣播影視管理部門要嚴(yán)格把握好“尊重原著精神,不許戲說調(diào)侃”的原則,加強(qiáng)對(duì)“紅色經(jīng)典”改編電視劇的審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廣電總局這則《通知》所列出的41部“紅色經(jīng)典”中,不僅有《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創(chuàng)作于20世紀(jì)50年代革命歷史小說,也包括《一江春水向東流》(蔡楚生/鄭君里,1947)、《地道戰(zhàn)》(任旭東,1965)、《紅色娘子軍》(謝晉,1961)等電影作品。不僅如此,廣電總局《通知》所列出的“紅色經(jīng)典”目錄中也包括了《家》《春》《秋》等20世紀(jì)30年代的左翼文學(xué)作品,所以從時(shí)間范疇上看,“紅色經(jīng)典”的創(chuàng)作源流不僅可以追溯到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之后,甚至在廣義上囊括20世紀(jì)30年代的左翼文學(xué)實(shí)踐。在此基礎(chǔ)上,廣電總局的《通知》文件以官方公文的形式將“紅色經(jīng)典”這一概念寬泛地定義為“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代表作”。這意味著“紅色經(jīng)典”這一概念可以最大限度地泛指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以來,所有反映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經(jīng)典文藝作品。其中,“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對(duì)應(yīng)“紅色經(jīng)典”概念中的“紅色”一詞,而“代表作”則應(yīng)了“經(jīng)典”的概念。
事實(shí)上,在《關(guān)于認(rèn)真對(duì)待“紅色經(jīng)典”改編電視劇有關(guān)問題的通知》中,用以概括“紅色經(jīng)典”核心特征的“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本身就是一個(gè)政治與藝術(shù)彼此限定的理論概念,有關(guān)其定義的討論同樣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不僅為中國帶來了有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chǔ)上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蘇聯(lián)的“無產(chǎn)階級(jí)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諾夫的“文藝組織生活”論等,均成為中國左翼文學(xué)的理論來源;魯迅、瞿秋白、茅盾、胡風(fēng)、周揚(yáng)、馮雪峰等人都以蘇聯(lián)革命實(shí)踐檢驗(yàn)過的馬克思主義來總結(jié)中國“左翼”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左翼文學(xué)”話語。而后,經(jīng)過1930年關(guān)于文藝通俗化、舊形式的采用和新形式的創(chuàng)造,1932年關(guān)于文藝大眾化的任務(wù)、內(nèi)容以及方法、形式,1934年關(guān)于大眾語言和文字拉丁化等三次討論,以及工農(nóng)兵通訊員運(yùn)動(dòng)、街頭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等實(shí)踐活動(dòng),左翼文學(xué)話語在中國文學(xué)學(xué)術(shù)研究中得到了快速發(fā)展。
1933年,周揚(yáng)首次系統(tǒng)地從蘇聯(lián)文論中引入并辨析“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一詞,進(jìn)而以之作為左翼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指導(dǎo)性概念。在《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一文中,周揚(yáng)指出“社會(huì)主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并非是對(duì)客觀現(xiàn)實(shí)的機(jī)械映射,而是一種將“英雄主義,偉業(yè),對(duì)革命的不自私的獻(xiàn)身精神”等“革命的浪漫主義”包含在內(nèi)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13]由此,作為藝術(shù)實(shí)踐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與作為政治實(shí)踐的“革命”之間實(shí)現(xiàn)了歷史性聯(lián)姻。新中國成立后,“現(xiàn)實(shí)主義”與“革命”、藝術(shù)與政治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變得愈發(fā)緊密。1953年,周恩來在新中國第二次文代會(huì)的政治報(bào)告里運(yùn)用了“革命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說法,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限定在革命政治范疇之內(nèi)。隨后,毛澤東在1958年的新民歌討論中正式提出“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將“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作為一個(gè)理論名詞固定了下來。
在這一視野下,“紅色經(jīng)典”的“經(jīng)典性”是政治權(quán)力依據(jù)“紅色”政治要求與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建立起來的,有論者并不認(rèn)可“紅色經(jīng)典”的說法,甚至尖銳地指出“把一些曾經(jīng)在特殊年代、特殊環(huán)境里的流行讀物稱為‘紅色經(jīng)典,這本身對(duì)‘經(jīng)典這個(gè)詞是一種嘲諷和解構(gòu)”[14]。可是,這樣的觀點(diǎn)無疑將“紅色經(jīng)典”概念內(nèi)部藝術(shù)審美與政治權(quán)力互動(dòng)視為一場藝術(shù)必?cái)〉慕橇Γ雎运囆g(shù)與政治二者彼此激發(fā)和周旋的潛能——或許后者才是“紅色經(jīng)典”這一概念的價(jià)值所在。誠如學(xué)者王斑所見,以革命影片為代表的“紅色經(jīng)典”作品實(shí)際上在藝術(shù)與政治之間構(gòu)建了一套精巧而幽微的運(yùn)作方式:一方面,“藝術(shù)所帶來的激情、快樂和痛苦既是審美的,又是政治的”;另一方面,政治本身亦不訴諸簡單說教,而是“根植于我們創(chuàng)造意義和推進(jìn)文化過程中所依賴的象征活動(dòng)與感知模式”,以藝術(shù)的形式在感官、感情、欲望和身體層面實(shí)現(xiàn)意識(shí)形態(tài)的再創(chuàng)造。[15]從這個(gè)角度看,“紅色經(jīng)典”的理論意義恰恰是對(duì)“經(jīng)典”概念本身的反思與解構(gòu),它從不為人們提供一系列封閉的、固化的、不可撼動(dòng)的作品目錄,而是始終在現(xiàn)實(shí)政治與藝術(shù)審美的彼此互動(dòng)中實(shí)現(xiàn)自我顛覆和更新。事實(shí)上,“紅色經(jīng)典”的這種不斷生成、永遠(yuǎn)未竟的特性,正是人們在不同時(shí)代一次次重返“紅色經(jīng)典”的動(dòng)力所在。
三、現(xiàn)實(shí)政治與藝術(shù)審美的互動(dòng)與回響
通過本文前兩部分的概念梳理,我們能夠明晰“紅色經(jīng)典電影”這一概念的定義:從狹義來說,它指的是1942年以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指導(dǎo)下,以革命歷史題材為主,以歌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為主要內(nèi)容的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代表作;而在廣義上,它則泛指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以來,所有反映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代表性電影作品,它可以是對(duì)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戲劇、電影等既有作品的改編,也可以是直接反映革命歷史的原創(chuàng)作品。
沿著廣義層面的概念所指,從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對(duì)大眾的關(guān)注,到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初期集體主義的革命激情,再到21世紀(jì)以來政治和商業(yè)交織的影像奇觀,“紅色經(jīng)典電影”作為一類極具中國特色的電影實(shí)踐,其發(fā)軔、確立和回響的整個(gè)進(jìn)程始終與中國波瀾壯闊的現(xiàn)代歷史彼此交織,構(gòu)成無數(shù)國人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記錄、反思、建構(gòu)現(xiàn)代經(jīng)驗(yàn)的重要場域。于是,在救亡與啟蒙、革命與詩情、藝術(shù)審美與現(xiàn)實(shí)政治的不斷角力中,借由一部部紅色經(jīng)典影片,可以看到一個(gè)積貧積弱的民族如何通過萬眾一心的革命斗爭,摧毀了一切不公的道德、名教和秩序。
從“經(jīng)典性”角度來說,“紅色經(jīng)典電影”作品的“代表性”并不指向任何因歷史沉淀而固定下來的公論,而是一項(xiàng)在現(xiàn)實(shí)政治和藝術(shù)審美的歷史互動(dòng)中不斷生成和更新的未竟事業(yè)。因此,即便是最新、最當(dāng)代的“紅色電影”實(shí)踐,也同樣具備某種程度的“經(jīng)典性”,而“紅色經(jīng)典電影”的歷史發(fā)展則始終呈現(xiàn)為現(xiàn)實(shí)政治與藝術(shù)審美在不同時(shí)代的彼此砥礪。“紅色經(jīng)典”在當(dāng)代的不斷改編、翻拍、衍生和回響,折射出當(dāng)代多種社會(huì)力量、歷史觀念、美學(xué)追求、再現(xiàn)機(jī)制、身份認(rèn)同的多元性。隨著時(shí)代的變遷,“紅色經(jīng)典”不可避免地要進(jìn)行各種“當(dāng)代化”的調(diào)整與改變,以使其能夠更好地被當(dāng)代觀眾所接受;而在這一過程中,傳統(tǒng)的紅色經(jīng)典作品借由媒介更新與技術(shù)升級(jí),實(shí)現(xiàn)了新的時(shí)代轉(zhuǎn)化。
在此借由一個(gè)例子來進(jìn)行說明。2015年,時(shí)值“紅色經(jīng)典”歌劇《白毛女》延安首演70周年,原文化部重新組織中國歌劇舞劇院復(fù)排歌劇《白毛女》,并于11月6日至12月17日在全國進(jìn)行巡回演出。與70年前的延安首演的歌劇《白毛女》不同,重新復(fù)排后的《白毛女》并不是單純的歌劇,反而以形態(tài)多樣的媒介實(shí)踐嘗試突破歌劇舞臺(tái)和銀幕影像之間的界限。首先,在舞臺(tái)置景的維度上,復(fù)排版《白毛女》除了運(yùn)用舞臺(tái)中央的布景道具之外,還在背景處以巨幕組成的環(huán)境影像拓展舞臺(tái)的縱深,制造虛實(shí)結(jié)合的視覺效果,使歌劇舞臺(tái)得以突破自身的空間限制。于是觀眾可以看到,當(dāng)白毛女表演經(jīng)典唱段《北風(fēng)吹》的時(shí)候,舞臺(tái)背景處的銀幕上出現(xiàn)了漫天雪花;當(dāng)白毛女受盡欺凌,奔向深山的時(shí)候,背景處的高山影像又與舞臺(tái)中的巖石道具融為一體。不僅如此,復(fù)排版的《白毛女》還被攝制成3D舞臺(tái)藝術(shù)片。該片既通過3D拍攝技術(shù)保留了歌劇舞臺(tái)的現(xiàn)場感,又運(yùn)用大量數(shù)碼特效和蒙太奇手法構(gòu)造出一系列精彩的視覺影像,實(shí)現(xiàn)了歌劇舞臺(tái)本身所無法達(dá)成的藝術(shù)效果。例如,在呈現(xiàn)白毛女躲進(jìn)深山控訴舊社會(huì)的段落時(shí),白毛女站在前景處的山石布景之上,但攝影機(jī)卻以一個(gè)劇院觀眾視野之外的夸張角度向上仰視人物,為白毛女對(duì)舊社會(huì)的控訴增添了英雄主義色彩。
從這個(gè)角度看,歌劇《白毛女》似乎并不能被視為一出單純的舞臺(tái)戲劇,而是一種融合了舞臺(tái)戲劇和銀幕影像的跨媒介實(shí)踐。事實(shí)上,如果對(duì)歷史稍加回溯就不難發(fā)現(xiàn),“白毛女”故事的演繹從來都沒有被框定在單一的媒介形式之內(nèi),而是不斷擺渡于不同媒介之間。具體來說,“白毛女”故事最初的原型是20世紀(jì)40年代流傳于晉察冀邊區(qū)的民間故事,其主要內(nèi)容是八路軍抵達(dá)某邊區(qū)村莊之后,原本希望開展破除封建迷信的運(yùn)動(dòng),卻意外揭開當(dāng)?shù)亍鞍酌晒谩毙叛霰澈蟮臅r(shí)代悲劇——妙齡農(nóng)村孤女遭到惡霸地主欺負(fù),不得已逃入深山;由于少女在山洞中少見陽光,缺衣少鹽,因而渾身發(fā)白;走投無路的她以山中奶奶廟的供奉為食,卻被當(dāng)?shù)啬繐粽哒`信為“白毛仙姑”顯靈。1944年,《晉察冀日報(bào)》的記者林漫給時(shí)任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院長的周揚(yáng)提交了一份由民間故事“白毛仙姑”改寫的通訊稿件。此時(shí)中共七大即將在延安召開,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正準(zhǔn)備排演一出歌舞劇進(jìn)行獻(xiàn)禮,因此在周揚(yáng)和賀敬之、丁毅、馬可、張魯?shù)任乃嚬ぷ髡叩墓餐ο拢鑴 栋酌窓M空出世。[16]新中國成立后,東北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導(dǎo)演王濱、水華等人將歌劇《白毛女》改編為同名電影,并在1951年配合當(dāng)時(shí)新中國的土地改革運(yùn)動(dòng),在全國范圍內(nèi)公映。[17]自此,“白毛女”的故事跨越了民間傳說、新聞通訊、舞臺(tái)戲劇、電影等多種媒介形式,在不同時(shí)代一次次地演繹,且不同時(shí)代對(duì)“白毛女”故事的演繹又總是與現(xiàn)實(shí)政治的需要緊密相聯(lián)——延安時(shí)期的歌劇《白毛女》突出抗日民主根據(jù)地和國民黨統(tǒng)治地區(qū)所代表的新舊兩種社會(huì)秩序的巨大差異,進(jìn)而團(tuán)結(jié)和感召廣大民眾;新中國成立后的《白毛女》電影則將重點(diǎn)放在地主和農(nóng)民之間尖銳的階級(jí)矛盾上,旨在表現(xiàn)舊社會(huì)佃農(nóng)的悲慘命運(yùn)和反抗剝削的斗爭,宣傳和推動(dòng)新中國的土地改革運(yùn)動(dòng)。
從這個(gè)角度看,“白毛女”故事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演繹和改寫或許為人們提供了一個(gè)觀察“紅色經(jīng)典”電影發(fā)展歷程的基本模式。一方面,“紅色經(jīng)典”的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一個(gè)跨媒介的鏈?zhǔn)缴a(chǎn)過程,同一個(gè)故事文本可能衍生出多種媒介形式,因此,“紅色經(jīng)典”電影往往是對(duì)既有革命題材小說、戲劇、電影的跨媒介改編;另一方面,“紅色經(jīng)典”電影的出現(xiàn)總是因應(yīng)著現(xiàn)實(shí)政治的時(shí)代變化,它并不是以一種持續(xù)性的方式影響后續(xù)的創(chuàng)作,而是以間斷式的回歸、重復(fù)、衍生與改寫,將既有的故事文本及其歷史記憶召喚至當(dāng)下,產(chǎn)生跨時(shí)代的“回響”。
結(jié)語
借由對(duì)“紅色經(jīng)典”這一文藝?yán)碚撛捳Z歷史語境的回溯,可以更為明晰“紅色經(jīng)典”電影的精神本質(zhì)及理論價(jià)值。延安文藝作為“紅色經(jīng)典”概念及作品的源頭,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直接指引和領(lǐng)導(dǎo)下發(fā)生的,“人民性”是其根本屬性,“為人民服務(wù)”是其根本宗旨。這樣一種屬性和宗旨,令其擁有與時(shí)俱進(jìn)的生命力,并不斷在現(xiàn)實(shí)政治與藝術(shù)審美的互動(dòng)中實(shí)現(xiàn)自我更新,在不同時(shí)代的創(chuàng)作者和接收者中產(chǎn)生復(fù)雜而深刻的“回響”。
時(shí)至今日,“紅色經(jīng)典”既是一種“影響”也是一種“回響”。作為一種“影響”,“紅色經(jīng)典”電影傳承了革命文化和紅色基因,早已進(jìn)入中國當(dāng)代社會(huì)文化的血液之中,對(duì)于普通觀眾而言具有深入人心的影響力;作為一種“回響”,“紅色經(jīng)典”影片帶來了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的回旋與激蕩——這些文藝創(chuàng)作不斷重復(fù)、回應(yīng)、對(duì)照、發(fā)展、衍生與改寫原來的經(jīng)典電影文本,傳承“紅色經(jīng)典”精神的同時(shí),將“為人民服務(wù)”的本質(zhì)性特征牢牢銘刻在社會(huì)主義文藝作品上。換言之,“紅色經(jīng)典”作品的經(jīng)典化過程,本質(zhì)上既有故事文本在不同時(shí)代的跨媒介改編,也體現(xiàn)了不同時(shí)代的影視工作者繼承和弘揚(yáng)革命文藝傳統(tǒng),沿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dǎo)向繼續(xù)繁榮文藝創(chuàng)作的意識(shí)和使命感。
這些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人成長的“紅色經(jīng)典”影片,不僅早已成為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與藝術(shù)瑰寶,而且以各種當(dāng)代“回響”式的作品令紅色革命精神與歷史文化記憶得以傳承和發(fā)展。它們在基本理念、社會(huì)理想、道德繼承、創(chuàng)作范式、美學(xué)風(fēng)格上都存在著內(nèi)在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尤其都以人民性為本質(zhì)理念,汲取現(xiàn)實(shí)大眾的精神營養(yǎng),反映和再現(xiàn)了人民的智慧與經(jīng)驗(yàn),助力社會(huì)主義革命與建設(shè)。與時(shí)俱進(jìn)的“紅色經(jīng)典”影片,在記錄和反映時(shí)代精神的同時(shí),始終堅(jiān)持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shí)際相結(jié)合,令人們得以固守母體文化與民族根性,與時(shí)俱進(jìn)地肩負(fù)起歷史使命,從而不斷獲得新時(shí)代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和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精神動(dòng)力。
參考文獻(xiàn):
[1]陳濤,陳琳,改編、衍生與挪用:紅色經(jīng)典電影的當(dāng)代回響[ J ].電影藝術(shù),2021(04):69-74.
[2]楊經(jīng)建.“紅色經(jīng)典”:在現(xiàn)代性敘事中理解和闡釋[ J ].東岳論叢,2006(01):105.
[3]劉亭.新時(shí)代“紅色經(jīng)典”的電影改編[ J ].當(dāng)代電影,2019(11):107-111.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6.
[5]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2.
[6]洪子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106.
[7]黃偉林.中國當(dāng)代小說家群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94.
[8]孟繁華.眾神狂歡:當(dāng)代中國的文化沖突問題[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80.
[9]陶東風(fēng).紅色經(jīng)典:在官方與市場的夾縫中求生存(下)[ J ].中國比較文學(xué),2004(04):34-51.
[10]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重要講話公開發(fā)表[N].人民日報(bào),2015-10-15(01,04).
[11]侯洪,張斌.“紅色經(jīng)典”:界說、改編及傳播[ J ].當(dāng)代電影,2004(06):79-82.
[12]陳犀禾,趙彬.紅色經(jīng)典電影及其國家敘事[ J ].電影藝術(shù),2021(04):35-40.
[13]周揚(yáng),周揚(yáng)文論選[M].北京:人民出文學(xué)出版社,2009:16-28.
[14]陳思和.我不贊成“紅色經(jīng)典”這個(gè)提法[N].南方周末,2004-05-06(C14).
[15][美]王斑.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jì)中國的美學(xué)與政治[M].孟祥春,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151.
[16]黃科安.文本、主題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訴求:談歌劇《白毛女》如何成為紅色經(jīng)典[ J ].文藝研究,2006(09):106-115.
[17]石川.《白毛女》:從民間傳奇到紅色經(jīng)典[ J ].當(dāng)代電影,2005(05):60-64.
【作者簡介】? 陳 濤,男,山東萊州人,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副院長、教授,主要從事戲劇影視及新媒體藝術(shù)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xiàng)目“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學(xué)術(shù)話語體系的形成、建構(gòu)與反思研究”
(編號(hào):20&ZD28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