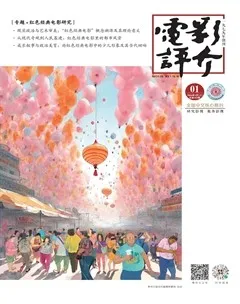從現(xiàn)代奇觀到人民基建:紅色經(jīng)典電影里的都市風(fēng)景
李逸



1956年,由長春電影制片廠出品的紅色經(jīng)典電影《上甘嶺》(沙蒙/林杉,1956)呈現(xiàn)了志愿軍戰(zhàn)士們合唱《我的祖國》的動人場面:“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此時,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士們望向遠(yuǎn)方,精心設(shè)計的蒙太奇段落里,雄偉的水壩、高聳的樓房、密集的工廠等都市風(fēng)光淡入淡出。這些風(fēng)景影像并不是對戰(zhàn)場環(huán)境的客觀反映,而是在悠揚的歌聲中被賦予主觀的情感向度,以聯(lián)想的方式喚起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熱情和對“祖國”的認(rèn)同。正如英國歷史學(xué)家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所見,“雖然我們總習(xí)慣于將外部世界和人類感知劃歸為兩個領(lǐng)域,但事實上,它們不可分割”,因此“風(fēng)景”(landscape)總是“如同層層巖石般在記憶層被建構(gòu)起來”,承載著“錯綜復(fù)雜的記憶、神話以及意義”。[1]
從這個角度看,《上甘嶺》當(dāng)中的都市風(fēng)景絕非一系列無關(guān)緊要的視覺客體,而是銀幕內(nèi)外的人們自我內(nèi)心世界的投射。一方面,“風(fēng)景”本身作為一種象征符號,其意義來自于文化經(jīng)驗的積累。既往文本對于同一風(fēng)景的不斷再現(xiàn)、言說、想象構(gòu)成人們接受和創(chuàng)造風(fēng)景及其文化意義的歷史場域;另一方面,風(fēng)景的建構(gòu)者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歷史環(huán)境影響,在國家、民族、性別、階級、意識形態(tài)等各種力量介入下,對風(fēng)景加以選擇、取舍、改變和加工。因此,誠如美國學(xué)者溫迪·達(dá)比(Wendy Darby)所見:“風(fēng)景的再現(xiàn)并非與政治沒有關(guān)聯(lián),而是深度植于權(quán)力與知識的關(guān)系之中。”[2]
基于這種對“風(fēng)景”的認(rèn)識,本文聚焦紅色經(jīng)典電影里的都市風(fēng)景,在勾勒紅色經(jīng)典電影及其都市風(fēng)景譜系的基礎(chǔ)上,揭示都市風(fēng)景影像背后的交鋒與知識生產(chǎn)。或許借助這些銀幕上的二維風(fēng)景,能有機會抵達(dá)現(xiàn)代歷史和社會人心的深處。
一、左翼傳統(tǒng):都市風(fēng)景的二元結(jié)構(gòu)
1933年,中國左翼文壇的領(lǐng)軍人物茅盾出版長篇名作《子夜》。該著作以20世紀(jì)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為舞臺,描繪社會各階級的生存畫卷。小說以一段都市風(fēng)景的描寫開篇:
“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fā)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3]
在這個段落中,茅盾不斷變換風(fēng)景描寫的視點,雄健短促的文字將鋼架橋、電車、火花、摩天大樓、霓虹燈、洋房等片段化的都市風(fēng)景以蒙太奇的方式組合在一起——由鋼鐵、電力、火焰、高樓組成的一個個“怪獸”匯聚著人們面對現(xiàn)代都市時的震驚體驗。就如王德威在《歷史與怪獸》一書中所見,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的書寫總是纏繞著“現(xiàn)代性”(modernity)與“怪獸性”(monstrosity)的辯證:現(xiàn)代性及其文學(xué)敘事的登場往往具有進(jìn)步和正義的表象,但在歷史經(jīng)驗和實踐中卻總是墮落為制造創(chuàng)傷和暴力的“怪獸性”。[4]從這個角度看,《子夜》開篇對都市風(fēng)景的描寫實際上揭示了現(xiàn)代都市的雙面性:一系列令人炫目的都市風(fēng)景既是由聲光化電等現(xiàn)代知識搭建起來的進(jìn)步之物,也是閃爍著“千百只小眼睛”,不斷噴出“赤光”和“綠焰”的“巨大怪獸”。現(xiàn)代都市看似科學(xué)、進(jìn)步的奇觀外表之下,潛藏著令人畏懼和不安的危機。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情感結(jié)構(gòu)(structures of feeling)同樣寄身于左翼電影對現(xiàn)代都市的再現(xiàn)之中。與小說《子夜》的開篇一樣,包括《都市風(fēng)光》(袁牧之,1935)、《十字街頭》(沈西苓,1937)、《馬路天使》(袁牧之,1937)在內(nèi)的左翼電影都是以一組展現(xiàn)都市風(fēng)景的蒙太奇段落作為影片開場:摩天大樓、霓虹燈、電車、汽車、橋梁等都市風(fēng)景畫面快速地切換,一系列新鮮的現(xiàn)代奇觀不僅沖擊著觀眾的感官,還深刻地揭示了現(xiàn)代經(jīng)驗本身的流變不居。正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現(xiàn)代都市經(jīng)驗的精妙洞見:“都市現(xiàn)象是移動的……一切都在移動和變化之中,都市就是一個充滿了沖突和矛盾的地方”。[5]因此,左翼電影的都市風(fēng)景影像似乎總是充滿不安和躁動。一方面,這些左翼影片在使用快速切換的蒙太奇段落呈現(xiàn)都市風(fēng)景的同時,都會為畫面配上一段多聲部合奏的交響樂,各式樂器在合奏段落中的快速交織和對話似乎隱喻著現(xiàn)代都市內(nèi)部紛繁復(fù)雜的矛盾沖突;另一方面,在這些展示都市風(fēng)景的影像段落中,《都市風(fēng)光》《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等電影都刻意采用傾斜的鏡頭視角拍攝都市中的各色景物,影像畫面內(nèi)部凌亂的構(gòu)圖和畫面之間的高速切換無疑為都市風(fēng)景增加了幾分怪異和不安。
事實上,對彼時的左翼電影創(chuàng)作者而言,現(xiàn)代都市固然是進(jìn)步文明之象征,但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剝削的墮落之所。例如,《馬路天使》片頭由都市風(fēng)光組成的蒙太奇段落最后停留在一棟高聳的摩天大樓之上,鏡頭從樓頂不斷地向下移動,直至地平線之下。此時畫面里出現(xiàn)了一行說明性的大字:“上海地下層”。摩天大廈的樓層高低在這里構(gòu)成了一個有關(guān)社會差異的隱喻,高樓林立的現(xiàn)代奇觀底下埋藏著一幅截然相反的都市風(fēng)景。于是在接下去的鏡頭里,低矮狹窄的木制民房和吵鬧擁擠的弄堂建構(gòu)起一個屬于普通人的生活空間。需要指出的是,在《馬路天使》當(dāng)中,“地上”的現(xiàn)代奇觀與“地下”的空間形成截然對立的兩個世界。來自“上海地下層”的男主人公陳少平為了幫助女主人公小紅擺脫惡霸的糾纏,曾前往“地上”的摩天大樓,尋求律師幫助。影片設(shè)置了一系列笑料百出的情節(jié)展現(xiàn)男主人公對高樓里諸多現(xiàn)代設(shè)施的好奇,可是律師輕蔑的態(tài)度和高昂的咨詢費又明確地為人們展現(xiàn)了普通民眾難以融入“地上”現(xiàn)代生活的困窘。手足無措的男主人公最終望向高樓外的都市風(fēng)景,在一個大角度的俯拍鏡頭里,他終于看清了大樓底層低矮的木制平房和交錯的弄堂,那才是屬于他的生活空間。這種對都市底層空間的俯拍視角一方面是高大的現(xiàn)代建筑與低矮的普通民房在空間關(guān)系上的客觀反映;另一方面,“地上”與“地下”這兩個世界、兩種生活方式、兩個群體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也在這種俯仰拍切換的鏡頭語言中獲得具體的視覺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世紀(jì)20年代,德國表現(xiàn)主義電影大師弗利茨·朗(Fritz Lang)就已經(jīng)在其電影《大都會》(弗里茨·朗,1927)當(dāng)中,借由“地上”和“地下”兩種都市風(fēng)景為人們呈現(xiàn)了一個階層分化的現(xiàn)代惡托邦(dystopia):權(quán)貴和富人奢靡地居住在夢幻般的摩天大樓當(dāng)中;貧窮的勞工卻只能在冰冷幽暗的地下城市中忍受剝削。不過,與這部科幻巨制中陰冷、機械的底層世界不同,中國左翼電影傳統(tǒng)下的底層空間反倒總是充滿溫情和救贖的力量。無論是《馬路天使》里賣唱女、吹鼓手、報販、理發(fā)師等普通民眾的守望相助,還是《十字街頭》里失業(yè)青年們在困頓中的彼此鼓勵,抑或是《萬家燈火》(沈浮,1948)和《烏鴉與麻雀》(鄭君里,1949)等紅色經(jīng)典電影里弄堂居民們的共克時艱……現(xiàn)代都市光鮮亮麗、物欲橫流的奇觀表象之下,是居民們平凡溫暖的日常生活。因此,如果說影片的“地上”世界對應(yīng)著現(xiàn)代都市生活中令人眼花繚亂的奇觀“表象”,那么有關(guān)“地下”空間的風(fēng)景建構(gòu)則始終致力于進(jìn)入都市建筑及民眾生活的“內(nèi)部”——這些空間的風(fēng)景影像很少呈現(xiàn)建筑的整體外觀,而是以石庫門老房的亭子間、喧鬧吵嚷的酒肆大堂、演詞唱曲的茶館戲臺等碎片化的室內(nèi)空間串聯(lián)起普通民眾真實的生活經(jīng)驗,成為人們反思和批判都市現(xiàn)代性的抵抗之所。
在左翼電影傳統(tǒng)的影響下,仍然可以在新中國成立后許多反映都市生活的紅色經(jīng)典電影中看到同樣的風(fēng)景建構(gòu)邏輯。比如,《永不消逝的電波》(王蘋,1958)對都市風(fēng)景的再現(xiàn)延續(xù)了左翼電影里的二元風(fēng)景結(jié)構(gòu)。在影片中,日軍控制的現(xiàn)代高樓與李俠夫婦生活的弄堂房間組成都市的兩種基本空間單元,將左翼電影有關(guān)“地上”和“地下”兩個空間的隱喻轉(zhuǎn)化成革命戰(zhàn)爭時期敵與我、善與惡的鮮明界限。二元的都市空間由此演變?yōu)槎牡赖路忠啊2煌凇恶R路天使》里男主人公陳少平對“地上”生活模棱兩可的好奇和困窘,《永不消逝的電波》女主人公何蘭芬對“地上”都市提出了堅決的批判:“我根本討厭這種生活”。與之相對的,夫婦二人私人的“地下”生活空間也成為反抗日軍侵略、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之所。
除此之外,《霓虹燈下的哨兵》(王蘋/葛鑫,1964)的二元都市風(fēng)景也同樣被賦予了道德訓(xùn)誡的意味。在影像呈現(xiàn)上,該片刻意將許多重要情節(jié)安排在夜間,用閃爍的霓虹燈和各式各樣的廣告燈牌建構(gòu)令人眼花繚亂的都市風(fēng)景。戰(zhàn)士們身處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陷入精神上的矛盾和迷茫。上海南京路上的一系列都市風(fēng)景影像再次呼應(yīng)了左翼電影的經(jīng)典視聽語言:一個傾斜的俯拍鏡頭里,高聳的現(xiàn)代建筑布滿了閃爍的霓虹燈,各式各樣的商場和夜總會伴著喧鬧嘈雜的爵士樂,快速地疊映于畫面之中,上海又一次被再現(xiàn)為一個紙醉金迷、充滿誘惑的現(xiàn)代都市。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紅色經(jīng)典電影對現(xiàn)代都市的負(fù)面再現(xiàn)實際上與中國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相關(guān)。這一時期,城市(尤其是東部城市)的經(jīng)濟地位開始下降,發(fā)達(dá)的現(xiàn)代都市反而被視為社會主義建設(shè)和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6]
從這個角度看,《霓虹燈下的哨兵》表面上是講述社會主義戰(zhàn)士的自我修養(yǎng)與堅守,但如何改造和建設(shè)一座符合社會主義理想的現(xiàn)代都市或許也構(gòu)成了影片未曾言明的又一重主旨——新中國的現(xiàn)代都市既不應(yīng)該充斥著奢華而墮落的現(xiàn)代奇觀,也絕不僅僅是一系列溫情卻困頓的普通人的生存空間。這意味著紅色經(jīng)典電影對都市的再現(xiàn)也必須突破既有的二元結(jié)構(gòu),尋找與之對應(yīng)的第三種都市風(fēng)景影像。
二、空間改造:現(xiàn)代都市的第三種風(fēng)景
事實上,《霓虹燈下的哨兵》早已借由工人領(lǐng)袖周德貴之口,揭示了現(xiàn)代都市在“資本主義溫床”之外的另一種歷史可能:“有一些資本家說,這南京路是外國人的金磅銀磅給堆起來的。我說呀,不!那是我們勞苦大眾用雙手開出來的!是我們烈士們用鮮血鋪起來的!”在影片的最后,戰(zhàn)士們克服了自身缺陷,準(zhǔn)備奔赴新戰(zhàn)場,一座充滿革命熱情、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市終于現(xiàn)身——摩天大樓上的霓虹燈再次亮起,只不過與影片之前所建構(gòu)的都市風(fēng)景不同,此時的電影鏡頭不再以傾斜角度制造充滿怪異感和壓迫性的奇觀,而是用一個正面的仰拍鏡頭配合昂揚的進(jìn)行曲,突出戰(zhàn)士們眼前都市風(fēng)景的崇高感。畫面的中心,閃爍的霓虹燈大字不再是五彩斑斕的商業(yè)廣告,而是紅色的政治標(biāo)語:“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在這個消費奇觀轉(zhuǎn)化為政治詢喚的時刻,上海從一個被金錢和資本支配的墮落之都,變成了一個充滿革命熱情和民族自豪感的社會主義之城。
由此可知,除了通過二元的都市風(fēng)景揭示階級矛盾、傳遞道德訓(xùn)誡之外,紅色經(jīng)典電影里的都市風(fēng)景實際上更強調(diào)都市空間的改造和轉(zhuǎn)化。1952年,改編自話劇《龍須溝》的同名紅色經(jīng)典電影上映。該影片以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首都北京進(jìn)行的城市改造運動為背景,展現(xiàn)北京龍須溝一帶大雜院內(nèi)四戶人家從1949年前到20世紀(jì)50年代初期的生活。影片以一場夏日暴雨作為開頭,攝影機鏡頭跟隨龍須溝漲漫的洪水進(jìn)入一間大雜院;之后,攝影機又順著大雜院住戶二春的運動軌跡,穿行在大雜院的不同房間之中,全景式地展現(xiàn)了城市普通居民的艱辛生活。獨特的運鏡方式和剪輯手法將大雜院內(nèi)的各個房間串聯(lián)起來,一方面反映了大雜院的破敗傾頹——千瘡百孔的門窗、墻體和屋頂使得本該封閉的各個房間在空間上彼此敞開,也讓攝影機的穿行式調(diào)度成為可能;另一方面,跟隨著攝影機的穿行視角,觀眾可以看到大雜院居民們互相串門、隔墻對話、交換物品,因房屋破敗而產(chǎn)生的空間連續(xù)性反倒消弭了多個家庭和個人之間的心理隔閡,成為整個大雜院在情感上“親如一家”的空間隱喻。從這個角度看,《龍須溝》(冼群,1952)同樣繼承了左翼電影對社會普通百姓的關(guān)照,它在無情的自然風(fēng)雨和社會環(huán)境中,營造了一個充滿苦難卻不失溫情的普通人生存的都市空間。然而與左翼電影對都市空間的影像建構(gòu)不同,《龍須溝》在呈現(xiàn)各式雜院和民居時,并沒有采取俯仰拍的鏡頭組合,也沒有延續(xù)左翼電影有關(guān)“地上”現(xiàn)代奇觀和“地下”空間的二分式風(fēng)景結(jié)構(gòu)。影片始終保持水平的拍攝角度,記錄了同一個都市空間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歷史變化:漆黑的畫面被一盞盞電燈點亮,低矮殘舊的大雜院變成修繕一新的磚瓦房,發(fā)黑發(fā)臭的龍須溝變成寬闊平坦的大馬路,原本雜亂的街邊商鋪也被衛(wèi)生所、大禮堂等公共建筑所取代……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社會歷史轉(zhuǎn)折被濃縮進(jìn)都市風(fēng)景的影像變化之中,馬路、衛(wèi)生所、大禮堂等城市基建直觀地展現(xiàn)了社會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革。有趣的是,這種“建筑”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隱喻性關(guān)系其實內(nèi)在于馬克思有關(guān)“經(jīng)濟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的經(jīng)典論述之中。對馬克思而言,“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其中,現(xiàn)實的社會生產(chǎn)方式構(gòu)成了所謂的“經(jīng)濟基礎(chǔ)”,而與之相適應(yīng)的文化、政治、法律等諸多制度形式構(gòu)成了所謂的“上層建筑”。[7]在這個意義上,《龍須溝》以基礎(chǔ)設(shè)施映射社會整體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影像形式或許正是對馬克思經(jīng)典政治經(jīng)濟原理的視覺化。
不僅如此,在《龍須溝》的影像再現(xiàn)中,這個經(jīng)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北京城既不是一個被金錢和消費主導(dǎo)的商業(yè)都市,也不是私人化的居民生活空間,而是一個公共性的、勞動的空間。事實上,電影開篇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對勞動場面的刻畫,龍須溝周邊街巷破敗的墻體將橫搖的長鏡頭分割成一個個具體的勞動場景:鋸木頭的木匠、砍柴的學(xué)徒、磨刀的幫工、編制草席的婦女、傾倒污水的挑夫……此時的龍須溝雖然是一個公共性的勞動空間,但畫面中的人們面無表情地工作,背景處低沉悲傷的弦樂似乎在訴說他們的苦難——三輪車夫的工資被老板惡意克扣、曲藝演員被惡霸趕下舞臺、商販也需要忍受流氓們的盤剝……普通人的勞動無法在過去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獲得承認(rèn),影像畫面里破舊的建筑和滿是雜物的水溝揭示了這種勞動的無望,也象征著舊有社會制度的搖搖欲墜。作為對比,影片的后半段也呈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同一地點的都市風(fēng)景。這個影像段落并沒有像開場那樣采用緩慢的長鏡頭和低沉哀傷的弦樂,而是用一組快速切換的蒙太奇和積極昂揚的進(jìn)行曲展現(xiàn)人們集體勞動的熱情,龍須溝的空間面貌在鏡頭的快速切換中徹底改變。不同于影片開場長鏡頭里單個勞動者的手工勞作,影片后半段的這組都市影像格外強調(diào)現(xiàn)代機器的使用和勞動者的集體協(xié)作,將龍須溝周邊破敗的手工作坊變成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現(xiàn)代化工地。不僅如此,影片還將這些興建基礎(chǔ)設(shè)施的畫面與勞動者的笑臉剪輯在一起,并且讓處于畫面中心的人物駕駛工程機械不斷地穿行并占據(jù)這個新的城市空間。
在這些畫面中,超越了舊有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不再受到剝削,能夠以生產(chǎn)者的身份自主地占據(jù)并享受他們自己的勞動成果;龐大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和集體化的勞動過程也將個體意義上的勞動者詢喚為主體意義上的“人民”,印證了朗西埃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理解:對馬克思主義而言,“解放被認(rèn)為是勞動與歷史的標(biāo)志”,因此在經(jīng)驗性社會形態(tài)層面上,“馬克思式的人民或廣義社會主義式的人民,總是將人民等同于勞動者”。[8]在此基礎(chǔ)上,借由大雜院居民們的對話,影片進(jìn)一步明確了都市風(fēng)景的政治詢喚,這些以人民為中心的基建工程最終確立了“人民政府”的合法性:“人民政府,真是咱們窮人自個兒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單牌樓不修,先給咱們來修這條幾十年沒人管過的臭溝”。
三、人民基建:從政治認(rèn)同到經(jīng)濟隱喻
類似的政治修辭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紅色經(jīng)典電影中頻頻出現(xiàn),宏偉的人民基建及其風(fēng)景影像成為新中國塑造政治認(rèn)同的重要方式。1959年,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開啟了又一輪城市改造運動。以“國慶十大工程”①為代表的一系列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改變了北京的城市面貌,也塑造了廣大人民對于新中國和社會主義的強烈自豪感。同年,中央新聞紀(jì)錄電影制片廠攝制了《北京新建筑》(張建珍/李堃,1959)紀(jì)錄片,再現(xiàn)了“國慶十大工程”的建設(shè)過程。影片開頭是一組北京城的俯拍風(fēng)景鏡頭。不同于左翼電影的都市風(fēng)景俯拍對普通人生存空間的揭示,也不同于《龍須溝》水平視角鏡頭所營造的紀(jì)實性和參與感,《北京新建筑》開篇的俯拍鏡頭始終洋溢著一種“當(dāng)家作主”的豪情。一方面,平坦寬闊的馬路、鱗次櫛比的大樓、布局有序的工廠和排放濃煙的煙囪在昂揚的配樂中交替出現(xiàn),北京被再現(xiàn)為一個充滿秩序感的現(xiàn)代工業(yè)城市。觀眾們透過攝影機的俯瞰視角分享了對城市公共空間的規(guī)劃和掌控,成為現(xiàn)代都市的主人;另一方面,影片在展現(xiàn)天安門廣場附近新舊空間變化的兩個俯拍鏡頭中插入了一系列反映勞動場景的影像,將城市居民再現(xiàn)為城市的建設(shè)者和改造者。在這個快速切換的勞動場景里,影片還使用了一組并列蒙太奇,把云南大理石、河北曲陽紅、北京石膏花、廣東琉璃瓦等來自五湖四海的建筑材料剪輯在一起,將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造過程轉(zhuǎn)變?yōu)閲颐褡迳矸莸娜坭T。從這個角度看,《北京新建筑》里的“人民基建”不僅被社會環(huán)境與社會關(guān)系所形塑,更是對社會關(guān)系的生產(chǎn)。事實上,影片所再現(xiàn)的“北京新建筑”本身就是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而建設(shè)的,這些建筑在設(shè)計之初就肩負(fù)著塑造民族認(rèn)同感的功能——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訴說著新中國的革命歷史及其起源神話;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等建筑則直接傳遞著多元一體的民族認(rèn)同。
與此同時,貫穿全片的旁白也在深情地強調(diào)“人民基建”的歷史意義:
“現(xiàn)在這里還是平房土屋,明天這里將是高樓大廈。這個宏偉的建筑計劃符合了廣大人民的愿望。我們要清除一切落后陳舊的環(huán)境,我們是嶄新的人民,我們在創(chuàng)造嶄新的生活,我們將創(chuàng)造嶄新的城市……”
事實上,無論是《龍須溝》,還是《北京新建筑》,這些影片都借由都市風(fēng)景的空間改造建構(gòu)起一整套線性進(jìn)步的歷史敘事。宏偉的基建計劃被賦予時間維度上的未來性,它永遠(yuǎn)屬于“明天”,或處在“將”被創(chuàng)造的狀態(tài)之中,成為革命事業(yè)和共產(chǎn)主義偉大理想的視覺化身。這一切讓人們想起馬克思(Karl Marx)曾說:“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9]因此,紅色經(jīng)典電影對“人民基建”的影像再現(xiàn)似乎總是帶有烏托邦式的浪漫主義色彩:在《龍須溝》的最后一個場景里,溫暖的陽光灑下,原本居住在龍須溝的普通民眾不見了身影,一群少年少女穿著統(tǒng)一的白襯衫和紅領(lǐng)巾,騎著自行車迎向鏡頭。改造后的龍須溝被再現(xiàn)為一個充滿希望和朝氣的世外桃源。這里的一切都如此嶄新,舊社會的磨難和哀愁已經(jīng)徹底過去。類似的,《北京新建筑》將人民大會堂、北京火車站等建筑放置在遼闊、空曠的背景當(dāng)中。這一方面當(dāng)然是為了突出這些工程的宏大雄偉;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筑物本身脫離了周邊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獲得一種空間上的懸置性和視覺上的夢幻感。正如影片最后的旁白所說,這些宏大的建筑工程是如此不可思議,以至于只能將之視為“一個奇跡”。從這個角度看,紅色經(jīng)典電影銀幕內(nèi)外那些脫離了現(xiàn)實空間環(huán)境的宏偉工程雖然建立起一套線性的進(jìn)步敘事,用浪漫化的未來許諾確認(rèn)人們當(dāng)下生活的合法性,但是也將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本身永遠(yuǎn)地懸置在未來。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社會發(fā)展邏輯的變化,許多紅色經(jīng)典電影中的基建影像在保留其線性進(jìn)步敘事的同時,弱化了政治認(rèn)同的意味。例如《牧馬人》(謝晉,1982)的開篇將敕勒川的自然風(fēng)光和北京的都市風(fēng)景以對比蒙太奇的方式組接在一起,作為鄉(xiāng)村與城市、過去與當(dāng)下的一組對照。在展現(xiàn)都市風(fēng)景的畫面中,影片并沒有像《北京新建筑》一樣,選擇帶有明確政治指涉的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等建筑,而是用川流不息的長安街、首都機場、西直門立交橋等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將北京塑造為一個對外開放的、崇尚溝通和交流的國際化都市。類似對交通基建的強調(diào)也出現(xiàn)在《美麗新世界》(施潤玖,1998)的都市風(fēng)景之中。該片以男主人公寶根乘坐公交車在高樓間穿行的視角作為開場,為觀眾呈現(xiàn)了上海繁華的都市風(fēng)景。然而不同于《永不消逝的電波》《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紅色經(jīng)典電影將南京路作為上海富庶和繁榮的地標(biāo),《美麗新世界》卻將鏡頭更多地對準(zhǔn)了1990年以來新開發(fā)的浦東地區(qū)。不僅如此,在男主人公寶根乘車穿行的移動視角中,占據(jù)畫面前景的再現(xiàn)對象并非是城市的高樓大廈,而是寬闊繁忙的道路和橋梁。事實上,浦東地區(qū)的規(guī)劃和建設(shè)從一開始就沒有延續(xù)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基建工程對于紀(jì)念館、體育場、大禮堂等集會空間和宏偉建筑的偏重,而是首先興建了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羅山路立交橋、浦東機場等一大批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①這種基建類型的變化揭示了中國城市發(fā)展邏輯的歷史轉(zhuǎn)折——如果說20世紀(jì)50年代紅色經(jīng)典電影的基建影像通過公共的紀(jì)念碑式建筑為人們標(biāo)明了革命事業(yè)的未來許諾;那么《美麗新世界》里川流不息的馬路和方便快捷的交通則構(gòu)成了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生產(chǎn)要素自由流通和配置的一個縮影,它運送了無數(shù)來自外鄉(xiāng)的“寶根”進(jìn)入城市,為上海的社會發(fā)展注入新鮮活力。在這個意義上,四通八達(dá)的馬路既提供了空間穿行和交流的便利,也是新時代勞動者奔赴美好未來的時間隱喻。
結(jié)語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改革開放后的紅色經(jīng)典電影一度弱化了基建影像的政治召喚,但20世紀(jì)50年代紅色經(jīng)典電影里那些宏偉壯觀、浪漫激情的“人民基建”并沒有就此消逝。
2019年,隨著《流浪地球》(郭帆,2019)上映,人們似乎看到了“人民基建”影像及其政治修辭的復(fù)歸。一方面,無論是地下城市各式顯示屏上的紅色宣傳標(biāo)語,還是地上巨大的行星發(fā)動機,抑或是冰天雪地里操縱工程機械的普通勞動者,《流浪地球》延續(xù)了《龍須溝》《霓虹燈下的哨兵》《北京新建筑》等紅色經(jīng)典電影對集體勞動、工業(yè)秩序和政治召喚的強調(diào);另一方面,不同于紅色經(jīng)典電影里都市“地上”與“地下”的階層和道德二分,《流浪地球》用行星發(fā)動機這一巨型的基建將“地上”與“地下”兩個世界變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體:“地上”的工人負(fù)責(zé)建造和運營發(fā)動機,為“地下”的居民提供生活所需的熱能和電能;而“地下”生活的家人們則是“地上”工人不斷工作和奮斗的理由。在初次介紹未來北京都市風(fēng)景的鏡頭中,《流浪地球》從道路中行駛的工程車輛出發(fā),用一個急速上拉的鏡頭調(diào)度,沿著道路一側(cè)的巨大山體依次向上,再現(xiàn)縱橫交錯的運輸網(wǎng)絡(luò)、精密繁復(fù)的工程機械、龐大堅實的行星發(fā)動機,乃至整個“流浪”中的地球——在這個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體的畫面轉(zhuǎn)換中,每一個勞動者和他們的工程創(chuàng)造都變成了更大基建的組成部分,因此改造和搬運整個地球成為影片所再現(xiàn)的一種終極的基建,它規(guī)范和生產(chǎn)著影片中一切個體努力的價值和社會生活的形態(tài)。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說20世紀(jì)50年代紅色經(jīng)典電影對龍須溝、北京十大建筑等“人民基建”的再現(xiàn)只是意在塑造一個以國家、民族為核心的“中國人民”身份,那么這個名為“流浪地球”基建工程則維系著全人類未來千百年的共同命運。影片里那些更加雄偉壯觀、且充滿浪漫主義豪情的基建影像在重述革命理想的同時,超越了單一的民族國家敘事,展現(xiàn)出全球主義愿景。
①“國慶十大工程”項目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全國農(nóng)業(yè)展覽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釣魚臺迎賓館、華僑大廈。
①關(guān)于浦東開發(fā)過程中的基礎(chǔ)設(shè)施規(guī)劃及建設(shè)情況。詳見:浦東市政府史志辦.浦東開發(fā)開放20年大事記(1990-2009)[EB/OL].(2023-09-18)[2023-09-18].http://szb.pudong.gov.cn/pdszb_pdds_dsj/2012-01-31/Detail_410991.htm.
【作者簡介】? 李 逸,男,浙江杭州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早期電影和視覺現(xiàn)代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