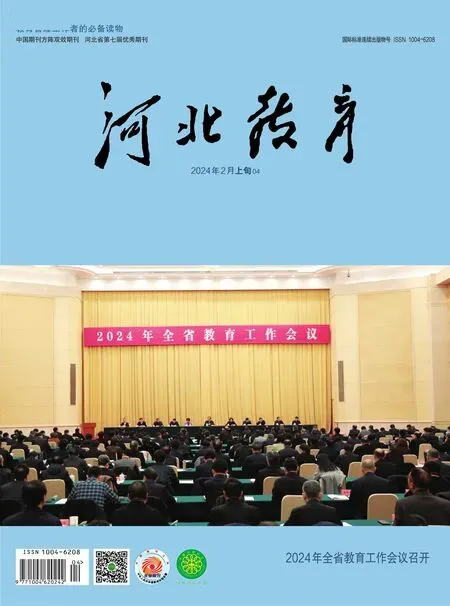用最初的心,走最長的路
——記河北省沙河市蟬房中心學校鄭平芳老師
○河北省沙河市渡口學校 鄭艾珺
從沙河市一路向西,穿越平原、丘陵后,就是一座座高聳的大山。一條公路環山蜿蜒西去,消失在群峰環繞的太行山深處。行駛60 公里,就到了蟬房中心學校。初冬的清晨,天氣微冷,教學樓里傳來陣陣悅耳的讀書聲,而在樓里的三尺講臺上,那雙充滿智慧的明眸正深情地凝視著朝氣蓬勃的莘莘學子。沿著她的視線看去,目光所及,仿佛觸摸到冬日的陽光,頓時令人倍感振奮和溫暖。
堅守歲月,培植希望
從1996 年師范畢業到今天,鄭平芳在沙河最西部深山區的蟬房學校,一待就是二十七年,她以為她的家在這里,父母在這里,根也在這里,這便是留在山里的意義,可后來,父母雙亡,兒女上了高中、大學,也在市里買了房子居住,可是她依然沒有走出那片大山,甚至有兩次,縣城最好的初中要直接抽調她去任教,她依然選擇了留下來。
山區的環境艱苦,冬天特別冷,滴水成冰,連廁所的沖水都會被凍住,夏天倒是不太熱,但是蚊子成群,這讓你都不敢輕易去涼爽的樹下待著,賺一身“包”太正常了。年輕老師來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最多的就是本鄉本土的部分老師留了下來。國家在硬件設備上對山區的投入很大,山里學校的教學設備也足夠滿足教學需要,唯獨優質的教師欠缺,難以實現均衡。加上鄉村家庭教育環境的落后和整個家長群體的文化素質不高,鄉村教育面臨著巨大的困境。還有越來越多的山里人在外打工顧生活,把孩子留給爺爺奶奶,留守兒童的人數增加,都給山區的教育帶來了更大的困難。2020 年,由于市區學校抽調教師,該校一共32 位教師調走了11 位,同時新初一招生前30 名學生也隨著轉到了市里學校。
鄭老師的心疼啊,她生在這片土地,長在這片土地,對這片土地、這一片土地上的人們都有著深厚的感情,那么多的孩子們,那些無力走出大山上學的孩子們,她們為什么就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山區落后貧瘠,難道要一輩輩的落后下去嗎?她改變不了缺少老師、走馬燈似的輪換的現狀,但是,總要做點什么,否則,于心怎安。她要留下來盡微薄之力,這里的孩子們需要她,她還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改變,讓這片土地上的下一輩人享受著山清水秀空氣好的同時也過上豐饒富足的生活。
于是她利用負責教務工作的職務便利,把影響、帶動、培養學校的教師向優秀靠攏作為一項重要教學工作來抓,利用“賽課”“磨課”“青藍工程”等各項活動促進教師的專業化成長。另外,她還充分利用課題的推動作用來幫助年輕教師迅速成長,2014 年以來,她先后主持參與了五項省市級課題,用課題研究來帶動教師與學生的共同成長。到目前為止,學校有8 名教師已成長為沙河市各名師工作室的骨干成員。用鄭老師的話說:“優秀老師都是培養出來的,咱們蟬房的老師以后無論走到哪兒,都不輸于人。”
師澤如光,微以致遠
臉龐瘦瘦、膚色黝黑的杰第一次引起鄭老師的關注是在元旦“包餃子”的活動上。
元旦集體包餃子是班里的家校活動之一。家長們帶了面,調好了餡兒,甚至還帶著案板、刀、搟面杖來陪孩子們過元旦。
“這是誰家小男孩兒呀,跑來跑去地忙著,煮好餃子卻怎么也不肯先吃,非等同學們都吃了他再吃……”在家長們此起彼伏的贊揚聲中,她看到了那個黑瘦的小男孩兒——杰!
夜幕降臨的時候,元旦晚會正式開幕了,杰帶來了一個朗誦節目——其實也不能叫作朗誦,他就是讀了讀自己寫的一篇普通的隨筆。他的文采顯然不好,但正像他不出眾的臉上掛滿了陽光一樣,格外吸引人。他那不夠通順的文章,因為真誠打動了在場所有的師生。原來杰的媽媽在前年冬天因為難產去世了,留下他與爸爸相依為命,過著艱難而清貧的日子。
讀著讀著,他的眼淚掉下來了,同學們、家長們的眼淚也不由自主地掉了下來,只見這個孩子將父親干活用的手套拿在手中向大家展示著——五個手指頭都有一個大洞的破手套。這是一封寫給爸爸的信,字里行間是對爸爸的感恩,對爸爸辛苦勞作的不忍,還有對逝去的媽媽深深的思念。

那一刻,她記住了這個黑瘦的小男孩兒,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呵護這個沒媽的孩子。
之后的學雷鋒活動中、感恩節演講比賽中、拔河比賽中……杰的身影都在眼前出現,這個13歲的孩子顯示了與年齡極其不符的成熟,言行之間處處透露著他美好的品質:勤勞、感恩、執著、善良。
他們之間的小互動多了起來,杰的成績不是太好,尤其是數學,幾乎很難跟上學習的節奏。他們開始一起讀書、補習,雖然最終杰的學習仍然跟不上,但他們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好,慢慢的杰有什么心事都開始跟老師說。“送給爸爸一雙運動鞋和將來考上高中以后去當兵”是他的兩個心愿。恰好上一周杰的作業被小組推選為優秀,那就把實現他的一個心愿作為獎品發給他吧。
當杰把鞋遞到爸爸手上的時候,那個樸實的莊稼漢結結巴巴地只說出兩個字——“謝謝”,可是那一刻,孩子眼中卻閃過欣喜的光芒。
提燈引路,育夢成光
濤同學高高的個子,魁梧的身材,大眼睛,濃眉毛,是一個英俊的小伙子,唯有走起路來卻一拐一拐的樣子,有點令人惋惜。初次見面,濤的眼神里有一點羞澀和回避,帶著最初的試探和不信任,鄭老師則在他閃爍的目光里看到了道遠且阻的責任。
每每就是這樣,越是想要做好一件事,越是不敢輕易地出手,就是怕這個開頭沒有開好,事與愿違。小心地觀察這個孩子,濤有一顆敏感又脆弱的小心靈。一方面“享受著”在這個班里特殊的待遇,一方面又在用自己的“小觸角”來感受判斷著外界一切人事對他特殊待遇的反饋,所以濤說話做事總是小心翼翼的,對老師說的話會很敏感,唯恐說話做事不對頭,這是如此脆弱,不敢讓人輕易觸碰的一顆心啊。
用什么樣的辦法才能靠近他呢?跑操和體育課的時候,濤獨自坐在教室里的孤獨身影,讓鄭老師找到了機會,也成就了他們共處的美妙時光。問題講題、小組管理探討、數學課堂管理甚至批改小組長作業、檢查周末作業等等,在這些時間里的忙碌,讓濤很享受,每次他都會非常主動的來找老師請示怎么做事、布置什么作業、什么時候檢查督促、如何督促學生完成等等,同時在這個過程里濤對數學有了特別的興趣,數學作業等也是超常地完成,濤開始一天天開朗陽光起來,和班里孩子也在一點點地打成一片,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于教育來說,教師要做的就是“全力培育,靜待花開”,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花期,尊重教育規律,才是教育的真諦。可是對這個孩子,鄭老師很難做到靜靜地等待,總希望濤能學得更好一些,面對這種特殊的情況,知識才是今后立足的力量。他的數學作業練習冊完成得都是最好的,可每次測驗的成績總是不理想,那么,必然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存在著問題。鄭老師曾經嘗試多次與他探討過如何把數學題做好的問題,也反復地試了很多的方法,有一點成效,但顯然并不理想。這孩子平時數學作業做得特別好,怎么一到考試就不行了呢?

一個暑假開學后,濤在數學學習上還是表現出了非常積極的態度,甚至比以前更熱情。他從以前的管好自己的學習到現在一直在關注著班里面其他學生的學習,雖然只是在數學課上。索性,讓濤當數學課代表。他當了課代表以后不但沒有覺得負擔重,反而是學習更積極了。從這時候開始,鄭老師的數學課后輔導、學生管理等問題就好像有了一位全職秘書似的,“秘書”會安排什么時間做什么講什么,學生們哪道題不會他都會反饋給老師。濤在這里找到了存在感、成就感、成功感,有了更大的學習動力。
有一次,在班里活動時,突然有位學生就冒出一句話:“我們數學課代表也就數學學得認真,其他的科目人家可是不在乎。”鄭老師聽到了,朝濤看過去,濤的臉紅了。于是鄭老師斬釘截鐵地說了一句:“我相信濤的其他學科也會像數學這樣的。”濤的臉上露出了釋然的表情,他最終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開始在別的學科上用心學習,順利升入了市里的高中。
臨近畢業的演講比賽中,濤和杰合作朗誦了一首原創作的詩歌——《感恩的心,感謝有你》。杰的詩是寫給他深深思念的媽媽,濤的詩是獻給他最愛的鄭老師。這首詩真摯地描述了他們的生活點滴,抒發了他們心中潛藏的蓬勃的感情,打動了所有老師和全校學生的心,因為真實,因為深愛,因為感恩。
在鄭老師二十七年的教學生涯里,她和許許多多孩子的故事每天都在這樣發生著,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個孩子又都不止一個故事。蘇霍姆林斯基說,沒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孩子。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活潑的、有著獨特故事的生命,尊重故事、創造故事、改變故事,就是鄭老師一生的堅守和熱愛。
鄭老師經常說:“每一個孩子都是一道獨特的風景。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跟這些孩子們在一起的日子里,總是被這些樸實的心靈教育著、影響著,他們時刻刷新著我對勤勞、善良、堅毅、執著的認知,這何嘗不是我的一場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