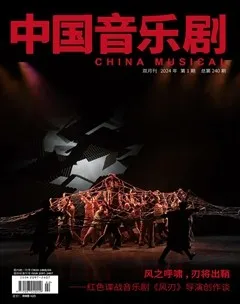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
龐夢雅



作為一部被譽為“真正具有中國氣魄的,并且可以走向世界的歌劇”,1995年,歌劇《蒼原》一經首演,便廣受贊譽,在全國各地上演百余場,先后獲“文化部文華大獎”、“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等多個獎項。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歌劇《蒼原》復排并在遼寧大劇院震撼上演,雖然筆者因故未能親臨現場,但2022年4月30日,筆者通過遼寧文化云平臺觀看了復排線上直播,并在一睹其藝術風采后,感受頗深、感慨頗多。通過此次觀演,筆者對復排版《蒼原》的藝術風格、舞臺演繹及場景設計方面有了一些認識與評價。
一、大氣磅礴的藝術風格
復排版《蒼原》由馮柏銘、黃維若編劇,徐占海、劉暉作曲,作為一部史詩性的正歌劇,其題材、創作、演繹均圍繞“雄渾、粗獷、宏大”的風格進行,在“均衡的高層次營造中極具藝術說服力地揭示了本劇的史詩氣概和悲壯情懷”。通過對復排版《蒼原》的觀看,筆者認為其大氣磅礴的史詩風格主要體現在題材、音樂、舞臺三個層面。
復排版《蒼原》的故事發生在250多年前,寄居在伏爾加河下游的土爾扈特族歷時七個月、歷經萬余里返回中國天山,該部族在東歸途中遭受沙俄的追殺和內部的分裂,領導東歸的渥巴錫和破壞東歸的艾培雷明爭暗斗,女主角娜仁高娃與英雄舍楞的愛情貫穿其中。從亞里士多德的戲劇觀來看,一部戲劇的成功之處體現在劇作家對情節的鋪陳、結構的布局,而其中“發現”和“突轉”則是劇作家創作一部成功作品的重要手法。在復排版《蒼原》中,“發現”和“突轉”被運用多次,構造出作品的戲劇感,也支撐其“逆境—順境—逆境—順境”的發展過程。艾培雷借娜仁高娃的身世,對其進行一番興風作浪的誘導,致使娜仁高娃意識到自己與渥巴錫之間的殺父之仇以及渥巴錫對自己的愛戀,這一“發現”使她刺傷渥巴錫,并離開部落;部族歷經千難萬險,舍楞從“叛徒”到英雄,部族已完成勝利會合,眼看要到達天山,但伊利總督對舍楞的追捕又使部族陷入兩難境地,這一出乎意料的“突轉”直接促成了娜仁高娃為勸說舍楞東歸而自殺。錯綜復雜的情節、愛恨糾葛的沖突,復排版《蒼原》宏偉壯闊的史詩性風格在曲折的戲劇發展中被一一呈現。
如美國音樂學家科爾曼所言,“音樂是歌劇中最根本的藝術媒介,它承擔著表達戲劇的最終職責”,復排版《蒼原》在音樂上共分為四幕,涉及詠嘆調、合唱、重唱、宣敘調等多種音樂形式,充分展現出土爾扈特族來自草原的英姿豪情。例如娜仁高娃的《情歌》,其旋律以不同形式出現三次,貫穿娜仁高娃與舍楞的愛情中,不斷將戲劇推向高潮,徐占海老師在創作中采用具有長調風格的蒙古民歌《四歲的海騮馬》作為旋律素材,抓住蒙古族音樂以短音開始后進入長音持續的特點,以此來構造音樂主題的綿延與悠長,并與唱詞“遼闊的草原”“蜿蜒的小河”“渴飲的馬”“悠長的牧歌”共同塑造娜仁高娃的鮮活形象,也將娜仁高娃對舍楞的深情展現得淋漓盡致。此外,200余人合唱隊人員的配置及多次展現合唱充分呈現出復排版《蒼原》的壯闊氣勢,徐占海老師在其中對復調手法的運用也進一步助力歌劇的戲劇性呈現,例如描繪東歸路途艱辛的《沙海茫茫》、與英雄舍楞會合的《燃燒吧,永生的火啊》等。總的來說,復排版《蒼原》在音樂創作上緊緊把握悲壯的史詩風格,展現出草原民族的豪邁氣勢。
除了音樂的詮釋外,戲劇中復雜情節的呈現也在歌劇舞臺上得到進一步強調。例如第一幕和尾聲中聲勢浩大的東歸部隊站滿整個舞臺,代表著土爾扈特族宗教信仰的喇嘛、手持兵器的士兵、身著民族服飾的族人以及歌劇的四位主角等依次上場,場面極為壯觀,此外還有第四幕娜仁高娃死后從天而降的白色哈達以及尾聲中呈現東歸途中犧牲族人鮮血的巨大的LED屏等都是在舞臺設計上對歌劇磅礴氣勢的呼應。從場景的戲劇設計到視覺呈現,隨處可見復排版《蒼原》史詩性的雄渾壯闊。
總的來說,復排版《蒼原》的“創”“排”“演”牢牢把握土爾扈特族聲勢浩大的東歸壯舉,從題材、音樂到舞臺深刻貫徹作品大氣磅礴的藝術風格。
二、扣人心弦的舞臺演繹
歌劇作品的最終呈現離不開舞臺的演繹,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舞臺藝術要“創造人的精神生活并通過舞臺藝術形式將這種生活反映出來”。復排版《蒼原》中,么紅老師及女聲合唱團對《情歌》的演繹就呈現出對娜仁高娃這一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該唱段在劇中依托詠嘆調、重唱及合唱的音樂形式呈現三次,演員在層層遞進的戲劇發展中完成舞臺的精彩演繹。
當“叛徒”舍楞被抓后,娜仁高娃第一次唱起詠嘆調《情歌》。詠嘆調是人物在特定情境中對內心情感的集中抒發,也是人物自我表達最直接的方式。舞臺上,么紅老師對《情歌》的演繹從氣息的控制、腔體的共鳴到附著哭腔的聲音塑造、悲痛柔弱的肢體表達,將蒙古長調式旋律的寬廣及悠長的節奏完美呈現出來,再加之管弦樂隊的烘托,共同構造起《情歌》的戲劇張力。當出走的娜仁高娃與歸來的英雄舍楞擦肩而過時,《情歌》旋律再次出現在兩人的愛情二重唱中。重唱為作曲家從“單一角色的戲劇行為和心理闡述轉向多角色的行為和心理的錯綜交織的發展”提供了實現的可能。這里,《情歌》被娜仁高娃的獨唱與女聲合唱交替演繹,構造了富有層次的空間感,舍楞對娜仁高娃的呼喊與柔美的女聲合唱形成一剛一柔的契合與平衡。么紅老師在此處的聲音表現較第一次更為堅毅,減少哭腔的修飾,強化了娜仁高娃對部族東歸的大愛。當娜仁高娃為部族東歸大業自殺后,《情歌》再次以合唱形式出現。合唱在以群體視角對作品進行豐富的同時,也貢獻著對戲劇發展的推動作用。第四幕中
《情歌》的女聲合唱就做到了對戲劇氛圍的渲染、場景色彩的描繪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首先女聲獨唱呈現主旋律,后在副歌中聲部以遞增式進入,織體越發豐滿,女聲合唱團將《情歌》展現得空靈、莊嚴,塑造出娜仁高娃的圣潔形象。舞臺上一條白色的哈達從天而降,落在死去的娜仁高娃身上,族人在白色煙霧的圍繞中,手捧哈達緩緩走向死去的娜仁高娃,整個舞臺充滿蒙古式的圣潔與莊重。
另觀復排版《蒼原》中其他角色的演繹也可圈可點,例如車英老師將渥巴錫英姿颯爽的出場、捉拿“叛徒”舍楞的堅定、面對娜仁高娃質問時的鐵漢柔情及對逝去族人的深情緬懷演繹得淋漓盡致;飾演舍楞的王澤南老師以男高音明亮的音色,將年輕英雄舍楞的朝氣鮮活地呈現出來;而同樣作為男高音的張元君老師通過舞臺上的來回踱步、俯身表達等身體語言呈現艾培雷對東歸的“破壞”的計謀等。
總的來說,復排版《蒼原》的舞臺演繹是極為成功的,幾位主演將“唱”與“演”完美結合,深入挖掘作品立意,出色地呈現了史詩歌劇的雄渾壯闊。
三、獨具匠心的場景設計
歌劇作為一門綜合性藝術,除演員對舞臺的演繹外,導演對舞臺場景的設計也是歌劇的戲劇氛圍及表達中不可忽視的部分。曹其敬導演在復排版《蒼原》的場景設計中深入對土爾扈特族文化的挖掘,使舞臺成為與作品本身高度融合的成功范例。
復排版《蒼原》的多個場景中,喇嘛被搬上舞臺,雖然他們在表演中未發一聲,卻實現了對土爾扈特族宗教信仰的文化表達。“喇嘛”是對藏傳佛教僧侶的尊稱,其在土爾扈特族中有著重要地位,也在其東歸大業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喇嘛在歌劇中共出現四次,第一次出現在序幕的合唱“歸來啊”,舞臺上喇嘛們面對土爾扈特族人而坐,直到族人對“歸來啊”的呼喊結束,喇嘛們起身下場,接著便開始義憤填膺地合唱“我們恨你,葉卡捷琳娜”。結合音樂與舞臺的呈現,導演展示了佛教對土爾扈特族的意義——和平與祈禱。喇嘛第二次出現在第一幕的進場中,聲勢浩大的東歸部隊走上舞臺,先由兩名手持矛的士兵走在前列,接著喇嘛們列隊而行,其后兩名士兵抬著觀音菩薩像上場,所有喇嘛轉身朝向觀音菩薩像,大喇嘛進行朝圣跪拜(磕長頭)。在其之后,渥巴錫、舍楞、娜仁高娃及其他大臺吉上臺,最后士兵、族人跟隨行進。從導演對東歸部隊的展示可以看出喇嘛在土爾扈特部族中的重要地位,其代表著對部族的指引和護佑。喇嘛第三次出現在第四幕,娜仁高娃死后,族人對她進行祭拜,這里僅有一個喇嘛上場,位于舞臺中央,面對著死去的娜仁高娃與族人一同跪拜。跪拜禮是清朝極為盛行的一種規范性禮節,喇嘛與族人共行的跪拜禮也暗喻著土爾扈特族對天山的回歸。喇嘛第四次再次出現于尾聲合唱《我們回來了,母親》,這里與第一幕東歸部隊的展示相呼應,但其中沒有了手持矛的士兵開路,也沒有了喇嘛的朝圣跪拜,場景傳達出戰斗的結束,東歸的完成。綜上所述,喇嘛這一對土爾扈特族有著重要意義的群體被貫穿戲劇發展中,在與戲劇發展呼應的同時,也豐富了部族的形象塑造。
關于舞臺的場景設計,居其宏老師曾說過,要將“藝術構思和設計思想化為具體的、實在的視覺和聽覺形象,并把它們組合起來,按照歌劇表現內容的需要塑造出一個個特定的戲劇空間和戲劇氛圍,為歌劇人物的活動和戲劇沖突的展開提供不斷變化的環境與背景”。因此,導演在場景設計中不僅要有把握大局的宏觀視角,還需要對舞臺的各個細節進行“斟字酌句”,在綜合性上力求盡善盡美,這是歌劇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四、結語
復排版《蒼原》是極為成功的,其大氣磅礴的藝術風格、扣人心弦的舞臺演繹和獨具匠心的場景設計都準確呈現出作曲家創作中對作品雄渾壯闊風格的核心立意。音樂上,以娜仁高娃的詠嘆調《情歌》、舍楞的詠嘆調《讓我化作泥塵》、合唱《沙海茫茫》及重唱《月光是這樣清涼》等核心唱段來演繹東歸途中的愛恨糾葛,舞臺上,藏傳佛教的喇嘛、蒙古圣潔的哈達等極具土爾扈特族特色的元素融入歌劇表達。復排版《蒼原》對題材立意風格的準確把握也正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刻認同與呼應,正所謂“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復排仍由遼寧歌劇院完成,其作為歌劇《蒼原》最好的詮釋者,準確把握住了其中雄渾磅礴的史詩特質。以筆者看來,本次對《蒼原》的成功復排不僅在于作品技術創作、演員演繹及導演統籌的完美配合,更深層的原因應追溯至作曲者及遼寧歌劇院本身對魯藝精神的承載。魯藝精神伴隨1938年延安魯藝成立至今,已走過85年的歷程,其凸顯民族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創作理念深深烙印于復排版《蒼原》之中。而作為魯藝傳承人的徐占海老師在復排版《蒼原》的音樂創作中也始終秉持西體歌劇中國化的原則,聚焦“借西方歌劇之體,話中國故事之神”的創作期待,最終打造出“符合中國觀眾審美情趣的中國史詩性大歌劇體裁形式”,這不僅彰顯了雄渾壯闊的中華正氣,也實現了對魯藝精神的完美呈現。再觀遼寧歌劇院的排演,其正是做到對歌劇核心立意的深刻挖掘,才完成對復排版《蒼原》的成功詮釋,這是生長于魯藝精神土地上的自覺解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一部優秀文藝作品的創作要反映時代呼聲,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回答時代課題,唯有包含對時代精神的深刻體現,才能創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2023年正值沈陽音樂學院成立85周年,筆者謹以對復排版《蒼原》的再思、再感來致敬老一輩音樂家為中國音樂發展所作的重大貢獻,期許能有更多《蒼原》式的中國歌劇問世,也期許青年學子能繼續傳承和發揚魯藝精神,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歌劇道路。
(作者單位:沈陽音樂學院)
參考文獻:
[1]居其宏.史詩氣概 悲壯情懷——大型歌劇《蒼原》觀后[J].人民音樂,1997(0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