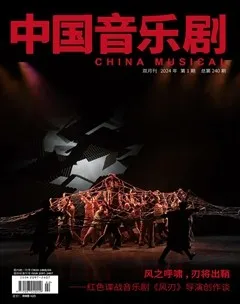傳承與創(chuàng)新: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演變與發(fā)展
馮欣



摘要:絲綢之路不僅是古代東西方文化傳播的關(guān)鍵路徑,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互動(dòng)的重要紐帶,它不僅推動(dòng)了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增長(zhǎng),也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shí),由于歷史上各民族間相互交往頻繁,各國(guó)人民之間形成了深厚的友誼和聯(lián)系。在古代中國(guó)音樂(lè)歷史進(jìn)程中,絲綢之路的誕生與壯大對(duì)音樂(lè)的演變與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深遠(yuǎn)影響。古絲綢之路為中國(guó)音樂(lè)的多樣性創(chuàng)造了有利環(huán)境,伴隨著絲綢之路的日益暢通,來(lái)自中亞、西亞、印度等地區(qū)的藝術(shù)家和商業(yè)人士紛紛帶來(lái)了他們的音樂(lè)作品和樂(lè)器,這些外來(lái)的藝術(shù)文化也給當(dāng)時(shí)的音樂(lè)注入了活力,這批音樂(lè)和樂(lè)器與中國(guó)的傳統(tǒng)音樂(lè)相結(jié)合,創(chuàng)造出了獨(dú)特的音樂(lè)形態(tài)和風(fēng)格,進(jìn)一步豐富了我國(guó)音樂(lè)中的樂(lè)器和樂(lè)曲種類(lèi)。
關(guān)鍵詞:傳承與創(chuàng)新;絲綢之路;音樂(lè)演變;發(fā)展
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具有多樣化特點(diǎn),需要關(guān)注和積極傳承。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代表著我國(guó)音樂(lè)發(fā)展的一個(gè)重要階段,確定了當(dāng)代音樂(lè)發(fā)展的方向和深度。音樂(lè)是我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種精神物質(zhì)、精神寄托,研究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對(duì)提高我們的生活質(zhì)量、促進(jìn)社會(huì)的發(fā)展有著重要價(jià)值和作用。音樂(lè)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反映了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各個(gè)民族以及各個(gè)地域的長(zhǎng)久社會(huì)文化積累,這些積累在相對(duì)性、穩(wěn)定性以及整合性上都展現(xiàn)出明顯的特征。所以,對(duì)絲路音樂(lè)進(jìn)行研究時(shí),不能僅僅局限于某一種音樂(lè)風(fēng)格或體裁的分析上,而是應(yīng)綜合多種因素來(lái)探討其產(chǎn)生、發(fā)展及演變過(guò)程中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所以說(shuō),深入研究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需要得到社會(huì)各界的重視并落實(shí)在研究實(shí)踐中,以進(jìn)一步揭示音樂(lè)固有形態(tài)的穩(wěn)定性,促進(jìn)絲路音樂(lè)與外部音樂(lè)的融合與發(fā)展。
一、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分析
對(duì)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探索象征著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dòng)下,音樂(lè)藝術(shù)的深度演變與進(jìn)步,這也構(gòu)成了當(dāng)前全球經(jīng)濟(jì)與文化互動(dòng)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音樂(lè)作為一種重要的載體,其地位得到了進(jìn)一步提升。東漢時(shí)期,張騫被派往西域,正式開(kāi)啟了陸上絲綢之路。這條路線從中國(guó)古代的洛陽(yáng)開(kāi)始,途徑長(zhǎng)安(現(xiàn)今的西安),經(jīng)過(guò)河西走廊,最終到達(dá)中亞的多個(gè)國(guó)家,這也就是現(xiàn)在我們所說(shuō)的陸路絲路。這條道路被視為古代東西方文明在亞歐大陸交匯的重要通道,成為東西方在經(jīng)濟(jì)、政治和文化等多個(gè)領(lǐng)域進(jìn)行交流的核心路徑。音樂(lè)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載體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其發(fā)展歷史可以追溯到遠(yuǎn)古時(shí)期,隨著人類(lèi)社會(huì)的不斷變遷,音樂(lè)也逐漸形成自身獨(dú)特的魅力,成為各國(guó)人民之間相互交流、建立友誼的紐帶。音樂(lè)作為東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絲綢之路上已有數(shù)千年的交流歷史。
二、絲綢之路上音樂(lè)演變和發(fā)展的意義
絲綢之路為中國(guó)音樂(lè)的技術(shù)進(jìn)步和理論創(chuàng)新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這一歷史過(guò)程中,東西方文化不斷交融碰撞。來(lái)自中亞和西亞的眾多音樂(lè)家與音樂(lè)研究者訪問(wèn)了中國(guó),與本土音樂(lè)家進(jìn)行了深入的交流與研討,其中不乏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教育家。他們向中國(guó)展示了一些創(chuàng)新的音樂(lè)理念和技巧,例如吉他和固定音程(也稱(chēng)為定弦法)等。此外,他們還對(duì)傳統(tǒng)樂(lè)舞中的吹打樂(lè)、彈撥樂(lè)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引入這些創(chuàng)新的理論和技術(shù)手段,不僅能夠豐富音樂(lè)的表達(dá)方式和技藝,也能夠促進(jìn)中國(guó)音樂(lè)器樂(lè)表演和理論研究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
絲綢之路的出現(xiàn)加強(qiáng)了中國(guó)音樂(lè)與全球音樂(lè)之間的互動(dòng)與整合,絲綢之路為中國(guó)與中亞、西亞、印度等地區(qū)的音樂(lè)家和音樂(lè)文化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交流互鑒的平臺(tái),他們之間的相互學(xué)習(xí)使不同國(guó)家的人民能夠共享音樂(lè)文明,這對(duì)我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舉例來(lái)說(shuō),當(dāng)中國(guó)的藝術(shù)家和音樂(lè)家經(jīng)由絲綢之路訪問(wèn)中亞和西亞時(shí),他們帶著自己獨(dú)特的音樂(lè)和表演風(fēng)格來(lái)到那里,進(jìn)一步推廣了中國(guó)的音樂(lè)文化。在此過(guò)程中,他們也吸取了其他音樂(lè)的風(fēng)格和獨(dú)特性,這對(duì)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的演變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絲綢之路為中國(guó)音樂(lè)的傳承和保護(hù)創(chuàng)造了寶貴的機(jī)遇與舞臺(tái),長(zhǎng)久以來(lái),絲綢之路的存在和廣泛的文化交流為中國(guó)音樂(lè)提供了更多的機(jī)會(huì)進(jìn)行記錄和保存。在這一過(guò)程中,不同地域、民族以及國(guó)家之間相互借鑒和影響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眾多音樂(lè)家和藝術(shù)家在絲綢之路上的游歷和互動(dòng)中,留下了豐富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和表演技藝,并成功地將其傳承到了全球各個(gè)角落。
三、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演變與發(fā)展
(一)對(duì)絲綢之路上音樂(lè)的理解
絲綢之路是西方、阿拉伯、東方和古印度文明的交融之地,其音樂(lè)文化也正是這些文明相互影響的結(jié)果。在古代,東西方各民族都曾創(chuàng)造過(guò)燦爛而輝煌的古代文明,并以各自獨(dú)特的方式傳承古老的音樂(lè)藝術(shù)。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各個(gè)國(guó)家中,他們的傳統(tǒng)音樂(lè)并非固定不變,而是經(jīng)歷了多次轉(zhuǎn)變和融合,這不只是對(duì)其原有的文化結(jié)構(gòu)的合理化調(diào)整,更是一個(gè)逐步邁向“現(xiàn)代化”的過(guò)程。而對(duì)于這個(gè)被稱(chēng)為“現(xiàn)代化”的過(guò)程來(lái)說(shuō),與各個(gè)歷史階段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背景以及絲綢之路的交通情況有著緊密聯(lián)系。只要絲綢之路暢通無(wú)阻,音樂(lè)和文化的交流就會(huì)變得更加活躍,不同文明之間的音樂(lè)互動(dòng)也會(huì)持續(xù)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絲路中斷或斷航,音樂(lè)文化交流就會(huì)相對(duì)緩慢,甚至出現(xiàn)停滯狀態(tài)。盡管絲綢之路的斷裂對(duì)音樂(lè)文化的交流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對(duì)不同音樂(lè)事件的吸納、沉淀、潤(rùn)化,最終它會(huì)回饋給其文化中的音樂(lè)傳統(tǒng)。
(二)深化音樂(lè)史
絲綢之路上音樂(lè)的發(fā)展和變遷不僅是藝術(shù)研究的基礎(chǔ)工具,也是社會(huì)文化研究的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具有極高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作為一種文化交流形式,它不僅促進(jìn)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與溝通,而且為不同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人們提供著各種娛樂(lè)方式。毫無(wú)疑問(wèn),對(duì)于音樂(lè)歷史的探索,中西方音樂(lè)的交融歷程是一個(gè)必須考慮的關(guān)鍵點(diǎn),并且它對(duì)于理解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由于絲綢之路是中西方音樂(lè)溝通的主干線,因此對(duì)于這條線的音樂(lè)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在中國(guó)音樂(lè)的演變過(guò)程中,西方音樂(lè)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這種影響表現(xiàn)在樂(lè)曲的形式、內(nèi)容、演奏技巧等方面,而在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東西方音樂(lè)風(fēng)格和樣式的差異與交融。
(三))傳承傳統(tǒng)文化和落實(shí)文化交流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我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都有了顯著發(fā)展,社會(huì)的開(kāi)放程度也在持續(xù)增長(zhǎng)。社會(huì)的快速進(jìn)步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也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存在和發(fā)展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比如,歐美、日韓等國(guó)家流行音樂(lè)的大量涌入,導(dǎo)致我國(guó)年輕人對(duì)傳統(tǒng)音樂(lè)的熱情逐步降低,許多傳統(tǒng)音樂(lè)甚至面臨失傳的風(fēng)險(xiǎn)。面對(duì)這種情況,必須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來(lái)應(yīng)對(duì)這一問(wèn)題,尤其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促進(jìn)我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成為當(dāng)下一個(gè)值得深思的話題。顯然,這與目前對(duì)傳統(tǒng)音樂(lè)的研究、保護(hù)和傳播的不足有著緊密聯(lián)系。因此,如何更好地保護(hù)并傳播優(yōu)秀的民族傳統(tǒng)音樂(lè)成為當(dāng)下亟須解決的問(wèn)題。當(dāng)前,音樂(lè)研究的重點(diǎn)放在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文化與音樂(lè)交流方面,這為我們進(jìn)一步理解古代音樂(lè)文化產(chǎn)生了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它不僅是維護(hù)并延續(xù)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構(gòu)成了絲綢之路音樂(lè)研究的主要價(jià)值所在。
在當(dāng)前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互動(dòng)成為一個(gè)核心議題,它對(duì)于經(jīng)濟(jì)的共同繁榮和地緣政治的穩(wěn)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為文化傳播手段之一的音樂(lè)學(xué)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促進(jìn)人們之間的相互了解。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是以絲綢之路作為其傳播載體的,這條絲綢之路從西安開(kāi)始,一直延伸到歐洲,全長(zhǎng)超過(guò)七千公里。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研究有助于加強(qiáng)絲路周邊國(guó)家和地區(qū)之間的交流和互動(dòng)。例如,在研究琵琶樂(lè)器的起源時(shí),伊朗、印度和中國(guó)的音樂(lè)學(xué)者都應(yīng)該參與進(jìn)來(lái),深入探討琵琶的起源、發(fā)展和變遷。總體來(lái)說(shuō),絲綢之路的音樂(lè)對(duì)于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應(yīng)該大力弘揚(yáng)。
(四)絲綢之路上音樂(lè)的傳承和發(fā)展
唐代的音樂(lè)和舞蹈豐富多彩是眾所周知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今天我們無(wú)法聽(tīng)到唐代或更早時(shí)期的音樂(lè)和聲音。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人們似乎忘記了那些曾經(jīng)伴隨著唐代音樂(lè)發(fā)展而出現(xiàn)過(guò)的各種不同類(lèi)型的樂(lè)舞形式和風(fēng)格流派,也忘記了它們之間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中國(guó)的音樂(lè)史被戲稱(chēng)為“啞巴”音樂(lè)史,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樂(lè)舞表演也就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變得更加神秘而又遙遠(yuǎn)。盡管如此,目前許多被叫作“絲路”“敦煌”“漢唐樂(lè)府”等具有絲綢之路特征的復(fù)古音樂(lè)以及舞蹈的商業(yè)表演一般是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并不是為了傳承和發(fā)展復(fù)古樂(lè)舞,所以這種形式的演出大多表現(xiàn)出缺乏歷史感、功利化傾向嚴(yán)重等問(wèn)題。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lái),我國(guó)專(zhuān)門(mén)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團(tuán)體產(chǎn)生了許多注重歷史研究的獨(dú)特藝術(shù)成果。他們或以自己對(duì)歷史文化和傳統(tǒng)音樂(lè)藝術(shù)的深刻理解為基礎(chǔ),或?qū)F(xiàn)代作曲技法融入其中。比如,譚盾在他的絲綢之路音樂(l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一直堅(jiān)定一個(gè)信念,那就是深入挖掘中國(guó)古樂(lè)譜中所具備的深遠(yuǎn)意義,并探究其中所體現(xiàn)的歷史價(jià)值。葉國(guó)輝的交響樂(lè)《唐朝傳來(lái)的音樂(lè)》嘗試從唐樂(lè)《酒胡子》中重新找回古樂(lè)的活力。這些作品既體現(xiàn)出作曲家對(duì)古代音樂(lè)文化的重視和探索精神,也反映出時(shí)下人們對(duì)于傳統(tǒng)藝術(shù)傳承方式的反思及對(duì)當(dāng)下音樂(lè)發(fā)展方向的關(guān)注。
觀察絲綢之路音樂(lè)的發(fā)展歷程,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中國(guó)特有的音樂(lè)時(shí)代,從遠(yuǎn)古、夏商一直到秦漢;漢唐時(shí)代是多元音樂(lè)交融的時(shí)代;從宋代到明清,這是民族文化的鼎盛時(shí)期;從明末清初到當(dāng)代,世界音樂(lè)經(jīng)歷了四個(gè)主要的發(fā)展階段。每個(gè)階段又有不同的特點(diǎn)和表現(xiàn)方式。在其中的第二階段,由于張騫出使西域,成功地開(kāi)辟了絲綢之路,并成功地引入了外國(guó)文化,為我國(guó)的民族音樂(lè)文化發(fā)展打下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第三個(gè)階段為隋唐五代時(shí)期,這是一個(gè)承前啟后、繼往開(kāi)來(lái)的歷史大變革時(shí)期,為中國(guó)古代文化貢獻(xiàn)了一篇豐富多彩的樂(lè)章。
絲綢之路以河西走廊作為主要的貿(mào)易路線,由于該地區(qū)是東西方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之樞紐。因此,在此形成了一個(gè)龐大的文化圈。如印度和波斯這樣的外國(guó)文化通過(guò)佛教這一媒介,持續(xù)不斷地傳入中國(guó),進(jìn)一步催生了隋唐燕樂(lè)的二十八調(diào)和雅樂(lè)的八十四調(diào)理論,這些理論已經(jīng)成為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理論的核心部分,并且在唐代得到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使其不僅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duì)后世的音樂(lè)藝術(shù)發(fā)展亦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在我國(guó)的周代散樂(lè)時(shí)代,印度系的百戲藝術(shù)對(duì)其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逐步塑造出了獨(dú)特的中國(guó)表演風(fēng)格。
許多外國(guó)音樂(lè)通過(guò)絲綢之路,大范圍、群體性地流向中原地區(qū)。起初,西域的五種樂(lè)器,即天竺樂(lè)、蘇勒樂(lè)、龜茲樂(lè)、安國(guó)樂(lè)以及康國(guó)樂(lè),對(duì)中國(guó)的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南北朝時(shí)期,這些音樂(lè)開(kāi)始在闐(和田)、龜茲以及高昌(吐魯番)三個(gè)文化中心匯聚,并逐漸向中原地區(qū)的東部擴(kuò)展。隋唐時(shí)期,胡樂(lè)發(fā)展到頂峰,其規(guī)模之大、音樂(lè)之盛、表演之繁為歷史上其他朝代難以企及,這一時(shí)期出現(xiàn)的音樂(lè)內(nèi)容豐富而又具有鮮明的時(shí)代特征。到了唐代,創(chuàng)作了《燕樂(lè)》,并將其擴(kuò)充為“十部樂(lè)”作品,已經(jīng)形成一個(gè)比較系統(tǒng)的音樂(lè)體系。8世紀(jì)的唐朝,以空前繁榮的局面和政治穩(wěn)定為基礎(chǔ),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而成為當(dāng)時(shí)世界上最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之一。唐王朝在繼承前代的基礎(chǔ)之上,又吸收了外來(lái)的先進(jìn)思想和技術(shù),自那一刻開(kāi)始,唐朝的文化對(duì)東亞的朝鮮、日本以及越南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并由此塑造了東亞的漢字文化氛圍。
自20世紀(jì)起,尋找和恢復(fù)古代歷史遺音成為一個(gè)受到廣泛關(guān)注的研究課題。學(xué)者們正在努力從現(xiàn)存的石窟群中,或者通過(guò)大量與音樂(lè)相關(guān)的壁畫(huà)、浮雕和古譜歷史資料中,來(lái)尋找和恢復(fù)神秘的絲綢之路音樂(lè)。絲綢之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gè)充滿魅力的音樂(lè)領(lǐng)域,而傳承下來(lái)的樂(lè)譜成為我們尋找和恢復(fù)古代音樂(lè)遺跡的重要工具。對(duì)古代樂(lè)譜的解讀在重塑唐代的音樂(lè)舞蹈和重新定義我國(guó)古代音樂(lè)的“無(wú)聲化”方面具有深遠(yuǎn)的歷史影響。從出土實(shí)物來(lái)看,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存在大量以人聲為主的古樂(lè)遺存。然而,對(duì)于樂(lè)舞的恢復(fù),我們還需要對(duì)古代樂(lè)器的再現(xiàn)、樂(lè)舞和服飾進(jìn)行深入了解,以及對(duì)歷史審美趣味的重新評(píng)估提出更為嚴(yán)格的標(biāo)準(zhǔn)。盡管歷史為我們留下了燦爛的痕跡,但要重新展現(xiàn)它的真實(shí)面貌,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努力。總體來(lái)說(shuō),在歷史長(zhǎng)河中,東西亞與亞歐大陸通過(guò)絲綢之路,在眾多國(guó)家的音樂(lè)文化領(lǐng)域中建立了緊密聯(lián)系,互相學(xué)習(xí)和借鑒,這不僅豐富了各自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還提升了其音樂(lè)藝術(shù)水平,為全球音樂(lè)文化的進(jìn)步做出了卓越貢獻(xiàn)。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絲綢之路在中國(guó)音樂(lè)歷史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它不僅豐富了古代中國(guó)音樂(lè)的樂(lè)器選擇、旋律和演奏手法,還推動(dòng)了中國(guó)音樂(lè)的多元化和發(fā)展進(jìn)步。絲綢之路作為商業(yè)和旅游的重要通道,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許多西方的音樂(lè)和樂(lè)器正是通過(guò)這條路線傳入中國(guó),并在中國(guó)的音樂(lè)文化中占據(jù)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也使許多具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的民族音樂(lè)形成新的風(fēng)格流派和藝術(shù)形式。總之,絲綢之路為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與中亞、西亞、印度等地區(qū)進(jìn)行音樂(lè)文化交融和交流的平臺(tái),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中國(guó)音樂(lè)與全球音樂(lè)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交流。
(作者為曲阜師范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xiàn):
[1] 管建華.音樂(lè)人類(lèi)學(xué)導(dǎo)引[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2]王光祈.中國(guó)音樂(lè)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3]方雪揚(yáng).新史料、新研究與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的重建[J].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音樂(lè)與表演版),2023(4):31-35.[4]程金城,馬碩.藝術(shù)表達(dá)在絲綢之路文化中的獨(dú)特價(jià)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9(04):55-59.[5]孔德民.絲綢之路上的音樂(lè)文化——陜西省墓室壁畫(huà)實(shí)地考察研究報(bào)告[J].當(dāng)代音樂(lè),2021(4):64-71. [6]馮喜超.為中國(guó)音樂(lè)一辯的葉伯和《中國(guó)音樂(lè)史》——從蘭茨貝格的《中國(guó)音樂(lè)之外論》說(shuō)起[J].音樂(lè)藝術(shù),2023(2):110-118.[7]夏雄軍,張雅萌.漢唐之際的中西音樂(lè)交流[J].中州學(xué)刊,2022(9):129-135.[8]肖堯軒,陳怡,滕瑩.新疆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帶核心區(qū)高校音樂(lè)美育建設(shè)路徑探索[J].藝術(shù)教育,2022(5):65-68.
[9]盛文標(biāo).北齊宮廷音樂(lè)“胡化”淵源論及對(duì)隋唐宮廷音樂(lè)的影響[J].藝術(shù)評(píng)鑒,2023(15):87-92.
[10] 關(guān)冰陽(yáng).談“鼓”論“樂(lè)”——第27屆國(guó)際傳統(tǒng)音樂(lè)學(xué)會(huì)(ICTM)專(zhuān)題研討會(huì)“絲綢之路上的與鼓樂(lè)”述評(píng)[J].人民音樂(lè),2021(4):82-85.
[11]姜國(guó)峰.漢代絲綢之路文化生成與傳播的歷史鏡像[J].鄭州輕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2):91-98.[12]周菁葆.絲綢之路上伊拉克古典音樂(lè)木卡姆的樂(lè)器(上)[J].樂(lè)器,2023(10):24-26.[13]許國(guó)紅.從“海上絲綢之路”看福建南音樂(lè)器的融合與傳播[J].集美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2):8-20.[14]葉春.我國(guó)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音樂(lè)傳播的形態(tài)變遷與文化根基[J].藝術(shù)探索,2020(1):1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