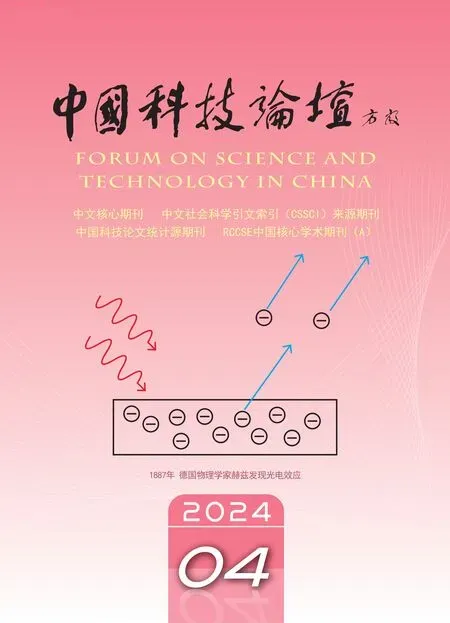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的脫鉤與反脫鉤:來自中國制造業企業微觀數據的經驗證據
郭萬山,滕 飛,侯翔瀚,李科霖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0 引言
早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不久,美國國內就針對中國可能的崛起開始鼓吹“中國威脅論”。Thayer[1]在 《對抗中國:美國選擇的評估》一文中提出,美國選擇什么樣的政策,將對其在世界的安全和霸權地位產生深遠影響,美國必須做好與中國對抗的準備。反觀美國當今的對華政策,現實也確實如此。無論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和制裁策略,還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對中國的圍堵,迫使中國企業與全球價值鏈脫鉤,無不體現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的霸凌心態。中美貿易戰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和擔憂。盡管沒有哪個國家相信美國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崛起,但中美貿易戰對全球價值鏈的沖擊卻是顯而易見的,世界經濟正從 “超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向 “慢全球化” (slowbalization)轉變[2]。美國的價值鏈脫鉤策略是一把雙刃劍[3],在遏制中國企業創新的同時,也會激發中國企業自主創新的內在動力。遏制與激發效應孰強孰弱,這不僅關系到中美雙方的博弈勝負,也關系到中美兩國未來對全球價值鏈的控制權和影響力。脫鉤策略的疊加效應會對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造成怎樣的影響仍有待考察和經驗驗證。
遏制與激發具有相互抵消的作用,兩種效應的疊加構成脫鉤策略的總效應。本文選擇Koopman等[4]提出的價值鏈地位指數和Antràs等[5]提出的上游度指數衡量脫鉤策略效應。價值鏈地位指數用于表征一國部門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上、下游地位[4]。該指數值越大,表明該國部門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越上游,對價值鏈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就越強[6]。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憑借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和對核心技術的壟斷而處于價值鏈的高端;相反,中國、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處于劣勢,需要依靠進口大量的中間投入品參與全球價值鏈活動,因此,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7]。
Antràs等[5]提出的上游度指數被定義為一個產業部門生產的產品到最終使用的平均距離。經驗研究表明:上游度越高,產業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地位就越低端[8]。Fally[9]發現,在制造業內部,上游度與技術密集度負相關。該發現揭示了上游度與產業技術密集度間存在的內在的關聯關系。
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和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微觀數據,以及基于WIOD和亞行的世界投入產出表數據計算得到價值鏈地位指數和上游度指數,研究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企業創新產生的遏制與激發的疊加效應及其對價值鏈地位的攀升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此外,本文還研究了R&D和FDI對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所起的作用。R&D是技術和知識的主要源泉[10],為企業價值鏈地位攀升提供了主要源動力。FDI可以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促使東道國的技術水平、組織效率不斷提高,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的綜合要素生產率[11],促進價值鏈地位的升級[12]。
與以往的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體現在:①本文基于制造業企業微觀數據,研究了美國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創新內生動力的激發作用,并發現激發效應大于遏制效應,給出了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企業技術水平攀升的經驗證據。②脫鉤策略對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疊加效應顯著為正,與產業上游度負相關,表明美國的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和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③發現國內企業自主創新存在 “低質低效”的雙低現象,降低了價值鏈地位攀升的效率;中美貿易摩擦并不會減少FDI流向中國。雖然FDI對產業價值鏈地位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但與Antràs等[5]的上游度指數正向相關,對產業技術水平攀升存在抑制作用。
1 理論背景:全球價值鏈的控制權與中美貿易沖突的本質
1.1 價值鏈的比較優勢互補:中美蜜月期 (2001—2008年)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中關系處于 “合作>競爭”的蜜月期[13]。這得益于兩國全球價值鏈中的比較優勢具有互補性,即美國擁有雄厚的資本、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相關知識、知識產權和技術優勢,而中國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但卻面臨資金、技術和全球價值鏈治理專業知識的短缺[14-15]。為了獲得中國廉價勞動力資源,美國開始將低附加值的制造、組裝環節向中國轉移。作為向美國開放市場的交換,中國獲得了就業機會、資本、技術和進入海外市場的機會。同時,大量廉價中國制造產品滿足了美國巨大的消費欲望[2]。比較優勢的互補性造就了 “中美經濟共同體”式的共生關系。
1.2 后發企業快速追趕:中美摩擦期 (2009—2017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開始進入中美貿易摩擦期。制造業轉移導致美國制造業出現 “空心化”現象[16],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減少,就業壓力加劇,實際工資停滯不前[17]。越來越多的美國媒體、學界和政界人士認為, “中國制造”的產品奪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18]。相反,中國利用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機會,實現了人力資本、資金和市場優勢的積累[2]。一大批后發企業迅速崛起,進入快速追趕階段[19]。以華為為代表的高技術企業正逐漸從追趕向超越甚至創新前沿挺進[20]。中美對全球價值鏈的控制和影響開始出現重疊,并逐漸產生摩擦。中美關系開始從 “合作>競爭”向 “競爭>合作”轉變[13]。這也引起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崛起的警覺,并制定了 “亞洲再平衡”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TPP)等政策[2]。
1.3 后發企業崛起:中美沖突期 (2018年至今)
競爭越激烈,國家就越注重尋求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21]。盡管中國一再重申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中美關系不是零和游戲,而是合作共贏[22],然而,美國更看重對全球價值鏈的控制權和主導地位[23],并將中國視為真正的威脅[2]。無論是特朗普政府發起的中美貿易戰,以及對中國高技術企業的制裁,還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對中國微電子領域的圍堵,均表明中美關系開始進入 “沖突>競爭>合作”的第三個階段。維護美國全球價值鏈的控制權和霸權地位是美國設定的與中國合作的前提和基礎[23],美國并不接受中美合作共贏的主張[24]。然而,中國對全球價值鏈的控制力或影響力的增強,得益于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多邊合作[25]以及后發企業優勢[26],并非美國所賜。雖然沒有哪個國家相信美國對中國的圍堵策略能夠奏效,但美國的脫鉤策略對中國后發企業的自主創新所產生的遏制和激發效應孰強孰弱仍有待于實證考察,如何跨越美國的脫鉤策略屏障,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和影響力,是中國贏得中美博弈的關鍵性問題。
2 變量、數據與模型
2.1 變量定義及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二值選擇變量decoupling來定義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采取的脫鉤策略行為。若i產業在時間t有中國企業受到美國制裁,則在此后時期decouplingit=1。否則,decouplingit=0。
本文使用Koopman等[4]提出的價值鏈地位指數和Antràs等[5]的上游度指數衡量美國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所造成的影響。
價值鏈地位指數 (GVC_Position)數值越大,對價值鏈的控制能力就越強,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上游;Antràs等[5]提出的上游度 (upstreamness)與技術密集度負相關,揭示了上游度與產業技術密集度間存在的內在的關聯關系[5]。
專利申請量能夠更好地衡量企業創新活動的實際成果和創新效率[27]。參照黎文靖等[28]的作法,本文使用有效專利數 (inforcepatent)作為企業創新成果的替代變量。另選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作為有效專利的替代變量。
本文使用R&D和FDI作為企業創新的來源變量。R&D表征了企業的內在創新動力[10]。R&D投入是決定美國脫鉤策略的遏制與激發效應孰強孰弱的關鍵性變量。FDI對國內企業創新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技術外溢效應[29]和市場競爭效應[30-31]實現的。在中介效應模型中,R&D和FDI是影響美國脫鉤策略效應的兩個重要中介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①企業規模 (size),用企業總資產的對數表征。②企業年齡 (age),用企業正式注冊成立年限衡量。③資產收益率 (ROA),用以表征企業盈利能力[32]。④SA指數 (sa),用以反映企業的相對融資約束程度[33]。⑤政府補助 (subsidy),政府創新補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具有直接補充和對外部投資的間接帶動作用,表明了產業政策中有限有為政府的作用[34]。⑥所有制 (ownership),該企業是否為國企,是為1,否為0。
2.2 數據
價值鏈地位指數和上游度指數是基于WIOD和亞行的世界投入產出表數據經計算得到的,反映了一國部門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分工地位。企業在全球價值鏈所處地位用所屬部門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替代。
WIOD和亞行的世界投入產出表均采用ISIC Rev.4行業分類標準,因此,數據具有兼容性。其中,WIOD時間覆蓋為2000—2014年,亞行世界投入產出表的時間覆蓋為2007—2021年。銜接后的世界投入產出表的時間覆蓋為2000—2021年。企業微觀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其他變量的數據來源見表1。在剔除數據缺失樣本后,共整理收集13478個樣本。

表1 變量定義及數據來源
2.3 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的中介效應模型由3個方程構成[35]:
(1)
(2)
(3)
其中,下標i和t用于識別企業和時間;模型 (1)是對總效應的估計,回歸系數c代表自變量x作用于因變量y的總效應;模型 (2)的系數a估計的是自變量作用于中介變量M的效應;模型 (3)中的系數b表示中介變量作用于因變量的效應,參數c′表示在控制中介變量M后,自變量x作用于因變量y的直接效應c=ab+c′,其中,ab為自變量通過中介變量M作用于因變量y的間接效應。Z為控制變量向量,ε為誤差項。
3 回歸結果分析
3.1 遏制效應與激發效應的疊加分析
美國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創新內在動力的激發效應見表2。所有的P值和R2均顯示有效,表明模型設定合理。脫鉤策略對企業創新內在動力 (R&D)具有顯著的激發作用。脫鉤策略對企業創新的遏制與激發的總效應為0.2146,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激發效應大于遏制效應。脫鉤策略對企業創新產生的間接作用為0.0766,占總效應35.6%,意味著美國脫鉤策略并不能阻斷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

表2 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創新內在動力的激發效應
脫鉤策略對FDI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美國的脫鉤策略并不會減少FDI流向中國。這可能得益于中國龐大的市場體量、經濟發展的強勁和互利共贏的 “一帶一路”政策。脫鉤策略通過FDI對中國企業創新所產生的間接效應a×b為0.0227,占總效應的10.4%。這表明,脫鉤策略通過FDI對中國企業創新的影響有限。
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和上游度的影響見表3,控制變量與表2相同。所有的P值和R2均顯示模型的設定合理。

表3 脫鉤策略對企業價值鏈地位和上游度的疊加效應
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總效應為0.0051,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美國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脫鉤策略對價值鏈地位的影響主要來源于直接效應,占比高達92.2%。
從Antràs等[5]的上游度視角看,脫鉤策略與產業上游度呈顯著負相關,總效應為-0.0474,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依據Fally[9]的上游度指數與技術密集度負相關理論,脫鉤策略與產業上游度負相關,意味著美國的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一個重要原因是制裁減少了中國對美國中間投入品的依賴,取而代之以國內中間投入品替代進口投入品,這種替代效應提高了國內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
Sobel檢驗結果表明,自主研發對產業技術水平攀升的貢獻并不明顯,表明中國企業的自主研發質量和效率較低,具有明顯的 “低質低效”特征。
3.2 價值鏈地位攀升路徑分析
R&D和FDI對價值鏈地位的影響見表4。P值和R2均顯示有效,表明模型設定合理。R&D對價值鏈地位攀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總效應為0.0013。其中,R&D通過自主創新對價值鏈地位攀升的間接效應僅占總效應的7.7%,表明企業自主創新存在 “低質低效”的雙低現象[36]。FDI對價值鏈地位攀升的總效應為0.0226,但FDI通過自主創新對價值鏈地位提升的間接貢獻僅為0.4%。這表明FDI對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來源于企業對FDI技術外溢的吸收和轉化等 “學習效應”[37]。

表4 R&D和FDI對價值鏈地位攀升的作用
在表5中,使用上游度替代價值鏈地位,考察R&D和FDI對提高產業技術密集度的影響。P值和R2均顯示有效,表明模型設定合理。

表5 R&D和FDI通過有效專利對上游度的影響
R&D對產業上游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與Fally[9]的結論是一致的。R&D對提高企業自主研發能力的直接效應為0.1333,但對改善產業上游度所起的間接作用a×b為-0.0013,僅占總效應的16.0%。研究結果再一次證實了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存在 “雙低”問題。FDI通過自主創新對改善產業上游度的間接效應為-0.0007,僅相當于R&D總效應的8.6%。這表明,國內企業創新對FDI技術外溢的吸收和轉化等 “學習效應”過于依賴。FDI對國內企業 “高質高效”的自主創新具有抑制作用。
3.3 分樣本回歸
(1)R&D對上游度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6。由表6可見,在電子與光學設備、機械與裝備制造和運輸設備制造業中,R&D對上游度的總效應顯著為負,但間接效應不顯著。在化學品與化學制品和橡膠與塑料制品業,雖然R&D與有效專利顯著正相關,但對產業上游度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再一次證實了企業自主創新的 “雙低”特征。

表6 分樣本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結果變量:上游度)
使用FDI替換表6中的R&D,主要結論如下:在基本金屬及其制品業、機械與裝備制造業和運輸設備制造業,FDI與產業上游度顯著負相關,這意味著FDI有利于產業技術密集度的攀升。這種效應并非來自企業的自主創新,這也間接地證實了FDI對產業技術密集度的提升作用主要來源于企業對FDI的技術外溢的吸收和轉化等 “學習效應”。在化學品與化學制品、橡膠與塑料制品、電子與光學設備行業,FDI通過自主創新對產業上游度的改善作用均不顯著。
(2)R&D對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7。由表7可知,在電子與光學設備和機械與裝備制造業中,R&D并未起到提升價值鏈地位的作用。相反,R&D與產業價值鏈地位指數負向相關。這是因為,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著價值鏈地位的攀升。價值鏈地位反映了本國與他國在國際中間投入品市場上的比較競爭優勢。只有當本國的產業技術水平提高并在中間投入品市場取得相對于他國的比較優勢時,本國的自主研發才會對產業的價值鏈地位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若他國的技術研發效率遠超本國,則本國的技術研發不僅無法提高本國的價值鏈地位,甚至會出現R&D與價值鏈地位負相關的現象。

表7 分樣本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結果變量:價值鏈地位)
在化學品與化學制品和橡膠與塑料制品業,R&D對價值鏈地位的攀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結合表6結果,雖然R&D并沒有顯著地提高產業技術水平,但通過對價值鏈的技術外溢的吸收和轉化顯著地提高了企業在國際中間投入品市場的競爭力。
使用FDI替換表7中的R&D,主要結論如下:FDI對各產業的價值鏈地位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這主要得益于中國借助FDI,拓展了國際市場空間,使得中國的中間投入品有更多機會進入國際市場。此外,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是促進FDI提高產業價值鏈地位的重要影響因素。
3.4 穩健性估計
以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作為自主創新的替代變量,重新對脫鉤策略的效應進行估計,結果見表8。結果表明,脫鉤策略對企業創新的激發效應大于遏制效應,意味著美國的脫鉤策略并不能阻斷中國企業的創新。這與表2的實證結果一致。

表8 企業創新內在動力激發效應穩健性檢驗結果
使用FDI替代R&D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在此省略。主要結論:使用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替代有效專利,得出了與表2 相同的結論,即美國的脫鉤策略并不會減少FDI流向中國。
脫鉤策略對企業價值鏈地位的疊加效應見表9。表9的結果表明,脫鉤策略對價值鏈地位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美國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

表9 脫鉤策略對價值鏈地位影響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以上游度替換價值鏈地位,對模型重新進行估計,結果在此省略。主要結論:脫鉤策略與企業創新顯著正相關,表明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創新具有正向激發作用。脫鉤策略與產業上游度顯著負相關,表明脫鉤策略并不能阻斷中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表9的實證結果表明,表3的結果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微觀數據和WIOD及亞行的世界投入產出表數據,考察美國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創新內在動力的激發效應,以及對中國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影響。發現如下:首先,美國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創新內生動力存在顯著的正向激發作用,且激發效應大于遏制效應。其次,美國脫鉤策略對中國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疊加效應顯著為正,表明美國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脫鉤策略對產業上游度的總效應顯著為負,意味著美國的價值鏈脫鉤策略并不會阻斷中國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最后,企業自主創新存在 “低質低效”的雙低現象,降低了價值鏈地位攀升的效率。美國的脫鉤策略并不會減少FDI流向中國。國內企業創新對FDI技術外溢的吸收和轉化等 “學習效應”過于依賴。從這個意義上說,FDI對國內企業 “高質高效”的自主創新具有抑制作用。
本文的政策含義是明顯的,面對美國的價值鏈脫鉤策略,R&D和FDI是提升中國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重要途徑。企業自主創新應重點解決 “低質低效”的雙低問題以及對FDI技術外溢的吸收和轉化等 “學習效應”的過度依賴問題。雖然FDI對產業的價值鏈地位有顯著的提升作用,但FDI對國內企業 “高質高效”的自主創新存在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