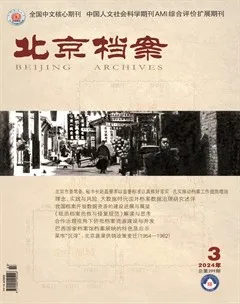沈鈞儒“我是中國(guó)人”手跡里的家國(guó)情懷
崔貽彤

沈鈞儒(1875—1963),字秉甫,號(hào)衡山,浙江嘉興人,著名愛國(guó)民主人士、法學(xué)家、原民盟中央主席,被譽(yù)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愛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光輝榜樣”。抗戰(zhàn)時(shí)期,沈鈞儒等先生勇赴國(guó)難,為爭(zhēng)取民族團(tuán)結(jié)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貢獻(xiàn),南京市博物館藏有一份沈鈞儒手跡,為我們了解那段崢嶸歲月、感悟先賢家國(guó)情懷提供了見證。
一、“我是中國(guó)人”手跡的緣起
南京市博物館館藏一級(jí)文物“沈鈞儒‘我是中國(guó)人手跡”寫于1942年1月,篇末落“衡山”篆書陽文鈐印,全文如下:
這五個(gè)字,是戈公振先生臨逝只剩一絲絲口氣后,若斷若續(xù)中吐出留在世間的一句話。五年前在上海,某夜讀韜奮先生所為哀悼文,至此非常感動(dòng),因擬作五絕句以記之。三首就,第四首先寫一句,即用戈先生語,竟不能續(xù),再寫,仍為此五字,到底寫了四句“我是中國(guó)人”,一句重一句,幾于聲嘶極叫。當(dāng)時(shí)寫畢,淚滴滿紙,但不自承為詩也。行知先生見而許之,并囑書。此三十一年一月。沈鈞儒記。
手跡所提戈公振先生是我國(guó)著名新聞學(xué)家、愛國(guó)報(bào)人,曾任《時(shí)報(bào)》編輯,在上海國(guó)民大學(xué)、南方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等學(xué)府任教,后加入《申報(bào)》。九一八事變后,戈公振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聯(lián)合鄒韜奮等7位報(bào)人在《生活》周刊登載《援助東北義勇軍之實(shí)際辦法》,呼吁各界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1932年,戈公振冒險(xiǎn)隨國(guó)際聯(lián)盟組織的李頓調(diào)查團(tuán)赴沈陽調(diào)查九一八事變真相,在《申報(bào)》連載《東北之謎》長(zhǎng)篇通訊,并應(yīng)鄒韜奮之請(qǐng),在《生活》周刊發(fā)表《到東北調(diào)查后》。1934年,戈公振赴蘇考察期間與鄒韜奮在莫斯科會(huì)面,兩人就世界大勢(shì)的觀察研究多次長(zhǎng)談。應(yīng)鄒韜奮之邀,戈公振1935年10月15日回國(guó)重辦《生活日?qǐng)?bào)》,卻不幸于22日病逝,[1]彌留之際他對(duì)前來探視的鄒韜奮說:“在俄國(guó)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國(guó)勢(shì)垂危至此,我是中國(guó)人,當(dāng)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鄒韜奮在《悼戈公振先生》中悲痛地寫道,“他說這幾句話的時(shí)候,雖在極端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睜得特別的大,語言也特別的激昂,但因太疲乏了,終至力竭聲嘶,沉沉地昏去”[2]。11月25日,沈鈞儒夜讀此文,甚為觸動(dòng),隨即提筆作詩,并在題記中說:“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xù),仍為此五字,再寫,仍為此五字,寫竟,淚滴滿紙,不自禁其感之深也。”詩曰:
一
浙江古越國(guó),勾踐人中杰。
嘗膽臥則薪,我是浙江籍。
二
蘇州有胥門,炯炯懸雙睛。
怒視敵人入,我是蘇州生。
三
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
死猶斷續(xù)說,我是中國(guó)人。
四
我是中國(guó)人,我是中國(guó)人。
我是中國(guó)人,我是中國(guó)人。
絕句前兩首化用勾踐兵敗臣吳,歸國(guó)后“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伍子胥奔吳遭饞毀,被逼自殺前憤而說出“掛吾目于門,以觀吳國(guó)之喪”的典故,表達(dá)踔厲奮發(fā)、視死如歸的豪情壯志。沈鈞儒之女沈譜、長(zhǎng)孫沈人驊所編《沈鈞儒年譜》[3]及沈老詩集《寥寥集》均指此詩寫于1935年11月25日,且題記內(nèi)容與手跡相印證,但據(jù)手跡所示此詩寫作時(shí)間應(yīng)為1937年,考慮到1942年時(shí)沈老已67歲,“五年前”或?yàn)樯蚶嫌洃浻姓`。
1942年1月,正在重慶嘔心瀝血建設(shè)育才學(xué)校、招收戰(zhàn)爭(zhēng)難童、培養(yǎng)熱血青年的陶行知,看到沈老的這四首絕句,想到戈公振壯志未酬身先死,逝世前仍在為抗日救亡搖旗吶喊,同志們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令人感慨萬千,便建議沈老題寫墨寶,于是有了這幅手跡。
二、沈鈞儒等愛國(guó)民主人士參與的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
沈鈞儒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dòng),經(jīng)常與陶行知、鄒韜奮等在一起討論抗日救亡工作,醞釀籌組救國(guó)會(huì)等事宜,由于沈老德高望重,救國(guó)運(yùn)動(dòng)經(jīng)驗(yàn)豐富,很自然地成為眾望所歸的領(lǐng)袖人物。1935年12月12日,沈鈞儒牽頭起草并發(fā)起征集簽名運(yùn)動(dòng),與馬相伯、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283人聯(lián)名發(fā)表《上海文化界救國(guó)運(yùn)動(dòng)宣言》,指出“盡量的組織民眾,一心一德的拿鐵和血與敵人做殊死戰(zhàn)”才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4]12月27日,沈老與鄒韜奮、陶行知等9人在上海文化界救國(guó)會(huì)成立大會(huì)上當(dāng)選為主席團(tuán)成員,沈老慷慨陳詞,“我國(guó)現(xiàn)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國(guó)民,均應(yīng)自動(dòng)奮起,以負(fù)救亡圖存之重任。文化界為國(guó)民之先導(dǎo),更應(yīng)悉力赴難”[5]。
1936年5月31日—6月1日,沈鈞儒當(dāng)選為全國(guó)各界救國(guó)聯(lián)合會(huì)主席,鄒韜奮等40余人當(dāng)選為執(zhí)行委員,陶行知等14人當(dāng)選為常務(wù)委員。沈老致開會(huì)辭:“全國(guó)不愿意做亡國(guó)奴的同胞,實(shí)在有大家團(tuán)結(jié)起來的必要。同時(shí),我們一定要促進(jìn)全國(guó)各黨各派各實(shí)力分子,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聯(lián)合抗日救國(guó)。”大會(huì)宣言強(qiáng)烈譴責(zé)國(guó)民黨以往在政治上放棄民族革命的任務(wù),現(xiàn)今對(duì)外放棄民族共同的大敵,孤注一擲只圖鏟除異己的政策,表明救國(guó)會(huì)愿以中介人立場(chǎng),全力保證各黨各派忠實(shí)履行共同抗敵綱領(lǐng)的決心,得到中共積極回應(yīng)。為更好地鞏固救亡聯(lián)合戰(zhàn)線,中共派地下黨負(fù)責(zé)人潘漢年找到流亡在港創(chuàng)辦《生活日?qǐng)?bào)》的鄒韜奮和出訪歐美途經(jīng)香港的陶行知交換意見,并安排胡愈之負(fù)責(zé)救國(guó)會(huì)事務(wù)及起草公開信《為抗日救亡告全國(guó)同胞書》,陶行知參與修改,初稿經(jīng)鄒、陶兩人簽名后,由鄒韜奮赴滬交給沈鈞儒、章乃器最后修正并簽名。7月15日,4人聯(lián)名以《團(tuán)結(jié)御侮的幾個(gè)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為題發(fā)表,詳細(xì)闡述了聯(lián)合救亡的立場(chǎng),并對(duì)各黨各派提出希望和要求,后被印成10萬余冊(cè)發(fā)往全國(guó),在國(guó)內(nèi)外引起重大反響。[6]
沈老等人的救國(guó)活動(dòng)日益激起國(guó)民黨的忌憚和日本帝國(guó)主義的仇視。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鄒韜奮等7位救國(guó)會(huì)領(lǐng)袖在上海被非法拘捕,陶行知被通緝。數(shù)日后,赴海外參加歐洲世界新教育會(huì)議、世界青年和平大會(huì)、世界和平大會(huì)的陶行知得知“七君子事件”十分憤慨,他一面受救國(guó)會(huì)委托,作為國(guó)民外交使節(jié),四處奔走宣講中國(guó)救亡運(yùn)動(dòng)實(shí)況,參與籌備全歐華僑抗日救國(guó)聯(lián)合會(huì),尋求外國(guó)政要名流的支持,一面聯(lián)絡(luò)華僑發(fā)起《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游說老師杜威聯(lián)合愛因斯坦、孟祿、羅格等學(xué)者16人致電南京政府,積極營(yíng)救“七君子”。[7]被關(guān)押8個(gè)多月后,7人終于被蔣介石下令“交保釋放”,沈老等出獄時(shí)堅(jiān)定地表態(tài),“當(dāng)不變初旨,誓為國(guó)家民族求解放而斗爭(zhēng)”[8]。
1939年沈鈞儒寓居重慶時(shí),為遏制日趨嚴(yán)重的國(guó)民黨反共“摩擦”事件,與鄒韜奮、陶行知等向國(guó)民參政會(huì)提案要求組成“華北視察團(tuán)”奔赴華北各戰(zhàn)場(chǎng)“傳達(dá)中央及本會(huì)對(duì)國(guó)內(nèi)團(tuán)結(jié)之意旨”,鞏固團(tuán)結(jié)抗日大局,卻反被國(guó)民黨借機(jī)用來搜集材料以歸咎于共產(chǎn)黨,沈老等人也被排除在視察團(tuán)名單之外。[9]1941年,獲悉“皖南事變”實(shí)情的沈老等對(duì)國(guó)民黨破壞團(tuán)結(jié)深感失望,對(duì)共產(chǎn)黨的正義自衛(wèi)表示同情,在國(guó)共兩黨之間反復(fù)磋商斡旋,竭力謀求折中轉(zhuǎn)圜之法,在最終看清國(guó)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后,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等堅(jiān)定宣布拒絕出席國(guó)民參政會(huì),與中共共進(jìn)退。[10]
1942年1月,沈鈞儒與陶行知、鄒韜奮等人以救國(guó)會(huì)成員名義正式加入中國(guó)民主政團(tuán)同盟,他們繼續(xù)為實(shí)踐民主與團(tuán)結(jié),維護(hù)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奮斗,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事業(yè)掀開嶄新的一頁。
三、手跡蘊(yùn)含的家國(guó)情懷
1942年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異常艱難的時(shí)期,也是國(guó)共力量此消彼長(zhǎng)的轉(zhuǎn)折期,時(shí)局復(fù)雜。沈老等人深知內(nèi)戰(zhàn)陰霾對(duì)全民抗戰(zhàn)大局的危害,對(duì)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將黨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行徑深感痛心,對(duì)中國(guó)革命的未來充滿憂慮。想到從上海、武漢到重慶,無數(shù)像戈公振一樣的仁人志士已經(jīng)為抗日救亡、民族團(tuán)結(jié)獻(xiàn)出寶貴的生命,愈發(fā)意識(shí)到全國(guó)各界人士團(tuán)結(jié)抗戰(zhàn)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我是中國(guó)人”短短五個(gè)字,平凡之中體現(xiàn)了一代先賢深厚的家國(guó)情懷,代表著不甘做亡國(guó)奴的億萬中國(guó)人民的戰(zhàn)斗誓言。他堅(jiān)定地呼吁各方力量彌合分歧、凝聚共識(shí),激勵(lì)全體中華兒女生死與共,以鋼鐵般的意志守護(hù)山河無恙,振奮了全民族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心,表達(dá)了至死不變的愛國(guó)情操和民族氣節(jié),激蕩著維護(hù)民族獨(dú)立和民族尊嚴(yán)的革命力量。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無論時(shí)局如何動(dòng)蕩,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戈公振等先生始終從民族大義出發(fā),以筆為槍,襟懷坦蕩,寵辱不驚,勇毅前行,把個(gè)人理想與祖國(guó)前途、民族命運(yùn)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即使身陷囹圄也不改初衷,以一身正氣和傲骨書寫了愛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使命與擔(dān)當(dāng)。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qǐng)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guó)的脊梁”。
注釋及參考文獻(xiàn):
[1]涂鳴華,王小杰.戈公振年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97,302-305,331,344-346.
[2] [5] [6] [9] [10]周天度,孫彩霞.沈鈞儒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6,118,123-132,197-199,210-212.
[3] [8]沈譜,沈人驊.沈鈞儒年譜[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140,187.
[4]周天度.沈鈞儒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9.
[7]周毅,向明.陶行知傳[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237-246.
作者單位:南京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