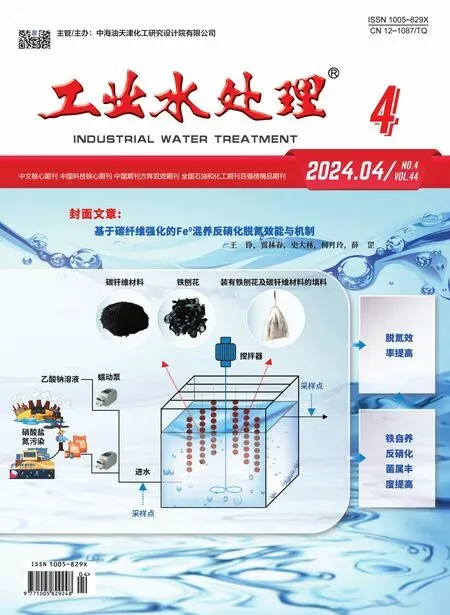剝離黏液層改性污泥回用對污泥顆粒化過程的影響
上官一將,文正紅,賈燕茹,楊成建,李志華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環境與市政工程學院,陜西西安 710055;2.西安市環境工程裝備智能化技術重點實驗室,陜西西安 710055;3.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西北水資源與環境生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陜西西安 710055)
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EPS)是污泥微生物細胞分泌或自溶后排放至體外的生物聚合物,因結合強度不同,可看作由黏液層、松散性EPS(LB-EPS)、緊密性EPS(TB-EPS)組成〔1〕,其中黏液層是易分離、無毒、可再生的生物聚合物,可用作重金屬吸附劑、防腐材料等,具有較高的回收利用價值〔2-4〕。相較于黏液層的資源化利用,剝離黏液層后的污泥處置也得到了廣泛的研究。已有研究表明,黏液層中因含有大量羧基、氨基、羥基等親水性官能團,影響污泥的黏度與脫水性能〔5〕。因此,降低污泥黏液層質量分數可以改善污泥壓縮脫水性能,提高污泥脫水效率〔6〕,提高污泥的可過濾性〔7〕,污泥的聚集性能也得到提升〔8〕。當前對于剝離黏液層改性污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水處理工藝中的污泥處置單元,而對剝離黏液層后污泥就地回用至污水生物處理系統卻鮮有研究。為此,筆者采用離心剝離活性污泥黏液層的改性處理方法,探究改性處理后污泥回收利用的可行性,并深入分析改性污泥回用于典型的連續流代表工藝DE型氧化溝系統后,系統性能與污泥性質的變化情況,以期為連續流系統內的污泥顆粒化提供一定的技術指導。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污泥與接種污泥
試驗污泥與DE型氧化溝系統接種污泥取自西安市某市政污水處理廠A2/O工藝的好氧池末端,使用實驗室基質進行污泥培養后,MLSS約為6.98 g/L,SVI為126 mL/g左右。試驗污泥使用磷酸鹽緩沖溶液(PBS)稀釋至2~3 g/L范圍內,約為2.30 g/L,污泥混合均勻后分為兩份,一份為原泥,另一份污泥進行離心剝離黏液層改性。接種污泥稀釋至2.67 g/L左右后投入DE型氧化溝系統培養。
1.2 反應器設置
DE型氧化溝系統主要裝置為有機玻璃制成,由DE型氧化溝、中心輻流式沉淀池、回流系統組成。氧化溝長1.70 m、寬0.40 m、高0.28 m,有效水深0.23 m,有效容積為150 L;沉淀池直徑0.35 m,有效容積為58 L,DE型氧化溝系統示意見圖1。實驗期間,控制DE型氧化溝的進水流量為250 mL/min,水力停留時間為10 h,污泥齡為20 d,污泥回流比為90%。DE型氧化溝周期性運行由PLC控制,單個運行周期為6 h,每個周期包括4個階段,每個階段運行90 min,具體運行工況見表1。

表1 DE型氧化溝運行工況設置Table 1 Operating condition setting for DE oxidation ditch

圖1 DE型氧化溝系統示意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DE oxidation ditch system
由圖1可知,在A溝與B溝分別布置兩組曝氣裝置,分別通過PLC控制啟閉,單組曝氣系統的曝氣流量為40 L/min。DE型氧化溝為周期性階段式運行,雙溝運行工況見表1,以A溝為例,階段1時DO為0~0.2 mg/L,階段2時DO為0.2~0.5 mg/L,階段3時DO為0.8~1.5 mg/L,階段4時DO為2.5~3.0 mg/L,運行期間系統溫度為(24±2) ℃。
1.3 進水水質
進水采用實驗室配水,以CH3COONa為碳源,NH4Cl為氮源,COD容積負荷為0.72 kg/(m3·d),氨氮容積負荷為0.087 kg/(m3·d),反應器中添加微量元素溶液為0.4 mL/L,微量元素溶液包含0.15 g/L H3BO3、0.03 g/L CuSO4·5H2O、0.18 g/L KI、0.12 g/L MnCl2·4H2O、0.06 g/L Na2MoO4·2H2O、0.12 g/L ZnSO4·7H2O、0.15 g/L CoCl2·6H2O、1.54 g/L FeSO4·7H2O、12.74 g/L EDTA、3 mg/L KH2PO4、9 mg/L CaCl2、60 mg/L MgSO4·7H2O。
1.4 黏液層、LB-EPS及TB-EPS的分離方法
EPS采用陽離子交換樹脂法(91973,鈉型陽離子交換樹脂)〔9〕分層提取。
1)黏液層的分離。取一定體積質量濃度為2~3 g/L的污泥,在分離因數2 000下離心5 min(4 ℃),收集上清液與沉積物,此時收集到的上清液為黏液層。
2)LB-EPS的分離。將分離黏液層后得到的沉積物放入pH為7.2的PBS中,使沉積物重懸至原刻度,在分離因數2 000下離心5 min(4 ℃),棄去上清液并加入PBS再次重懸至原刻度后,在冰水浴條件下使用超聲細胞破碎儀進行超聲分散,超聲功率為5 W,超聲時間為5 min,超聲波頻率為20 kHz。隨后于分離因數10 000下離心15 min(4 ℃),收集上清液與沉積物,上清液經0.45 μm濾膜過濾后,所得即為LB-EPS。
3)TB-EPS的分離。將分離LB-EPS后得到的沉積物加入PBS中,使沉積物重懸至原刻度,按單位質量SS加入70 g/g的陽離子交換樹脂,冰水浴攪拌2 h,吸取溶液在分離因數10 000下離心30 min(4 ℃),取離心后上清液在同等轉速下離心15 min,重復3次,取上清液經0.45 μm濾膜過濾后,所得即為TB-EPS,沉積物即為改性污泥。
1.5 原泥與改性污泥的理化特性分析
對原泥和改性污泥的呼吸速率、總菌濃度、活死菌比例、高核酸(HNA)與低核酸(LNA)分布、EPS組分及Zeta電位進行檢測,分析活性污泥經剝離黏液層改性后的理化性質,探究改性污泥回用的可行性。使用磁力攪拌器在低轉速200 r/min條件下,對原泥與改性污泥攪拌0、10、20、30、60 min后進行生物絮凝,每次攪拌后沉淀15 min,收集上清液并測定濁度,出水濁度水平表明污泥絮凝和出水澄清性能〔10〕。
1.6 DE型氧化溝系統監測
對DE型氧化溝系統的反應器性能及污泥性質變化進行長期監測,探究改性污泥回用過程對DE型氧化溝系統的影響。DE型氧化溝運行分為4個過程:過程Ⅰ(污泥培養期,第1~37天,MLSS 2.30~2.67 mg/L,SVI 126~247 mL/g)、過程Ⅱ(污泥一次回用期,第38~56天,MLSS 2.66~2.92 mg/L,SVI 216~335 mL/g)、過程Ⅲ(正常運行期,第57~76天,MLSS 1.90~2.33 mg/L,SVI 411~480 mL/g)、過程Ⅳ(污泥二次回用期,第77~94天,MLSS 1.94~2.55 mg/L,SVI 319~490 mL/g)。
在改性污泥回用過程中(過程Ⅱ、過程Ⅳ),取氧化溝排放污泥通過1.4章節中黏液層的分離改性后,將改性處理后的污泥分別于每日10點、16點、22點各2.5 L,共7.5 L(為氧化溝有效容積的5%)投加至氧化溝前端進水部位(圖1),完成單日改性污泥回用,20 d左右完成一次改性污泥回用過程。
1.7 分析指標及測試方法
多糖與蛋白質含量分別采用硫酸-蒽酮法〔11〕與改良的Lowry法檢測〔12〕。采用呼吸計量法測定活性污泥的呼吸速率〔13〕。使用激光粒度分布分析儀(LS230/SVM,美國貝克曼)測量污泥樣品的尺寸。使用掃描電子顯微鏡(JSM-6510LV,日本技術株式會社)拍攝顆粒污泥的表面結構〔14〕。使用流式細胞儀(Accuri C6,美國BD公司)檢測污泥樣品中的總菌數量、活死菌比例及HNA與LNA數量。采用Zeta電位儀(Zetasizer Nano ZS 90,馬爾文儀器有限公司)測定Zeta電位。使用臺式濁度儀(WGZ-20s,上海昕瑞儀器儀表有限公司)測定上清液濁度。常規水質指標、MLSS及SVI按照《水和廢水檢測分析方法》(第4版)進行測定。
2 結果與討論
2.1 剝離黏液層改性處理對微生物活性的影響
好氧呼吸速率可以有效表征污泥微生物的生理狀態、生物活性,從而分析環境變化對微生物的影響〔15〕。活性污泥原泥及剝離黏液層改性污泥的比內源呼吸速率(SOURe)、比自養菌呼吸速率(SOURA)、比異養菌呼吸速率(SOURH)變化情況見表2。

表2 原泥與改性污泥的呼吸速率變化Table 2 Variation of respiration rate between raw sludge and modified sludge
由表2可知,改性污泥的SOURe、SOURA、SOURH分別為1.12、0.79、1.46 mg/(g·h)。這表明雖然改性污泥的呼吸速率較原泥有所下降,但仍具有良好的呼吸代謝活性,具備一定的底物降解能力,可支持污泥進行污染物的生物降解〔16〕。
進一步地,通過流式細胞儀對原泥和改性污泥的總菌數量、活死菌比例及HNA與LNA數量進行測定,結果見圖2。

圖2 原泥與改性污泥的微生物活性變化Fig.2 Microbial activity changes between raw sludge and modified sludge
由圖2(a)可知,相較于單位質量SS原泥總菌數量(2.55×1010cells/g),單位質量SS改性污泥的總菌數量提高至2.79×1010cells/g。這是因為EPS具有包裹物質功能,改性污泥中之前被黏液層包裹在內的微生物暴露在環境中使總菌濃度升高〔9〕。死菌率對微生物行為具有指示作用〔17〕,與原泥的死菌率相比,改性污泥的死菌率只是略微升高,由26.97%升至27.98%。這表明改性處理污泥并未抑制污泥微生物的活性進而影響對污染物的降解潛力〔18〕。由圖2(b)可知,與原泥相比,改性污泥的LNA比例由12.07%上升至12.61%,略有提升;而HNA比例由61.13%下降至59.42%,略有降低。這可能是因為活性污泥經剝離黏液層后,位于污泥表面或間隙的LNA被釋放,沒有觀察到HNA的進一步釋放,說明剝離黏液層是一種溫和的污泥改性操作,并未破壞污泥的內部結構〔19〕,因此改性后的污泥仍具有降解污染物的潛力,可回用至生物反應器進行生物處理。
2.2 剝離黏液層改性處理對活性污泥理化特性的影響
活性污泥改性前后EPS組分變化,影響污泥表面電荷特性,進而影響出水濁度,對污泥EPS組分、Zeta電位及污泥在不同攪拌時間下沉降后濁度的變化進行考察,結果見圖3。

圖3 原泥與改性污泥的理化特性變化Fig.3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raw sludge and modified sludge
由圖3(a)可知,相較于原泥,改性污泥中剝離的黏液層占比為11.11%,EPS質量分數下降了14.78 mg/g,m(PN)/m(PS)升高,由1.37提高至1.84,這是因為剝離黏液層改性操作致使污泥EPS外層的PS質量分數降低〔20-21〕。活性污泥的表面特性與EPS組分密切相關,Zeta電位常用來表征污泥的表面電荷屬性,以評估表面特性的變化〔22〕。由圖3(b)可知,原泥的Zeta電位絕對值為15.4 mV,此時污泥間的靜電斥力較大,具有良好的分散穩定性;當對原泥進行改性處理后,Zeta電位絕對值為11.4 mV,降低了25.97%。這表明m(PN)/m(PS)升高導致污泥Zeta電位絕對值降低〔23〕。污泥表面的電荷屬性影響著污泥的沉降性能,圖3(c)表明,原泥與改性污泥在初始時刻的上清液濁度分別為32.81、30.76 NTU,相差不大,在攪拌10 min后,原泥的上清液濁度出現最低值,為30.36 NTU,而改性污泥組在攪拌20 min后濁度最低,為28.13 NTU。這表明污泥經剝離黏液層改性后,促進污泥微生物保持長時間的生物絮凝作用,有助于大尺寸微生物聚集體的形成〔24〕。原泥的上清液濁度從第10分鐘起表現出升高的趨勢,在第60分鐘升高至45.32 NTU,而在同一時間段,改性污泥組濁度控制在26.34~28.13 NTU范圍內。這可能是因為隨著攪拌時間的延長,原泥絮凝形成的絮體結構易在流體剪切力的作用下破碎,導致出水濁度上升;而改性污泥在絮凝過程中形成密實的微生物聚集體,受流體剪切力影響較小,因此上清液較為澄清〔10〕。
EPS組分對活性污泥的絮凝能力及細胞表面的黏附能力起著重要作用〔20〕。通過剝離污泥外側黏液層改性處理,去除了大量的電負性基團〔25〕,提高了改性污泥的m(PN)/m(PS),從而使改性污泥的Zeta電位絕對值降低〔23〕,有利于促進微生物間的相互碰撞從而團聚形成大尺寸的微生物聚集體。絮凝特性實驗也表明剝離黏液層改性的調控方式可以促使污泥微生物間的相互團聚,因此改性污泥回用至污水生物處理系統后具有促進系統內污泥顆粒化的潛力〔26〕。因此,進一步將改性污泥回用至連續流代表工藝DE型氧化溝系統,并分析改性污泥回用對污水生物處理系統內污泥性質及反應器性能的影響。
2.3 改性污泥回用對反應器性能的影響
反應器在運行過程中分4個過程,其中過程Ⅱ、Ⅳ為改性污泥回用過程,整個運行過程中系統出水COD、TN變化情況見圖4。

圖4 COD和TN隨DE型氧化溝系統運行的變化Fig.4 Variation of COD and TN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DE oxidation ditch system
反應器進水碳源為易降解碳源乙酸鈉,接種污泥投放至氧化溝并培養一段時間后處于穩定微膨脹狀態,為氧化溝系統常見的運行工況〔27〕,此時系統表現出良好的COD去除效果。由圖4可知,在過程Ⅰ期間,COD和TN的平均出水質量濃度分別為9.80、8.09 mg/L,過程Ⅱ、Ⅲ、Ⅳ的COD平均出水質量濃度分別為19.22、6.66、33.41 mg/L。已有研究表明污泥的外側黏液層用于包裹異養菌〔9〕,剝離黏液層改性處理污泥,導致污泥的異養菌數量減少,其COD處理能力下降。隨著改性污泥連續回用天數的增加,反應器內改性污泥占比升高,異養菌活性下降,出水COD上升,而在停止污泥回用的過程Ⅲ運行期間,溝內異養菌活性逐漸恢復,出水COD穩定處于較低水平。過程Ⅱ、Ⅲ、Ⅳ的TN平均出水質量濃度分別為7.49、6.54、7.22 mg/L。在改性污泥回用期間,TN去除效果略有提升。
2.4 改性污泥回用對反應器內污泥性質的影響
反應器整個運行過程中,過程Ⅱ、過程Ⅳ為兩次改性污泥回用過程,系統中污泥的PN、PS隨時間變化情況見圖5。

圖5 PN和PS隨DE型氧化溝系統運行的變化Fig.5 Variation of PN and PS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DE oxidation ditch system
如圖5所示,在過程Ⅰ運行過程中(第1~37天),系統污泥EPS質量分數由253.67 mg/g降至133.38 mg/g,m(PN)/m(PS)從1.43降至0.49,這與氧化溝系統的推流混合式特征有關,反應器在過程Ⅰ運行時,基質進入反應器后立即被稀釋,反應器內底物濃度低,微生物長期處于饑餓狀態進而消耗EPS,使EPS含量下降〔28〕。經過兩次改性污泥回用過程后(過程Ⅱ,過程Ⅳ),EPS質量分數提升至203.00 mg/g,m(PN)/m(PS)升至1.55,其中主要是PN質量分數由43.62 mg/g提升至123.46 mg/g所致,而PS質量分數在79.54~89.76 mg/g范圍內波動。連續從反應器取泥改性處理并回用至反應器后,溝內改性污泥占比不斷增加,微生物之間不斷聚集形成較為密實的聚集體,隨后微生物聚集體為適應環境變化,分泌EPS至顆粒表面,導致反應器內污泥的EPS質量分數增加,尤其是PN質量分數明顯上升〔26〕。通過改性污泥回用的方式改變了反應器內污泥的m(PN)/m(PS),提升了污泥的疏水性能,促進了微生物間的相互團聚,有利于污泥向顆粒化轉變〔29〕。整個反應過程中,污泥顆粒粒徑的變化見圖6。

圖6 污泥粒徑分布隨DE型氧化溝系統運行的變化Fig.6 Variation of sludg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with the operation of DE oxidation ditch system
如圖6(a)所示,過程Ⅰ運行中(第1~37天),污泥的平均粒徑由53.05 μm升至96.85 μm,粒徑大于200 μm的污泥尚未形成,此時污泥呈絮體狀態。在改性污泥一次回用期間(過程Ⅱ),反應器內逐漸出現了粒徑大于200 μm的污泥,占比為11%。在正常運行期(過程Ⅲ),反應器內粒徑大于200 μm顆粒污泥比例提升至17%。直到改性污泥二次回用末期(過程Ⅳ末期,第94天),反應器內粒徑大于200 μm顆粒污泥比例再次出現明顯提高,升至32%。此時,反應器內污泥粒徑分布呈現出明顯的雙峰結構,左峰代表絮體污泥,右峰代表顆粒污泥,且可以觀察到右峰大粒徑的顆粒污泥在反應器中占據主要部分〔圖6(b)〕。此外,通過SEM掃描電鏡拍攝了反應器內出現的顆粒污泥(圖7),圖像顯示顆粒粒徑大于200 μm,表面較為粗糙,這可能與DE型氧化溝系統無法提供足夠的剪切力有關〔30〕。

圖7 DE型氧化溝系統內顆粒污泥的SEMFig.7 SEM of granular sludge in DE oxidation ditch system
在改性污泥一次回用過程中(過程Ⅱ),反應器內污泥質量濃度由2.66 g/L升至2.92 g/L,SVI隨污泥質量濃度升高而上升〔31〕,達335 mL/g。將剝離黏液層后的改性污泥連續投加至反應器,系統中m(PN)/m(PS)升高促進了微生物間的相互聚集,同時觀察到大顆粒污泥占比超過10%,污泥絮體開始向顆粒化轉變〔32〕。在正常運行期(過程Ⅲ),SVI升至較高水平,為480 mL/g,反應器內污泥較為松散,污泥質量濃度降至1.90 g/L,而m(PN)/m(PS)未發生明顯變化,顆粒污泥占比略有增加,可能是在物理選擇壓作用下,輕質絮體污泥從上方出水堰排出所致〔30〕。直至改性污泥二次回用過程(過程Ⅳ)時,SVI的上升趨勢被抑制,降至452 mL/g,污泥質量濃度出現回升,此時m(PN)/m(PS)再次升高,顆粒污泥占比超過30%,表明系統內污泥顆粒化作用持續增強。然而,當反應器處于絮體污泥與顆粒污泥共存狀態時,顆粒污泥并未依靠沉淀性能優勢與絮體污泥完全分離,經污泥排放后導致顆粒污泥流失,未能有效富集〔33〕。
3 結論
本研究的污水生物處理系統為氧化溝系統,不具有采取提供水力選擇壓、水力剪切力、飽食-饑餓期控制的調控屬性,通過將剝離黏液層改性污泥就地回用于氧化溝系統,優化反應器內污泥顆粒化過程同時實現污泥中的黏液層EPS資源回收,是一種經濟可行、具有應用前景的造粒技術。
1)離心剝離黏液層的改性操作是一種溫和的改性方法,并未破壞污泥結構。剝離黏液層改性處理后的污泥仍具有較強的微生物活性和良好的底物降解能力。
2)剝離黏液層改性后污泥的EPS含量降低,m(PN)/m(PS)升高,Zeta電位絕對值降低,絮凝性能提升,從而有利于微生物間的相互團聚,形成結構緊密的微生物聚集體,回用至污水生物處理系統后具有促進系統內污泥顆粒化的潛力。
3)將污泥改性后回用至連續流生物處理系統,觸發了系統內絮體污泥的顆粒化轉變,通過剝離黏液層改性處理污泥回用,一方面可實現從污泥中回收黏液層EPS資源,另一方面促進了系統內的污泥顆粒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