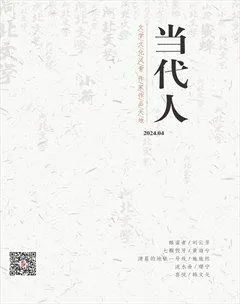行走山海間
從秦皇島北戴河向西不足二十公里,是我的家鄉撫寧。
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人在這里繁衍生息,存有大量歷史遺跡。西漢時置驪城,唐朝時因其地處邊徼,為企盼安定,便取“撫我黎庶,寧我子婦”之意改稱撫寧縣。后來又經多次建制變更,于2015年由撫寧縣改設為秦皇島市撫寧區。
撫寧枕燕山銜渤海,北部重巒疊嶂,峽谷縱橫,長城盤旋,南部田疇煙樹,海邊波濤洶涌,沙軟灘平,是全國唯一同時擁有山、河、湖、海、長城的地區。民間的鼓吹樂、太平鼓名聞遐邇,曾被命名為“中國吹歌之鄉”。我調到省城工作后,懷著魂牽夢縈的深切感情,每年都要回這里看一看。
這次回撫寧,不看海不看河也不看湖,就看山,走山海之間的天路。
先去大新寨,它地處北部山區。當年人們說“大新寨窮山惡水,號稱大心窄”。如今,這里滿眼青山綠水,開發了龍云谷、冰塘峪、背牛頂等知名生態景區。
有人說“南有九寨溝,北有冰塘峪”,足見它超凡脫俗,風景迷人。走進幽長的峽谷,依次有七座潭,稱“七星潭”,潭水幽深,碧綠如玉。兩側以山形命名的雞冠山、筆架山,危石累卵,險勢逼人。我爬到雞冠山山頂,那兒鋪設的玻璃滑道,猶如長龍盤繞林間,同伴問我敢不敢滑一滑,我說敢啊。進入滑道,恰似脫弦之箭,瞬間就到了山下,難怪它被譽為“華北第一滑”。一一走過網紅打卡地“搖擺橋”、由喊聲高低決定泉水噴涌高度的“吶喊噴泉”,這些精心設計的所在,為峽谷平添了濃濃的詩意。同行的朋友卻說:“詩眼在后邊呢。”繼續前行,終于尋到“詩眼”的芳蹤。原來這兒之所以冠名“冰塘峪”,是因為峽谷中有個神秘莫測的山洞,夏天洞中寒冰如柱,等到隆冬季節,周邊草木枯黃凋謝,冰洞卻熱氣蒸騰。
背牛頂凌空壁立,上去必須腳踏四面懸空的垂直天梯,俯看山下是萬丈深淵,確要有非凡的膽量。然而人們卻憑著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勇氣和執著,展開建設這塊風水寶地的曠世“接力賽”,使之造福人間。明代就有僧人到此鑿井建廟,逐漸成為佛教勝地,到了清朝在此又建了道觀,從此這里成為佛教和道教并存的香火繁盛之地。近年來,在當地政府帶領下,把垂直柏木天梯改建成圓籠形金屬天梯,既為游人攀登方便又確保了安全。登上山頂,望長城內外群山起伏,天邊浩瀚大海帆影點點。愛山,親山,護山,用山,讓山的青水的綠,更多了一種人與自然相互成就的美好內涵。
“撫寧天路”有另一種雄渾厚重的韻味。它是老百姓給起的名字,坐落于兔耳山片區。
兔耳山,是冀東名山。據光緒十年《畿輔通志·輿地·山川》記載:“兔耳山在縣西十五里,雙峰尖聳,狀如兔耳,絕頂有潭,微徑屈曲,盤折而登,上平廣,可容數萬人。”此言不虛,明洪武七年知縣婁大方曾率屬吏士民避難于兔耳山的險峰叢林中,后婁大方曾賦詩描繪兔耳山:“形盤龍尾連滄海,勢拱鰲頭直接空,云覆寒潭晴作雨,霜凋老木夜生風。”因為撫寧地處東北、華北咽喉地帶,是兵家必爭之地。明宣宗朱瞻基曾巡視兔耳山,清朝皇帝凡去盛京祭祖往返必經撫寧,曾在與兔耳山近在咫尺的天臺山建有行宮,興之所至也登臨兔耳山。乾隆皇帝曾賦詩《兔耳峰》,有“兔耳峰頭常罩云,果然玉筍矗氤氳”之句。嘉慶在天臺山行宮迪康書齋中吟詩贊撫寧:“策馬撫寧郭,民風喜迪康,平原無曠土,比戶有余糧,峭壁楓輝赤,閑庭菊燦黃,天臺標勝概,秋野畫屏張。”其實,這些吟風弄月的帝王,哪里真正體恤到百姓的疾苦,幾千年間,山里生活苦不堪言。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才真正使百姓過上“比戶有余糧”的幸福生活。
進入新時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念深入人心,撫寧區全面謀劃兔耳山片區的開發,在山麓東起舊縣村西至南山村,修建了一條約十公里隨山勢蜿蜒盤曲的公路,這便是人們所說的“撫寧天路”。天路彎彎,搖醒了昏睡多年的荒山,打開了滿懷希望的畫卷。
去兔耳山,我們拜訪了承包千畝荒山多年的張立存老人。他已在山上安家,造林,做農副產品加工銷售。他在山中的家,有精致的臥室和寬敞的客廳。客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滿墻錄毛主席詩詞的書法作品。這引起了與我同行的韓志華的極大興趣。韓志華是秦皇島收集和展播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北戴河活動影像資料的知名人士,他與張立存探討起如何把綠色美景與紅色文化相結合,拓展旅游內涵的發展之路。張立存透露:“政府幾年前就有了安排和統籌規劃,還要發展康養呢。”
有了天路,登高覽景也便捷多了。在兔耳山的“了洼”,參觀先人生活遺址。在“空中草原”,則見綠波蕩漾,繁花似錦。在“怪坡”,車掛空擋,竟然由低處向坡上溜滑,可見大自然的神奇。登上天路旁的觀景臺,兔耳山風景盡收眼底,“河馬戲龜”“猴王點兵”“雄獅嘯天”“八王爺拜壽”,目不暇接。登臨玉皇頂,來到“兔耳籠云”雙峰并峙的“兔耳”跟前,舉目遠望,長空麗日下,遠方海天一色;俯瞰,廣袤田疇上村舍點綴,炊煙裊裊。
山腳下和“天路”兩旁,望不到頭的山楂樹結滿紅燦燦的圓果,就像早霞紅遍半邊天。張立存說,這一帶盛產桑葚、蘋果、板栗、核桃等山貨,可過去卻難以運出去。有一位農婦,給她在遠方工作多年未歸的兒子寫過一封信,說“母音傳千里,穿進你心房。過去這兒山窩里交通不便,收果的客商來了不僅壓低收購價錢,還讓把果品給送到山下,溝溝坎坎,磕磕絆絆,那年月你爹成了沒尾巴的驢呀。現在好了,天路一修,客商可以把車開到門前收購山貨啦。咱這山溝溝里頭的窮窩窩,成了金窩銀窩。咱這兒峰峰都是景,坡坡都是樹,樣樣都是財”。講完這些,張立存意猶未盡,他又高聲背誦起自己寫過的一首詩:“云籠兔耳山,古今有名傳,唐王征東過,乾隆留詩篇,朝陽升碧海,紫氣繞青山,兔耳山峰嫦娥望,最美莫如咱家鄉。”
站在山巔,俯瞰山間南來北往的貨車沿著天路奔馳。汽車的鳴笛聲和山里的風聲、山民的歌聲融成一片,奏響美好生活的交響。
(劉克仁,河北省著名報人,作家。出版散文集《明月清風》等。)
特約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