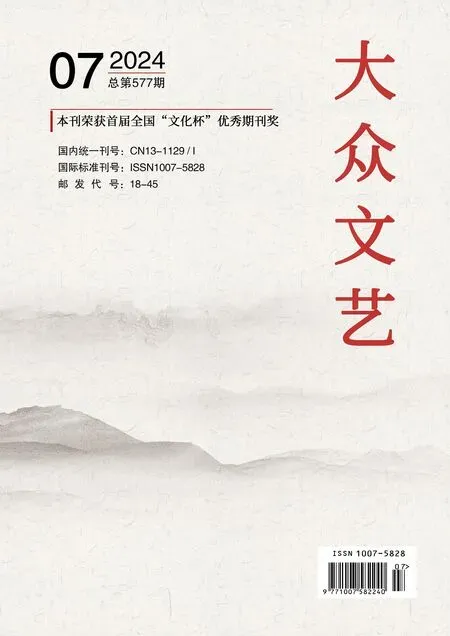基于生態美學視域的王羲之書法藝術研究
董詩祺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海淀 100875)
生態美學從定義上來講,它融合了生態學和美學元素,不斷啟發了人們關于經驗美學和哲學美學的探索。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具有豐富文化內涵和民族精神的文明古國,在歷史沉淀中不斷促進各個領域的蓬勃發展,其中書法、文學等領域在國際上均有足夠的影響,并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王羲之書法藝術為代表的草書對后人的影響十分深遠,美學視域下的王羲之書法,獨具神韻和藝術風格,也是后人學習和臨摹的典范,基于生態美學視角研究王羲之書法,對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也具有重要價值。
(2) 污染物泄露濃度越高,隨著地下水遷移距離會越長。在未采取任何措施情況下,污染物泄漏不易被發現,污染源濃度持續上升,則污染物會隨著地下水運移到廠區下游夾馬石村,危及村民飲用水安全。
一、王羲之的書法藝術風格研究
1.王羲之書法藝術的結字
王羲之書法在結字上講究一個“變”字,變即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讓字體的形態與眾不同,在落筆的過程中自己成章法,也是這種變化王羲之書法的藝術風格更加旨在豪放,在研究王羲之書法藝術結字時,需要細細品味他書法字體的神韻和風格。比如《行穰帖》的刻篆石碑中(如圖1),可見其整體結字緊湊,結字十分精致,相比以往粗率風格,這種藝術風格更加偏向于北魏楷體的由寬結樸拙特征。王羲之書法作品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開辟了書法的新篇章,并且能夠將前人的書法經驗用于其中,集各大家所長的基礎上不失個人風格。通過結合相關文獻進行分析,對王羲之結字變化規律進行總結后不難發現,《行穰帖》筆畫鋒棱隱藏,筆畫十分渾厚,有別具一格的篆籀意味。整個作品字勢呈傾斜之狀,姿態萬千,復制者也十分想讓這一特征重現于世。復制中需要注意的是用筆的壓力、速度等,盡量不影響原跡的墨色,必要的時候可調整墨色,進而完美體現王羲之書法在色調上的獨特魅力[1]。

圖1 王羲之《行穰帖》
2.王羲之書法藝術的章法
無界格式更加偏向于字體結構的曲折以及在轉變上進行動態趨勢處理,王羲之書法藝術章法分為無界格式、界格式。經過深入研究會發現,這種章法的字體之間分布是錯落有致的落筆中心在左右偏斜中呈現豐富變化,縱觀書法整體不難發現有靈動之美,書法表現更加輕盈流暢,這種章法形式在王羲之作品中運用較多,比如《得示帖》《初月帖》《闊轉久帖》等,總結可知這類章法下的作品有飄逸靈動、行云流水、擴張自然之象,在疏朗峻爽之間呈現出變化萬千的章法體系。界格式的表現特點則以單體直線為主,所有字體呈現垂直線條狀,字體不如其他字體有曲折的結構變化,此種章法多見于草書以及行書中,并且有一定的章法表現。在研究王羲之的書法中,在他的北魏楷體中發現很多運用界格式章法的作品,因此此種章法也成為王羲之書法中最常見的章法。在這樣的作品中,界格本身起到很好的限制作用,因為作品本身是通過黑白關系的對立來創作作品,其性格不拘一格,對于字體線條和空間都有相對獨立的處理,如果沒有界定,由于所有字體線條之間并不是那么的循規蹈矩,因此看起來線條是比較分散的。
3.王羲之書法藝術的用筆
王羲之書法用筆分圓筆和方筆,這兩種用筆方式之間存在一定關聯性。方筆是在圓筆和隸書篆書以圓筆用筆推演而來,大部分行書的書寫則采用圓筆更多。在實際研究中我們發現,王羲之書法在用筆藝術上,首先會用到頓筆套寫的方式,頓筆就是指在書寫的時候,起筆處的力道和轉折處之間有一定的停頓。另外再王羲之書法自己也有字態豐盈的感覺,并且用筆十分舒展,整體結構很強,不失大家風范。最后,關于王羲之書法的總結歷史上的文章也層出不窮,總體而言都能概括出其書法的獨特之處,在生態美學視角下,其書法和筆力更顯獨特。可見其用筆風格整體更為藝術,具體作品見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這一作品中充分展示了筆理論的風格,并且在這一作品中,可發現王羲之筆力之雄勁,起筆藏鋒逆入,橫畫整齊規整,欲右先左[2]。
二、基于生態美學視域的王羲之書法藝術研究
1.虛實相協的意蘊之美
(2)在NE向斷裂構造體系,特別是新老地層呈壓性斷裂接觸時,也就是說在封閉的構造條件下,有利于含礦偉晶巖的形成。含礦偉晶巖的規模及鈮鉭礦化受其嚴格的控制,特別是靠近斷裂處,更有利于鈮鉭元素的富集。
(1)筆畫的連接與斷開,王羲之的草書中“連”和“斷”的書法很多,這種主要和線條的動靜有關,其中代表作有《十七帖》,研究該作品的線條可知,其中線條十分自然,有動靜相合的形態美,“斷”和“續”也銜接自然,大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象,其中包含了作者對自然的贊美,由景寄情,作者并不是可以追求“行”和“止”,更重要的是“動靜結合”,并且自然而然地將相關的美學結合到一起,就算寫至硬朗處也是一氣呵成,整個作品反復呼吸之間,剛柔并濟,循環格外流暢,有太極圖般的氣息流暢,讓整個作品看起來十分具有生機,在落筆之處盡顯其獨特風骨,并在行云流水之間體現出造化自然的情境,縱觀王羲之作品,除了虛實結合之外,其字和字之間的聯系也十分微妙,這有賴于作者的手法和連貫作用,在“斷”和“續”的牽拉之下,字和字之間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牽拉,相生相共。仔細研究王羲之的書法作品,可以看出其收筆入筆頗有細節感,“尖入尖出”是其主要特征。正是由于這一特征,讓作品的篇幅之間有一定的神韻存在,讓字和字之間相互影響而非獨立存在,字和字之間顯得更加連貫和透徹。而在其作品《姨母帖》中,卻鮮少見到“牽拉”之象,字和字之間相對獨立,連帶不明顯,即便如此,認真觀察該作品的每個字,也會發現他的每個字和每一筆也有“尖入尖出”的特點,他的書法細節處理十分謹慎,并且書寫十分特別在字里行間呈現出線條的變化,不光有直線的變化,更有毛筆呈現的曲線變幻之美,線條剛柔并濟、粗細恰當,線條十分有質感,《哀禍帖》與《姨母帖》是兩幅相反的作品,但是在王羲之書法中,這兩幅作品連帶是相對比較多的。另外在它的書法中,墨色的變化也有虛實結合之美,用墨的程度也能體現線條的“潤”和“枯”,字體之間的牽拉則表現出一定節奏。縱觀王羲之所有作品,他對于墨色處理十分微妙,能讓后人明顯感受粗細線條變化給字跡帶來的改變,墨的濃淡讓整幅作品的節奏有一定變化,粗細的對比又突出了字體的明暗變化。在線條的處理上,不平直,有彎曲的處理會讓線條產生波動,字體空間的靈活性也會上升,線條的彎曲程度,遠近程度等都會影響字跡,不管是行與行之間,字和字之間,都會有不規則變化,這樣在不同的筆畫之間的過渡就會呈現不同的風格,通過不同的形狀展示出書法的獨特韻味,呈現出不一樣的靈活姿態,呈現出遠和近,連接與斷開的姿態[5]。
(1)亦剛亦柔的藝術風格,王羲之書法在后人看來無疑是書法史上的巔峰之作,他的書法境界也是后人望其項背的,后人甚至將其稱為“書圣”,主要是他“學于師”而又“高于師”,他的書法風格更多出幾分對自己領悟的沉淀。在后世評價王羲之書法中,觀點和看法也都各不相同,有一種被稱為“妍麗”的評價,這種評價更趨向于女性化,主要是王羲之咋走年拜衛夫人為師,對其書法風格產生一定影響,因此在王羲之書法中,能看到女性柔美的一面。在生態女性主義觀點之下,王羲之書法的“妍麗”更多出于師傅衛夫人,而在這種觀點中,將女性和大地、自然聯系到一起,在研究王羲之書法時,理解其“妍麗”的部分,更多是理解其書法歸于自然的獨特魅力。再追溯王羲之生平經歷,在他辭官縱情山水,追求逍遙自在其間的作品,更有幾分虛實相協的意蘊之美,他的《蘭亭集序》本質上就是關于和友人在山林聚會的記錄,不光有書法研究價值,更具備文學價值[3]。
(3)思想境界十分高尚,甚至可以說是儒道兼備,王羲之所在家族曾經亦是名門望族,這一大家族在魏晉時期已經逐漸衰敗,在這樣的家族中,對子弟培養更多的是基于傳統儒家思想,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曾大起大落,但是經過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重新被人們熟知。王羲之作為王氏子弟的一員,從小免不了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家族傳統思想以及各種思想的交匯影響下,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也會受到一定影響,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其不同心境,在《官奴帖》中,能夠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對其作品進行分析,這時人們的人生信條更趨向于縱情山水、豁達自然,這種思想影響了當時的一眾士族,王羲之自然也會受到這種思想影響,并且很明顯地出現在他后來的作品中,這時的書法既有文雅風范,更有“道”的飄逸,虛實結合[4]。
2.動靜相合的形態之美
(2)在對王羲之的一生進行回顧我們發現,他的人生其實是跌宕起伏的,他本人是追求高潔志向和遠大理想的,并且在為官期間他能做到體察民情,并且能夠肩負起為天下太平努力的任務,想百姓所想,立志為百姓謀一方天地,他心中渴望世界和平。但是無奈身處亂世,空有一腔遠大抱負卻無法實現,他開始意識到僅憑一己之力無法改變黑暗的現實,之后對官場產生厭倦,借病辭官從此不再涉足官場。在世人看來王羲之辭官是不得志之后的無奈之舉,但也是他開始書法藝術的開始。王羲之在歸隱田園之后開始研究書法,在經歷人生坎坷之后,他開始大徹大悟,并明白自己的理想寄托和現實之間的關系,這種轉變讓他的思想升華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這一點可以從其創作的書法中體現出來,并且能看出這個時期的他對理想有了更多參悟,這一時期的作品也充分體現了他的藝術靈感,這正是他在人生“虛”和“實”境界中的感悟。
基于學習者習得狀況的日語情態意義擴展研究 ………………………………………… 周 萌 游衣明(3.38)
(2)線條與布白,“線條”是書寫時產生的,也被稱為“動勢”,“布白”指的是不同線條在過渡的過程中對紙面的分割,是一種被動的形態審美。這里說的“勢”指的是書寫時候字的神韻,說寫字不能僵化和固態。書法作品在創作的時候雖然是趨于靜態的,但是站在藝術的層面而言,書法表達需要具有動態美,并且再好的書法作品要具有涌動的生命力。書法本身是一種文字的體現形式,作品經過線條、布局的調節之后打破原來的形態,才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美感。線條在書法創作過程中是運用最多的,線條能讓人產生空間分割感,并且這種空間的思考能帶給人們更多創作的靈感,能帶來之前從未有過的立體感。線條的變化讓原本的空間變得更加靈動,在書法創作中,作者不光要注重黑色線條的變化,對于白色塊面和線條也要運用的當,白色塊面也是字體構造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此為基礎進行書法創作,才能讓書法作品更加有空間感和線條感,產能讓那個書法作品具有靈動、趣味盎然的神態。不管任何風格的書法作品,它們在筆畫以及具體落筆上表現出來的感覺是不同的,姿態也各不相同,這種排列方式像小朋友排隊,前仰后合卻不失自由自在的風范,看上去充滿趣味。在具體的書法創作中,線條的排列要根據字體本身的結構而定,這樣寫出的字才能更加通透,不壓抑。把握好線條和布白。書法作品會更具有層次感,呈現“點”“線”“面”的和諧感,比如在王羲之書法作品《蘭亭集序》中,第一個字“永”,以擬人的視角來看,就仿佛一位謙謙君子,迎風而立,通過線條的不同布局,打造出人如書法,書法如人的畫面感。
3.陰陽相生的生發規律
藝術的發生講究“中和”,王羲之書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充滿了形態美,字跡的意趣和神韻也躍然紙上。我們研究藝術作品,更加要尊姓一種循環、辯證的藝術道理,這和生態美學中追求和諧是一個道理,只有遵循美學基礎的研究,才能不斷超越,發現書法的藝術真諦。萬事萬物均有一定共生關系,萬物均不可脫離自然追求自我成長,這也和生態美學提倡的宗旨一致。“道”講究陰陽相合,即“一陰一陽”。在魏晉時期,很多書法、畫作等都能演變成為后來的藝術作品,之所以有這樣的文化,主要是當時很多人士具備一定的學識沉淀和思辨能力,它們都有一種寄情山水、親近萬物的智慧。人類為了實現更好地發展,需要不斷放大自身力量,譬如曾繁仁教授的《生態美學導論》中所說的“人與自然的嶄新關系——從‘祛魅’到部分‘復魅’”。在科學技術和理性主義不斷發展的今天,經過近些年的發展,人們對于‘復魅’的反思也逐漸深入。除了魏晉朝,中國各個時代的作品都在追尋“從自然中來,到自然中去的”,王羲之書法之所以被后世所稱羨,就在于其作品有真正地把自己“歸園田”“返自然”的意境,呈現出陰陽相生的生發規律。生態美學的目標宗旨,即在于實現“綠色審美世界”和“生態藝術人生”的統一,王羲之書法符合了生態美學追求,呈現出了一種“生態”的藝術性[6]。
三、結語
總而言之,書法對中國文化影響十分深遠,基于生態視角下研究王羲之書法藝術,能讓后人對美學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分析王羲之書法藝術風格后我們發現,其藝術用筆可分為方筆與圓筆,而書法的藝術結字在表現上也是千變萬化的,正是這種變化讓每個字都具有不同神韻。基于生態美學視角而言,王羲之書法既具備虛實相協的意蘊之美,更具備動靜相合的形態之美,通過研究其書法作品,能讓人們感受到中華民族文化審美的藝術價值,并能為后世的書法藝術創作提供更多靈感,相關人員需以前人作品為榜樣,不斷為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