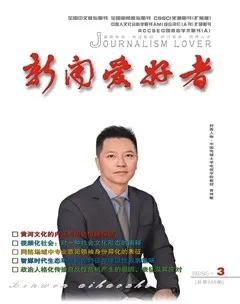“Z世代”數字化生存視域下大學生網絡輿論引導探究
端木怡雯 王麗娜 李睿
【摘要】以“Z世代”數字化生存為研究視角,探究了高校大學生數字化生存特征,具體體現為“趣緣化”社交取向與網絡社群圈層化,網絡輿論場重塑與公眾話語權回歸,個性化網絡參與與意見領袖的崛起和“在場”式傳播與沉浸式“狂歡”等四大方面。最后,提出要堅持弘揚主流價值觀,把握網絡輿論引導的主導權;要優化內容供給,把握網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要破壁出圈融圈,把握網絡輿論引導的話語權。
【關鍵詞】融媒體;網絡輿論引導;“Z世代”;大學生;數字化生存
“Z世代”(Generation Z)被學界普遍定義為1995—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們出生即與網絡時代無縫對接,已成為大學校園中的生力軍,身體力行地詮釋著“無人不網、無時不網、無處不網”的媒介化生存場景[1]。網絡繁榮極大地改變了傳統信息傳播格局和媒介交互生態,對“Z世代”大學生的思維認知、價值塑造與行為養成均產生了不容小覷的影響,同時為高校提升大學生的網絡輿論引導能力帶來全新挑戰。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強高校大學生輿論引導的實效性則成為亟待破解的現實難題。基于此,本研究擬從“Z世代”數字化生存特征入手,洞察高校大學生網絡輿論引導面臨的挑戰,并嘗試探究融媒體時代高校優化大學生輿論引導機制的實踐路徑。
一、“Z世代”數字化生存的現實樣態
(一)人以群分:“趣緣化”社交取向與網絡社群圈層化
興趣聚合是社群的基本功能,社會交往是社群的重要功能,而圈層化則充分彰顯了網絡社群的興趣聚合功能,并以實現“趣緣化”社交作為社交的主要方式為旨歸。在數字化媒介場域中,“Z世代”不再受制于物理世界的身份標簽和社會現實環境,而是基于一致性的興趣需求和個性偏好,同質化的價值觀念和話語體系,尋求“志同道合”的群體而集聚于共同的虛擬場域,進而構筑認同度高、代入感強的網絡圈層。圈層內部成為“Z世代”彰顯個性、價值認同與情感慰藉的重要場域,形成“同類聚集”的網絡社交文化景觀。譬如,在bilibili,“Z世代”會因同款游戲而加入家族,因喜愛同一本小說而成為“道友”;在“Melon”、微博等平臺,會為支持的偶像“買磚”“切瓜”(指為偶像歌曲打榜),進而聚集成線上追星社區等。無論是漢服熱、手辦潮,還是洛麗塔服飾和cosplay(扮裝游戲),抑或是電競和二次元,“Z世代”依賴于自身熱衷且熟知的“部落化”圈子以獲取信息、溝通情感、互動交流,在“趣緣化”的朋輩社交中形塑自我、深化認同,并建構形成前衛新潮的“Z世代”圈層文化。該圈層文化與生俱來的個性鮮明的話語模式、表達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習慣,有效迎合了Z世代“做更真實的自己”的強烈訴求,推動圈層文化呈現封閉、固化的趨勢,并不斷延展圈層文化內涵[2]。
(二)技術賦權:網絡輿論場重塑與公眾話語權回歸
數字技術的賦權,為公眾開辟了媒介信息自由傳播、情緒觀點暢快表達的廣闊渠道,網絡傳播格局日漸呈現出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分眾化、平民化、社會化等特征,傳統的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信息生產機制被消解,公眾被廣泛賦予能夠自由發聲的網絡話語權。網絡傳播模式的重大變革,打破了傳統的“輿論一律”模式,引發人類的傳播行為由單純的信息傳播轉向權力和關系重構,由傳遞、獲取轉向分享、參與。[3]網絡社會以其自由性、開放性、虛擬性等特質贏得了青年的關注和參與,尤其是社交新媒體的勃興儼然成為青年網絡社會參與和話語表達的新型陣地,網絡話語場演變為公眾交流信息的不設界的意見廣場[4]。“Z世代”作為“網生代”,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各大網絡媒介平臺的浸染和影響,借助于其先天具有的“網言網語”優勢,以及很強的互動、交流、表達、分享和社交的欲望[5],更容易在網絡輿論場中圍觀集聚并引發熱點,并且能夠根據媒介議程設置和社會邏輯框架來闡釋社會現象、表達個人觀點并作出價值判斷,甚至還會影響其身份認同、社會參與和個體的社會化進程。
(三)圍觀集聚:個性化網絡參與與意見領袖的崛起
Web2.0時代社交媒體的興起,最大限度地賦予了普通個體網絡話語權,增強了其意見表達和內容生產的能力,更激發了作為普通公眾的“Z世代”的參與熱情。社交媒體這種自我賦權的特點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學生在網絡輿論話語結構中的被動地位。[6]已有研究表明,大學生依托知乎等社會化網絡社區實現非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參與意愿較強的大學生群體呈現著互聯網依賴度強、內生性驅動力強以及圈層化符號性強等典型特征。[7]在知識生產泛化、知識傳播社交化、知識共享扁平化的網絡社會中,大學生只要對特別事件或特定領域擁有話語權,便可以在其中有效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通過對信息的解構和重構來實現信息或知識的生產,并借助社交化媒介完成信息傳播,并在特定場域中形成一定的影響。
(四)可視可感:“在場”式傳播與沉浸式“狂歡”
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短視頻不僅能夠自由轉發分享,還能夠實現實時評論,其場景營造和展示手段也更為多元立體,實現了“多中心”的實時互動和資源共享,成為廣受“Z世代”歡迎的資訊獲取、娛樂社交和意見表達的重要渠道。沉浸傳播通過“感官共振”與“形象還原”為受眾提供了一種“在場參與”的沉浸式體驗,彰顯了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價值。[8]在線直播在全社會風靡并作為一種亞文化在網絡社群形成熱潮,更成為大學生生活場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向互動、共同在場、深度參與、情緒共振的直播社交模式給“Z世代”營造了直觀的視覺沖擊力和身臨其境般的沉浸式體驗,娛樂、社交和求知成為其收看網絡直播的主要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Z世代”網絡社交的參與感和融入感。[9]
二、“Z世代”數字化生存視域下高校大學生網絡輿論引導的現實挑戰
(一)網絡不良社會思潮蔓延,削弱高校網絡輿論引導效果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導致了非主流價值觀在網絡中快速傳播,網絡生態龐雜叢生,非主流價值觀呈現滲透傾向,影響著主流價值觀的弘揚與傳播。隨著商業資本的涌入、網絡技術的支持和公眾焦慮情緒的宣泄,戲謔、惡搞、審丑、擺爛等泛娛樂化傾向逐漸抬頭,并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思潮,推動著公眾逐步進入了波茲曼提出的“娛樂至死”狀態。加之網絡媒介特別是短視頻媒介的迅速興起,泛娛樂化作為娛樂的“異化”進階,躋身國內十大社會思潮。“Z世代”正處于心理和生理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受網絡社會多元思潮影響,其身心容易呈現出相對矛盾且不平衡的狀態。長期以來,高校通過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弘揚主流價值獲得了較為理想的效果,大學生往往能夠樹立正確清晰的價值取向。然而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歷史虛無主義、拜金主義、極端自由主義等不良社會思潮也隨之在網絡輿論場蔓延。“Z世代”正處于價值觀養成的關鍵時期,不良思潮的傳播成為影響大學生思想觀念和價值選擇的重要變量。此外,自媒體的快速發展打破了主流媒體的壟斷地位,作為 “鮮明旗幟”和“絕對權威”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優勢逐漸被消解甚至旁落,高校主流價值引導正遭受嚴重沖擊。
(二)圈群文化建構“信息繭房”,圈層壁壘阻礙主流價值傳播
因共同的興趣愛好、風格志趣和價值立場等而集聚形成的圈層化的網絡社群,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往往能夠逐層過濾、屏蔽掉與圈群內部不一致的信息、觀點和價值觀,集體無意識地構建內容局限、渠道封閉的認知環境會逐步形成“信息繭房”。圈層內部的青年基于意見氣候感知的自我判斷與觀點選擇,如有某些意見、立場的偏向,他們在集體商議后會進一步強化既有的群體認同,堅持向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導致群體極化現象。這種群體極化思維導致圈層之間形成對沖、區隔和分裂,忽視、抵制甚至排斥圈外群體的不同意見,進而形成具有偏好度極強且難以融入的圈層文化。圈群里的青年人將網絡空間作為其獲取影響力、存在感和認同感的重要來源之一,甚至會在網絡平臺表達乃至宣泄自己對各種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極端情緒和消極態度。在網絡話語場“沉默的螺旋”效應下,圈群中的“意見領袖”能夠通過重復、感染、強化等方式來引導圈群的輿論導向和個體信息選擇。網絡圈群的高進入壁壘,給高校破壁入圈帶來極大阻礙。如若主流價值與“圈群”成員日常傳播和接受的主流話語和信息內容有差異,便極易導致主流價值被自動忽視或屏蔽。高校在“圈群”中網絡陣地是缺失的,輿論宣傳隊伍是缺位的,主流話語是失聲的。[10]
(三)現實網絡形象分化,大學生的“雙面人格”難以把握
“Z世代”的網絡形象與現實形象顯著分化,在真實社會與虛擬世界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呈現出“社會人”與“虛擬人”的雙面性特征。作為“社會雙面人”,“Z世代”能夠在網絡場域建構“另一個我”,其往往在網絡連接和斷掉的瞬間切換著不一樣的面具,且他們在不同的媒介社交平臺亦表現出異質性的參與特征。譬如,在微信朋友圈只發布寥寥數條的青年,可能會在微博平臺大量發帖;在QQ、微信、微博、小紅書等APP擁有大量粉絲的青年,現實中可能沒有幾個可以傾訴的朋友。在如今高度原子化的社會場景中,積極的網絡參與和媒介表達在較大程度上滿足了青年自由社交的內在需求和空虛迷茫的外在釋放。相較于實際人格,“Z世代”的網絡人格更加真實地展現了“Z世代”渴望博取關注的存在感和主導輿論走向的滿足感。因此,僅僅研究現實中的大學生群體的思想動態、行為表現仍具有局限性,更需要借助數字技術精準地捕捉網絡輿論引導對象個性化的社交特征與表達特點,從而有效增強輿論引導效果。
(四)信息獲取方式碎片化,排斥精深思維引發供給與需求失焦
網絡媒介的蓬勃發展和數字技術的快速革新,顛覆性地形塑著公眾的信息獲取習慣和媒介接觸模式。在“人人皆媒”的時代,公眾借助于技術賦予的網絡話語權,在網絡公共空間自由地進行信息的加工、生產、發布和傳播,網絡媒介信息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碎片化成為受眾獲取信息的典型特征。同樣,“Z世代”也容易被碎片化的媒介信息裹挾和左右,甚至自身也是碎片化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他們沉迷于淺表速覽所帶來的即時刺激和便利歡愉,久而久之形成了“快餐式”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容易將碎片化的淺層速覽誤認為是系統性的深度思考,陷入碎片信息的淺表化認知困境而排斥精深思維,甚至呈現出機械圍觀、懶于思考的畸形樣態。然而,傳統的高校輿論引導所供給的正向敘事往往具有思想深度,風格也更為嚴肅客觀,這就導致大學生對輿論話題的思考容易“蜻蜓點水”,較少作深層次、本質性的探究,有的甚至忽視挖掘事實真相和底層意蘊,進而陷入人云亦云的認知處境,這對融媒體時代高校網絡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挑戰。
三、高校大學生網絡輿論引導的路徑探析
首先,高校要堅持培根鑄魂,增強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啟智潤心的作用,從黨史學習教育、打贏脫貧攻堅戰等鮮活的“大思政課”教材中挖掘輿論引導的生動素材,以積極向上的主流價值賦能媒介場域,把正能量、高質量、有分量的主流文化融入大學生日常學習生活,增強他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
其次,高校要堅持示范引領,積極培養青年“意見領袖”。組建一支媒介素養好、媒介技術強的融媒體學生骨干隊伍,有效打造“自帶流量”的學生“意見領袖”,引領其成為學校溝通師生的橋梁。
再次,培育網絡媒介素養,引導大學生理性發聲。引導他們進行邏輯縝密、嚴肅認真的思考,有效區分理性表達與情緒宣泄的本質性差異,準確把握網絡輿論背后的立場觀點,引領其成為倡導主流價值的主力軍。
最后,高校要引導青年突破圈層對沖思維。積極引領大學生深刻認識到圈層中也有美好、正向的一面,而不應該是與“他者”隔絕對立的桎梏和枷鎖,圈層邊界的打破也不意味著喪失個性、獨立性和群體認同,真正優秀的圈層文化應該是有“圈”無“壁”,能夠實現圈層之間的良性交互。
參考文獻:
[1]鐘宇慧.零零后的“長大”:教化與內化互構的典型媒介形象呈現[J].中國青年研究,2021(3):5-12.
[2]王肖,趙彥明.“Z世代”大學生媒介化生存的審視與應對[J].思想理論教育,2022(3):90-95.
[3]葛自發,王保華.從博弈走向共鳴:自媒體時代的網絡輿論治理[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39(08):140-144.
[4]鄧鵬,陳樹文.網絡話語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論析[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9(9):103-107.
[5]高菲.Z世代的短視頻消費特征分析[J].新聞愛好者,2020(5):40-42.
[6]布超.社交媒體環境下大學生網絡參與的新動向及引導策略[J].思想理論教育,2018(6):84-87.
[7]李濟沅,孫超.大學生非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意愿研究:基于1159名在校大學生的實證分析[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2,41(03):64-74.
[8]李蕾.新傳播生態下主流媒體傳播力構建路徑探析:以中央級主流媒體二十大融合報道為例[J].新聞愛好者,2023(1):30-32.
[9]樂曉蓉.大學生參與網絡直播的實證分析及應對策略[J].思想理論教育,2018(2):76-80.
[10]葉荔輝.高校“網絡圈群”輿論引導的困境及路徑[J].思想教育研究,2018(1):135-138.
作者簡介:端木怡雯,同濟大學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宣傳處處長,副研究員(上海 200092);王麗娜,同濟大學宣傳處理論與輿情科副科長,講師(上海 200092);李睿,同濟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副教授(上海 200092)。
編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