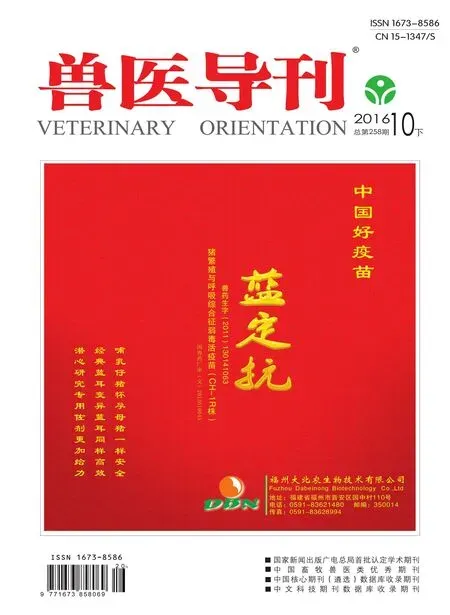淺析雞大腸桿菌病的綜合防治
謝安康
(融安縣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廣西融安 545400)
淺析雞大腸桿菌病的綜合防治
謝安康
(融安縣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廣西融安 545400)
雞的大腸桿菌病是近年來養雞業發病率最高、危害最為嚴重的疾病之一,是由不同血清型的大腸埃希氏桿菌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的總稱,由病原性大腸艾希氏桿菌引起的禽類傳染病,筆者對雞大腸桿菌病的發生、流行癥狀以及防治進行初步探討,以提供養殖戶參考。
雞;大腸桿菌;防治
1 發病情況
2015年10月,某肉雞場姓發病并有死亡的病例,用土霉素拌料和氟哌酸飲水進行治療,病情得不到控制。
2 臨床癥狀
病雞主要表現為精神沉郁,羽毛粗亂,雙翅下垂、厭食、閉目昏睡,腹部膨大下垂;排白色或綠色水樣稀便,糞便污染泄殖腔周圍;有的可見黃綠色糞便入紅褐色盲腸便,死亡率高,個別病雞單側眼流淚,結膜潮紅,眼瞪微腫。發病2~5d死亡。
3 流行病學及發病因素
3.1 病原病原體為埃希氏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是健康雞腸道內的常在菌,一般可分為致病性和非致病性兩大類。本病的病原體為條件性致病性大腸桿菌,一般當環境、氣候、飼養管理條件及飼料發生變化,雞的應激性增加時易引起發病。大腸桿菌的血清型很多,目前可根據菌體抗原(0抗原)和鞭毛抗原(H抗原)的不同,分成很多血清型。不同的血清型可引起同種或不同種的雞發病,不同的血清型對不同的抗菌素的敏感性也不相同。
3.2 流行病學探討
(1)條件性大腸桿菌是因條件變化而引起雞發病的,一般生活在健康動物體的腸道內,在衛生條件差、飼養管理不良、氣候多變(忽冷忽熱)的情況下,雞的應激性增加時很容易引該病發生。通常情況下大腸桿菌對環境的抵抗力很強,可附著在糞便、土壤、雞合內的塵埃和碎蛋皮等地方長期存活,成為養雞業難于消除的傳染源。
(2)雞大腸桿菌病對各年齡段的雞均能引起發病,但作為急性敗血型大腸桿菌病,20~45日齡雞易感性較強。該病在雞群中可水平傳播和垂直傳播,如帶菌種蛋在孵化過程中可出現死胎,孵化出的雛雞多為隱性感染;雞若遇到某些降低抵抗力的因素時,可通過被大腸桿菌污染的飼料、飲水、墊草、空氣塵埃等傳染媒介,以消化道、呼吸道、臍帶及皮膚創傷等途徑感染。大腸桿菌還可繼發或并發其它病原體性疾病,使病性更加復雜,發病死亡率增高。
3.3 發病誘因
(1)氣候因素晝夜溫差大,特別是一天內隨著陰晴變化而呈忽冷忽熱的氣溫反差,給雞生理機能的適應性帶來巨大影響。
(2)飼養管理因素一是廄舍的通風、換氣、溫控系統功能調節作用差;二是單位面積飼養群密度大;三是飲水不足或飲用不清潔的水;四是自然光照光線強弱變化快,差異大。
(3)不合理的藥物預防措施一是飼養戶從購進育雛開始,就使用各種藥物預防雞群發病,但往往是所使用的藥物一用到底,這樣做一是可能造成一些對該藥不敏感的菌群得以加快繁殖;二是破壞了雞腸道內菌群的相互平衡失調和產生拮抗作用;三是長期使用某一類抗菌藥物,易造成一些細菌逐漸產生耐藥性。
(4)生長發育因素商品肉雞由于生長發育較快(正常時45~60日齡可長到2~2.5kg)。導致龐大的機體與自身心血管系統的發育生長發育過快,而心血管系統發育慢,造成雞的心血管功能遠遠不能適應自身的代謝需要,超負荷運動,功能十分脆弱,極易受到更大損害,如嚴重的腹水等病癥。
4 防治措施
在日常生產中為避免發病,需要做好經常性的預防工作,減少或防止誘因的出現和發生,保持環境的清潔。要控制其發生,減少損失,必須采取如下一些綜合性防制措施:
4.1 加強飼養管理
對飼料進行合理搭配,保證禽所用飼料符合標準、飲水清潔,及時清除糞便等垃圾。飼料的采購、貯存和加工等環節要加強衛生管理。防止繼發感染以及病毒細菌和寄生蟲感染,嚴格按照獸醫衛生標準檢測。降低雞舍中NH3和CO2的濃度,保持良好的通風換氣,此外定期交替使用。污染嚴重或常發病雞場,要根據情況適當縮短消毒間隔時間,一般5~7d要進行一次徹底消毒。全進全出的飼養方法是預防該病的有效方法。可有效避免不同日齡、不同批次雞群間的交叉感染。同時雞群盡可能采用封閉式管理,這樣可減少或杜絕雞群與大腸桿菌的污染物接觸,防止本病發生。
4.2 疫苗接種預防
接種大腸桿菌疫苗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該病的發生。但因大腸桿菌血清型較多,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對已發生污染的雞場可以用分離的大腸桿菌菌株制作滅活菌苗進行免疫接種。
4.3 加強種蛋管理、建立健康的種雞群
大腸桿菌可因種蛋帶菌而垂直傳播,因此必須做好種雞群大腸桿菌病的凈化工作。對病雞不能留做種用,一律淘汰。另外,種蛋本身不帶菌,但由于撿拾不及時或者產蛋箱衛生狀況不良,使種蛋與糞便接觸而受到污染。因此,孵化場還須作好對種蛋的消毒,以減少種蛋污染,在種蛋孵前必須做好藥物消毒工作。如果有條件,種蛋產出后兩小時內應用藥物熏蒸消毒或用0.3%的過氧乙酸進行帶雞噴霧消毒,確保種蛋有最高的孵化率和健雛率。也可以對剛出殼雛雞在3~5日和4~6日齡分別給予2個療程抗生素預防。
5 結束語
在防治工作中,診斷是先導,只有及時正確地進行診斷,才能有效地把疫病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及時撲滅,盡量減少損失。如果只注重治療而忽視預防工作往往收不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因此對雞大腸桿菌病的防治應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綜合性防治措施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1] 寧秀云.雞大腸桿菌病的診治[J].畜牧獸醫科技信息,2012,(11):89.
[2] 楊廣德,楊輝,杜光波.草雞盲腸肝炎和大腸桿菌病混感的診治[J].畜牧獸醫科技信息,2012,(11):91-92.
[3] 張進亮.雞支原體和大腸桿菌混合感染的診治[J].中國畜禽種業,2012,8(11):149-150.
[4] 劉瑞磊.蛋種雞產前至高峰階段大腸桿菌病的防控[J].養禽與禽病防治,2012,(1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