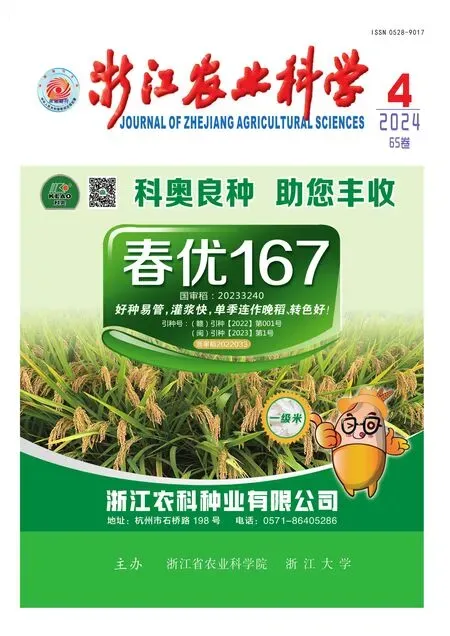新時代種業科技人才隊伍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
黃吉祥,游兆彤,王其飛,高聳,白永鑫
(浙江省農業科學院 作物與核技術利用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科技人才成長和農業科技工作,始終是習近平總書記關心重視的問題。2017年在致中國農業科學院建院60周年賀信中習近平同志指出“農業科技要面向世界農業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現代農業建設主戰場”。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海南考察三亞市崖州灣種子實驗室時強調:“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緊中國種子,才能端穩中國飯碗,才能實現糧食安全”。糧食是社稷之本,種業是糧食之基,因此建設一支高水平種業科技隊伍對種業科技創新意義重大。
本研究在參考相關研究問卷的基礎上根據種業研究實際情況和研究目標設計了一份種業科技人才隊伍現狀調研問卷,問卷分為三大模塊,包括調查對象個人基本情況、當前科研狀況和有關建議。調研問卷面向國家、省、地市農業科研院所中涉及育種工作的科技人才,并與部分科技人才進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調查通過“問卷調查星”進行線上發送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82份,其中男性128名,女性54名;26~30歲8人,31~35歲48人,36~40歲41人,40歲以上85人;正高級職稱19名,副高級職稱65名,中級職稱92名,初級職稱6名,調查數據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科學性。通過調研,了解種業科技人才的發展現狀,分析種業科技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及成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為進一步加快建設一支高素質新時代種業科技人才隊伍提供參考。
1 當前種業科技人才的現狀分析
1.1 種業隊伍總體情況
調查結果(圖1)顯示,在182名調查對象中,呈現出以下3個鮮明特點。

圖1 種業科技人才基本情況Fig.1 Basic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in seed industry
一是青年種業人才已經成為中堅力量。其中31~40歲的青年人群的占比達到48.9%;40歲以上的人群占比為46.7%;26~30歲的人群占比最低,僅為4.4%。
二是高學歷的中共黨員身份已經成為種業科研隊伍的主要特征。受訪人員中,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比例達到62.6%;整體受訪人群中,博士比例達63.2%,其中31~35歲的人群中博士比例達到了79.2%,36~40歲的人群中博士比例達到了73.2%(圖2)。

圖2 不同年齡段博士學位和中級職稱情況Fig.2 Doctoral degrees and intermediate professional titl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三是青年種業隊伍的職稱和收入相對較低。從職稱上看,40歲以下的科研人員中級職稱占主要部分(圖2)。其中36~40歲中級職稱比例是56.1%,31~35歲中級職稱比例是93.8%;以36~40歲之間的群體為例(圖3),年收入在20萬~25萬元的占29.3%,15萬~20萬元的占39.0%,15萬元以下的占19.5%。

圖3 36~40歲種業科技人才收入情況Fig.3 Income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aged 36-40 in seed industry
1.2 種業隊伍的科研狀態
從統計數據來看,目前種業隊伍在科研工作上主要有以下3個特點。
一是科研工作分工定位出現明顯分化。在40歲以下的種業科研人員中基本上以基礎研究為主,有78.4%的人主要從事基礎研究,41.2%的人從事田間育種;在40歲以上人群中,有48.2%的人主要從事推廣轉化、45.9%的人主要從事田間育種工作,34.1%的人從事頂層設計工作。
二是科研產出的年齡特征愈發清晰。40歲以下科研人員中有64.9%的人主要科研產出為論文,有11.3%的人科研產出以品種為主,有13.4%的人科研產出品種與論文兼有;40歲以上科研人員中品種與論文的產出相對均衡,有34.1%的人科研產出以品種為主,有27.1%的人科研產出以論文為主,31.8%的人科研產出品種與論文兼有(圖4)。

圖4 不同年齡段種業科技人才科研產出情況Fig.4 Research out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in seed industry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三是單位內部對科研人員的經費支持重點明確。高級職稱人員中有20.2%的人入職以來獲得單位內部支持的經費100萬元以上,有26.2%的人獲得單位內部支持的經費在10萬~25萬元 (圖5)。中級職稱及以下人員中入職以來有44.9%的人獲得0~5萬元科研經費支持,有20.4%的人獲得單位內部支持的經費在10萬~25萬元 (圖5)。

圖5 單位對不同職稱人員經費支持情況Fig.5 Funding support from academies for personnel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titles
1.3 種業隊伍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是種業隊伍面臨的挑戰共性與個性并存。針對品種選育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受調查的男性科研人員中,35%以上的人認為選育技術過于傳統、一線育種工作人員收入低、種質資源多樣性不足(圖6)是當前品種選育存在的主要瓶頸;在受訪的女性科研人員中,有40.7%的人認為是品種選育團隊過小,38.9%的人認為是團隊成員之間合作不足,31.5%的人認為是種質資源多樣性不足(圖6)。針對種業科技人員當前面臨的最大的困難,40歲以下的人群中,有74.2%的人認為是項目爭取,69.1%的人認為是高水平SCI論文發表,58.8%的人認為是薪酬過低;40歲以上人群中,有81.2%的人認為是項目爭取,52.9%的人認為是高水平SCI論文發表,61.2%的人認為是考核體系(圖7)。

圖6 品種選育上存在的主要問題Fig.6 The main problems in variety selection and breeding

圖7 種業科技人員面臨的最大困難Fig.7 The biggest difficulties fac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in seed industry
二是種業隊伍面臨的巨大挑戰是項目爭取困難。導致項目爭取困難的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首要原因是科研項目過多向優勢團隊聚焦,受調研科研人員中,有70.88%的人認為當前重大科研項目過多地向中央級科研單位集中,特別是一部分地方特色鮮明,應用導向明確的項目,省級科研單位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第二個原因是研究基礎不夠。從調查數據上看,62.64%的受調研人群把這個原因列為最重要因素;有34.07%的受調研人群認為導致項目爭取困難第三個原因是研究團隊之間合作不夠;此外,認為是硬件條件支撐不足、對科研申報信息了解過遲、科研管理部門服務不到位、其他等原因的依次占受調研人群的24.73%、20.88%、10.99%、8.79%。
三是當前品種推廣轉化競爭非常激烈。受調研人群中,有62.09%的人認為主要原因是品種市場競爭力不強,54.40%的人認為當前品種同質性現象突出,還有41.76%的受調研人群認為品種轉化后留主要科研人員獎勵部分過低;此外,單位宣傳力度不夠、農民不愿意有償試種、種業公司推廣力量不強、管理部門不愿意幫助推廣及其他問題依次占受調研人群的26.37%、20.33%、16.48%、8.79%和8.79%。
2 種業科技人才培養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根據上述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的種業科技人才現狀,我們針對性地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2.1 種業科研的目標導向與人才考核的學術導向存在不一致性
人多地少是我國最大的國情,十幾億人口要吃飯,我國每年大量進口農產品,糧食供求總量始終處于緊平衡狀態[1]。浙江在這個方面問題更為嚴重,浙江人口超6 500萬,人均耕地僅200 m2,浙江省目前糧食自給率僅26%左右。浙江作為全國第二大糧食主銷區,在人多地少、人增地減的形勢下,穩面積穩產量難度大,糧食保供壓力巨大[2]。因此政府對種業工作的重點依然是在增量上做文章,在單產上挖潛力。然而當前農業科研院所對育種研究隊伍考核的需求導向、問題導向意識不夠,比起種子的市場價值更加重視學術價值[3]。在調研中我們發現“破四唯”和“立新標”突破口尚未完全打開,“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人才考核傾向沒有根本性改變。有些科研人員反映,省里現在對破解“非糧化”、“非農化”要求非常迫切,市場對適應多熟制的新品種需求量很高,目前重點是在品種選育上取得突破,而實際上當前人才考核多以課題、論文和成果獎勵為導向,對品種選育、品種育成后的成果轉化和推廣應用的關注較少,脫離了產業需求,如果人才考核還停留在一些學術指標上,甚至是“一把尺子量到底”,會導致一些能出品種,出好品種的種業科研人員的創新工作積極性受到極大壓抑和挫傷。
2.2 種業科學研究團隊分散,種業企業創新力不強,種業育繁推脫節
從全球發展態勢來看,種子產業已由小規模分散化向大規模集約化轉變,種子生產和銷售的集中度顯著提高[4]。發達國家的種業企業的科技創新貫穿于整個產業鏈的上、中、下游。上游的創新主要包括種質創新、品種選育、育種方法、分子生物技術等;中游的創新主要有制種技術、種子生產、種子檢測、種子加工等;下游的創新主要集中于試驗示范網絡、產業化基地、科技培訓、科技服務等環節。建立了從“實驗室-人工氣候室-智能溫室-田間”呈流水線式的規模化運作方式和集研發、加工、銷售、服務為一體的高效產業運行體系。而我省目前的種業科研一方面受農業自身的遲效性、高投入、低回報等特點影響,導致高層次人才引不來、留不住。近年來,科研單位、項目負責人被賦予了更多自主權,科研團隊內部和科研團隊之間受個人利益最大化目標驅動影響,存在“單兵作戰”或“互相封鎖”現象,各自自主發展,難以結成協同的種業創新網絡和高效能的創新系統,導致存在大量的重復性工作和研究。這不僅破壞了良好的科研環境,而且不利于集體智慧的發揮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科研氛圍形成,難以做到真正激活科技人才隊伍整體的積極性、創新性,從而無法共同攻堅克難,發揮團隊力量[5]。另一方面,目前種業一般運營模式是體制內科研人員從事農作物品種的選育,然后將品種轉讓給種子公司生產包裝,最后由種子公司或個人進行市場經營。但是從事育種的科研院校不從事市場化運作,不了解市場需求;從事生產、銷售的種子公司參與創新不足,并沒有品種研發的能力,而且往往是將種子售出后并不注重種子的市場推廣,也沒有深入了解農戶的需求,造成種業育繁推相互脫節的現象嚴重。
2.3 種業企業追求短期效益與種業科研需要長期積累之間存在矛盾
我們在調研中也注意到有16.48%的受訪對象認為種業公司推廣力量不強,26.37%的受訪對象認為當前對品種的宣傳力度不足,部分種業公司人員和科研人員雙方的互信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科企合作的“剛性”和“黏性”需要進一步加強。自2022年新《種子法》頒布并實施以來,種業“放管服”政策不斷出臺,品種審定渠道變寬、試驗周期變短、多種審定標準分類以及引種備案制度實施,導致市場上的品種數量急劇增加,出現了階段性“井噴”現象。僅“十三五”期間,我國就審定了各類型品種1.68萬個,其中審定的品種中種業企業占了近一半。但與此同時,審定品種質量遠遠沒有跟上品種數量,農作物新品種同質化問題突出,新審定品種在產量、品質、抗性、生育期等方面沒有明顯差異[6]。其中主要原因是多數企業急功近利的思想比較重,希望快出成果,品種研發上“模仿育種”問題嚴重,缺乏資源創新能力,種質資源的全面系統鑒定、發掘、創新不足,突破性和優質原創品種不多。相反,新品種的形成要經歷復雜漫長的過程,品種的選育工作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而多數科企合作的時間一般是3~5年,在這么短的合作時間內育出品種是比較難的。即使在合作期間產生了成果,歸根結底是科研人員用國家投入的大量財力和物力而形成的積累,如果作為合作的成果,知識產權需和企業一起分享,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要報成果獎和晉升職稱,這些問題達不到妥善解決就會產生意見和糾紛,直接影響科企雙方合作進一步發展[7]。
3 建設高素質新時代種業科技人才隊伍的建議
針對種業科技人才隊伍當前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分析,我們認為應該從優化種業科技人員的考核評價機制,尊重種業科技人才自身成長規律,理順科企合作利益機制等三個方面積極落實、謀劃相關舉措。
3.1 尊重種業科技人才成長規律,進一步優化考核機制
育種研究需要理論的支撐和引領,同時又是經驗科學,需要科研人員通過長期在田間地頭,埋頭苦干,不斷積累、訓練、提升自己的選擇眼光。因此種業人才既有普通科研人員的共性,也有種業科研的特殊性。為此,我們一方面要鼓勵科研人員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耐心,另一方面要有“雪中送炭”的氣度,精準分析不同年齡段種業科研人才的不同需求,“對癥下藥”。在制訂種業科研人員的考核政策上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既要考核科研人員工作以來取得的業績數量,更要考核該業績對社會的價值和貢獻。對種業科研來說,首先要考核的是品種的推廣面積大小,如果是雜交種子,則考核受讓企業的銷售額;其次要考核相應的育種方法是否成熟,具體是應用了此方法后育成相應品種的數量和推廣面積大小。二是既要考核科研人員的個人業績也要考核團隊業績。當今社會,科技創新更加強調跨界融合、學科交叉。團隊成員對內是否協調創新、團結一致,對外是否積極交流、共同協作,往往對科研工作的成功和大成果的凝練至關重要。因此,在業績考核時,應當將團隊內部合作情況融入有關條款,特別是在重要論文或者重大成果的業績計算時,應適當提升本單位除主持人外前二位的團隊成員分值。三是既要考核科研人員的品種競爭力也要考核技術支撐能力。世界先進種業已進入到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信息技術相結合的育種 4.0 時代,我國仍處在以雜交選育和分子技術輔助選育為主的 2.0時代至 3.0 時代之間。因此品種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水平的競爭。要重視作物種質資源儲備,充分挖掘作物高產、高抗和營養高效等重要基因和性狀,加快發展現代生物育種的底層技術的突破[8]。
3.2 突破育繁推一體化瓶頸,進一步細化利益分配機制
實質性的育繁推一體化需要在三個方面下真功夫:一是加強種業人才的雙向培育。種業科研院所要重視對人才的開發與引進,增強自己的人才儲備量,不僅需要與種業企業聯合培養起一系列科研骨干和學科帶頭人,還要相應地提升高水平種業科研人員。另一方面要加強對人才的培養與激勵,要鼓勵科研人才下基層鍛煉,探索推動種業人才在院所企業間的流動機制,在實踐中提高創新意識,以創新轉化和市場評價為指標,明確高水平論文的應用前景。企業必須建立自己的科研育種團隊,或是通過整合資源,與科研院所、高校等合作對新品種進行培育,在企業成為種業創新主體之前的過渡期,與這些科研實力強大的科研育種平臺合作是保障種業具有競爭力的必然選擇。二是加快突破知識產權保護、評估、分配機制。完善品種保護機制,維護品種權人利益加強對知識產權的宣傳,加大對《種子法》、種子認證制度等法律法規的普及。大力保護創新,激發種業科研人員的創造性與積極性,促使種業可持續發展。完善種業科研成果評估體系,構建成果價值分析評價體系,對農作物新品種、品種權及優質高效配套栽培技術的價值進行科學合理的評估,形成與品種實際價值相對接近的定價模式。完善獎勵激勵機制,落實科研成果使用、處置、收益管理、科技人員股權激勵、人才分類評價等制度機制,以及知識產權轉化獎勵收入稅收政策和股權激勵政策[9]。三是加快基于產業鏈的育繁推一體化模式。以種業發展的整條產業鏈為主,完善各方面利益分配機制,加強產業鏈中各個部門的聯系,促進研發、育種、推廣、監管一體化,最終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科研、管理為輔的種業管理模式。
3.3 完善“科企合作”政策支撐體系,進一步吸引企業加大育種研發投入
種業育種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具有研究周期長、積累多、成果產出慢等自身規律,一般需要8~10年才能培育出一個新品種,目前科研院所、高校依然是種業科技創新的主力軍。開展種業科技交流與合作是提升種業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有效途徑[10]。推進科企深度融合,提高種業公司和科研單位的“剛性”和“黏性”,一方面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以政府投入經費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在科技投入上融合科企育種創新工作;另一方面打造科技聯合體開展育種攻關,探索企業“出題、出資”,農業科研機構或高校“答題”模式,科企共同搭建技術研發平臺,打通種業成果轉化通道,按市場需求推動育種發展,加速種業科技成果向企業轉移,緩解種業企業追求短期效益與種業科研需要長期積累之間的矛盾,穩定種業育種研發工作、團隊和種業人才,進而激發種業人才活力。
當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種源安全已經被提升到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保障糧食安全,就要抓住種子安全,意味著就要全方位加強育種科研人才隊伍建設。為此我們要積極采取相應政策,吸引和鼓勵人才投身育種科研。制定更加適應育種科研特點的考核和績效管理辦法,讓有志于從事育種的青年人才安心做科研,愿意把畢生精力投入到育種事業,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從根本上解決種業“卡脖子”問題,培育出更多更好的農作物新品種,把中國人的飯碗端得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