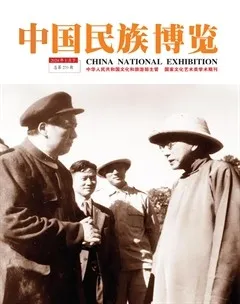我國鄉土電影中的人情禮俗及社會秩序
魏文驕
【摘 要】鄉土電影作為記載我國禮儀習俗、地緣特征的特有類型,通常在敘事文本中融合著人情關系、臉面觀念及心照不宣的權力生產,并在其熟人社群中延續發展至今,是展現我國文化傳承、社會變遷過程中重要的動態圖景。
【關鍵詞】鄉土電影;人情關系;面子;社會秩序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02—014—03
鄉土、鄉村、農村電影作為現實主義題材中的一具象空間表達,約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在我國語境下,電影的“城市性”結合了“中國社會的鄉土本色”[1],可以說鄉村電影的存在前提是鄉土,也可以說鄉土電影是大于鄉村電影的概念范疇,“農村”與“鄉土”。雖然它們的共同所指都是中國鄉村,但在幾十年的文化實踐和文藝批評中,這二者卻意指著不同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內涵,包含不同的價值取向。鄉土似乎更多聯系美好的自然風光、淳樸的民風民情,而農村似乎聯系著貧窮、落后的社會學意義、守舊的文化以及階級斗爭和社會變革等意識形態方面的色彩。因此可以說“鄉土”可以歸入文化層面范疇,而“農村”則是政治意義上的概念。[2]基于以上考慮,采用“鄉土電影”的說法。
鄉土電影發展至今雖衍生出了較為豐富多樣的流變形態,但其仍未跳脫出現實主義母體,經由長期依存孕育,發展出諸多結合了地緣特征及民族特色的影片架構,當我們討論地緣與民族時,兩者的共性一定程度上同樣可用“土地”來指代。“土”的本義為土地又指土壤。而在《周禮·地官司徒》中的土地觀念首先表現為對土地這一自然綜合體的整體性認識。[3]在《詩經·北山》中曾提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由于在周要將土地經過等級分封,封出的土地為“邦國”,邦國管理者為“侯”,諸侯即諸多的侯,而邦國的土地再經由二次分封為“家”,故土地不歸“王”所有的,而是根據層級步步劃分,有王、侯、卿大夫、士、平民。基于層層分封,該概念從宏觀指向微觀,“土地”亦可引申為家鄉、生存空間、本地的、地方的,而具體的物理空間衍生出了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對話交流方式,所以可引申為出自民間、當地習性等。此外,在“土”的諸多釋義中,有一條釋義為民俗的、非現代的、不合潮流、過時的。尤其在現代社會激速發展的進程中,陌生化的社群在生活中習以為常,因為陌生,所以需要相對應的具象法理進行約束,故而現代社會或者說城市更以法理社會為主體,“曉之以理”的硬性約束占據更大的比例。而在鄉村則反之,不可流動的土地代表著固定、熟絡的面對面社群,人們生于斯死于斯,往往由長者掌控相應的禮儀規則,出現了諸如鄉紳、族長這樣約束力度近似官職又不同于官職、地位身份類似于村民又高于村民的稱謂,他們往往借助村落中約定俗成的行為秩序,進行人們道德情感層面的軟性約束,“動之以情”占據更大比例。追溯其源頭可以說是我國影響深遠的宗法制建構了這種特有的秩序,所謂宗法制指的是關于確立、行使和維護宗子權力的各種規定。儒家所建構的天然血緣與地緣關系同樣長期參與著我國社會的軟性建構,可以說是一種依托著信任關系的地理空間格局關系。因此在我國鄉土電影中,血緣、親緣、地緣可以將信任關系的強度順位排列,由于地緣關系脫離切實的親情關系,敘事的起始、人物的往來則依托著我國集體主義思潮下的人情關系與臉面觀念等來推進。
一、熟人社群中的人情建構及信任關系
在我國鄉土電影中禮俗現象常以不足為奇的方式出現在敘事的瑣碎片段中,我們約定俗成、習以為常,而西方觀察家則指出另一種社會現象——“人際關系”,認為給禮和其他互惠交換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尤其在維持、再造和改變人際關系中發揮主要作用。[4]我國學者翟學偉認為真實的中國人際關系是由“情”“倫”“緣”構成的三位一體,只有系統地研究這三者及其相互關系,才能看出中國人際關系的本質。我國人際關系的構成基礎,從“情”“倫”“緣”中大致可以獲得相應的認知,即天命觀、家庭集體主義和儒家為中心的傳統倫理思想。在吳天明導演的《百鳥朝鳳》中,影片開頭游天鳴的父親帶領游天鳴,跋山涉水從土莊趕去焦三爺所在的水莊拜師,與焦三爺的對話為:“哪個村子的?”“土莊,游樹華介紹來的,我堂哥,土莊的村長。”后在藍玉來拜師的時候同樣帶著禮品,通過對藍玉氣力的考驗,藍玉父親微躬腰道“您就收了他吧!”從兩位徒弟拜師中可以看出,焦三爺作為無雙鎮傳承嗩吶的匠人,雖生活在水莊,但是德藝雙馨的品格在整個無雙鎮頗具盛名,上文提到儒家精神中的軟性約束,而焦三爺的人物形象正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典型書寫,焦三爺能夠獲得無雙鎮所有人的贊譽離不開自我的修身,當土莊村民聽說游天鳴成為了焦三爺的徒弟時,榮譽感也油然而生,尤其是游天鳴的父親倍感自豪,“長臉”“長面”。
在影片《百鳥朝鳳》中,無雙鎮是一個總體性的生活大場域,金木水火土五個村莊則是五個微型生活場域,包含與被包含的地理位置使得其人際往來需要借助于某種親緣、地緣關系才得以搭建。除了《百鳥朝鳳》外,《黃土地》《白鹿原》《人生》《小武》中同樣存在類似的搭建。在電影《小武》中,小武與靳小勇本就存在較為深厚的交情,靳小勇脫離了過去消極頹靡的生活后想要割裂以往的人情關系,所以他結婚時未通知小武。小武知道靳小勇結婚后基于從前的關系送了禮金,而靳小勇的拒絕就代表著他們的情誼不再互欠,親密關系也就此止步。“親密社群的團結性就依賴于各分子間都相互的拖欠著未了的人情”[5]。這種人際關系的搭建已然打破了某個地區的村落范圍,在整個地域環境中都約定俗成:由人物引薦建立聯系,再通過送禮贈予,建立聯系,再將此時的弱信任關系轉化為強信任關系,從而達到辦成某件事或提供某種參考的最終目的。
依據社會學理論中的人緣、人情和人倫構成的三位一體來解讀,在日常的行為準則里,人情始終居于核心位置,同時在社交習性中人情往往不以對等的形式出現,若即若離的人情牽絆才能使得關系進入長久的延續,當《百鳥朝鳳》中焦家班傳承為游家班,外來文化的傳入,傳統技藝難以維新,嗩吶班逐漸在時代浪潮中分崩離析,往日嗩吶班班主坐太師椅的威望不復存在,游家班的成員難以依靠嗩吶技藝維系生機,對嗩吶的熱愛也在日復一日的冷板凳中消失殆盡,在這里焦三爺為傳統民俗的傳承焦慮以及游家班精神世界的坍塌感到無比痛心,癡笑怒罵中再一次支撐起了嗩吶的演奏,竭力延續著嗩吶民俗的生命線,孕育了嗩吶民俗的農耕文化同樣也滋養著倫理綱常,他們怕師父、尊師父,父與傅的雙重教導使得焦三爺對徒弟們有著無形的壓迫感、震懾力。人倫本是承襲的制度規定,在人倫關系中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服從、認同的。影片中的游天鳴拜師學藝的契機是為了滿足父親未遂的嗩吶匠之夢,幼時的他跟隨著父親踏上了這樣一條讓父親欣喜滿意的道路,也因父親摔倒時游天鳴的關懷與熱淚,使得焦三爺愿意接納他并傳其衣缽。而人緣則將人與人的一切關系都放置在本土化的說法中,我們將某個社群中親疏關系的遠近、對具體事務建立聯系的能力稱作人緣,這僅僅是一種說法,沒有歷史因素的承襲。故而在鄉土電影中,因為社群之小,人情、人倫與人緣則共同構建著囊括了情感、秩序、規范的自然則律。
二、熟人社群中的臉面觀念與秩序建構
中國社會是一個講人情面子的社會。從儒家的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儒家所講的人情同心理學里所講的情緒和情感幾乎沒有區別,其原意指人天然的和自生的感情,即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6]當人情中含有了理和義的成分后,人情的意思就發展成了中國人的主要交往方式。其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結合出來的原則就是《禮記·曲禮》上所說的“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7]。而臉面觀如此受到中國人的重視,是因為它的運作方式同情理社會相契合,這種社會中的人在行事的時候總是力圖在情理上找到一條平衡的中間路線,并通過同情心的方法獲得特殊主義向普遍主義的過渡。
魯迅在《說“面子”》一文中提到:任何身份都有“面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臉”。這個“臉”是有一條界限的,如果落到了這條線下面,那就是丟失了面子,簡稱“丟臉”。[8]“臉面”在我國的含義在諸多俚語中屢見不鮮,如“樹有皮,人有臉”等,往往代表著一個個體在生活社群中的人品、地位。在電影《二嫫》中,村婦二嫫為贏回臉面以及相匹配的村落地位,為了買一臺價值昂貴,有收入的縣長書記也支付不起的大電視機而拼命掙錢乃至賣血,最終導致身體虛弱、勞累過度,在此同樣可以看出臉面對于二嫫的重要性。電影《Hello!樹先生》中表達出了貧苦農民在貧富懸殊的臉面尊嚴以及其城鄉發展選擇上的困境。在電影《三峽好人》中,沈紅為尋夫,找到了郭斌的朋友東明幫忙,愿意幫忙以及相應的舉措也是因為給郭斌面子,而在許多電影中面子觀念與人際關系的搭建也密切相關,“給面子”一定程度上能夠推進事件的進度或者提供了“門路”。比如在《落葉歸根》中,講述了農民工老趙跟老劉進城打工,最后老趙帶領因工傷死亡的老劉的尸體返回農村的故事,在該片中,老趙與老劉真摯樸實的情誼相對弱化了臉面觀念,但在途中遇到養蜂人和他毀容的妻子時,通過對話不難發現臉面觀在此成為了他們生活中無形的束縛,因為臉面觀和尊嚴感他們選擇在人煙稀少的地方養蜂,脫離人的社群。
在以鄉土為表現空間、以文學作品為改編文本的電影中,也多會出現以村落、家族等熟人社群中的關系呈現,如《白鹿原》《黃土地》,尤其以我國第五代導演的鄉土美學風格為主,拍攝場景多在以自然村光為主的西部地區。電影《白鹿原》對整個陜西關中地區白鹿原上白鹿村的鄉土社會進行了描寫,該片以白嘉軒為敘事核心,白鹿兩家矛盾糾葛組織情節,以反映白嘉軒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倫理道德,在時代變遷與政治運動中的堅守與頹敗為敘事線索,講述了白鹿原村里兩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間的故事。在該片中,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以家族和村落為中心的社會生活、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并涉及民間價值體系等構成中國人社會關系基礎的內容體現較多。長期的農耕性與聚居性的家庭生活要求人們在彼此面對面的關系上將“情”而非“理”作為日常生活的核心。宗法制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父系家長制為內核、以大宗小宗為準則、以仁義為精神要義、按尊卑長幼關系制定的封建倫理體制。[9]在白鹿村這樣一個以族長為中心的村落,不論在日常生活還是重大節日,族長都有權利把全村的人聚集起來,在小說文本中提及到的“白狼之災”“誦讀《鄉約》”的事件,都無一例外的說明了族長是白鹿村的精神意識領袖。在這種原始集體主義下,人們只能依靠系族群體才能使白鹿原人歷經災難卻又不衰。與此同時,要穩定宗法制度的地位就要通過修建祠堂來進行具象體現,同時也是秩序建構的外在形式。黑娃在《白鹿原》中,被塑造為一個具有反抗精神的角色,這就能夠清楚地看出來修建祠堂的作用。儒家的“仁”“禮”蘊含在《鄉約》中。族長白嘉軒作為《鄉約》最固執的實際操作者,也是儒家文化忠誠的傳播者。他要求村民們在背記同時學習《鄉約》的內涵并付諸實踐,必須按照《鄉約》言行。在影視作品中,白嘉軒帶領村民讀《鄉約》,《鄉約》成為白鹿村的精神意識領袖,帶領了村民走向忠誠和善意。從《鄉約》里面的措施在村民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三、結語
鄉土電影作為我國鄉土社會的影像縮影,蘊含著中華文化五千年來約定俗成的民俗特征、秩序觀念以及地域環境,其創作內容旨在呈現真實、生動的農村畫面,深入探討農民的心理狀態、家庭故事和社會問題。中國鄉土電影發展至今也演變出了非常豐富的故事內核,費孝通曾說“我們不妨集中注意那些被稱為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10]諸多鄉土電影例如上文提到的《百鳥朝鳳》《白鹿原》等都通過真實客觀、留白化的敘事結構和小人物細膩入微的情感描寫,展現了鄉土養育的群眾百態,或是堅韌、或是寂靜、或是苦難、或是追尋。鄉土作為我國電影體系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我國詩意化影像的重要表現對象。
我國鄉土電影的源泉來自國人本體的血脈相連及生命召喚,同樣在國際語境中的文化自信傳播中也有著重要的價值意義。我國鄉土電影從創作的角度來看,約定俗成、潛移默化的社會交往方式作為鄉土電影在表達與呈現時重要的構建依據往往和鄉土空間中的民俗文化、地域特征、人物形象交叉融合出現在影片創作中。從觀看的角度來看,我國鄉土電影中的人情禮俗及社會秩序以靜默觀看、息聲體會的方式棲息于每一個本土觀看者心中,鄉土電影通過影像對抗當下對鄉土的遺忘,基于此,我國鄉土電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和反饋鄉土生活及其變遷的動態窗口,作為極具本土民族特色的電影類型, 鄉土電影值得更多的人去思考研究其中的文化內核。
參考文獻:
[1][5][10]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凌燕.回望百年鄉村鏡像[J].電影藝術,2005(2).
[3]肖樹文,茹英杰.關于《周禮·地官司徒》中土地觀念的研究[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2).
[4]馬歇爾·莫斯.禮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7]胡平生.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22.
[8]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9]張景忠,李金秒.試論《白鹿原》中的民間宗法制[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