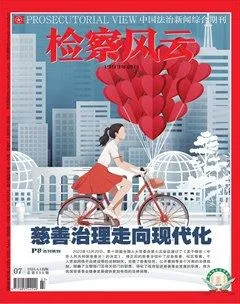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慈善法》規制
孫伯龍

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將于2024年9月5日起施行,其中規范對個人求助行為和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條款,引起了各方廣泛關注。結合近年來“輕松籌”“水滴籌”等個人求助平臺迅猛發展并產生的一些問題,本次《慈善法》的修改是對慈善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回應,也是對基于惻隱之心幫助特定受益人的行為的法律認可。由于個人求助與慈善公益活動有本質區別,個人求助部分并未出現在慈善捐贈、慈善募捐等章節,而是放置于附則中。那么,這一條款具體如何細化落實,如何讓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真正得到規范與健康的發展呢?
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興起?
在本次修法的背后,是我國個人求助平臺近十年的發展。自2014年9月,輕松籌上線以后,愛心籌、水滴籌、悟空籌、無憂籌、360大病救助等個人求助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與慈善組織的公開募捐相比,個人求助依靠社交媒體快速傳播,更容易觸及群眾,有額小量大的特點,為個體籌措大病救治資金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因此,其在緩解患者家庭困難、防止因病致貧返貧等方面有著顯著的成效。
毋庸置疑,個人大病求助平臺已成為目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有益補充。在過去幾年間,遭遇重病卻無力支付高額醫療費用的人,已經習慣了到個人求助平臺上尋求捐贈。2022年10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等機構發布的《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平臺研究報告(2022)》顯示,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9月至2021年底,累計超過500萬人次大病患者通過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發布個人求助信息,超過20億人次通過各個求助平臺捐贈資金,籌款規模超過800億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3月31日,水滴籌累計向286萬多名患者家庭、籌款共計約584億元,輕松籌已累計幫助253萬個家庭、籌款超過255億元。
從社會公眾的普遍認識來看,個人求助網絡平臺規模大、范圍廣、不收費,是一種具有公益屬性的捐助活動。但是從法律層面而言,個人求助是一種互幫互助,屬私益慈善,個人求助平臺的運營主體在性質上不屬于慈善組織,而屬于“營利法人”,在個人求助平臺上不論是募集方還是捐贈方,在捐贈時都明確受益方是某個特定的個體,因而這類活動尚不屬于“慈善募捐”。許多慈善組織通過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為個人大病救助發起募捐,這類公開募捐活動涉及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個人……為規制網絡募捐活動,《慈善法》出臺時就制定了“公開募捐信息平臺”條款,但是個人求助平臺與公開募捐信息平臺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也就造成對個人求助平臺的規制處于法律灰色地帶。近些年來,在愛心籌、輕松籌和水滴籌等網絡籌款平臺的助推下,個人求助比傳統慈善活動更加活躍、涉及人群和資金更加龐大,由此引發的問題也更加突出。
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亂象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迅猛發展和移動智能終端的全面普及,我國網民數量已達10.79億人,個人大病求助也逐漸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網絡)社會。據調查,個人求助大概36%的救助資金來自求助人的親朋好友,有64%的資金來自籌款鏈接,即陌生人的捐贈。從互助共濟、保障民生的角度來看,個人求助網絡平臺已不止于對個體的幫助,其已經成為我國多層次社保制度中的重要補充。以往,由于我國并未將個人求助網絡平臺行為納入《慈善法》的規制范疇中,造成了行政監管和司法實踐中無法可依,隨之而來的是個人求助平臺中的騙捐、收費、中介推廣等情況層出不窮,對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首先,是騙捐屢禁不止。2018年唐某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一氧化碳中毒為由,在某求助平臺發起籌款,后經警方偵查,唐某所披露的病歷、身份等多項信息系偽造,求助的文案內容系抄襲平臺某真實案例,預留的手機號則是網絡虛擬號碼。再如,莫某為患重病的兒子在某互助平臺上發起個人求助籌款,卻隱瞞家庭財產和其他社會救助,后被舉報,籌款平臺將其訴至法院要求返還籌集款。2019年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莫某違反約定用途將籌集款項挪作他用構成違約,法院判決莫某全額返還籌款15萬余元并支付相應利息,這也是我國首例網絡個人求助糾紛案。此外,各種偽造病歷、隱瞞家庭財產的騙捐事件層出不窮,從而引發了個人求助平臺的“信任危機”,也侵蝕著個人獲得網絡救助的信任基礎。

個人大病求助平臺已成為目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有益補充(圖文無關)
其次,是平臺收費“吃相難看”。運營一個公益眾籌平臺,不僅需要人力成本,還包括開發費用、維護費用、服務器費用等,因此需要較高的資金成本。網絡眾籌平臺本身不是公益性組織,具有一定的商業屬性,主要的運行模式是:求助平臺雇傭線下推廣人員幫助患者發起求助,再將患者的各種社會關系轉化為平臺用戶,在取得用戶流量后平臺通過銷售“互助產品”或者保險產品進行變現。盡管籌集的資金不收取手續費,但一些平臺會在用戶捐款時,默認引導用戶點擊一種“綠醫服務”或者是“平臺支持費”“平臺服務費”,由此在捐款數額外產生扣款,并且收費的標準在不同區域并不相同。客觀而言,網絡求助平臺免費運營多年,設定合理的服務費標準能夠幫助平臺良性持久發展,但是對捐助人或者求助人隱藏收費、誘導收費、捆綁收費只會引起公眾反感。
最后,是平臺顧問惡意推廣毫無底限。個人求助平臺在實際運行中需要大量推廣人員將籌款人與捐助方匹配起來,因此一些第三方組織或個人以幫助籌款人推廣籌款鏈接為由,除了與部分醫院“合作”外,還會主動聯系發起籌款的患者及家屬幫助推廣籌款鏈接,向籌款人收取高額的“推廣費、傭金”,甚至按照實際募集到的資金抽成。例如,陳某為患白血病兒子在某一平臺籌款1萬元,卻被籌款中介李某索要8000元推廣費,雖然最終查明是籌款顧問的個人違規行為,但無疑揭開了“公益”背后的“生意”,最終損害的是個人求助平臺的信譽。
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法律規制路徑建議
第一,立法明確平臺定位,凸顯公益屬性。
正如我國首例網絡個人求助糾紛案的判決書中指出的,“目前僅有部門規章規定個人求助行為不屬于慈善募捐、慈善公開募捐信息,對于互聯網個人大病求助中網絡平臺與贈予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尚無明確規定”。2023年修改后的《慈善法》對個人求助行為與網絡平臺專門作出規定,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法律明確了網絡求助平臺的定位。筆者注意到,原來修正草案中表述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正式公布的法律文本中被改為“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并且在市場準入門檻上要求“需經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通常來說,“指定”是一種行政許可,這就意味著未經指定的平臺,一律不得提供個人求助發布的服務。未來民政部在制定具體管理辦法時,很可能對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進行更加嚴格的資質認定,平臺的公益屬性將大幅增強,有助于形成更具特色的“醫療互助制度”。這也符合2020年國務院《關于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提出的“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體,醫療救助為托底,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慈善捐贈、醫療互助共同發展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
第二,細化規制主體監管職責。
修改后的《慈善法》在附則中對個人求助網絡服務納入法律規制,實際也是明確這類活動是一種具有“私益與公益重疊復合的慈善”。從規制主體來看,是由“國務院民政部門會同網信、工業和信息化等部門”制定具體管理辦法,因此有權對此類平臺管理的部門包括民政、網信、工業和信息化等部門。通常個人求助網絡平臺的運營主體如果不是慈善組織,還應當由市場監管部門進行監管。因此,在政府對個人求助平臺規制中,需要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社會的關系,由民政、醫保、網信、工信、市監等多部門對平臺上開展慈善募捐活動的過程展開合理細化和協調。
第三,明確平臺查驗義務的范圍和規則。
修改后的《慈善法》規定從事個人求助網絡服務的平臺應當對通過其發布的求助信息的真實性進行查驗。個人求助平臺在對求助人發布信息查驗時,應當包括病患者身份信息、基本病情、家庭財產、收入來源等信息,但是這一范圍仍然比較模糊,在實際操作中平臺也只能對求助人主動提供的材料予以審核,很難通過政府部門對求助信息進行共享和比對。因此,平臺這一義務的前提是求助信息發布者要履行提供真實信息的義務。同時,對平臺的信息查驗周期、查驗方式(線上或者線下)、查驗真偽的標準、結果反饋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予以明確。
第四,健全網絡平臺自律規則,引導形成自我規制。
早在2018年10月,在相關部門的推動下,水滴籌、輕松籌和愛心籌等便已聯合發布《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自律倡議書》和《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自律公約》(1.0版)。2020年8月,在民政部的引導下,愛心籌、輕松籌、水滴籌、360大病籌聯合簽署了上述自律倡議書和自律公約的2.0版,內容包括加強信息審核、信息公示、資金監管,平臺約束員工和合作伙伴等。個人求助平臺企業應當以修改后的《慈善法》的實施為契機,在主管部門支持下健全平臺行業自律規則,嚴格落實行業自律規則,形成以個人信用和企業信用為依據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定期公布行業內存在不規范行為的“黑名單”。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