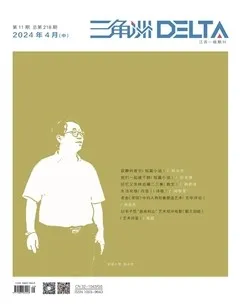創傷困境下的身份重構
李金蔚 楊素珍 康春雪 楊文菲 張馨月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華裔女作家譚恩美作品的研究日益增長,但鮮有學者用創傷理論對其進行研究。本文擬采用創傷理論對譚恩美代表作品《喜福會》中華裔女性族群所受的創傷進行分析,探究作品中兩代華裔女性移民在“失語”創傷困境下擺脫種族與性別的枷鎖、療愈創傷的過程,從而豐富對華裔女性族群的創傷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譚恩美為代表的美國華裔女作家躋身于美國主流文壇。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的蓬勃發展和東方文化的深入傳播,她們作品中所展現出的華裔女性堅韌勤勞、追求平等的優良品質也為國外學者所重視并加以研究。
創傷“Trauma”一詞在希臘語中原指身體上的疤痕。創傷理論最先由美國學者凱西·卡魯斯提出,主要研究人們在受到創傷后的反應和應對方式,其研究的焦點對象是女性、兒童、少數族裔等群體。創傷最先被認為是對人外部身體上的傷害,之后的心理學范疇定義它為某一突發事件或經歷導致人心理上產生的長期不可控影響,使受害者經歷大腦、身體和情感上的各種痛苦。創傷對主體的影響會一直存在,直到處理和解決該事件。創傷理論被運用到文學文本分析當中來,以便了解小說中主人公成長生活中所經歷的各種創傷性事件對其未來生活的影響。
試用創傷理論來看譚恩美的代表作品《喜福會》,聚焦作品中展現的身份認同危機、文化沖突、代際沖突、種族歧視等主題,深入解讀其中華裔女性族群所受的創傷,以探究她們擺脫“創傷”困境和重構自我身份的深遠意義。
華裔女性族群的創傷
譚恩美的《喜福會》是一部描寫美國華裔女性的小說,它展示了兩代人在不同歷史、文化和家庭背景下所經歷的創傷,以及她們如何通過敘述、交流和認同來修復創傷。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可以分為兩代:第一代是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母親們,她們在中國時遭受了戰爭、貧窮、壓迫、虐待等各種創傷,來到美國后又遭受了文化沖突等創傷;第二代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女兒們,她們在美國面臨了種族歧視、文化沖突、身份困惑等各種創傷。
在《喜福會》中,女性弱勢群體的創傷經歷得到了充分的敘述和交流。她們在“喜福會”中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經歷,傾聽彼此的心聲,從而緩解孤獨和痛苦,建立起互相支持的關系。同時,她們的創傷敘述也是一個重要的治療過程,能夠促進個體的心理成長和自我認知。
第一代母親們在舊中國受到了男權社會的壓迫和剝奪,以及戰爭和貧困的摧殘和傷害。她們從小生活在戰爭中,戰爭摧毀了她們的家園,摧毀了她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吳素云帶著雙胞胎女兒狼狽逃難,最后由于身體原因被迫與女兒骨肉分離,而戰時的“棄女”行為也成了她一生的創傷。家庭暴力和虐待給第一代母親們帶來了身心的雙重傷害。這些經歷留下了深刻的身體痕跡,比如,母親們手指的指節因為長時間勞動而變得粗糙;她們因為裹小腳這一陋習而留下了永久性的傷害。這些身體記憶代表著母親們在中國時所受的創傷,也讓她們的身體成為了承受創傷的載體。
譚美恩筆下的中國母親們,以第一代移民的身份成為了美國華裔。她們難以忍受在舊中國遭遇的那些讓人無奈的教化和冷酷的規訓,因此紛紛黯然出走,懷著美好的期待奔向了美國這塊想象中的樂土,以為能治愈好原生家庭帶來的創傷。但是當她們踏上美國的土地、開始嘗試融入美國社會時,她們發現美國社會主流話語中所謂的“自由平等”到了華裔身上就不再發揮作用,她們被忽視、被邊緣化。對所有喜福會的母親而言,她們深受種族歧視的壓迫,但又無從發聲,陷入了“失語”的創傷困境,陷入了更深并且更為持久的壓抑。
女兒們的創傷敘述則更加復雜和微妙。女兒們在美國出生長大,她們的身份認同建立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基礎上。作為美籍移民,女兒們的身份不被中國文化接納。同時,盡管她們受美式教育、想做美國人,但由于“他者”身份和與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形象而被排斥在邊緣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立法中關于種族歧視的條款大多已被廢除,雖然形式上的種族歧視不存在了,但是美國社會依然存在隱性歧視,依舊有種族歧視的文化土壤。女兒們盡管全面接受了美國主流文化,但仍然存在身份認同上的各種困擾,害怕自己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擔憂自己成為徹頭徹尾的“異鄉人”。對于看多了母親們悲慘遭遇的女兒們來說,那些亞裔女性被排擠的悲慘記憶無疑是令她們恐懼的,她們懼怕過上像母親一樣的生活,于是女兒們極力想出逃,她們努力想做一名真正的美國女性。
女兒們認為只要她們拋棄了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和語言,就可以真正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小時候她們不肯聽從媽媽的勸告,不會講漢語;長大之后,她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唐人街,與白人結婚,試圖改造自己身上的亞洲血統。比如麗娜就努力地將自己的眼角向中心傾斜,讓自己看上去更像她的愛爾蘭人爸爸,從而顯得更大更圓。“生為華人心里總有羞恥和自賤的感覺,我們迷信美國的民族熔爐神話,但實際上我們故意選擇美國的東西如熱狗和蘋果派而忽視來自中國的東西。”
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無疑會讓喜福會的女兒們產生一種亞裔身份的原罪感,這種原罪論讓她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驚恐不安,繼而內化為女性對華裔身份的“自我憎恨”。帶著這種身份原罪感和“自我憎恨”,她們憎恨母國文化,無法理解自己的母親,對于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中國思維嗤之以鼻,比如精美就這樣形容過在文化上令她十分費解的母親:“她和安梅阿姨都穿著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領中國式衣衫,前胸繡著花卉,這樣的衣服對真正的中國人來說是太時髦了……那時在母親還沒有給我講述過桂林故事時,我想象中的喜福會是一個有著特殊儀式的團體。好比3K黨的集會和電視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禮,反正有著一套神秘古怪的儀式。”然而諷刺的是,喜福會女兒們的所有反抗與嘗試最終都是徒勞的:女兒們仍然被美國主流社會拒絕在門外,她們繼她們的母親之后,成為了失落的第二代移民。
女兒們無法輕松地融入美國社會,她們幻想她們能努力依照美國流行文化與美國媒體中的成功形象塑造自己就能融入美國社會。但是她們的命運中依舊會遇到與母親們類似的遭遇,創傷仍然無法避免,難以有更好的機會得到治愈。第一代移民無法治愈的創傷會代際傳遞,類似的創傷體驗會重復上演——這不僅是個體的創傷,也是華裔女性族群集體性的創傷。種族歧視對華裔少數族群的壓抑與性別歧視對女性群體的壓抑相似,這些都會導致一個結果:創傷性體驗作用于個體會通過代際傳遞影響到群體,而群體性的創傷性體驗也會反過來作用于并壓抑個體。創傷是一種無意識模仿或認同創傷情境的局面。如果經歷過創傷的人沒有對外部世界重構起新的意識,那么如果之后創傷性情境再現,就仍會讓受害者再次經歷創傷。
創傷療愈
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們創辦的“喜福會”成為了她們重新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喜福會”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母親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這種分享和交流讓她們感到自己是被尊重和接受的。
女兒們的創傷敘述也在“喜福會”中逐漸展開,通過傾聽其他女性的經歷和感受,她們逐漸理解了母親們的經歷和心境,同時也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根源和身份。通過創傷敘述,女兒們得以抒發內心的痛苦和困惑,同時也得到了其他女性的支持和鼓勵,幫助她們更好地應對生活的挑戰。在喜福會的交流和互助中,女兒們逐漸接受母親們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理解了她們的經歷和心境。通過對母親們的了解和共情,女兒們建立了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即華裔女性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不是簡單地被賦予,而是通過交流和互助得到的。這種跨代的身份認同和交流不僅幫助女兒們更好地理解接受自己的文化和身份,也使她們更有信心和力量面對外部的歧視和壓力。
“喜福會”是一個重要的創傷修復機制,它提供了一個溫暖包容、互助共情的空間,讓女性群體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傾聽他人的故事和意見,找到共同點和差異點,建立信任和友誼。通過“喜福會”,女性可以將自己的創傷經歷轉化為創傷敘述,將自己的創傷記憶轉化為敘述記憶,將自己的創傷真相轉化為敘述真相。通過敘述,女性可以將自己的創傷經歷從潛意識層面提升到意識層面,從無法言說的狀態提升到可言說的狀態,從孤立無援的狀態提升到社會參與的狀態。通過敘述,女性可以將自己的創傷經歷從個人層面擴展到集體層面,從個體層面擴展到歷史層面,從文化層面擴展到跨文化層面。通過敘述,女性可以將自己的創傷經歷從消極層面轉變為積極層面,從被動層面轉變為主動層面,從破碎層面轉變為完整層面。
“喜福會”不僅是一個創傷修復機制,也是一個身份重構機制,它幫助女性重新認識自己和他人,重新定義自己和他人的關系,重新塑造自己和他人的形象。通過“喜福會”,女性可以重新構造自己和母親、祖國、文化、社會、歷史等方面的聯系。“喜福會”是一種女性主義的實踐和表達,展示了女性角色的自我覺醒和解放,也展示了女性角色的團結和力量。“喜福會”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和對話,它促進了兩代女性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也促進了中美兩種文化之間的融合和創新。
《華盛頓郵報》贊美《喜福會》“具有神話般的魔力”。在當時,譚恩美不懼華裔女性作家在美國主流文壇集體“失聲”的困境,融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文化創作了《喜福會》來揭示華裔女性移民的創傷經歷,她具有摒棄男權中心論和突顯女性權利的前瞻性思想。
對創傷的恢復治療是了解和分析創傷的最終目的,作為華裔女性作家,譚恩美通過創作書寫來分析華裔女性所經歷的獨有的創傷體驗,展示了兩代華裔女性移民在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中產生的身份困惑,并試圖通過自傳式創傷敘事策略來探討其身份定位,以喚起同處于相似境地的華裔女性們去獲得認識和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來感知到創傷來源,主動尋求途徑治愈創傷。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云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