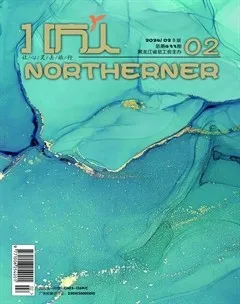抵達(dá)、看到與安放
黃燈

2017年暑假,應(yīng)黎章韜(我2010級(jí)中文班的學(xué)生)邀請(qǐng),我開(kāi)始了去學(xué)生家看看的漫長(zhǎng)旅途。首站是云南騰沖。隨后五年,我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斷斷續(xù)續(xù)去過(guò)臺(tái)山、懷寧、東莞、孝感等許多地方。在中國(guó)的教育語(yǔ)境中,這個(gè)過(guò)程被稱為“家訪”,也是傳統(tǒng)教師角色的一項(xiàng)日常工作,但對(duì)我而言,這種跨越時(shí)空的走訪,完全超出了日常“家訪”的邊界,成為我從教生涯中,從“講臺(tái)之上”走進(jìn)“講臺(tái)背后”的發(fā)端。
如果說(shuō),《我的二本學(xué)生》是一本立足講臺(tái)視角,建立在從教經(jīng)驗(yàn)之上的教學(xué)札記,那么,這本《去家訪:我的二本學(xué)生2》是我走下講臺(tái),走進(jìn)學(xué)生家庭實(shí)地考察和親歷的家訪筆記。本書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學(xué)生,出場(chǎng)的年輕人,同樣來(lái)自廣東F學(xué)院。
回想起五六年來(lái)在全國(guó)不同的村莊、集鎮(zhèn)、街巷走訪的經(jīng)歷,有太多難忘的瞬間值得銘記。我在夏天的溽熱中,到過(guò)喧囂而紛亂的南方小鎮(zhèn),也在年關(guān)將近的冬日寒風(fēng)中,抵達(dá)過(guò)蕭瑟而蒼茫的北方村莊。它們或庇護(hù)在高黎貢山之下,或湮沒(méi)在高速公路隔絕的群山之中,或在夸張房地產(chǎn)廣告的包裹里,顯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煙塵。我在不止一所廢棄小學(xué)的操場(chǎng)后面,目睹到曾經(jīng)的教室,隨著孩子們的消散,早已一片狼藉;同時(shí)也在多所莊重、整潔的高中校園,看到了我講臺(tái)下的年輕人曾經(jīng)燃燒的夢(mèng)想和青春。我也一次次在漫長(zhǎng)的遠(yuǎn)行中,將家訪變?yōu)楝F(xiàn)實(shí),并由此獲得機(jī)緣,回溯一個(gè)個(gè)年輕人成長(zhǎng)的足跡。
為了更完整地俯覽村莊的全貌,李敏怡曾帶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頂;為了進(jìn)到廢棄的小學(xué)看看曾經(jīng)的課桌,何境軍多次示范怎樣翻越學(xué)校的狹窄圍欄;為了告訴我養(yǎng)蠔的流程,羅早亮爸爸親自駕船,帶我穿梭海灣抵達(dá)蠔場(chǎng);為了感受茶園的遼闊,林曉靜媽媽豪情滿懷地開(kāi)著摩托車,載我在崎嶇的鄉(xiāng)村小徑一路馳騁;為了體驗(yàn)爸爸的工作強(qiáng)度,于魏華和我一起溜入了韻達(dá)快遞遼闊的分裝車間;為了更清楚地還原高三的緊張和勞累,張正敏翻出她塵封已久的日記,翻出她高三寫過(guò)的近兩百支圓珠筆,我到現(xiàn)在都無(wú)法忘記,圓珠筆擺滿一地給我?guī)?lái)的震撼和觸動(dòng)。
當(dāng)然,更讓我觸動(dòng)的是,在這種走訪中,以家庭為錨點(diǎn),往往能輕易看到其所帶來(lái)的豐富鏈接:我終于擁有機(jī)會(huì)看到講臺(tái)下年輕人的父母以外的親戚群體,看到這個(gè)群體和他們的具體關(guān)聯(lián);也得以擁有機(jī)會(huì)感受到家庭作坊、進(jìn)廠打工、養(yǎng)蠔修船、擺攤售賣、種植茶葉、宰殺牲畜等具體生計(jì),是如何作用到一個(gè)個(gè)孩子的生命中,并在無(wú)形中塑造他們的勞動(dòng)觀、金錢觀和對(duì)求學(xué)深造、成家立業(yè)諸多事情的認(rèn)知。
這所有的片段、場(chǎng)景和抵達(dá),在我腦海中繪就了一幅動(dòng)態(tài)而清晰的畫卷,接通了一個(gè)豐富而真實(shí)的中國(guó)。
我想起第一站到達(dá)章韜家,坐在雨天的茶桌旁,聽(tīng)他爸爸講起早年在緬北的伐木經(jīng)歷,他平淡地?cái)⑹鲆磺校覅s聽(tīng)得心驚肉跳;我想起正敏帶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濘小徑,想起我們?cè)诟吒呱綅徤系男W(xué)所感受到的絕對(duì)寧?kù)o,盡管媽媽不在身邊,但在故鄉(xiāng)的山間田地,無(wú)處不是媽媽勞作的身影;我想起源盛帶我重走課堂上描述過(guò)的“打火把上學(xué)的路”,目睹他最喜愛(ài)的堂弟車技驚人,卻無(wú)法獲得駕照進(jìn)入城市謀生的事實(shí),而我在此種遺憾和現(xiàn)實(shí)中,突然理解了無(wú)法與我謀面的媽媽,為何在生完孩子后,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堅(jiān)定;我想起曉靜媽媽跨上摩托,帶我在茶場(chǎng)的山路上風(fēng)馳電掣,她人到中年,卻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齡人才能明白的孤獨(dú)和不甘;我想起境軍媽媽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樹(shù)下,和我講起兒子的懵懂給她帶來(lái)的憂慮和無(wú)奈,以及決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掙扎和堅(jiān)持。
事實(shí)上,雖說(shuō)是家訪,和家長(zhǎng)見(jiàn)面原本應(yīng)為這一環(huán)節(jié)的核心,但不少時(shí)候,就算來(lái)到學(xué)生家,我也有可能見(jiàn)不到他們的父母,他們要不雙雙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有幸能夠見(jiàn)到雙方,我們大都沒(méi)有特定的時(shí)間用來(lái)交流,他們無(wú)法停下手中的活計(jì),生存嚴(yán)絲密縫,日復(fù)一日的既定勞作,填滿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們難得的聊天機(jī)會(huì),更多只能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yǎng)殖場(chǎng),或者鍘豬草、煮豬食、織漁網(wǎng)、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的間隙中進(jìn)行。這些場(chǎng)景如此具體、日常而又必然,無(wú)不浸潤(rùn)了快速流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在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他們堅(jiān)信勞動(dòng)創(chuàng)造價(jià)值,勤勞、質(zhì)樸而又堅(jiān)韌,他們對(duì)個(gè)人消費(fèi)保持警惕,但對(duì)孩子的教育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重視、不計(jì)代價(jià)的付出和讓我羞愧的耐心,承載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龍的樸素心愿。和我們的父輩比較起來(lái),這群來(lái)自中國(guó)傳統(tǒng)家庭的最后一代,無(wú)論在生活方式還是在價(jià)值觀念上,依然延續(xù)了父輩的精神底色。
毫無(wú)疑問(wèn),他們是中國(guó)最為廣大的勞動(dòng)者群體,在敘述中國(guó)高等教育的整體圖景時(shí),他們是不可忽視的、沉默而龐大的主體。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觀照中,我進(jìn)一步堅(jiān)定了此前的判斷,他們的孩子,我龐大的二本學(xué)生群體,構(gòu)成了中國(guó)大學(xué)生的多數(shù),成為社會(huì)的重要支撐。作為家長(zhǎng),他們以自己的勞作和付出,作為勞動(dòng)者的主體,同樣構(gòu)成了中國(guó)社會(huì)正常運(yùn)轉(zhuǎn)的重要基石。
在和學(xué)生共同的尋訪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剝離掉985、211、雙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環(huán),對(duì)更多年輕人而言,哪怕進(jìn)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盡全力,同樣離不開(kāi)家庭奮不顧身的托舉。
(摘自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去家訪:我的二本學(xué)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