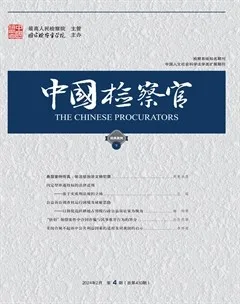檢察機關辦理倒賣文物犯罪案件難點與要點
苗婧 劉雅妹
摘 要:對于行為人明知是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所獲取的文物,仍多次收購且拒不交代文物去向的,可綜合全案證據,認定其具有牟利目的,以倒賣文物罪追究刑事責任。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時應當樹立數字檢察思維,充分運用大數據法律監督,破解漏罪漏犯發現難題,挖隱案、繳文物,依托多部門聯動協作機制,形成保護合力,促進源頭治理。
關鍵詞:倒賣文物 牟利目的 數字檢察 綜合治理
一、基本案情及辦案過程
2012年至2016年,被告人王某某以出售為目的,多次從董某、王某甲、史某某、蔡某某(均另案處理)等人處購買青銅簋、青銅圓鼎、青銅提梁壺、青銅花觚等青銅器數十件。上述文物系董某、王某甲、史某某等盜墓人員從殷墟遺址保護范圍內盜挖所得。案發后,共追繳青銅器37件,經鑒定,二級文物2件,三級文物17件,其余為一般文物。
2018年,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殷都區院”)結合近年來辦理的文物案件,進行綜合數據分析,排查出王某某倒賣文物線索并移送公安機關。2019年11月11日,公安機關將王某某抓獲到案。
2020年9月1日,殷都區院以王某某涉嫌倒賣文物罪提起公訴。11月25日,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殷都區法院”)以王某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殷都區院以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為由,于12月9日提出抗訴,河南省安陽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2021年3月13日,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次年2月25日,殷都區法院重新審理后作出判決,改判王某某構成倒賣文物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并處罰金。王某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二、倒賣文物案件辦理難點及突破路徑
(一)數字賦能辦案破解漏罪漏犯難題
文物犯罪案件呈現出團伙性、專業性、作案隱蔽性、銷贓隱匿性等特征,嚴重危害文物安全。一是多為團伙作案,人數少則五六人,多則二三十人,且團伙內部分工明確,組織、挖掘、運輸、倒賣形成專業化、鏈條化的作案模式。二是交叉作案事實眾多,同一文物犯罪參與人數眾多,且多用綽號、代號單線聯系,甚至互不相識,辦案時難以鎖定全部參與人員的真實身份,易遺漏同案犯;同一名犯罪嫌疑人參與多個盜墓團伙連續作案,盜墓事實多,辦案時易遺漏犯罪事實。
基于此,檢察機關可充分發揮數字檢察作用,建立文物犯罪法律監督模型,破解漏罪漏犯發現難題。檢察機關以文物案件為基礎,采集、錄入以案發時間、盜掘地點、參與人員、涉案文物等信息為要素,建立基礎數據庫和已到案人員比對數據庫,通過兩個數據庫對比碰撞,基礎數據庫大于已到案人員比對數據庫的即為未被處理的漏罪漏犯線索。每當新錄入一個案件,數據畫像就更加完善、精準,并再次碰撞得出線索。此外還可以通過檢索到案人員供述的可疑人員特征、盜掘地點等信息進行數據碰撞、比對,精準鎖定漏罪漏犯。
本案中的王某某即通過檢察機關構建的文物犯罪漏罪漏犯數字檢察模型篩查出來的可疑數據線索。檢察機關通過數據庫信息比對發現,蔡某某等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案的涉案文物被出售給“鄭州老張”,董某等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案的涉案文物被出售給“鄭州老李”,但模型對兩名收購者進行數字畫像后發現兩者的所在地、年齡、體型、外貌特征等關鍵信息基本一致,可能系同一個人。檢察機關及時將該線索移送偵查機關,通過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辦公室(以下簡稱“偵監協作辦公室”)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組織兩起案件的在案人員對收購者進行辨認,印證了“鄭州老張”和“鄭州老李”系同一人的判斷,鎖定其真實身份為王某某,并將其抓獲歸案。
(二)從牟利目的入手破解定罪難題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倒賣文物罪均規定在我國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規定在第六章第二節妨害司法罪中,即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倒賣文物罪則規定在第六章第四節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第326條,即以牟利為目的,倒賣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情節嚴重的,構成倒賣文物罪。
從犯罪構成要件分析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點:從侵犯的客體來看,是司法秩序還是文物管理制度;從客觀方面來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是通過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倒賣文物罪是出售或者為出售而收購、運輸、儲存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從主觀方面來說,雖然兩罪均要求故意,但倒賣文物罪比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多出了以牟利為目的。兩罪從主體來看并無區別,均要求行為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有學者論述兩罪并非是對立排斥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競合關系。[1]筆者同意該觀點,為出售而收購他人盜竊文物,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等犯罪所得文物既符合倒賣文物罪的構成要件,又同時符合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構成要件。而收購文物時是否具有牟利目的,是準確區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倒賣文物罪的關鍵所在。當行為人收購、運輸、儲存明知是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等犯罪所獲得的三級以上文物時,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但行為人以牟利為目的,為出售而收購、運輸、儲存被盜掘文物時,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認定行為人構成倒賣文物罪。且需注意的是,牟利目的的實現與否并不影響倒賣文物罪的成立。對行為人“牟利目的”的認定,需證明行為人明知是盜竊文物、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所獲取的文物,而進行收購、運輸、儲存等行為是為了獲取某種利益而為。“為了獲取某種利益”,是一種主觀心態,理論上,刑法不調整單純的心理活動。但在主觀心態的支配下實施某種犯罪行為,并達到法律禁止的程度時,就有可能被刑法所規范和調整。
理論上行為人的“牟利目的”主要體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應用到司法實踐中一般通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來證明,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做有利于自己的供述,而將其具有的“牟利目的”隱藏。因此,認定“牟利目的”成為實踐中的難題。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牟利目的”,應當結合行為人的從業經歷、認知能力,交易價格、次數、方式、件數、場所,文物的來源、外觀形態等綜合審查判斷。[2]
本案中王某某辯稱自己從事文物收藏行業,持有收藏證,其購買文物是為收藏而非倒賣,不具有“牟利目的”。檢察機關經過全面審查證據發現,一是王某某以經營古玩店為生,并無其他收入來源,若不出售古玩店內的文玩物品,則無法維持生計。二是從交易次數、方式上來看,王某某先后6次從盜墓分子手中收購青銅器,均以高價成交并現金支付,且交易時間均在夜晚凌晨,不符合正常商品交易習慣。三是從保管文物的態度上來看,王某某不顧青銅器毀損風險,將所購青銅器隨意堆放或掩埋,文物保管方式與收藏文物的目的大相徑庭,與文物收藏者的行為習慣不相符。四是王某某到案后無法退繳全部文物且無法交代文物去向,對公安機關在其家中查獲的部分文物也無法說明來源。綜合王某某上述行為及其職業、收入來源、交易記錄等,足以認定王某某直接從盜墓分子手中收購文物,具有從中牟利的主觀目的。檢察機關精準認定其行為構成倒賣文物罪,對一審法院判決王某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依法提出抗訴,二審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法院經重新審理后,判決王某某犯倒賣文物罪,王某某未上訴。
三、檢察機關辦理文物犯罪的要點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安全保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應當立足檢察職能,依法嚴厲打擊、嚴密防范文物犯罪,注重挖隱案、繳文物,依托多部門聯動協作機制,促進源頭治理,形成保護合力,切實保護國家文物安全。
(一)樹立數字化思維提升文物犯罪打擊效能
最高檢黨組強調,“深入實施數字檢察戰略,賦能新時代法律監督,促進和維護公平正義,更好以檢察工作現代化服務中國式現代化”[3]。檢察機關應樹立數字化辦案思維,將文物犯罪案件信息及時轉化為數據資源,以大數據技術作為智能辦案輔助手段,提高工作質效,實現個案辦理向類案分析研判的轉變。
(二)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實現全鏈條打擊
檢察機關要把準案件的定性和取證方向,引導公安機關取證,查明盜掘、盜竊、倒賣、走私、收贓等各個環節的違法犯罪人員,摒棄“就案辦案”思想,實現對文物犯罪全鏈條打擊。要從源頭上提高辦案質量,充分發揮偵監協作辦公室作用,提前介入引導偵查機關取證。探索從交易環節入手,上追下查,與偵查機關會商研判,分析已有盜墓人員供述,準確厘清證據材料中的矛盾和疑點,查明相關盜墓事實中文物的去向情況,鎖定收購文物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三)強化刑事指控提升法律監督工作質效
針對文物犯罪案件呈現的長期性、團伙性、專業性,以及作案隱秘、銷贓隱匿等突出特點,檢察機關應當綜合審查證據,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堅持“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監督的力度和精準度,對判決認定罪名確有錯誤的,發現后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權,及時提起抗訴,監督糾正錯誤裁判,做到不枉不縱、罰當其罪。
(四)協同發力促進社會綜合治理
注重通過部門聯動推進文物保護綜合治理,協同發力實現文物犯罪“治罪”與“治理”并重,以法治之力守護中華文脈。如本案中,檢察機關在打擊犯罪方面與公安機關建立定期會商機制,協調解決涉文物犯罪案件在偵辦、訴訟中的難題。在強化文物社會治理方面,與公安、法院、文物局等部門成立了殷墟保護行政與司法聯動公益訴訟協作機制,同時針對一些問題發出檢察建議督促整改,落實治安防范責任。針對殷墟遺址周邊村民法律意識淡薄問題,檢察機關聯合多部門積極走進社區、學校、遺址公園等地開展各項專項活動,定期對國家遺址管理工作進行“法治體檢”,共同促進社會治理。
*河南省安陽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 [455000]
**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五級檢察官助理 [455004]
[1] 參見李哲、王學東:《收購文物贓物行為的司法認定》,《中國檢察官》2023年第6期。
[2] 參見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和國家文物局《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3] 《最高檢:加快推進數字檢察戰略賦能法律監督 促進和維護公平正義》,最高人民檢察院網https://www.spp.gov.cn/tt/202306/t20230619_618011.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