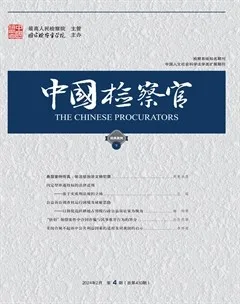涉水下古文化遺址犯罪案件辦理重點及啟示
沈標 陳康嬌 詹金洲
摘 要:檢察機關經綜合評估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對犯罪情節確實輕微且符合法治精神、立法原意的,應決定不起訴,做到法理情有機統一、罪責刑相適應,全面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同時增強檢警協作配合,能動發揮監督職能,聯動多部門加強對水下古文化遺址等國家文物的多渠道、全方位保護,并改變“坐堂辦案”的習慣,主動通過公開聽證、法治教育、專家說法等方式強化釋法說理。
關鍵詞:多次盜掘 水下古文化遺址 罪責刑相適應 公開聽證
一、基本案情及辦案過程
2003年某日,陳某某、黃某甲、黃某乙等組織十幾人在廣東省湛江市硇洲島西面海域捕撈帶子螺作業時,在海底淤泥中無意發現并“撿拾”了部分古錢幣,陳某某對該海域進行了定位。后陳某某等人將古錢幣送到金鋪鑒定為銀材質。次日,陳某某等十幾人到該海域打撈了古銀幣1000余枚、古銅幣10000余枚以及部分瓷器和碎片等。陳某某將打撈到古錢幣的情況托人上報至湛江市博物館。2003年7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2年更名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會同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對該海域進行水下考古調查。考古人員在陳某某等人協助下確定位置進行試掘,挖出了大量文物,初步判定該遺址范圍內存在一艘清嘉慶年間沉沒的商船。考古人員告知陳某某等人不能擅自打撈水下文物。自媒體對海底打撈到寶物進行報道后,當地漁民紛紛借打漁之名打撈文物。截至2007年,陳某某、黃某甲、黃某乙等人十余次組織人員在該遺址進行打撈,每次均打撈到少量古錢幣。
2021年5月,在公安部、國家文物局聯合開展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行動中,偵查機關發現陳某某等人行為可能涉嫌違法犯罪,遂電話通知陳某某、黃某甲、黃某乙三人接受詢問,陳某某等三人主動投案如實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實,并將27件涉案器物和19塊瓷器、金屬碎片上交。經鑒定,該批涉案27件器物均為一般文物,包括明清瓷器3件、清代石印章1枚、18世紀外國銀幣8枚、清代銅錢15枚。
2021年9月,廣東省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決定對三名犯罪嫌疑人不起訴。
二、盜掘古文化遺址案件的辦案重點
(一)對盜掘古文化遺址行為社會危害性的評估
犯罪的本質特征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否達到嚴重程度要全面客觀評估。[1]一是要評估考量被盜掘文物的等級、古文化遺址的保護單位等級和二者損害程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文物保護法》)第3條規定,文物分為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又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涉案古文化遺址尚未確定保護單位等級,且涉案27件器物為一般文物,均可獨立于該古文化遺址,仍然保留了文物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可認定社會危害性不大。二是要評估考量作案手段和危害后果。陳某某等三人系在海底淤泥中以“撿拾”的方式打撈到文物,相較于以損毀性較大的開挖、鑿割等手段獲取古文化遺址文物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小;且在被告知不能擅自打撈后仍多次打撈的文物數量不多,危害不大。三是要評估考量作案動機和主觀惡性。陳某某等三人無意中發現涉案文物,后又主動聯系文物部門、協助考古調查隊確定古文化遺址位置并上繳文物,在客觀上有利于專業人員發掘、保護文物和促進科研工作,主觀惡性較小。檢察機關從上述幾個方面辯證看待涉案的多個行為和一個行為的多面性,結合被侵犯的對象損害程度、作案手段、危害后果的大小、行為人主觀惡性等各方面因素,全面、客觀評估整個涉案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小。
(二)對犯罪嫌疑人主觀故意的認定
陳某某等三人歸案后均辯稱在海底打撈到古錢幣屬于拾得無主物依據慣例“先占為主”,無犯罪故意,不構成犯罪。雖然三人的辯解符合當地漁民對海里捕撈物“先占為主”的傳統觀念,但是文物因其特殊的價值和意義區別于無主物,《文物保護法》第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陳某某等三人雖不能確切判斷私自打撈文物的具體價值和確定涉案海域屬于古文化遺址,但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在主觀上并不要求行為人具有文物專業人士的認知,而是對文物、古文化遺址屬于受國家保護、禁止私自挖掘的常識明知即可[2],且根據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的規定,古文化遺址不以公布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古文化遺址為限。陳某某等三人在被告知不能擅自打撈水下文物后仍多次打撈的主觀故意尤為明顯,故其無犯罪故意的辯解不能成立。
(三)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理解與適用
案發時刑法尚未明確規定何為“多次盜掘”,但結合盜竊罪、搶劫罪等其他罪名對“多次”認定慣行標準,應當將三次以上盜掘古文化遺址認定為“多次盜掘”。由于陳某某等三人多次盜掘行為的跨度長達4年之久,每次間隔時間難以確定,有別于一年內數月之間對同一地點故意多次盜掘的情形。[3]三人在被明確告知不能私自打撈文物后“從眾”多次打撈的文物數量較少,如按“多次盜掘”的加重情節處罰則罪責刑明顯不適應,且刑罰的輕重須與罪行的輕重、再犯可能性相適應,以實現刑罰的正義和預防犯罪的目的。[4]為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綜合考量陳某某等三人“多次盜掘”情形,且具有自首、認罪認罰、主觀惡性不大、及時退贓等情節,結合公開聽證聽取意見,認為其犯罪情節確實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最終決定對陳某某等三人作出不起訴處理。
2022年8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文物局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條規定“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多次盜掘是指盜掘三次以上。對于行為人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犯意,在同一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本體周邊一定范圍內實施連續盜掘,已損害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盜掘”。辦案當時檢察機關經全面評估犯罪情節后對陳某某等三人作不起訴決定,遵循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符合法治精神和立法原意。
三、辦理盜掘水下古文化遺址案件的實踐及啟示
(一)提前介入,發揮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作用
為提升辦案質效,檢察機關應發揮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作用,提前介入引導偵查,確保案件的順利辦理。本案中,在立案前,偵查機關就能否立案、行為定性、追訴時效和追訴人員范圍等征詢檢察機關。考慮到涉案行為時間跨度長、涉及人員眾多、社會危害性不大,檢察機關提出打擊面不宜過大、僅對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立案并慎重適用強制措施的建議,被全部采納。在立案偵查后,檢察機關引導偵查機關圍繞水下古文化遺址的認定、主觀故意、影響量刑檔次的盜掘次數、文物價值等問題重點取證,特別是對明確告知不能擅自打撈文物后仍多次打撈文物的主觀故意及時收集、固定證據,進一步完善證據鏈條,既能做到適度介入又能強化檢警協作配合。
(二)公開聽證,在監督制約中保障司法公正
為提升司法公信力,對存在較大爭議的不起訴案件,檢察機關應召開公開聽證會,以公開促公正、贏公信。在作出不起訴決定前,檢察機關廣邀人民監督員、偵查人員、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群眾代表等參加公開聽證會。針對陳某某等三人受拾得無主物“先占為主”的傳統觀念影響和缺乏法律認識的情況,檢察機關詳細解讀了刑法和《文物保護法》相關規定,闡明文物的價值、意義和權屬、涉案行為的違法性,講清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法律適用、懲治并重的辦案效果、法理情的有機統一等理由而擬決定對陳某某等三人不起訴的綜合考量。聽證員一致同意檢察機關擬作不起訴的決定。陳某某等三人在聽證會上最后陳述認罪悔罪并接受不起訴決定。檢察機關以公開聽證方式接受監督,提升不起訴決定的可接受性,使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三)以案促治,助推文物全鏈條、全方位保護
檢察機關在履行打擊犯罪職責的同時需延伸檢察職能,探索形成長效治理機制,多渠道、全方位保護包括水下古文化遺址在內的國家文物。該案中,檢察機關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部門聯動評估會商,于2021年11月向偵查機關發出廣東省湛江市首份文物保護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建議及時查辦類案,妥善保管涉案文物并及時移交文物行政部門。偵查機關快速落實,將涉案文物移交廣東省湛江市博物館。檢察機關還與偵查機關、文物行政部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席商討水下古文化遺址保護工作,至2022年10月,廣東省湛江市博物館已完成涉案可移動文物預防性保護項目工作,對各種材質文物實施分類恒溫恒濕、防水防震專門保存措施。
(四)釋法說理,強化法治宣傳教育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5]檢察機關除履行辦案職責外,還需重視落實普法責任,檢察官應“走出卷宗、走出辦公室”進行法治宣傳教育。該案中,檢察機關結合廣東省湛江市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一帶一路”海上合作戰略支點城市,存在一定數量文物和古文化遺址的特點,將公開聽證會開成一堂“現場法治課”,并走進漁村漁船、漁民家中,以“家長里短”聊天、發放宣傳冊、專家說法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引導教育廣大群眾,把“難懂的法言法語”轉化為保護文物和古文化遺址的共識,讓“沉默的文物”闡釋鮮活的歷史意義。
*廣東省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一級檢察官[524000]
**廣東省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五級檢察官助理[524000]
***廣東省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書記員[524000]
[1] 參見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
[2] 參見《卞長軍等盜掘古墓葬案——盜掘古墓葬罪中主觀認知的內容和“盜竊珍貴文物”加重處罰情節的適用》,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編:《中國刑事審判指導案例》(第5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頁。
[3] 參見《孫立平等盜掘古墓葬案——如何認定盜掘古墓葬罪中的既遂和多次盜掘》,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編:《中國刑事審判指導案例》(第5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頁。
[4]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44頁。
[5] 《習近平對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2/c_1118599561.htm,最后訪問日期:202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