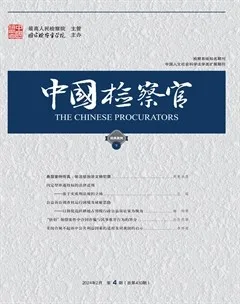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論處的路徑檢視*
鄭法梁 蔡雅芝
摘 要:當(dāng)前,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論處的定罪路徑較為混亂。應(yīng)厘清毒品與麻精藥品的關(guān)系,從販賣毒品罪的立法原意出發(fā),遵循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確定行為人明知是管制的麻精藥品而向吸毒、販毒人員販賣或者被購(gòu)買人用于特定犯罪活動(dòng)的,以販賣毒品罪論處。具體適用時(shí),應(yīng)對(duì)行為人對(duì)麻精藥品的認(rèn)識(shí)內(nèi)容和認(rèn)識(shí)程度、是否有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是否存在非法用途等予以考量。
關(guān)鍵詞:麻精藥品 販賣毒品罪 主觀故意 非法用途
一、出售麻精藥品的定罪爭(zhēng)議
[基本案情]2021年至2022年間,張一在某省從事“泰勒寧”及多種處方藥的收購(gòu)、販賣活動(dòng)。張一明知“泰勒寧”系國(guó)家規(guī)定管制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藥品,為牟利多次從醫(yī)院病人處回收“泰勒寧”,并每盒加價(jià)2元出售給張二,總計(jì)600余盒。張二在該省亦長(zhǎng)期從事藥品倒賣生意,從張一處購(gòu)入“泰勒寧”后又將每盒加價(jià)5元左右出售給張三經(jīng)營(yíng)的藥房(不具有出售資質(zhì))及其他藥房。張三明知張四吸食“泰勒寧”成癮,仍每盒加價(jià)20元左右出售給張四,總計(jì)100余盒。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張一、張二以不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作撤案處理,法院審理認(rèn)定張三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
《2022年中國(guó)毒情形勢(shì)報(bào)告》指出,部分吸毒人員因受毒品供應(yīng)大幅降低影響,轉(zhuǎn)而尋求其他麻精藥品等替代濫用,或交叉濫用以滿足毒癮。[1]在辦理涉麻精藥品案件時(shí),其定罪路徑不同于海洛因、冰毒等傳統(tǒng)毒品案件。具體而言,傳統(tǒng)毒品案件的定罪路徑相對(duì)簡(jiǎn)單,僅需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客觀上實(shí)施相關(guān)犯罪行為;而麻精藥品大多具有藥用屬性,認(rèn)定為毒品時(shí)需滿足多個(gè)限定條件,對(duì)行為人主觀認(rèn)知有較復(fù)雜的要求,以販賣毒品罪論處時(shí)需更為慎重。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論處的路徑未形成統(tǒng)一認(rèn)識(shí),在適用時(shí)仍有諸多紛爭(zhēng),本案中張一、張二、張三是否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即存在較大爭(zhēng)議,相關(guān)問(wèn)題亟待厘清。
二、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論處的定罪路徑評(píng)析
(一)出售麻精藥品的三種定罪路徑
當(dāng)前,對(duì)于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論處主要存在三種定罪路徑。第一種路徑為限縮的認(rèn)定模式,即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論處要求相關(guān)行為必須滿足三個(gè)前提條件:一是行為人出售的麻精藥品受國(guó)家規(guī)定管制;二是出售去向?yàn)槲净蛘哓湺救藛T;三是行為人明知所出售的藥品為受國(guó)家規(guī)定管制的麻精藥品,且去向是吸毒或者販毒人員。采用此種定罪路徑的代表性案例有吳某某、黃某某等非法經(jīng)營(yíng)案等,該案中被告人吳某某等人在未取得藥品生產(chǎn)、銷售許可的情況下,生產(chǎn)鹽酸曲馬多等藥品,后多次將加工好的鹽酸曲馬多藥片及包裝盒、說(shuō)明書(shū)交給多人轉(zhuǎn)賣,法院未認(rèn)定吳某某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2]該案例為進(jìn)一步論證被告人的販毒故意,還在上述三個(gè)條件外增加“獲得遠(yuǎn)超正常藥品經(jīng)營(yíng)所能獲得的利潤(rùn)”,出售利潤(rùn)大小往往能反映出行為人是以藥品還是毒品出售的故意,該增加條件意為兼顧麻精藥品和毒品的雙重屬性。但在司法實(shí)踐中,該條件并非必然存在,如少量、零包出售的,利潤(rùn)差并不明顯。
第二種路徑為擴(kuò)張性的認(rèn)定模式,即將第一種路徑中的出售去向從吸毒或者販毒人員擴(kuò)張到“非法用途”。在這種定罪路徑中,即使出售的麻精藥品未被用于吸毒或者販毒,只要是醫(yī)療等合法用途以外的非法用途,行為人明知而出售的,即可以販賣毒品罪論處。
第三種路徑是在第二種的基礎(chǔ)上,對(duì)非法用途作出限制,即麻精藥品是被用于吸食、販賣或者實(shí)施搶劫、強(qiáng)奸等較明確的犯罪活動(dòng),行為人明知而出售的,可以販賣毒品罪論處。
(二)三種定罪路徑的證明體系差異
傳統(tǒng)的販毒案件證明體系的核心在于主觀明知是毒品以及客觀有販賣行為,而出售麻精藥品案件證明體系的核心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明知內(nèi)容以及麻精藥品的用途去向。不同的定罪路徑中,出售麻精藥品案件的證明體系存在較大差異。
第一種定罪路徑中,需要證明的是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包括認(rèn)識(shí)到出售的是管制的麻精藥品,且具有將麻精藥品作為毒品替代品出售的意愿;客觀上,麻精藥品系用于吸毒或者販毒。引申到本文案例中,就要求證明張一、張二、張三積極追求或者放任購(gòu)買者將“泰勒寧”作為毒品的替代物吸食,并且查實(shí)購(gòu)買者系吸毒者或販毒者。
第二種定罪路徑中,僅需要證明行為人明知是管制的麻精藥品,且具有將麻精藥品作為非醫(yī)療用途出售的意愿。第三種定罪路徑和第二種定罪路徑基本相符,但在非法用途的證明上,需具象為吸食、販賣、強(qiáng)奸、搶劫等違法犯罪活動(dòng)。引申到案例中,第二種路徑要求證明張一、張二、張三明知他人購(gòu)買“泰勒寧”并非用于醫(yī)療活動(dòng),且購(gòu)買者無(wú)醫(yī)療等合法需求,第三種路徑要求證明張一、張二、張三明知他人購(gòu)買“泰勒寧”并非用于醫(yī)療活動(dòng),且購(gòu)買者系用于吸食、販賣或者實(shí)施搶劫、強(qiáng)奸等違法犯罪活動(dòng)。
(三)三種定罪路徑的選擇
根據(jù)2023年《全國(guó)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huì)議紀(jì)要》(以下簡(jiǎn)稱《昆明會(huì)議紀(jì)要》),行為人符合第一種定罪路徑的情形,以販賣毒品罪論處不存在爭(zhēng)議。按照第一種定罪路徑,本案中的張一、張二不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張三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但第一種定罪路徑過(guò)于限縮,不能很好應(yīng)對(duì)當(dāng)下的毒品犯罪形勢(shì),其最明顯的弊端在于只有查實(shí)吸毒人員吸食了麻精藥品才能定罪,無(wú)疑放縱了一些犯罪。比如,個(gè)別類型的麻精藥品吸食后無(wú)法以尿檢等方法檢出,此時(shí)下游買家有無(wú)用于吸毒未能查明,導(dǎo)致無(wú)法以毒品犯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
對(duì)于第二種擴(kuò)張性的定罪路徑,《昆明會(huì)議紀(jì)要》既未明確反對(duì),亦未直接支持。《昆明會(huì)議紀(jì)要》征求意見(jiàn)稿中曾將第二種擴(kuò)張定罪路徑吸納其中,后在正稿中又予以刪除,表明該路徑有較大爭(zhēng)議。若采用第二種定罪路徑,案例中張三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無(wú)爭(zhēng)議,張一、張二均有可能因未妥善履行審核義務(wù),未嚴(yán)格把握“泰勒寧”去向,從而被認(rèn)定為販賣毒品罪。支持?jǐn)U張定罪路徑的主要理由為“實(shí)踐中,一些行為人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向不特定主體出售麻精藥品,并冠以‘迷奸水‘催情水等稱謂,僅概括知悉他人可能用于實(shí)施違法犯罪,但是不了解、不關(guān)心他人的具體行為,且向多人進(jìn)行銷售,確有通過(guò)販賣毒品罪予以規(guī)制的必要性” [3]。誠(chéng)然,第二種定罪路徑的突破、擴(kuò)張是有必要的,但若擴(kuò)張幅度過(guò)大,將所有網(wǎng)絡(luò)倒賣麻精藥品的行為均以毒品犯罪定罪,可能導(dǎo)致錯(cuò)用罪名。
相較第二種定罪路徑,筆者認(rèn)為第三種定罪路徑更為妥當(dāng),主要理由是第三種定罪路徑將非法用途限定于為實(shí)施明確的、具有較嚴(yán)重社會(huì)危害性的違法犯罪行為,能兼顧主客觀相統(tǒng)一原則。《昆明會(huì)議紀(jì)要》涉及麻精藥品的規(guī)定共有6條,其中出罪條款是為了與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藥品管理法》條文規(guī)定保持一致;入罪條款則對(duì)非法用途作了條件限制。在傳統(tǒng)毒品犯罪中,毒品也不一定是用于吸食,基于其他違法目的而出售的,同樣可以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按照第三種定罪路徑,本案中的張一、張二均不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張三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
三、出售麻精藥品定罪路徑的進(jìn)一步釋明
筆者在贊同第三種定罪路徑的基礎(chǔ)上,對(duì)該定罪路徑中的核心要素作進(jìn)一步釋明。
(一)行為人對(duì)麻精藥品的認(rèn)識(shí)內(nèi)容和認(rèn)識(shí)程度
刑法中毒品的概念還包括國(guó)家規(guī)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因此,麻精藥品被認(rèn)定為毒品有兩個(gè)前提,一是國(guó)家規(guī)定管制,二是能夠使人形成癮癖。那么,行為人對(duì)這兩個(gè)要素主觀上是否都要有認(rèn)識(shí),并且需要達(dá)到何種程度,就能認(rèn)定明知是毒品?案例中張一就曾提出其不知道“泰勒寧”受管制,不知道“泰勒寧”能夠讓人成癮,只知道在外面藥店買不到,因此張一認(rèn)為不能認(rèn)定其明知“泰勒寧”是毒品。
癮癖性是麻精藥品的客觀屬性,是常人所知的常識(shí),無(wú)須例外證明。如案例中的“泰勒寧”是作為癌癥病人的常用止痛藥,而止痛藥不能濫用、容易成癮系一般常識(shí)。管制性則是國(guó)家規(guī)定列管后才具有的,檢察機(jī)關(guān)對(duì)行為人明知是管制藥品具有證明責(zé)任,證明內(nèi)容為行為人明知麻精藥品受到管控,不能隨意買賣。當(dāng)前,我國(guó)管制目錄主要有《麻醉藥品品種目錄》《精神藥品品種目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增補(bǔ)目錄》以及其他列管公告。如國(guó)家藥監(jiān)局、公安部、國(guó)家衛(wèi)生健康委《關(guān)于將含羥考酮復(fù)方制劑等品種列入精神藥品管理的公告》在2019年將“泰勒寧”列管,列管前“泰勒寧”在市場(chǎng)上可以自由買賣,列管后“泰勒寧”只能在醫(yī)院憑醫(yī)生處方開(kāi)具,流通受到嚴(yán)格控制,這是列管前后最為直接的變化。檢察機(jī)關(guān)在論證時(shí),無(wú)需要求行為人意識(shí)到具體的列管規(guī)定,只需對(duì)列管結(jié)果有概然性的認(rèn)知。具體到案例中,張一經(jīng)手的“泰勒寧”都是帶完整包裝的,包裝盒上顯眼之處注明系精神藥品,其提到的“泰勒寧”不能隨意買賣實(shí)際上就是明知受管制的供述。
當(dāng)然,對(duì)于列管不久的麻精藥品,在行為人是否明知管制的認(rèn)定上要更為慎重。如依托咪酯于2023年10月1日起正式列管,對(duì)于行為人在列管前后連續(xù)出售的,要進(jìn)一步核實(shí)行為人對(duì)管制狀況、何時(shí)列管、知曉渠道等情況的認(rèn)識(shí),以免作出錯(cuò)誤認(rèn)定。
(二)以毒品替代物出售故意的認(rèn)定
販賣毒品罪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間接故意,在涉麻精藥品案件中,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也應(yīng)包括直接追求和間接放任。實(shí)踐中常有四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行為人沒(méi)有作為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第二種情形為行為人出售時(shí)認(rèn)識(shí)到有作為毒品替代物的些許可能;第三種情形為行為人有作為毒品替代物的高度懷疑而放任出售;第四種情形為行為人確定有作為毒品替代物的直接故意。
其中,存在爭(zhēng)議的是第二種和第三種情形,正如案例中的張一和張三,張一在向張二出售“泰勒寧”時(shí),知道張二是倒賣藥物的,藥物去向有可能流向黑市;張三在向張四出售“泰勒寧”時(shí),前期懷疑張四短期、多次、大量購(gòu)買“泰勒寧”系用于吸食。張一堅(jiān)稱自己沒(méi)有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張三認(rèn)可自己有該故意。對(duì)于第三種情形,可以認(rèn)定具有販毒故意。對(duì)于第二種情形,就不能認(rèn)定販毒故意。盡管張一多次向張二出售“泰勒寧”,未盡到審核義務(wù),亦未排除“泰勒寧”流入毒品市場(chǎng)的可能。但張一的這種可能性不明顯,與張三所持的高度懷疑程度上有較大差距,張一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認(rèn)識(shí)尚不充分。同時(shí),張一僅有倒賣藥物從中牟利的追求故意,不能以未盡到審核義務(wù)直接推定為張一具有作為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放任故意。
涉麻精藥品的毒品案件中,行為人主觀必然交織著擾亂藥品管理秩序的故意和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在不認(rèn)罪的情況下,判斷販毒故意的關(guān)鍵在于行為人對(duì)他人購(gòu)買用于替代毒品的認(rèn)知程度,若達(dá)成高度懷疑的則可以認(rèn)定。
(三)非法用途的界定
毫無(wú)疑問(wèn),將麻精藥品作為毒品替代物吸食是非法用途之一。實(shí)踐中在判斷非法用途的對(duì)象、方法上存有偏差,如判斷對(duì)象混亂不清,又有以最終去向倒推認(rèn)定為非法用途等問(wèn)題。具體到案例中,張一作為出售者,其始終具有倒賣藥品獲利的非法目的,能否就等同于非法用途?判斷張二的非法用途時(shí)是站在張二、張三角度綜合判斷,還是要考慮張四?“泰勒寧”從張一、張二、張三層層流轉(zhuǎn),最終被吸毒人員吸食,能否認(rèn)定張一、張二、張三均是非法用途?
其一,倒賣牟利的非法目的不等于非法用途,對(duì)非法用途的評(píng)判需要兼顧買賣雙方。《昆明會(huì)議紀(jì)要》規(guī)定,對(duì)出于治療疾病等相關(guān)目的,未經(jīng)許可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或者自救、互助的,不以毒品犯罪論處。換言之,買方作為麻精藥品持有者,其是否用于治療疾病,能夠反映賣方的主觀故意。賣方明知買方需要麻精藥品進(jìn)行治療而提供,表明賣方是出于治療他人疾病的目的。倒賣牟利與否與麻精藥品是否用于治療疾病沒(méi)有必然聯(lián)系,無(wú)法推定為非法目的。否則,所有無(wú)許可經(jīng)營(yíng)管制的麻精藥品行為人都可直接認(rèn)定為非法用途,顯然不妥當(dāng)。
其二,在連環(huán)倒賣的情況下,需要多環(huán)節(jié)判斷非法用途。在販賣毒品罪認(rèn)定中,明知是販毒分子而販賣管制的麻精藥品同樣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該種情形下,為論證買方的販毒分子身份,需對(duì)買方的下線進(jìn)行考量,全維度審查行為人—販毒分子—吸毒人員鏈條。如張二向張三出售“泰勒寧”,販毒分子張三又向吸毒人員出售,只有張二明知張三是販毒分子方可認(rèn)定非法用途,張二才可能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若不審查張三對(duì)“泰勒寧”的處置去向,則對(duì)張二不便進(jìn)行非法用途的判斷。
其三,非法用途是主客觀相結(jié)合的認(rèn)定,而非客觀事實(shí)的簡(jiǎn)單倒推。不是麻精藥品最終流入毒品市場(chǎng),就能對(duì)流轉(zhuǎn)鏈的出售人均進(jìn)行打擊。如張一將“泰勒寧”出售給張二,張一無(wú)法確認(rèn)張二如何使用“泰勒寧”,或是否按照約定使用“泰勒寧”,此時(shí)以最終流向是毒品市場(chǎng)推定張一系非法用途,既不現(xiàn)實(shí),也不符合法理,不當(dāng)擴(kuò)大了販賣毒品罪的犯罪圈。
其四,非法用途的限制條件應(yīng)為較明確、具有一定社會(huì)危害性的違法犯罪行為。出售人明知麻精藥品用于上述危害行為,其將麻精藥品用于違法性目的的故意相對(duì)明確,以販賣毒品罪追究刑責(zé)并未超出公眾認(rèn)知。
本案中張三明知張四將“泰勒寧”作為毒品替代物吸食,其行為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張一、張二明知轉(zhuǎn)手的“泰勒寧”實(shí)際流向藥房,但對(duì)藥房私下向吸毒人員出售“泰勒寧”并不明知,故無(wú)法認(rèn)定張一、張二的購(gòu)買者系非法用途,二人不具有販毒故意,不構(gòu)成販賣毒品罪。
*本文所稱麻精藥品是指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
**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四級(jí)檢察官[325200]
***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325200]
[1] 參見(jiàn)《2022年中國(guó)毒情形勢(shì)報(bào)告》,中國(guó)禁毒網(wǎng)http://www.nncc626.com/2023-06/21/c_1212236289_3.htm,最后訪問(wèn)日期:2024年2月1日。
[2] 參見(jiàn)林鐘彪、曹東方:《吳名強(qiáng)、黃桂榮等非法經(jīng)營(yíng)案——非法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國(guó)家管制的第二類精神藥品鹽酸曲馬多,應(yīng)如何定性》,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廳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2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0頁(yè)。
[3] 元明、黃衛(wèi)平、肖先華:《加大對(duì)新型毒品犯罪的懲治力度——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導(dǎo)性案例解讀》,《人民檢察》2022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