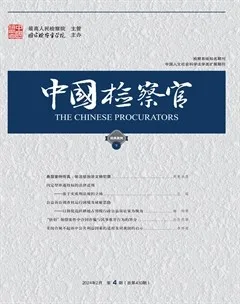“快招”加盟案件中 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分*
應亦然 胥嘉平 劉群
一、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起,金某等人成立A餐飲管理公司從事餐飲招商加盟活動。2018年初起,為謀取巨額利潤并規避法律風險,金某等人又先后成立B網絡科技有限公司、C管理咨詢有限公司、D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等多家關聯公司,將A餐飲管理公司內設的業務部門分割管理,分置于上述關聯公司運行,形成“A集團”。在此過程中逐步形成以金某為首要分子,劉某、韓某等人為重要成員,程某、趙某等人為一般成員,有較為明確、固定分工、具有一定層級的犯罪集團。
金某等人為騙取高額加盟費,在明知A集團不具備相應運營能力及資質的情況下,或自營或與他人合作,采用“快招”方式對外招商加盟。在招商過程中,A集團謊稱所推介品牌和知名品牌屬同一集團或有合作關系進行“貼牌”[1],通過虛構運營能力、提供虛假授權、聘請明星代言等方式誘使被害人簽約,騙取加盟費。之后A集團一方面對已加盟被害人的正當運營需求敷衍了事,甚至不管不顧,放任經營失敗,在因此產生訴訟后,又通過轉移資金的方式逃避退款義務,另一方面再以相同手法包裝推介新品牌,繼續以“貼牌”“快招”方式騙取更多被害人加盟費。自2018年1月1日至案發,A集團以24個品牌名義累計騙取全國5800余名加盟商共計人民幣4.4億余元。
2022年5月5日,S區人民檢察院根據不同層級和部門,以合同詐騙罪對金某、劉某等人提起公訴。后S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均采納指控意見,以合同詐騙罪分別對金某、劉某等人判處14年6個月至3年1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相應罰金。判決后,金某等人不服,提出上訴。
二、分歧意見
本案是一起“套路加盟”合同詐騙案件,同時又是刑民交織案件,如何區分罪與非罪,如何體現犯罪分子非法占有目的,是本案重要爭議焦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金某等人的行為屬于民事違約而非合同詐騙,理由如下:
一是本案存在真實交易。加盟商是與真實的品牌方合作,獲得了加盟服務,收款方沒有逃逸。且金某等人確實對加盟商進行了選址、培訓、供貨、授權等加盟服務,提供了真實的加盟內容,僅是在售后服務過程中存在瑕疵,沒有服務好加盟商,故系合同違約,不屬于刑事犯罪。二是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本案加盟商大多獲得了真實有效的加盟服務,雖然后期存在經營不善的情況,但多由于加盟商自身原因、疫情耽誤或未完成選址等客觀因素造成,并非涉案團伙不履行合同所致。且簽訂的合同系真實有效的,加盟服務也真實,部分加盟商也仍在經營,不能簡單地因涉案團伙在前期宣傳上有夸大虛構成分就直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綜上,在金某等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況下,前期的夸大、虛假宣傳行為可以認定為虛假廣告罪,但不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金某等人的行為屬合同詐騙,理由如下:
一是金某等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A集團在抖音、微博等平臺投放知名品牌需要招商的虛假廣告,并建立虛假的知名品牌網站,吸引大量客戶尋求加盟。在與被害人溝通過程中,謊稱系知名品牌的招商總部、推介品牌系知名品牌的合作或升級品牌,虛構運營團隊、用料、技術與知名品牌為同一團隊等情況,夸大運營能力,使被害人對所推介品牌的可靠度和期望值產生錯誤認識。在與被害人簽約過程中,亦存在提供虛假授權委托書、雇人排隊制造虛假繁榮等行為,騙取被害人信任,使被害人誤以為加盟后可以獲得高品質的品牌推廣與經營扶持服務從而簽約支付加盟費。二是金某等人沒有真實履約的意愿及能力,在收取費用后亦未提供實質性服務。A集團在人員配備、資金分配上以營銷為主,缺乏運營所需的基本條件,無法滿足數千名加盟商的運營服務要求。A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客戶的加盟費,為了賺取更多的加盟費,采用短期內頻繁推出新品牌的模式把客戶引流至新品牌。而新品牌無論是種類還是區域都與老品牌高度一致,導致運營能力分散、老品牌經營失敗。可見,A集團自始就沒有切實履行合同的真實意愿,也沒有去創造履行合同的條件,主要目的是吸引被害人簽約,騙取加盟費。三是金某等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金某等人在明知A集團運營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仍與被害人簽約且未提供應有的運營服務。在遇到大量被害人投訴后,短期內使用多家公司、頻繁更換招商品牌、搬遷辦公地址等逃避責任,后又繼續進行招商騙取加盟費。被害人運營失敗并非客觀原因所致,而系金某等人沒有運營意愿和能力,沒有適當的履行行為所致,不屬于正常的商業風險。A集團通過出售老品牌、關停相關公司的方式來應對大量的客戶投訴、訴訟,逃避承擔責任,應認定金某等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錢款的故意。
綜上,雖然金某等人在犯罪的過程中實施了虛假宣傳的行為,但對于犯罪行為應作整體評價,而不應割裂開來就某個環節進行評價。金某等人以招商加盟的方式,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被害人財物,其行為不僅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權,同時也擾亂了市場秩序,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的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本案犯罪確實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取證難度也較大,導致許多類似案件最終只能以民事訴訟解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真正保障。筆者認為,在辦理這種民刑交叉案件時,既要重視民刑區別,更要關注民刑關聯。實踐中,有不少欺騙行為會突破民事違法而上升至刑事犯罪。因此,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合同欺詐行為對于罪與非罪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區分民事合同欺詐與合同詐騙,筆者認為并不存在單一的區分標準,而是應當從欺騙內容、欺騙程度和非法占有目的這三個方面加以界分[2],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尤為關鍵。
(一)欺騙內容
刑法理論上認定合同詐騙罪的特征主要是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虛構事實是指行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信任。隱瞞真相是指行為人故意隱瞞客觀存在的事實,故意隱瞞另一方應該知悉的內容。本案中,金某等人以“A集團”名義,采用“貼牌”手法虛構事實,隱瞞公司“快招”本質,以簽訂、履行合同的民事行為掩蓋詐騙的本質。A集團雖然使用真實的品牌與加盟商簽訂合同,但在宣傳過程中通過傍名牌的方式使客戶誤認為與知名品牌有關聯,誘使客戶加盟,單從這一方面而言仍屬于欺詐范疇,根本還是在于隱瞞公司“快招”本質,防止客戶得知真相。所謂“快招公司”,就是短時間內利用各種手段包裝打造出一款品牌“爆品”,大規模快速招商,獲取巨大加盟費等利益,但后期服務支持無法提供。這類公司往往注冊多家公司,借大品牌的名頭進行宣傳,當其所創造的“爆品”熱度消失,會通過再次包裝新的“爆品”獲利。一般而言,“快招公司”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宣傳成本高,往往花費大量資金來宣傳加盟公司;二是后續開店難,短期內頻繁更換品牌,后續開店也缺乏責任心;三是缺乏產品研發,往往只注重招商加盟,對產品的研發不重視。A集團就屬于較為典型的“快招公司”,其自營品牌不具備運營能力,被害人不可能正常運營,這與單純虛假廣告、虛假宣傳存在本質不同。因此,本案認定的關鍵在于A集團系“快招公司”,沒有運營能力。A集團在明知自身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的情況下,隱瞞了沒有穩定運營品牌的意愿和能力,并通過簽訂、履行合同的民事行為掩蓋其背后的詐騙行為。
(二)欺騙程度
欺騙程度是指行為人采用的欺騙方法,是否達到使他人產生認識錯誤并處分財物的程度。不論是民事欺詐還是合同詐騙都存在欺騙行為,只是欺騙的程度不同。合同詐騙罪的欺騙是達到了控制交易結果的程度,因而被害人是無對價的交付財物;而民事欺詐的欺騙則是在交易真實前提下的欺詐,盡管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但這是因為被欺詐而造成的財產損失。[3]本案中,A集團在吸引加盟過程中采用了虛構手段,使加盟商產生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物。在前期招商過程中,具有制作冒充知名品牌的假網站、假冒知名品牌、使用知名品牌商品冒充自營品牌商品給客戶試吃等進行招商行為,并與加盟商簽訂、履行合同,而上述行為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誤以為加盟后可以獲得高品質的品牌推廣與服務,從而進行加盟投資。在后期的運營過程中,也未提供幫助被害人正常經營的實質性服務,其所謂的運營行為實際上是為了安撫被害人而采取的拖延、應付行為,并沒有履行對價行為的意愿,繼而造成被害人損失。
(三)非法占有目的
套路加盟案件因其具有較強的民事經營偽裝,導致案發后各犯罪嫌疑人均存在自身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辯解。要排除此類辯解,需要立足于客觀證據,根據行為人之行為特征來認定。從單一個案來看,本案非法占有目的認定難度較大,但從大量報案、相同模式、眾多品牌的表征看,能夠反映出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已形成“套路”,系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加盟為形式,騙取加盟費的行為。一是沒有穩定運營品牌的意愿。A集團招商大部分都是代理加盟,一個縣一個市只要一個代理就結束加盟,代理中有一半左右甚至都沒有開業,在品牌根本沒有運營起來的情況下,A集團在短期內頻繁更換品牌招商,致使老加盟商利益受損,可見A集團沒有真正運營品牌的意愿。二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本案中,A集團不存在專業的研發團隊。所謂產品配方也僅是物料供應商所提供,既沒有相應產品研發也沒有良好的口味,無法保證產品的質量,沒有能力為加盟商提供應有的加盟產品的實際服務;不具備成熟的經營模式,根據《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特許人從事特許經營活動應當擁有成熟的經營模式......”,A集團在長達三年多的經營過程中,雖然表面經營過多個品牌,但沒有一個品牌獲得成功,且短期內頻繁更換品牌,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經營任何一個品牌,被害人不可能正常運營。被害人加盟后,A集團雖然提供了選址、帶店、培訓等服務,但其目的只是欺騙前期加盟商開店,從而獲取相應的照片、視頻進行宣傳,進一步誘使其他被害人簽約,且在收取加盟費之后通過拖延、掩飾等手段避免加盟商發現其騙局,等待加盟商自行倒閉,從而逃避自身責任。三是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A集團在簽訂加盟合同后,雖表面上為加盟商進行培訓、提供裝修圖紙、提供經營設備及物料,但實際上培訓流于形式,提供設備和服務也與先期承諾大相徑庭,加之在一定時間或遇大量投訴后迅速更換品牌等行為,充分證明這些行動均非其實際履行合同的表現,而是為了騙取更多加盟商進行的偽裝,實際是對合同的消極履行。四是逃避承擔民事違約責任[4]。A集團一方面先后使用多家公司、頻繁更換多個品牌,對客戶投訴采取拖延方式,不從提高經營品牌能力方面努力,而是在某個品牌獲得一定加盟費或者遭遇大量客戶投訴后立即予以更換,通過假倒閉、假破產方式逃避民事訴訟責任。另一方面,收取加盟款后,通過轉移資金的方式逃避退款義務,肆意揮霍加盟款,拒不用于后續品牌運營。
綜上,A集團采用夸大運營能力、貼牌等方式,隱瞞其沒有運營能力的真相,并采用快招方式騙取大量被害人簽訂加盟合同,并以此騙取加盟費,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2023年7月21日,S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辦理此類案件時,要加強對涉案企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和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這兩個關鍵性問題的審查,從而辨別民事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一是要加大對欺詐行為的審查力度。雖然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這兩類案件中都存在欺騙因素,但在性質和程度上存在區分。此類案件審查重點在于公司是否屬于“快招公司”,據此判定品牌運營能力的有無,如果一個品牌沒有相應運營能力,那么無論其如何向被害人承諾,被害人最終的損失從加盟伊始就是確定的;相反,如果一個品牌具有運營能力,那么即使其在招商過程中存在貼牌、夸大等欺詐行為,也不足以認定相關人員構成合同詐騙犯罪。二是要加強對非法占有目的的審查。無論是民事欺詐還是刑事詐騙,都會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失。因此,存在財產損失并不能就此認定為詐騙罪。在某些情況下,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在行為方式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不能單從行為方式上區分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而是要從行為人的主觀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上予以區分[5]。而非法占有目的作為行為人的主觀心理,需借助一定的客觀行為表現出來。故此類案件注意著重審查公司是否存在假倒閉、假破產、逃避法院執行義務的情況,同時查明資金流向,明確涉案加盟款最終走向,查證是否存在抽逃資金、肆意揮霍、拒不用于后續品牌運營的情況,以此判定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故意,從而準確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
*“快招”指犯罪分子短期內頻繁更換招商品牌以便于騙取更多加盟費的行為。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201620]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一級檢察官[201620]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四級檢察官助理[201620]
[1] “貼牌”指犯罪分子虛構涉案品牌與知名品牌存在合作關系以此誘使客戶相信涉案品牌實力的行為。
[2] [3] 參見陳興良:《民事欺詐和刑事欺詐的界分》,《法治現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
[4] 參見王延祥:《如何認定詐騙罪中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政治與法律》2003年第3期。
[5] 參見徐佳蓉:《論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區分》,《研究生法學》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