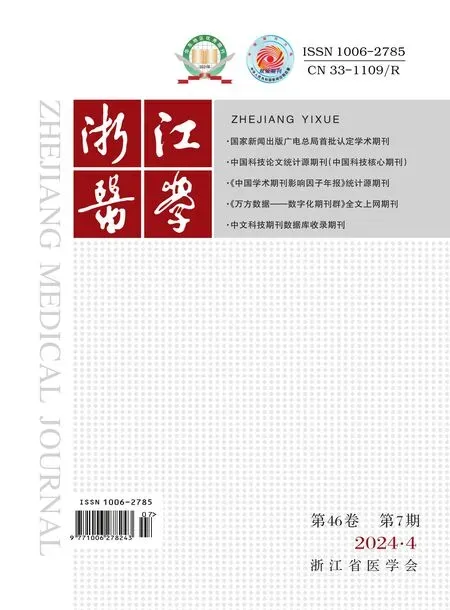妊娠哺乳期相關骨質疏松癥現狀及治療進展
譚晨蕾 李琰華
骨質疏松癥可以分為原發性骨質疏松癥和繼發性骨質疏松癥。原發性骨質疏松癥常見于絕經后婦女,這是一種因為雌激素水平下降對破骨細胞的抑制作用下降,成骨細胞介導的骨形成不足以代償破骨細胞介導的骨吸收而使骨強度下降產生的骨骼損害[1]。妊娠哺乳期相關骨質疏松癥(pregnancy and lactationassociated osteoporosis,PLO)屬于原發性骨質疏松癥的一種特發性骨質疏松,通常于第一次妊娠晚期或產后早期發作。研究表明,懷孕期間母體的面積骨密度(areal bone mineral density,aBMD)將會下降1%~4%,而哺乳期間aBMD 會下降4%~8%[2],而絕經后女性的aBMD 平均每年下降1%~2%[3],妊娠哺乳期間出現的骨密度下降水平大大高于絕經后女性,可見該疾病對母體的影響十分巨大。本文將從PLO 的流行病學、危險因素、發病機制、臨床特點及治療方法等作一綜述,為該疾病的預防、篩查、早期干預和治療提供理論依據,從而提高妊娠哺乳期婦女的生活質量,減少傷殘率。
1 流行病學
PLO 是一種罕見但嚴重的疾病。PLO 婦女妊娠或產后期間有可能發生脆性骨折,這與骨密度顯著降低有關。最早在20 世紀40 年代就有關于PLO 的研究,來自年輕女性木乃伊的組織樣本表明,這種疾病在5 000 年前就已出現[4]。有文獻曾提到每100 萬次妊娠將會產生4~8 次PLO[5-6],然而這一數據的來源尚不清楚。目前國內外關于PLO 的文獻多以病例報道為主,大多數屬于觀察性研究,同時PLO 患者發病前幾乎為健康的育齡期女性,所以缺少骨密度的檢測結果來確定她們是否為妊娠前骨質疏松癥。
2 危險因素
研究表明鈣攝入量低、維生素D 攝入不足、妊娠期間使用糖皮質激素及肝素、童年牙齒缺失、青少年時期缺少運動和骨質疏松癥家族史等可能是影響PLO發病的因素[5,7]。許多PLO 患者表示在兒童期和青春期后的體力活動較少,相關研究強調了體育活動對峰值骨量發展的影響[8]。因此,增強運動被認為可能是一種保護性因素。有研究發現肥胖或超重人群患PLO 的風險較高[9],另一項研究發現體重過低(BMI<18 kg/m2)是PLO 的危險因素[5]。同時,無論PLO 患者年齡如何,長時間的母乳喂養被認為是PLO 發生的危險因素之一[7]。除此之外,Butscheidt 等[6]認為低密度脂蛋白受體相關蛋白5、Ⅰ型膠原蛋白α1 和Ⅰ型膠原蛋白α2 中的新型基因突變也是PLO 發病的危險因素。
3 發病機制
目前因為PLO 在全球范圍內的確診數太少,所以它的病理生理機制尚無確切的定論。本節將從胎兒對母體的需求以及母體自身的改變兩個方面對其發病機制進行闡述。
3.1 胎兒對母體的需求 足月胎兒骨骼含鈣約25~30 g,相當于母體骨骼鈣含量的3%左右[4]。胎兒骨骼的增長大多發生在妊娠期的最后3 個月,這期間胎兒對鈣的需求量增加,而母體骨骼是胎兒骨骼生長的重要鈣源,所以在妊娠期間母體骨量顯著減少[5,10]。同樣的,在哺乳期中的哺乳動物會吸收母體骨骼中的礦物質,為乳汁提供鈣。純母乳喂養的女性每天將會失去大約210 mg 的鈣,這些鈣大部分來自于母體骨骼,雙胞胎或三胞胎的純母乳喂養母親失去的鈣量將增加1~3 倍[10]。這一過程不僅涉及到破骨細胞介導的骨吸收,而且與骨細胞溶骨有關[11-12]。
3.2 母體自身的改變 在妊娠期間母體對鈣的需求會增加,以滿足胎兒對鈣的大量需求。一方面,通過增加腸道的鈣吸收來滿足母體對鈣的需求[13]。另一方面,通過刺激來源于胎盤及胎兒腎臟1α-羥化酶活性,有助于血液循環中活性維生素D3[1,25-(OH)2D3]的增加,同時妊娠期間雌二醇和催乳素的分泌也會促進1,25-(OH)2D3的增加[14]。而在哺乳過程中,血液循環中1,25-(OH)2D3在分娩后迅速回到孕前水平,鈣在腸道的吸收也恢復到孕前水平[15],因此不再能充分確保母體對鈣的需求,導致鈣流失大于鈣吸收。
組織蛋白酶K(cathepsin K,Ctsk)是破骨細胞產生的半胱氨酸蛋白酶。它是介導脫礦骨基質降解的主要酶。哺乳期間骨細胞Ctsk 基因表達升高,Ctsk 通過調節骨細胞表達影響骨周圍的吸收,同時使骨細胞陷窩增大,使破骨增加[11]。
甲狀旁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有提高血清中鈣含量的作用。當鈣攝入量充足時,妊娠期孕婦體內PTH 濃度通常維持在較低水平。如果妊娠時孕婦鈣和維生素D 攝入不足,那么為了確保母體自身以及胎兒對鈣的需求,胎盤和乳房產生的妊娠期高甲狀旁腺素相關蛋白(parathyroid hormone-related protein,PTHrP)就會相應增加。因為PTHrP 的前34 個氨基酸與PTH 的結構相似,它是PTH/PTHrP 受體的配體,它的作用與PTH 相似。PTHrP 的中間區域可以刺激胎兒胎盤鈣轉運,其末端區域也可能有抑制破骨細胞活性來刺激骨轉化的作用。因此PTHrP 可以刺激骨轉化,動員骨鈣入血,導致妊娠期骨量的流失[4,15]。在哺乳期,PTHrP 通過成骨細胞和骨細胞產生NF-κB 受體激活因子配體(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κB ligand,RANKL),可間接激活破骨細胞[15]。骨細胞微環境的改變會導致PTHrP 和RANKL/骨保護素比值增加,從而增加破骨細胞生成,導致骨吸收和血清鈣的升高[11,16]。
雌激素缺乏將會促進破骨細胞活化,圍絕經期所致雌激素降低導致老年女性發生骨質疏松癥的風險增加。產后婦女常常可以被觀察到雌激素短暫下降。Miyamoto 等[17]在一項研究中觀察到年輕女性產前雌二醇水平比正常絕經前女性高100 倍,但在分娩后,其雌二醇在很短的時間內下降到絕經后女性的水平。同時在產后這一時期,PTHrP 水平升高,這兩個因素都會導致骨吸收增加,比起單一因素,協同效應對骨吸收的促進作用加強,這與骨量的流失有重要關系[18]。
4 臨床特點
由于PLO 病例數稀少,目前國內外尚無確切診斷標準。PLO 常因妊娠晚期或者產后早期出現下腰部、臀部或下肢的劇烈疼痛甚至身高下降或者脆性骨折而被發現[19]。一項納入了102 例PLO 患者的研究發現,88.8%的PLO 患者至少有過1 次骨折,平均骨折3.3次,這些骨折主要發生在胸腰椎,這將導致明顯的身高損失[5]。結合目前的相關研究,認為PLO 的骨折主要發生在第一次妊娠中,在妊娠的最后3 個月或產后的頭幾個月[5,20]。
5 治療方法
目前PLO 還沒有明確推薦的治療方案,基本按照絕經后骨質疏松癥的癥狀進行經驗性治療。骨質疏松癥的治療主要針對促進骨形成和減少骨吸收兩個方面進行。由于PLO 患者處于特殊病理生理時期,需要關注到該類患者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特征,本節就近期PLO 的新治療、新方向作一總結。
5.1 停止哺乳 一項縱向研究發現,在產后6 個月的哺乳期測量骨密度時,橈骨骨密度下降1%~5%,腰椎下降1%~8%,股骨頸下降3%~6%,全髖關節下降4%[21]。一旦發現PLO 相關癥狀,停止哺乳將作為首選推薦治療方式。
5.2 運動 有動物實驗提示動態負荷增強了各組大鼠皮質骨結構和骨膜骨形成,重量的負荷減少了泌乳引起的骨小梁丟失,并改善了皮質骨結構,這表明在懷孕和產后負重鍛煉對母體骨有正向影響[2]。佟喆等[22]發現通過運動可以調節信號通路抑制破骨細胞形成或促進成骨細胞分化而維持骨代謝的穩定性。因此,妊娠哺乳期婦女可以適當進行運動。
5.3 心理治療 由于激素、家庭環境變化等因素,妊娠哺乳期女性心理問題高發。Gehlen 等[20]研究發現PLO 對疼痛、精神狀態、生活質量和工作能力均有重大影響。而目前臨床診療中,尚未重視PLO 患者的心理狀況,導致患者遭受身體及心理的雙重痛苦。妊娠哺乳期女性可以前往心理門診進行精神情緒方面的相應評估,認知行為療法、不良情緒的心理疏導均為常見的有效心理治療方式。
5.4 補充鈣劑、維生素D 鈣是骨骼礦物質成分的一部分,鈣劑和維生素D 是人體骨骼健康的重要補充劑。目前各國對孕期及妊娠期的鈣攝入量未達成共識,根據健康參考指南,19 歲以上人群的鈣推薦量從700~1 000 mg 不等,指南推薦懷孕期間增加鈣的攝入量到1 300 mg/d[23]。鈣攝入量不足會增加孕婦孕期骨丟失,降低產后骨恢復。Cullers 等[24]研究發現接受1 000 mg 補充鈣的孕婦產后負重部位的皮質和總骨密度恢復率比接受安慰劑治療的孕婦提高4%~5%。一項Meta 分析認為育齡期婦女普遍缺乏維生素D 和鈣的攝入[25]。Polzonetti 等[26]也指出在抗骨質疏松癥治療中,患者需要每天補充維生素D 高于700~800 IU,從而使血清1,25-(OH)2D3>50 nmol/L,且膳食鈣攝入量為1 200 mg/d。因此推薦妊娠哺乳期婦女維生素D 的攝入>700 IU/d,鈣攝入>1 200 mg/d 是合理的。
5.5 骨形成促進劑 臨床中常見的骨形成促進劑有PTH 類似物和骨硬化蛋白單克隆抗體等。
5.5.1 PTH 類似物 特立帕特是國內已被批準使用的PTH 類似物代表藥物。一項PLO 婦女的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表明在治療12 和24 個月后,特立帕特聯合鈣和維生素D 補充組aBMD 和骨小梁評分明顯好于單純鈣和維生素D 補充組[27]。特立帕肽的一個重要不良反應是增加骨腫瘤的風險,但這取決于劑量和治療持續時間。特立帕肽尚未在人類胎兒發育中進行研究,也沒有臨床數據可以確定特立帕肽是否分泌到母乳中;但特立帕肽的半衰期為1 h,且不在骨骼中蓄積,這表明孕前停藥不會對胎兒造成影響[28]。特立帕特的總治療時長為24 個月,即患者終身僅可接受一次為期24 個月的治療。
5.5.2 骨硬化蛋白單克隆抗體 羅莫單抗是其代表藥物,具有促進骨形成和抑制骨吸收的雙重作用,其治療效果優于其他抗骨質疏松癥藥物[29-30]。該藥品于2019 年被FDA 批準用于治療高骨折風險的絕經女性骨質疏松癥患者,但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尚未完全被批準用于骨質疏松癥的治療。能否用于對PLO 患者的治療,仍需要更多的試驗來進一步論證。
5.6 骨吸收抑制劑 臨床中常見的骨吸收抑制劑有雙膦酸類藥物、降鈣素、雌激素、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類、RANKL 抑制劑等。
5.6.1 雙磷酸類藥物 雙膦酸鹽與骨骼羥磷灰石的親和力高,能夠特異性結合到骨重建活躍的表面,抑制破骨細胞功能,從而抑制骨吸收[31]。張欣欣等[32]研究中,2 例PLO 患者使用唑來膦酸治療后6 個月臨床癥狀緩解,后續隨訪發現全髖骨密度增加11.09%~13.34%。一項病例對照研究指出未發現雙磷酸鹽對妊娠結局的不良影響和新生兒的致畸作用[33]。Olvera等[34]通過對母鼠使用帕米膦酸鈉發現,該物質可以通過胎盤,進一步追蹤出生時和斷奶時的新生幼鼠,并未顯示出母鼠帕米膦酸鈉暴露對骨骼的不良影響。但也有動物研究顯示雙磷酸鹽對妊娠期大鼠有毒性反應[35]。由于雙磷酸鹽類藥物的半衰期較長,目前臨床對于PLO 患者的使用仍需要謹慎。
5.6.2 降鈣素 降鈣素是一種鈣調節激素,能抑制破骨細胞的生物活性、減少破骨細胞數量,減少骨量丟失并增加骨量,同時具有緩解骨痛的作用。目前長期使用從鼻腔途徑給藥的降鈣素已從市場上移除;而注射式降鈣素連續使用一般不超過3 個月[36]。
5.6.3 雌激素 雌激素的主要作用是抑制骨吸收,該藥物基本上用于絕經后女性骨質疏松癥患者[37]。雖然產后婦女的雌激素水平急速下降類似于絕經后狀態,但目前臨床暫時未有PLO 患者使用雌激素。雌激素可能導致心血管方面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腫瘤,例如乳腺癌、卵巢癌等[38]。
5.6.4 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類 這類藥物多采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成,這些調節劑發揮類似雌激素或抗雌激素作用,他莫昔芬是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類藥物的代表。Schuurman 等[39]認為妊娠期間使用他莫昔芬可能增加胎兒的致畸風險,但證據有限,不應該將其作為絕對禁忌證。他莫昔芬是第一代臨床治療乳腺癌的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類藥物,也被證明對人和動物都有保護骨的作用,但它增加了子宮內膜癌的發病風險。雷洛昔芬是第二代被批準用于治療骨質疏松癥的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類,是一種骨雌激素激動劑,并且不刺激子宮組織的生長[40]。
5.6.5 RANKL 抑制劑 地諾單抗是一種RANKL 抑制劑,它的主要作用是使RANKL/NF-κB 受體激活因子信號轉導被抑制,進而導致破骨細胞的發育和活性,從而減少骨吸收。1 例產后PLO 患者經地諾單抗治療18 個月后,其腰椎、股骨頸和全髖關節骨密度分別提高32.2%、13.0%和11.5%,無骨折發生,因其再次備孕,故停止地諾單抗的使用,第二次妊娠后,該患者腰椎、股骨頸和全髖關節的骨密度分別比地諾單抗治療期間的最大值下降了8.8%、6.9%和7.0%[41]。
5.7 β-羥基-β-甲基丁酸鹽(β-hydroxy-β-methylbutyric acid,HMB) Tomaszewska 等[42]通過給予妊娠中期母鼠HMB 發現該藥物可以增加骨小梁數量,加強骨代謝過程,防止懷孕期間骨丟失。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可以假設給孕婦服用HMB 對關節軟骨和骨有非常積極的影響[43]。在骨組織丟失之前,這種保護作用在骨小梁中比致密骨更明顯。
5.8 外科治療 PLO 患者常因為產后初期嚴重的下背部疼痛、身高下降和脆性骨折,尤其是椎骨骨折而被發現。除了上述藥物治療外,還可輔以腰托固定使患者可以站立活動從而促進骨量的恢復。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椎體、椎體后凸成形術、脊椎融合等外科手術也認為可能是必要的一種治療手段[44]。
5.9 中醫治療 目前針灸被發現可通過促進骨形成,抑制骨吸收的途徑來改善原發性骨質疏松癥患者的骨代謝[45],可以期待針灸對于PLO 患者的療效。中草藥如淫羊藿長期以來被用于治療骨病,它的骨保護作用可能是通過雌激素受體來實現的,根據PLO 患者中醫證型的不同,還可以行進一步的研究[40]。
6 小結
妊娠哺乳期婦女是臨床醫生的重點關注人群。然而由于PLO 的發病率較低,多數患者以腰痛為首發癥狀,因缺乏相關臨床知識,從而導致延誤診治,使該時期婦女的身心皆遭受痛苦。面對該類患者,醫生需要多方面進行評估,綜合地進行防治,長期追蹤該人群的骨密度恢復情況,避免造成更嚴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