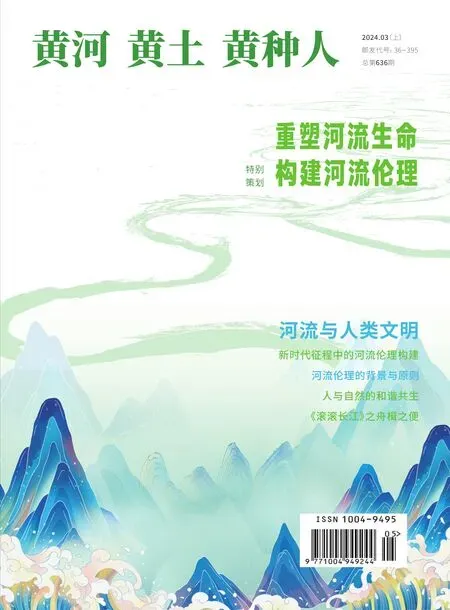《滾滾長江》之舟楫之便
陳松平
奔騰長江,水道縱橫,自古就便于行船。
遠古先民刳木為舟,到中流擊水,是為長江舟楫之便的肇始。其后,伴隨著社會進步、生產力發展,“南船北馬”成為古代交通運輸兩大方式。而水量充沛且終年不凍、承東啟西又接南納北的長江,堪稱國家交通大動脈,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水道。
數千年來,依托發達的水運交通,長江上下演繹了一幕幕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的繁華景象,杜甫在夔州江邊看到“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李白在江夏與友人感嘆“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均為長江水運興盛之生動寫照。
百舸爭流,千帆競發;舳艫相接,通江達海。如今,以長江黃金水道為骨架,公路、鐵路、航空和橋梁等為骨干形成的綜合立體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正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百舸爭流
唐廣德元年(763 年)春,杜甫正在蜀中寓居,聽聞官軍打敗叛軍收復了“河南河北”失地,雖然其時年已52 歲,但歷時8 年的安史之亂被平定,依然讓他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并馬上就盤算好了回家的路線:“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雖然這位飽受離亂的偉大“詩圣”,終其一生都未能走上這條北歸之路,但他在詩中規劃的這條路線,反映出長江水路在當時已是一條快捷通達四方的坦途,即使是從西南的成都到北方的洛陽,也可先順江而下到襄陽,再從漢江北上返回中原。
江寬水闊好行船。
長江橫貫西東、溝通南北,自古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水上交通運輸線。
早在七八千年前,長江先民就已“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成為蕩舟弄潮的先驅。他們掏空大原木,制作成獨木小舟浮于水中,然后攀附其上,或順水向前,或逆流奮楫,通過“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在沼澤密布、森林茂盛、山嶺起伏的江南卑濕之地,構建了順暢的水運網絡。

長江航道 夏晶攝
這是有考古實證的。位于浙江杭州市蕭山區的跨湖橋遺址,出土過一艘在整棵馬尾松上用火焦法挖鑿的獨木舟,經碳14 測定為距今8200—7600 年。距此不遠的河姆渡遺址(位于浙江余姚市)也發現了距今7000 年的船槳,而且是做工精細的雕花柄葉連體槳,一共出土7 支。到了距今5300—4300 年的良渚文化時期,人們已能熟練地駕駛舟船在各個大小聚落之間穿梭往來。
至青銅文明時代,體積更大、結構更為穩固的木板船出現了,人們駕著船,載運各種物資甚至是軍隊,從小河來到大江之上。
商王朝之所以將盤龍城建為南土行都,很大程度上就是著眼于舟楫之便。盤龍城正好處在古云夢澤的東緣,河湖水澤網絡密布,特別是盤龍湖與流經此地的漢江相通,給南銅北輸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長江中下游優質的銅料等戰略物資,稻米、陶器等生活物資,都是通過木板船運送到盤龍城集中后再中轉北送。城中的軍政商賈,北上可通過漢江及其支流,越過大別山、桐柏山的隘口直達位于中原的商王朝首都;向南進入長江后,順江向東可進入鄱陽湖水系,溯江往西可經荊州走向鄂西,南下可穿越洞庭湖直下湘桂,真可謂是四通八達。
周王朝興起后,漢江一長江水運通道依然助力周王室掌控著銅礦戰略資源。銅綠山(位于今湖北大冶市)、銅嶺(位于今江西瑞昌市)等地的銅礦被開采后,溯長江而上經由漢江運輸到西周國都鎬京(位于今陜西西安市長安區)。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長江干支流上水運開發利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楚國貴族鄂君啟手持楚王頒發的青銅符節,在長江干流、洞庭湖水系、漢江水系上轉運物資,開展商貿活動,最遠處可沿漢江上溯到南陽盆地,其艦隊一次可達幾百艘,足見當時長江流域水運之發達。這一時期列國爭雄,兼并戰爭劇烈而頻繁,發達的水運也被應用到軍事斗爭中,中原諸國驅長車在遼闊的原野對壘,南方諸國則駕戰船在交錯的江河上列陣,楚、吳、越等國“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拉開了將長江“舟楫之便”應用于軍事的序幕。此后2000 多年里,水深江闊的長江中下游到底發生過多少次舟船水戰,已無法統計,但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和元末的鄱陽湖大戰等著名水戰,至今仍被人們津津樂道。
江上水戰,促進了船舶制造技術的進步,南北朝時,造船業取得突破性進展,長江流域開始展開大規模航運。史載,南朝宋孝武帝劉駿自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溯江西巡,“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

長江黃金水道 肖本祥攝
長江,戰時用于軍事,和平時便用于民運與商貿,大大促進了國家經濟發展。秦漢開始的大一統王朝更看重這一點。西漢初建時期,政治中心在西北的關中地區,賦稅糧食則主要依賴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由于將糧食運輸到首都長安,溯黃河而上會遭遇三門峽的巨大落差,陸路運輸又損耗頗大。因此,有人提議利用長江一漢江水道,先從淮泗水系南下進入長江,再回溯長江進入漢江,最終從漢中將糧食轉運到長安。利用長江干支流與各地區相互連通水系的優勢,從而實現糧食的長途運輸,且高效安全,這一提議也成為漢王朝實行漕糧運輸的方法。
水運是古代唯一能進行長途大宗運輸的交通手段。秦漢以降,長江及其支流嘉陵江、漢江、洞庭湖水系、鄱陽湖水系、太湖水系組成的水運網,成為貫通東西、連接南北的貨物運輸大通道,更是把內陸與海上絲綢之路連接起來,沿岸城鎮的貨物通過長江出海后,銷往今天的印度、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及部分阿拉伯國家,是不折不扣的黃金水道。
隨著隋代大運河開通,以及唐宋以后江南成為國家財賦之源,長江流域的糧食、絲織品及其他各種物資,通過長江黃金水道和大運河源源不斷地被運往長安(今西安)、開封、洛陽、北京等歷代首都,運輸船隊甚至形成了“舳艫相接,二百余里”的盛況,酷似當今的堵車現象,以長江干流為中樞的運輸網絡基本成熟。歷代王朝也以這張水運網為基底,通過長江干支流的延伸,串聯起了北方與南方區域間的交流,從而實現了對全國的有效掌控。
長江水運成為朝廷漕糧運輸主通道,還帶動了長江沿線和周邊地區的經濟交流聯系。唐代安史之亂后,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長江黃金水道不僅將重要產糧地與大城市連在一起,也促進了各大城市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號稱天下最繁華的揚(州)、益(成都)二州,常有“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其間,運送糧、鹽、絲、茶。陸游在《入蜀記》中記述:“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
櫓聲搖月,帆影隨風。到明清之際,長江中游地區人口激增,土地開發迅速推進,農業墾殖和物產開采進入新時代,開始為國內市場提供大量糧食、木材、礦產等物資,也為邊境和國際貿易提供茶葉等產品,長江水運更加興盛,漢口、九江、蕪湖等港口,因物資轉運和商人聚集發展成為繁華城市。
明代嘉靖年間興起的漢口,因水運便捷,不僅聚集了來自四川、湖南、安徽、江西等長江上下的商人,也吸引了陜西、山西等地的商人前來經營,漢口港商船匯集,泊船常在千艘以上,由此形成鹽、典當、米、木材、棉布、藥材六大行業,沿江上下10 千米以內,店鋪林立、貨物山積,呈現出“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夜明”的盛況。到清代,漢口已發展成為中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港口城市,全國各地的商船、糧船在此匯集,然后分發中轉,以至于碼頭上的船只,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頭。清代乾隆年間發生在漢口碼頭的一次火災,大火足足燒了兩天,100 多艘糧船、3000 多艘商船化為灰燼。
近代以后,隨著晚清朝廷與列強之間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長江沿線布滿了通商口岸,一艘艘冒著黑煙的蒸汽輪船駛進吳淞口,從上海溯長江而上,最遠可到達重慶。為防止外國勢力沿長江攫取更大政治、經濟利益,張之洞等有識之士通過自開商埠以維護主權、發展經貿。長江干流各大口岸的通商,極大地促進了水運物流。一艘輪船從上海出發,只需3 天即可抵達漢口,而木船需要的時間長達20天。在輪船的帶動下,長江成為引領中國步入現代社會的快速通道。

武漢沌口安吉滾裝碼頭 姚忠輝攝
新中國成立后,長江航運事業進一步發展,在全國內河航運領域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的長江黃金水道依然繁忙,上行下行船隊密布江面,各色貨輪客船來來往往,一派百舸爭流、千帆競渡的壯觀畫面。
從刳木為舟到百舸爭流,數千年的時光里,濤聲依舊的長江上,船型變得越來越豐富,而永遠不變的是滾滾江水所承載的舟楫之便。
千里通波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這是唐代詩人皮日休寫的《汴河懷古》第二首,汴河即通濟渠,是隋唐大運河的中段。看到大運河流淌不息,南北舟楫暢通無阻,皮日休認為如果不是修龍舟巡幸江都的事情,隋煬帝的功績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
大運河作為中國古代南北交通大動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運河,隋代開通大運河的功績的確可以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不過,皮日休要將這彪炳千秋的功績算在隋煬帝楊廣頭上,卻太過偏頗,一則大運河早在春秋時期就已開鑿,二則隋代大運河的建設主體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非隋一代之功,更非楊廣個人之功。
中國是最早建設人工運河的國家。
舟楫之便,讓人們渴望從這一條河流通達舉目可見的另一條河流,于是連通不同水系的“捷徑”— 人工運河應運而生。人工運河,一方面,可縮短航程,提高運輸效率;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避開天然河道中的險灘急灣,提高運輸安全性。
春秋時期,長江流域主要諸侯國楚、吳、越之間展開了一段波瀾壯闊的爭霸故事,為提高運輸效率,更好地服務于軍事征伐,三國紛紛在所控制的區域內開鑿運河,溝通自然水系,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楚國的云夢通渠和吳國的邗溝。

當年李白高吟“天門中斷楚江開”處,如今已是百舸爭流
楚國早中期的核心區域主要在長江與漢江之間,這里也是古云夢澤所在地,湖泊星羅棋布,河渠縱橫交錯。為方便作戰和運輸,楚國令尹孫叔敖在公元前601 年主持修建了云夢通渠,這也是中國最早的人工運河。從此,楚國軍隊和糧船可從郢都(春秋時楚國都城,位于今湖北江陵縣)直抵漢江中游,使兩江的往來交通不必繞道至漢江匯入長江口(位于今武漢市)。因這條捷徑帶來的舟楫之利,楚國國運興盛一時,有了北上中原爭霸的底氣。公元前597 年,一鳴驚人的楚莊王率精銳之師,從云夢通渠入漢江北上,飲馬黃河,擊敗中原諸侯盟主晉國,成就楚國霸業。
無獨有偶,吳國在春秋末期修建邗溝,同樣是為了北上爭霸。為解決北上伐齊遠征軍糧和輜重的運輸問題,吳王夫差于公元前486 年下令開鑿的邗溝,利用長江與淮河之間密布的天然河湖港汊,就地度量,局部開挖,用人工河道串聯高郵湖、博芝湖、射陽湖、白馬湖等自然湖泊,從而貫通了長江與淮河。
邗溝作為大運河之濫觴,其歷史地位直到1000 多年后才顯現。
605 年正月初一,繼位不到半年的隋朝第二代皇帝楊廣改年號大業,毫不猶豫地向全天下昭告其欲成就千秋功業的遠大志向。楊廣“大業”的第一個項目就是一個大工程:修建大運河,連通南北水系。
若說楊廣下令修筑大運河,純粹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欲,方便去江南游山玩水,那倒是有些冤枉他了。加強隋王朝對全國的統治,這才是楊廣急欲開通大運河的真正原因。歷經魏晉南北朝期間數百年的衣冠南渡,長江流域已被開發成為經濟發達區域,是朝廷錢糧賦稅的重要來源。如何連通南北、消弭差距,把江南的錢糧快速高效地轉運到北方統治中心,是完成全國統一的隋王朝必須解決的問題。大運河在這個大的政治背景下應運而生,可謂是歷史的必然。
從隋大業元年(605 年)至大業六年(610 年),只用了6 年時間,長度超過2000 千米的大運河就建成貫通了,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為一體。隋代大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個系統,南運河是洛陽東南方向的通濟渠、邗溝、江南運河,連接江都(今揚州)、余杭(今杭州);北運河為永濟渠,直達涿郡(今北京)。據文獻記載,這4 段運河耗費人力共計300 多萬,“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運河所經之地幾乎是男女老少齊上陣,日夜趕工,等于是全民就役。大運河的修建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如此不惜民力的大干快上,用6年時間驅使300 余萬人鑿通數千里運河,是當時民眾不可承受之重,這也埋下了隋朝二世而亡的禍根,時稱“天下死于役”。
隋代大運河貫通后,立即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主通道,“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是不折不扣的歷代王朝之黃金線和生命線,對保持南北統一以及經濟、文化的交流發揮了重大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說,隋煬帝楊廣組織修建大運河之舉,可謂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運河舟楫穿行,往來如風。隋之后,李唐王朝締造的大唐盛世,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得大運河之利。長江流域的錢糧、物產,通過發達的水運網絡匯集到揚州,再通過揚州轉運到洛陽和長安。《新唐書·食貨志》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處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常轉漕東南之粟。”正是依靠大運河“常轉漕東南之粟”,唐朝才能“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所以皮日休亦有言“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
到了宋代,全國經濟重心南移已經完成,形成了“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的局面,長江和大運河成了北宋朝廷維持政權的生命線。北宋初年,通過江淮及南北運河的漕糧年運量都在600 萬石以上,宋真宗、宋仁宗時竟達800 萬石,創下了歷代漕運的紀錄。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為了縮短漕糧北運的距離,將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大運河進行了裁彎取直改造,修建了從大都到臨清的通惠河、濟州河、會通河,形成一條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縱向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900 多千米,這就是著名的京杭大運河。
明清兩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也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活動的發展,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被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為漕運所開,但隨著時代變遷也逐漸成為商運之河、民運之河。
大運河在歷史上雖然幾經翻修和變遷,其溝通南北的功能卻一直未曾變更。從南往北,大運河沿途連接村落、串起城鎮,促進了沿岸大批城市的崛起和商業的繁榮。杭州、嘉興、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淮陰、徐州、濟寧、聊城、臨清、德州、天津、北京,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商業都會。特別是揚州,自隋唐至明清,一直是中國最繁華富庶的城市。是故,“煙花三月下揚州”,一直是歷代文人騷客圈中最流行、最時髦的行為,猶如當今網紅打卡一般。
槳聲帆影中,大運河歷經了2500多年的滄桑風雨,至今仍在使用,使北國與江南相連、讓歷史與現實相通,如同一部流淌的民族史詩。
2014 年,第38 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被譽為“ 活著的、流動著的文化遺產”。
水上高速
重慶唐家沱碼頭,滾裝船滿載新下線的長安福特轎車,準備運往下游。
早在2001 年,福特汽車和長安汽車就在重慶成立了合資公司。福特選擇重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數年后三峽工程蓄水對川江航運條件巨大提升所帶來的交通便利。
不同于江寬水闊好行船的中下游航道,曾經的川江航道,因流經丘陵和高山峽谷地區,落差達120 米,航深和航寬不足,拖載能力低, 運輸成本高,而且影響航行安全,使長江航運優勢未能得到很好發揮。特別是三峽一段,有“西陵灘如竹節稠,灘灘都是鬼見愁”之說,以灘淺、礁多、水急而著稱,“夜不能航”。即使是白天,船只逆流而上,也必須依賴外部的牽引力渡過這些激流險灘。而纖夫,就是這些航船的動力。
曾幾何時,當人們談起長江航運,三峽纖夫精瘦的身體與地面平行的姿勢以及粗壯的纖繩幾乎成為標志性影像。每當逆水行船或遇上險灘惡水時,全靠纖夫合力拉纖,一聲聲船工號子,在空谷回蕩。千百年來,代代纖夫走著同一條纖夫路,根根纖繩摩擦著相同的纖夫石,日積月累,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纖痕。一塊塊纖夫石,更是三峽纖夫血淚和川江水運艱險的見證。
然而,相比于“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陸路,不管川江航道多么艱險,它始終是一條溝通巴蜀與東中部的便捷水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青藏、巴蜀、云貴的物產,都要借它進入長江中下游經濟發達地區。長江中下游的物產,也要借它進入大西南的廣闊市場,賺取利潤。
蕪湖市繁昌區長江荻港段 肖本祥攝
而在川江現代航運史上,有一個中國人的名字不應該被遺忘,他就是民生公司的創始人、被譽為“中國船王”的盧作孚。1925 年,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輪船駛入川江,經過10 年奮斗,民生公司成為長江實力最強的民營航運企業。1938 年10 月25 日,武漢淪陷,3 萬人員和9 萬件器材滯留在宜昌,盧作孚指揮民生公司船只日夜運輸,把中國重工業的寶貴器材搶運到重慶。這次連續40天的戰時運輸,被稱為中國實業發展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新中國成立后,有關部門對川江航道進行了大規模整治。1959 年,著名的滟滪堆(即滟滪灘)被人工爆破,沉入江中。然而,靠炸礁除灘來維持通航,并未徹底改善川江的航運條件。
1981 年,葛洲壩開始下閘蓄水,巴東官渡口以下100多千米的水位抬高,流速減緩,西陵峽三大灘險(泄灘、青灘、崆嶺灘)全部被淹沒,西陵峽航道條件得到較大改善。
此時的川江,上行宜昌至重慶段,只能通過最高1000 噸級船舶;下行重慶至宜昌段,也只可通過最高1500 噸級船舶或1000 噸級駁船組成的3000 噸級船隊。川江的年運輸量只有1000 萬噸,運輸成本比中游高1 倍以上,油耗高1 倍以上,單位馬力載貨量僅為中游的1/3。
2003 年6 月1 日,隨著三峽大壩20 號導流底孔的閘門徐徐關閉,工程攔蓄江水的功能開始正式發揮。6 月10 日,壩前水位達到135 米高程。
短短10 天,長江三峽段實現了由江到湖的巨變;短短10 天,創造了2000 多年川江航運不曾有的奇跡—三峽水庫回水長達500 千米,到達重慶涪陵。川江上,豐都以下的險灘已全部被江水淹沒,僅有的兩處禁止夜航的河段也被撤銷。
“自古川江不夜航”的歷史,就此宣告結束。
由此,3000 噸級的輪船或者萬噸級的船隊已經可以從上海直達重慶,川江單向年運輸能力從1000 萬噸提高到近5000 萬噸。庫區船舶單位馬力拖帶量提高了1 倍多,船舶單位平均能耗降低了20%以上,有效地降低了船舶運輸成本。
隨著壩前水位的不斷上升,進一步改善川江航道的工程,也繼續向上游的重慶延伸。2006 年10 月27 日,三峽大壩全線到頂5 個月后,水庫成功蓄水至156 米高程。庫區的回水從豐都延伸至重慶的銅鑼峽。包括蠶背梁在內的川江最后一些礙航礁石灘險,從此永沉江底。
4 年 后 的2010 年10 月26 日,三峽工程首次蓄水至175 米高程,水庫回水末端到達重慶市主城區,涪陵以下“窄、彎、淺、險”的自然航行條件得到根本改善,宜昌至重慶660 千米河段的航道等級從Ⅲ級升級為Ⅰ級。原來灘險水急的川江航道就此步入百舸爭流的航運新時代,實現了全年全線晝夜通航,顯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川江航道改善,帶來的是航運能力“水漲船高”。
如今,萬噸級船隊不僅可直達重慶朝天門,而且船舶的運行周期大大縮短,宜昌至重慶的深水航道,成為水上“高速公路”,以往航道“上行走緩流,下行走主流”的航行方式變為高速公路式的分邊航行,航行時間比以前可節省6至8 個小時,大大提高了航運效能。
2011 年,三峽工程過閘貨運量首次突破1 億噸,提前19 年達到船閘設計水平年2030 年的規劃貨運量,就是航運效能大幅提升的有力證明。截至2020年8 月底,三峽累計過閘貨運量14.83億噸。
川江航道的改善,也有效保障了航運安全。2003 年以前,川江航道平均每年有57 起事故,85 人死亡,1100 多萬元經濟損失,每12 個月發生一次死亡10 人以上的事故;2003 年,三峽蓄水成庫后,平均每年事故降至13 起,10人以上死亡事故未出現一起,安全形勢持續好轉。
借助水運優勢,一大批新興產業紛紛落戶長江上游沿江城市,并帶動這些城市的飛速發展。萬州、涪陵、長壽等城市迅速成為東部產業的西部承接地,正在加速崛起;巫山、奉節等城市正借助三峽成庫形成新的自然景觀積極打造旅游產業,已經探索出一條環保綠色的發展之路。
受益的不只是長江上游航道。每年10 月汛期過后,長江由豐水期轉入枯水期,航道水深不足,嚴重時可能導致輪船擱淺、堵航,甚至停航。如今,通過科學調度三峽工程,增大下泄流量,對長江中下游航道適度補水,增加航道水深,枯水季節也能行大船了。
毫無疑問,正是三峽工程運行后對長江上游航道的改善,才使得川江航道由天塹變為“水上高速”,長江“黃金水道”才真正名副其實。
黃金水道
長江南京段,水深江闊,浪花翻涌。一艘艘巨輪滿載各色集裝箱,上下穿梭,往來不斷。
這一派繁忙景象,正是長江黃金水道釋放的“黃金”效益。南京至長江出海口431 千米的12.5 米深水航道在2018 年5 月全線貫通后,5 萬噸級海輪可直達南京港,10 萬噸級海輪也可減載抵達,而20 萬噸級海輪可減載乘潮到達江陰。

梯級船閘是三峽工程重要的組成部分,游客觀賞船只過閘 陳文攝
長江南京以下航段是長江主航道中船舶通過量最大、經濟效益最顯著的航段,也是中國內河水運最繁忙的區域,年運量16 億噸以上。此前在10.5 米航道水深時,只滿足3 萬噸級海輪滿載通航,5 萬噸級以上大型海輪需大量減載、虧載運輸。12.5 米深水航道開通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航道通航條件改善,5 萬噸級以上海輪航道可深入長江400 多千米,從而帶來大型海輪吃水增加、實載率提高和航運成本下降,5 萬至7 萬噸級船型實載率將提升近25%,10 萬至20 萬噸級將提升近20%,運輸成本大幅降低。據測算,5 萬噸級以上進江海輪每多裝載1 萬噸貨物,可大致節約運輸成本23.3 萬元。
長江水系龐大、水量充足,終年不凍,干流橫貫東西,是溝通華東、華中和西南的交通主動脈,干流通航里程2800 余千米,上起云南水富港,下至上海入海口;7000 多條大小支流中,全年保持一定航深的通航河流有700 余條。支流航道與干流航道呈縱向連接,構成了縱貫流域南北的重要水運線,再加上京杭大運河的江南段(江南運河),以及洞庭湖、鄱陽湖、巢湖、太湖四大湖泊的湖區航道,相互交織,組成了以長江干流為主干,大支流、大運河為支干的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內河航運網,全流域總通航里程7 萬余千米,占全國內河總通航里程的70%以上。
長江航運以其密集的干支流水運網絡,連接著上中下游地區的中心城市及眾多中小城鎮,通江達海,溝通主要資源地和消耗地,是長江流域綜合交通體系的主骨架。在沿江地區各種運輸方式中,具有運能大、成本低、能耗小、污染少等優勢的長江航運,貨運量一直穩居首位,承擔了沿江地區85%的煤炭、鐵礦石以及中上游地區90%的外貿貨運量。
進入21 世紀,隨著長江沿岸經濟的快速發展,長江航運快速崛起,貨運量、周轉量和港口吞吐量迅速增長。2005 年,長江干線貨運量達到7.95 億噸,首次躍居世界首位;2008 年,長江干線貨運量突破12 億噸,為美國密西西比河的2 倍、歐洲萊茵河的3 倍;2014 年,長江干流貨物通過量突破20億噸,成為世界內河運輸最繁忙、運量最大的通航河流;2020 年,長江干線貨運量更是突破了30 億噸大關,再創歷史新高。長江航運每年對沿江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達2000 億元以上,間接貢獻達4.3 萬億元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黃金水道。
2014 年春天,“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被寫入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長江經濟帶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
長江黃金水道進入發展的黃金期。
航道是舟楫通行的基本資源,是航運發展的首位要素。2014 年以來,國家交通航運部門按照“深下游、暢中游、延上游、通支流”的發展思路,加快推進長江干線航道系統治理,先后實施了長江口南槽一期、南京以下12.5 米深水航道、武漢至安慶段6 米深水航道、荊江河段航道等一系列整治工程,長江干流2800 余千米的航道全部達到國家高等級航道標準。
一寸水深一寸金。隨著長江干線航道通航條件明顯改善,5 萬噸級海輪直達南京、5000 噸級船舶直達武漢、3000 噸級船舶直達重慶、2000 噸級船舶直達宜賓,有力支撐了長江航運快速發展,促進上海、武漢、重慶3 個航運中心和22 個主要港口的布局和建設,沿江億噸級大港已達15 個。

一望無際的長江賦予人們舟楫之便 肖本祥攝
大江東去,其勢在暢。黃金水道成色如何,沿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是其重要檢驗指標。
武漢新港陽邏集裝箱港區,集卡車不停來回轉運,碼頭上龍門吊伸出巨型手臂,抓起幾噸重的各色集裝箱輕輕放下,頻繁起吊之間,江面上的貨輪立馬變得五彩斑斕,裝滿貨后駛向遠方。
武漢新港涵蓋武漢、鄂州、黃岡、咸寧、黃石5 市港口,陽邏集裝箱港是其江北核心港。2013 年以后,武漢新港積極開拓多式聯運體系,優化運輸結構,江海聯運、水鐵聯運、水水直達、沿江捎帶等現代物流業快速發展,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從2013 年的85 萬標箱發展到2021 年的248 萬標箱。
從江邊的灘涂地到汽笛轟鳴、巨輪云集的國際港口,武漢新港的變遷見證了長江港口的發展史。長江干線已形成了重慶、武漢、上海三大航運中心、22個國家級主要港口,有近4000 座現代化碼頭泊位矗立在大江兩岸,晝夜不停地為長江上的16 萬艘船舶通江達海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務。
依托長江黃金水道開展的多式聯運,沿江地區聚集了全國500 強企業中的近200 家,更便捷的物流條件、更低廉的物流成本,增添了企業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也讓長江經濟帶成為中國最富活力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之一。
長江滾滾東流,晝夜不息,賦予我們舟楫之便。綿延2800 多千米的長江干流航道,如今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忙碌的內陸水上運輸大動脈。這條黃金水道通過進一步提升能力,對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主動脈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