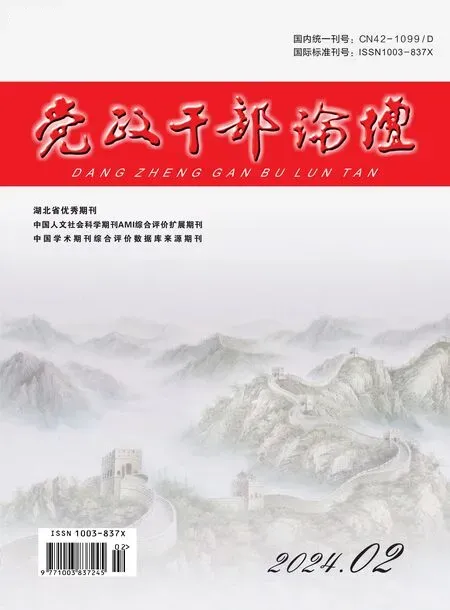《老子》“下知有之”的管理境界及其當代啟示
周黎巖 陳祥林
《老子》第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領導者的治理水平有四個等次之分,最高境界是“下知有之”,即最高明的執政者治理天下,老百姓只知道有那么一個人,卻感受不到他在管理。老子“下知有之”的“無為”思想以被管理者為中心,注重效法天道、地道、人道,實現和諧治理。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萬物包括人類社會,都是由“道”所產生的,天地萬物本身就是自然和諧體,人也是和諧自然中的一員,也應效法天道、地道,在管理活動中實現人與宇宙萬物的和諧共處。領導者要達到“下知有之”的“無為”最高管理境界,需要遵循“天道”“地道”“人道”。
一、做官之道:“道法自然”
做官之道即天道,天道即宇宙規律。《老子》第三十七章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莊子繼承了老子思想,在《莊子·至樂》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意思是“天道”的規律是剛健運行不息,萬物自我生成。領導者應該遵循天道,不要將自己的私欲、私念強加給自然萬物,不要人為地、故意地胡作妄為,而要順應自然規律、順應萬物本性,通過“不作為”的方式達到無所不為的目的。道家所謂的“無為”,并不是消極不作為,而是遵循事物的內在規律去作為,順應規律、順應民心達到“無為而不為”的治理目的。
(一)要順應規律
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治理大國就像煎小魚一樣,要用文火慢慢地煎,煎完一面,再翻過來煎另外一面,不能像煎大魚一樣不停地翻來翻去,否則就會變成一鍋魚泥。老子以烹魚之道談治國,告訴我們,領導者治理國家時要懂得從實際出發,順應規律,不能瞎折騰。歷史典故“蕭規曹隨”,同樣啟示我們治國理政要懂得順應規律。漢朝宰相曹參上任后,沒有頒布新的法令,繼續沿用前任宰相蕭何制定的規章制度,可謂是“無所作為”。曹參看似“無為”,實則大有作為,順應了朝代更迭時百姓希望休養生息的客觀利益訴求,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最終達到了歷史交替期順利過渡、富國強民的目的。如果不遵循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一味地胡作妄為,其結果必然是招來禍患,輕則身敗名裂,重則禍國殃民。如此,就會淪為老子所說的管理四重境界中的最差一等——“侮之”,與“下知有之”的最高管理境界背道而馳,相去甚遠。
(二)要順應民心
民心乃國政之大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歷朝歷代的榮辱興衰史啟示我們:得民心者得天下。現代管理學上說的領導力,其實就是一種領導凝聚民心的能力。治國理政,制度為本。大到國家、小到單位,都要重視規章制度的建立。在建章立制時,領導者要以民為本,順應民心。如果規章制度順應了民心民愿,一方面百姓都會自覺執行制度、遵守制度,制度可以得到有效貫徹和落實;另一方面百姓在遵守和執行制度時,會順理成章地認為這是自己分內的職責,進而形成自我約束管理、自我價值實現的文化氛圍。在這種氛圍里,人人都有一種“自我領導”而非“被領導”的感覺,領導者也無需時時處處發號施令,反復強調規章制度的存在,彰顯領導的“權威”和“存在感”,這樣就做到了《老子》第十七章所言:“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下知有之”的治理境界,意即英明睿智的領導其實是很少發號施令的,只要順應了民心,百姓都會認為依規行事是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做人之道:“無私用柔”
做人之道即“地道”。《周易》中講:“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道”意即做人要遵循“地”的“坤德”,也就是老子的“柔德”。老子講“知雄守雌”“知強守弱”,主張發揮領導者的柔性管理藝術,以柔克剛,以“柔”取天下。老子的“柔”在管理學中,體現為注重發揮領導者的人格魅力和對下屬的影響力,淡化強制性權力在管理中的作用,強化人格魅力這種“非權力因素”的作用。“無私用柔”是一種以人格魅力影響下屬的能力,最終達到無為而治的治理境界。
(一)要保持“無常心”
《老子》第四十九章曰:“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領導者不能存有私心,要以百姓之心為心,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心中時刻裝著百姓,真正做到關心百姓,愛護百姓,尊重百姓,敬畏百姓。《老子》第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的第一件法寶“慈”就是“柔德”。老子認為,高明的領導者應用母親愛孩子般的慈愛力量春風化雨,感動下屬,贏得民心,獲得支持。《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戰國名將吳起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名將,原因就在于他善用慈柔的人格魅力感化下屬,贏得民心。打仗時,他和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不搞特殊,甚至會放下將軍的威嚴,親自為受傷的士兵吮吸傷口,讓士兵備受感動,個個都愿意以戰死沙場的方式回報他。吳起以真心真情換得了士兵的鼎力支持,最終成就了自己的功業。這就是領導者“柔”的藝術,以母親般的慈柔感化下屬、母親般的慈愛溫暖下屬,下屬自然會用真情回報,不但積極工作,而且會拼命工作,關鍵時刻還會為領導化解危機。
(二)要保持“無多欲”
人是欲望的動物,人的欲望是無窮無盡的,正所謂“欲壑難填”。老子并不反對人適當追求自己的欲望,而是主張人不能有太多貪欲,要懂得知足,節制自己的貪欲。老子深知,如果任由欲望牽著鼻子走,結果必然會跌進萬丈深淵。《老子》第四十六章曰:“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主張領導者要帶頭摒棄私心貪欲,清心寡欲,清靜無為,以上率下,達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的“無為”境界。
老子講“上多欲則下多賊”,領導者貪欲太多,下面的官員也會紛紛效仿。官方高層一旦私欲膨脹、物欲橫流,基層官員就會蠅營狗茍、雞鳴狗盜,政治生態就會嚴重惡化,國家就很難治理好。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查處的腐敗案例中,山西、遼寧等省份甚至出現了“塌方式腐敗”,究其根源,就是高層官員帶頭貪污腐化、基層官員上行下效造成的。《老子》第五十七章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意思是領導者帶頭無為,百姓自然受到教化,領導者帶頭清凈,百姓自然正直,領導者不滋事擾民,百姓自然富足,領導者帶頭節制貪欲,百姓自然淳樸善良。只要領導者帶頭修身節欲,不滋事擾民,不胡作妄為,百姓就自然能安居樂業,就可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的出現都是領導帶頭節制貪欲的經典案例。
三、做事之道:“上無為而下有為”
做事之道即“人道”。《莊子·天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意即領導者治國理政要善于“上無為下有為”。“上”指的是一個組織的最高領導者,“下”則指除了最高領導者之外的所有成員。“上無為而下有為”的治理理念體現了單位組織分工的重要原則。在治國理政中,不管一個單位是大還是小,領導和下屬職責分工都要明確,崗位上的每個人都要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各自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下屬不能越權,領導也不能管理過頭。
(一)要“上無為”
《老子》第五十七章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道”的清靜無為屬性規定了最高領導者的思想與行為,就是要盡可能地從具體事務中擺脫出來,以便能發揮主導作用。“上無為”并不是說領導者什么都不做,而是要做職責內的事,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注重組織、引導和服務下屬,充分調動下屬的積極性,督促激勵下屬做好本職工作,而不能事無巨細,干預下屬的工作,更不能凡事親力親為。西漢初年,漢文帝曾問丞相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意思是一年中全國審理案件有多少件?丞相陳平回答:“有主者。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并進一步指出這些都不是宰相的事情,使公卿大夫、主管具體事務的官員都盡到自己的職責,才是丞相之責。
毛澤東曾經說過:“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其中“用干部”是領導者達到“上無為”的必修之功。歷史上有很多善于任用干部的領導。如,三國時期的劉備,雖然文韜武略不是最佳,但他知人善任。劉備用人不拘一格,除了用像諸葛亮、龐統、關羽、張飛、趙子龍這樣的高人豪俠、正人君子之外,他還會用張松、法正這樣的小人,還能用看不起自己的人劉巴。因為劉備知人善任,所以蜀國出現了一大批人才,他們個性鮮明,各有所長。同時,劉備注重平衡,崗位設置互補重疊,權責明晰,能夠讓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施展才華,從而成就了蜀國團隊的核心競爭力。
(二)要“下有為”
“下有為”的意思是,管理者要信任下屬,鼓勵下屬,尊重下屬,給下屬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和空間,充分激發下屬干事創業的內在驅動力,滿足下屬實現自我價值的心理需求,敢于放權,讓下屬積極主動地完成組織目標。
領導者要想“下有為”,就必須“為之下”。《老子》第三十九章曰:“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意思是說,權重的人以卑賤為根本,位高的人以低下為基礎。真正高明的領導者懂得“善用人者,為之下”的道理,愿意放低身姿,以謙卑柔和的方式對待下屬,以人格魅力感召、激勵、影響、帶動下屬,激發下屬的主人翁意識和自我價值,從而鼓勵他們自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富有創造性和激情地完成責任目標和任務。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三國時期的劉備善于用謙卑、低調、柔和“為之下” 的方式,激發下屬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劉備想請諸葛亮出山助其復興漢室,諸葛亮原本是不愿意出山的,但劉備放下“劉皇叔”的高貴身份,三顧茅廬拜求諸葛亮,表現得非常謙卑,諸葛亮最終被劉備謙卑柔和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像諸葛亮這類人中龍鳳、高潔名士,高官厚祿是無法打動他的,唯一能打動他的就是真情、真意。自從有了諸葛亮的輔助,劉備如魚得水,順利建立了“三分天下”的蜀漢政權。白帝城托孤后,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諸葛亮繼續為蜀漢效力,親率三軍五次北伐,盡心盡力輔佐劉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劉備雖然去世了,但他對下屬的影響力還在持續,這就是老子所講的“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無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