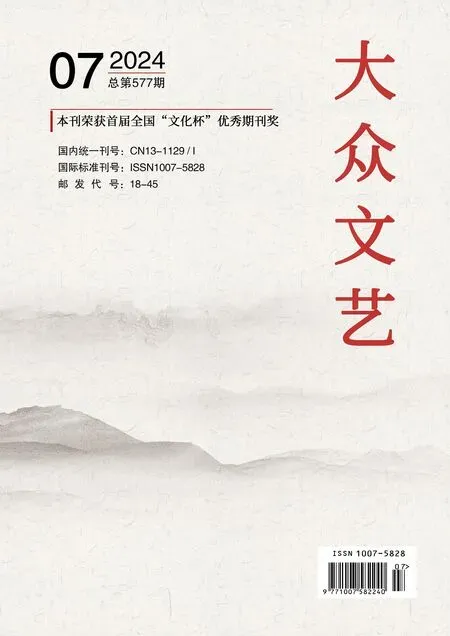伽達默爾與歷史主義問題
徐勛源
(鄭州大學,河南鄭州 450000)
伽達默爾的哲學思想與歷史主義保持了一種十分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從他對以往的歷史主義的反思批判里,我們發(fā)現(xiàn),如何克服歷史主義的弊病是深入理解伽達默爾的一條重要線索。
歷史學派的理論
以黑格爾歷史哲學為代表的啟蒙運動時期的歷史理性以目的論形式先天地構(gòu)造歷史,歷史學派的誕生正是出于反駁這種先天構(gòu)造歷史的要求。他們與歷史哲學相對立的歷史世界觀認為:“理念、存在和自由在歷史實在中找不到任何完全和恰當?shù)谋憩F(xiàn)”,因而一種替代哲學的歷史研究是有必要的,可以向人類啟示他們自身及其在世界中位置。[1]歷史學派正是在這樣一種觀念中確立起構(gòu)造歷史的原則。但是,歷史也并非全無精神性的一種僵死必然的實在,而是顯現(xiàn)著多樣性、豐富個性。一切事物存在的短暫性也正是歷史生命的過程,在消逝中存在,這樣一種不可中斷的生命聯(lián)系成為歷史實在,“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造性的奧秘就存在于這種不斷消逝的過程本身中”[1],一切時代與世界史的聯(lián)系就如一切時代與上帝的聯(lián)系。
蘭克作為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世界歷史觀中,“創(chuàng)造性的人物”創(chuàng)造著決定歷史的瞬間。這樣一種“自由”與“力”聯(lián)系在一起,“力”就是“人類活動的最初和共同的源泉”,這意味著一種更深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已經(jīng)生成的東西構(gòu)成了與將要生成的東西的聯(lián)系”[1]。
“力”具有一種與歷史實在的復雜的自由和必然的辯證關(guān)系,歷史學家以這個概念研究歷史實在的本質(zhì),而歷史展開的意義依據(jù)效果歷史得到認識——這種效果歷史具有某種隱含的目的論意義,因為只有在后果中先行東西的意義才能現(xiàn)象。“歷史是力的這樣一種產(chǎn)生連續(xù)性的活動”,世界史是“正在生成的總和”,而總和所要求的統(tǒng)一性必然“包含著世界史發(fā)展的不可中斷的連續(xù)性”。伽達默爾指出,這種連續(xù)性在蘭克那里并非一種世界歷史的形式結(jié)構(gòu),而是與西方文化的影響相適應(yīng),具有內(nèi)容上的意味,并且這種連續(xù)性愈來愈像是一種進入世界歷史觀中的先天物,正是由于世界歷史的連續(xù)發(fā)展,人們才能思考這種連續(xù)性本身,在此意義上,連續(xù)性不是“單純經(jīng)驗事實,而是歷史意識本身的條件”。試圖完全經(jīng)驗地構(gòu)造世界史的這種嘗試是有問題的。伽達默爾由此澄清了這一點:世界史統(tǒng)一性思想是某種規(guī)范性的理念,并且蘭克的這種歷史構(gòu)造是有內(nèi)容上的前提的,而這種前提不可避免,最終伽達默爾會在現(xiàn)象學的基礎(chǔ)上承認這種內(nèi)容上的前提具有合理性。人的意識是有限的,但歷史意識卻像上帝的無限知性,將所有歷史視為同時存在的,人類自我意識最終的完美就在于將所有歷史現(xiàn)象視為“大全生命的顯現(xiàn),參與歷史現(xiàn)象就是參與生命”,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是宇宙的自我意識。這里事實上有一種與唯心論的接近。
歷史學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德羅伊森以道德力解釋歷史的存在方式以及歷史認識。歷史認識就是“理解運動于其中的諸種中介過程”,誰想要進行歷史認識,誰就必須超越自身的特殊性,并承認自身對倫理領(lǐng)域的歸屬,在這種具體條件和限制內(nèi)達成公正理解[2]。這也即是將自身提升到作為歷史實在的道德力的一種過程。
歷史認識是一種無限的中介過程。這種無限在伽達默爾看來是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可見,因而與自然科學研究具有根本上的不同。德羅伊森主張的“探究性的理解”指向良知探究,“歷史世界依據(jù)于自由”,這意味著一種“良知的自我探究”才能接近的神秘性。傳承物作為無限中介,歷史學家與之保有距離,但與這種對象同樣也具有聯(lián)系,因為歷史實在作為道德世界的運動是與人同質(zhì)的,是可理解的。因此歷史認識和理解在德羅伊森這里既具有無限中介性也具有直接性:個別自我通過理解將自身提升到道德力、與倫理共同體聯(lián)系在一起,而倫理共同體作為歷史表現(xiàn)也是直接可理解的[3]。歷史認識不斷地向理念邁近,最終認識的頂點就是精神的在場,歷史就如同一個可深入理解有意義的文本。
狄爾泰與歷史主義
當歷史主義發(fā)展到狄爾泰時,他認識到在歷史學派中經(jīng)驗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歷史并非精神的顯現(xiàn)方式,在蘭克和德羅伊森那里歷史始終是一種精神物的表現(xiàn)和展開,因而在他們對唯心主義的拒斥中不自覺地保持了與唯心主義的關(guān)系。
如果歷史不是精神的顯現(xiàn)方式,“歷史認識被限制于經(jīng)驗,康德批判的問題也對歷史世界提出來了。”在狄爾泰這里,體驗作為內(nèi)在意識到的內(nèi)容具有直接確實性,是歷史認識的基礎(chǔ)前提,問題是,個別人的經(jīng)驗如何提升為歷史經(jīng)驗?為此,他使用了“結(jié)構(gòu)”的概念強調(diào)一種關(guān)系整體以及生命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它指示著生命在其外現(xiàn)中可理解的統(tǒng)一。這種聯(lián)系不依賴生成性的因果關(guān)系,而是與意向性意識相對應(yīng)的結(jié)構(gòu)和意義,這種結(jié)構(gòu)和意義即是生命的表現(xiàn)。
“狄爾泰的生命詮釋學總是立足于歷史世界觀的基礎(chǔ)之上”,但這種做法也不能完全避免唯心主義的影響。歷史中作為“精神的生命性”的個人是由個性和客觀的精神性實在關(guān)系所決定的。[4]這客觀的精神性就是一種對個體而言休戚相關(guān)的歷史實在,歷史實在是限制個體的經(jīng)驗,從而使得個體意識到自身的力,另一方面歷史實在也是一種對個體的支撐,在歷史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意義上,是生命的客觀化物,并且正因此而有了一種普遍性和理解的可能。在狄爾泰那里,客觀精神在藝術(shù)、宗教和哲學這些形式中實現(xiàn)了自我認識,區(qū)別與黑格爾將之視為絕對精神,狄爾泰只是將這些事物看作生命實在的表現(xiàn)形式,而完全擺脫異己的絕對精神被設(shè)想為是歷史意識。歷史現(xiàn)象、傳承物、客觀精神的諸種形式皆被歷史意識視為精神的客觀化物。
狄爾泰思想的難題也就是伽達默爾解釋學所試圖克服的難題:對一種無窮盡的創(chuàng)造的實在、對經(jīng)常變化的歷史意義來說,客觀性的知識如何可能?“有限的-歷史性的人受制于特殊時空關(guān)系”,這種條件性如何才能不妨害精神科學的真理要求?伽達默爾認為,在狄爾泰那里這個問題的解決依賴于歷史意識“對自身的不斷增強的占有”,它不是簡單地從當代出發(fā)理解和發(fā)展傳統(tǒng),而是以一種反思的態(tài)度理解傳統(tǒng),并從作為精神客觀化物的傳統(tǒng)出發(fā)理解自身。正是由于傳統(tǒng)是精神的客觀化物——與之具有一定距離——指向傳統(tǒng)的理解和反思才是可能的。
知識存在于生命之中,“無需思考就與體驗結(jié)合在一起”,這種知識對于人而言即是某種固定的東西,實現(xiàn)為人生活其中的倫理、宗教和道德世界,但這種知識也是某種前反思的生命的“自然觀點”。精神科學的目的就是超越這種原始所與的知識,以此達成歷史認識的客觀性。這即是所謂的“生命本身指向反思”。伽達默爾認為,這是試圖通過一種笛卡爾式的懷疑批判以取得某種確實有效的知識,來抵抗生命實在的壓力和不可探究性,這是理解和知識的真正任務(wù)。由于他受到笛卡爾式方法論的影響,探究性的、自然科學方法論式的反思成為理解和知識的真正任務(wù),致使“歷史經(jīng)驗的歷史性并不起真正的決定性作用。”
伽達默爾對狄爾泰的批判點在于,狄爾泰的浪漫主義詮釋學沒能區(qū)分經(jīng)驗的歷史本質(zhì)和科學的認識方式。歷史成為需要解釋的文本和意義蹤跡,最終被歸為精神史——這正是歷史學派所想否認的。
現(xiàn)象學與歷史問題
在伽達默爾看來,不論是胡塞爾還是狄爾泰,都沒徹底地展開“生命概念的思辨內(nèi)容”。胡塞爾現(xiàn)象學那里出現(xiàn)了一種對“客觀主義”的徹底批判,試圖從一種無名的、有作為的“意識生命”推出歷史世界的構(gòu)成,這個世界是經(jīng)驗的基礎(chǔ),同時是一種“生活世界”,是人作為歷史存在生活于其中的整體[5]。生活世界總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經(jīng)驗歷史的世界,綜合諸歷史生活世界的宇宙觀念——好似能將不同的生活世界同時呈現(xiàn)那樣,這是不可能的。生活世界并不是先驗意義上的世界,而是存在于一切經(jīng)驗中的被給定的東西,也即是我們稱之為限制的歷史性的東西。先驗主體“必須把自己設(shè)想為被生活世界所包圍”。
在這方面,約爾克伯爵在思辨唯心論和新經(jīng)驗之間梁設(shè)橋梁,以達爾文式的生命概念囊括了兩個方向。他認為生命是原始區(qū)分和對統(tǒng)一的肯定。“原始區(qū)分”區(qū)分自我與他者,根源于意識的自發(fā)性和依存性。意識、意識活動、對對象的反應(yīng)被看作生活態(tài)度。思想作為意識活動的結(jié)果與此種結(jié)果所從出的生活態(tài)度/意識這二者的關(guān)系是隱而未發(fā)的。并且,思想結(jié)果從生活態(tài)度/意識中作為結(jié)果脫離出來,這正是自我意識的本質(zhì),是意識的原始區(qū)分。而哲學是對這種脫離過程、生活傾向的逆向反思,去認識這些思想結(jié)果、意識結(jié)果、生活結(jié)果的條件關(guān)系。此外,約爾克伯爵的思想具有某種與黑格爾思辨唯心論的接近。
需要注意的是,生命與自我意識具有某種類似性:生命使自己區(qū)別于世界,并使自己保存于這種自我區(qū)分的過程。生命用異己滋養(yǎng)自身,因此是同化和非區(qū)分。與生命的結(jié)構(gòu)相對應(yīng),自我意識作為一種認識/知識,使一切事物成為認識對象,并通過一切事物認識自身,因此它是認識對象的認識與認識自身的認識的區(qū)分,同時是一種合并。至此,“生命是自我肯定和對統(tǒng)一的肯定”才得到闡明。
歷史主義在詮釋學探究中的重大關(guān)系在海德格爾那里愈發(fā)顯明,正如伽達默爾指出的,“事實性問題確實是歷史主義的核心問題——至少是以對黑格爾關(guān)于歷史中存在理性這一辯證前提的批判的形式。”事實問題與歷史問題,由批判黑格爾的歷史理性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現(xiàn)象學探究的本體論基礎(chǔ)應(yīng)當是生存,也即此在的事實性,而不是純粹我思。[1]事實性問題與歷史問題的關(guān)聯(lián)使海德格爾基礎(chǔ)本體論必須把歷史問題放在首位。“時間被顯示為存在的境遇”,最終存在物必須由時間來規(guī)定,存在本身就是時間。
絕對的歷史性也就是普遍生命的意向性作為。歷史性的和具有歷史性的存在方式,都不是“在者狀態(tài)上的”“現(xiàn)成事物”。而人類此在在其當下和遺忘的整個活動中的歷史性,乃是我們能根本再現(xiàn)過去的條件。正如伽達默爾所說,屬于經(jīng)驗本性的、使回憶和期待成為整體的內(nèi)在歷史性是歷史世界的基礎(chǔ)。
伽達默爾對歷史主義問題的回應(yīng)
對既往相關(guān)思想進行回顧后,接下來將進一步考察伽達默爾是如何與歷史主義保持聯(lián)系。他是如何在前人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詮釋學思想,其理論進路亦可以由此顯明。他批判蘭克的歷史構(gòu)造具有內(nèi)容上的前提,在這個方面他意指的是,歷史學派試圖進行的客觀構(gòu)造事實上具有“前見”。傳承物被理解為歷史性的,并且是與理性相對立的。又由于歷史意識的發(fā)展,人們意識到過去與現(xiàn)在皆是歷史性的,并且傳承物是普遍存在的東西。當人們試圖拋棄前見時,事實上否認了自身的歷史性。歷史主義的真正問題就在于,“有限的-歷史性的人受制于特殊時空關(guān)系”,在承認前見和歷史性的前提下,人的歷史有限性和條件性如何才能不妨害精神科學的真理要求?這也正是伽達默爾所面臨的理論困境。他的詮釋學嘗試從多個方面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理解傳承物得以可能的條件。傳承物并非某種斷裂的、完全異己的陌生存在。歷史存在本身是“時間廢墟中的保存”,傳統(tǒng)的本質(zhì)即是保存。人們共有基本的主要前見,這些前理解來自存在事物的意義,來自人們同樣地受到歷史實在的限制,來自人們共同生活其中的世界。當伽達默爾論述“古典型”時強調(diào)對“這個世界”的歸屬性時,他意指的似乎即是一個時間性的世界,時間在變遷,人們共同歸屬的這個世界是同一個世界,這也就是歷史。世界不變又更深地意味著,是人類所受到的限制不變。由于這些已經(jīng)存在的傳統(tǒng),由于這些共同的受限和必然的前見,因而說人們隸屬于傳統(tǒng),這正是傳統(tǒng)因素持續(xù)有效的原因。傳統(tǒng)和共有的前見使得理解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理解要求人們意識到自身的前見和歷史性,從而使得理解不僅是理解到人們自己放置進去的東西,這是一個不斷校準的解釋學循環(huán)過程。“從事情本身出發(fā)處理這些前有、前見和前把握”。這里關(guān)聯(lián)到另外兩個重要的東西。第一,生存的場域相同使得前理解對人們普遍有效,或者說,有一些東西使得前理解對人們普遍有效,即共通的時空有限性。例如說,如果以荷馬、莎士比亞、歌德為典范而確立起來的“人性”也是一種普遍有效的東西,那么這里似乎就有一種循環(huán),是人性的相同使得這些前有對人們普遍有效,同時是人們對這些典范的理解和認同確立起人性。第二,事情本身成為理解的預設(shè)標準,這不僅隱含了對事情本身的認識,而且,事情本身如果指向了那些對我們共同有效的東西之外,以事情本身為設(shè)準是否與理解事件中意義整體的對話、問答邏輯以及與一種理解實踐具有強烈的張力?這關(guān)系到伽達默爾所謂的“事情本身”究竟是指什么。事情本身就是把我們與傳承物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共同性,但這種共同性是生產(chǎn)性的,因為我們所參與的理解的事件屬于傳承物/理解對象自身的運動進程。
經(jīng)由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更新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解釋學循環(huán),是指我們必須通過前見和意義預期去理解,而要正確地理解,還必須在理解的過程中意識到自己的前見,解釋對象與解釋者處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和視域之中,既非斷裂的,也非同質(zhì)的,因此理解是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運動,永遠存在著理解者與理解對象之間的中介運動[6]。因而,理解活動應(yīng)當“被認為是一種置于傳承物事件中的行動,在這行動中過去和現(xiàn)在不斷地進行中介”[1]。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對德羅伊森“理解具有中介性和直接性”觀點的某種保留。更進一步,伽達默爾提出了“效果歷史”的概念: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
過去與現(xiàn)在具有緊張關(guān)系,詮釋學要求籌劃不同于現(xiàn)在視域的歷史視域,這就要求有一種歷史意識能夠區(qū)分二者。因此,對歷史視域的籌劃不僅是過去意識的某種延續(xù)、在當前的再現(xiàn)或異化,而是詮釋學意義上的理解和視域融合。對視域界限的消除強調(diào)的是新舊結(jié)合所能形成的富有生氣的有效的東西,以及一種生成性地對前見或傳統(tǒng)的把握。歷史思維必須同時想到它自己的歷史具體性。歷史對象是“自己和他者的同一體,在此關(guān)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理解活動就是傳承物的運動和解釋者的運動的一種內(nèi)在相互作用,也即“效果歷史事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