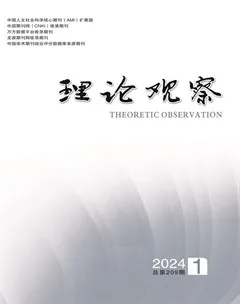平臺洪流中的生存游戲:網絡主播用工模式爭議與維權路徑探析
孫博雅 朱豪杰 潘茹雪
摘 要:數字平臺經濟發展下衍生了網約車司機、平臺外賣員等有別于傳統勞動的新型用工形態,網絡主播作為新型用工形態的典型,其用工模式和權益保障問題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本文基于政治經濟學和法律視角,通過對Y平臺S公會的田野調查及相關人員的訪談,發現當前數字資本通過更隱蔽和精明的手段對網絡主播進行壓榨、奴役,網絡主播看似獲取了相較于傳統勞動更自由的勞動空間,但實質上遭受著自我、平臺甚至第三方機構的多重剝削,主播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依舊異化為對立的力量,同時還面臨著勞動市場飽和、行業競爭激烈、勞動關系模糊、勞動強度過高、維權路徑艱難等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從立法、企業責任及行業資源等方面,擬對保障網絡主播權益提出相應意見。
關鍵詞:數字勞動;平臺經濟;網絡主播;權益保障;勞動關系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4)01 — 0103 — 06
在當代數字化轉型的趨勢下,數字資本伴隨著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以及數字化設備的成熟逐漸滲透進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促使社會發生結構性變化。當代勞資關系、勞動市場在數字資本邏輯下出現了新的特征,數據開始作為資本增殖的重要生產要素,逐漸趨于商品化、資本化,并成為數字平臺進行技術壟斷的關鍵性要素。數字平臺公司借助數據優勢,打破了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壁壘,將消費、服務、平臺、勞動等元素雜糅,并隨之催生了新型用工形態,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調整,以抖音為代表的數字平臺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逐步形成后福特式的細化分工和彈性生產,例如,Y平臺專門的內容審核工作就達到了兩萬人。網絡主播作為新型用工形態的典型,長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一方面,伴隨著數字勞工的“去技能化”以及智能設備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涌入“主播市場”,進行甘愿勞動,加之數字技術消弭了勞動場所的桎梏,大眾可以結合自有資產實現“在家辦公”,主播作為原子式勞動者與市場需求直接連接;另一方面,數字資本通過合法性話語建構[1]部分權利的讓渡[2]等隱匿技巧巧妙回避了勞動法的束縛,將主播權益置于社會風險之中,導致近幾年網絡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的用工爭議案件大量增加,主播身心問題愈發受到社會的關注[3]。因而,游離于資本控制邊緣的網絡主播的權益保障問題成為了當下關注的焦點。基于上述內容,筆者選取了當前主要直播平臺之一的Y平臺作為研究平臺與網絡主播①勞資關系問題的窗口。
一、文獻綜述
數字化技術在當代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逐漸滲透,純粹的物質勞動也帶有了數字化的特征,并呈現出轉向數字勞動的趨勢,因而衍生了適應于平臺經濟下的新型勞動形態,這些新形態的出現引發了各界學者的廣泛關注。《2020年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截止2020年底,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行業市場規模已達1930.3億元,網絡表演(直播)行業主播賬號累計超1.3億。[4]由此可見,網絡主播已經成為具有市場潛力且深受年輕人追捧的新興職業作為新型勞動形態的典型,網絡主播自然成為這些學者的研究焦點。
目前,有關網絡主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勞動過程、勞資關系、權益保障三個方面。在勞動過程方面,過往學者多圍繞“情感勞動”議題出發,探索情感在網絡主播勞動過程中的運用邏輯。俞富強、胡鵬輝站在消費社會角度,指出身體圖像與情感表達的相互結合對于直播互動的促進機制[5];之后,他們又通過量化研究的方式發現情感勞動在主播表演策略以及勞動成果中的新變化,指出網絡主播的情感勞動實現勞動“去異化”[6]。涂永前、熊赟立足于泛娛樂直播中女主播的勞動過程,強調情感制造在維系“勞-客”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身體符號化、打造“人設”以及重塑關系的情感制造過程[7]。然而這些研究主要從勞動形式出發,探索網絡主播的勞動過程,因而并未揭露其背后的資本剝削本質。呂鵬則在前人基礎上,從社會性別、傳播文化、勞動本質等角度出發,研究網絡主播的線上情感勞動。[8]雖然呂鵬的研究拓寬了情感勞動的研究視野,但是由于視角過于多元而導致每塊內容不夠深入,即使他提及了情感勞動者對資本的服從,但并未深層次剖析其中的剝削邏輯。隨著當前數字勞工研究的深入,部分學者指出網絡主播背后資本更為隱蔽的剝削機制,并圍繞平臺與主播或是公會與主播之間的勞資關系展開批判。
根據福克斯[9]對數字勞動的定義,即“指代所有與信息傳播技術的生產、分配和服務相關的勞動”,網絡主播屬于典型的數字勞動者,因而在分析網絡主播背后的勞資關系時,可以借鑒過往學者在政治經濟學角度對于數字勞工的批判。這些學者認為數字勞動依舊在資本剝削下發生異化,這種異化與傳統勞動異化是一致的,只不過具體的表現形式有所區別[10],甚至數字勞動異化背后的資本剝削更為隱匿[11]。技術形式裹挾下的數字勞動似乎因更多勞動自主權的獲取而轉向了對資本形式上的隸屬,實則依舊被深嵌在數字化生產過程,任由資本支配和控制,資本在勞資合作互利的幌子下賺取巨額利潤和剩余價值[12],這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隨著勞動場所禁錮的解除,資本對生命的治理從過去在固定時空的工廠轉變成現在流動時空的日常生活,資本變相地對勞動者進行“時間盜竊”[13],工作時間與休閑時間界限逐漸消弭,這意味著工人勞動時間的無限延長,獨立的數字生命個體淪為數字資本治理下的牽線木偶[14];第二,資本狡猾地將“勞資矛盾”轉向“勞客矛盾”,勞動者的收入報酬與受眾評價相掛鉤,其勞動價值均在數據化的結果中找到依據,而收入分配的“游戲規則”仍由資本決定,這無疑將勞動者生存的競爭風險推向市場,勞資權力依舊處于失衡狀態;[15]第三,平臺經濟下,數字勞工的自有資產在與勞動力的結合下再商品化或資本化,數字勞工深陷自我資本和平臺資本的雙重剝削,因而勞工創造的剩余價值仍有很大一部分被資本平臺占有。[16]數字技術下,數字勞動者依舊在實際上從屬于資本,資本仍舊是“趕工游戲”背后的最大贏家。這正如Wald J在《工作的終結》中描述的那樣:“每一次技術突破都會打破企業和工人之間的權力平衡,并且使其嚴重偏移到企業方”。[17]在這種隱匿的剝削本質背后,周孟杰等人還指出秀場女主播在資本強制下進行著“甘愿勞動”,女主播與公司始終處于不平等的霸權雇傭關系。[18]
在權益保障方面,法學界從《勞動法》入手,分析網絡主播與平臺、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判定問題。有學者指出,當前網絡主播呈現出“去技能化-去勞動關系化-去保障化”的趨勢,[19]網絡主播的勞動關系、權益保障問題似乎成為勞動者自由權競爭與資本博弈下的犧牲品。潘建青、[20]李澤誠[21]等學者從薪酬分配、勞資從屬性、競業限制等方面對網絡主播勞動關系難確立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網絡主播作為新型用工形態,與傳統用工形式大相徑庭,因而處于《勞動法》的保護邊緣,時常被判定為勞務關系而非勞動關系。由此引發的主播過度勞動、缺乏社會保障等問題也受到學者關注。[22][23]
綜上,過往的研究主要以學科孤立的視角圍繞網絡主播的勞動過程、勞資關系、權益保障展開,因而缺少綜合的視野全面認識資本和主播的雇傭關系。由此,本文將結合法律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對當下網絡主播與數字平臺或企業的勞資關系以及自身權益保障問題進行探討,深入挖掘內嵌其中的資本剝削邏輯和勞動控制機制,并嘗試為網絡主播的權益維護建言獻策。
二、案例介紹與研究方法
近幾年,Y平臺開始深耕直播行業。資料顯示,2019年,大量MCN涌入Y平臺,批量制造“街排號”。2020年開始,Y平臺開始探索專屬的直播運營法則,將直播與電商進行嫁接,與MCN機構、直播公會建立起其中較為良性的生態。筆者調研發現,近幾年,Y平臺加大了對于主播的扶持力度和監管力度。在扶持方面,Y平臺專門開設“直播攻略”板塊,對新人主播從直播技巧、內容優化等方面進行免費的“技能培訓”,同時還鼓勵主播成為“金牌主播”,給予一定的流量曝光和額外收益獎勵。在監管方面,Y平臺加強了實名制審核機制,制定了更為嚴苛的主播入駐協議以及平臺規則,同時還結合人機審核以強化對直播間和主播行為的監管。毫無疑問,隨著直播行業的發展,Y平臺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主播激勵和管理制度。但是在資本的趨利本性下,網絡主播的用工模式仍順服于資本邏輯之中,他們自始至終處于被剝削的端口,其生存與發展依舊受到勞動異化的羈絆。由此,本文選擇Y平臺作為典型個案展開研究。
筆者于2019年3月以“主播”身份于Y平臺S公會進行了六個月的田野調查,在體驗主播工作的同時了解平臺與公會對主播的用工模式。而后,筆者于2021年圍繞網絡主播的用工模式和權益保障問題,通過滾雪球方式對相關人員進行了訪談,其中包括Y平臺浙江地區公共事務總監1名、Y平臺S公會主播經紀人2名以及主播6名。此外,筆者還添加了部分訪談對象的聯系方式,并對其日常朋友圈內容進行記錄。
三、網絡主播的發展窘境
(一)僥幸的生存:飽和的市場與過剩的主播矛盾
直播平臺的涌現賦予了人們表現自我的契機,在資本邏輯最大限度地追求資本增殖以及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下[25],這一契機轉化為了資本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時機,網絡主播在依附于數字平臺的過程中,與平臺達成利益分成的合作契約,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平臺資本的管控。根據田野調查結果,網絡主播對數字平臺的依附形式可以分為直接依附和間接依附,直接依附即直接與平臺簽約,其中不存在第三方交易;間接依附即主播歸屬于某公會或某企業,以公會和企業的名義與數字平臺間接結合,90%的主播都是通過公會,通過機構進行簽約。然而這些第三方機構更像是數字平臺的“人力資源部門”,為平臺不斷篩選、吸納優質主播勞動力;也就是說,網絡主播的勞動力并不完全歸屬于企業,其仍植根于數字平臺的商品生產過程之中[26],因而主播的剩余價值依舊被平臺占有,甚至出現企業和資本雙重壓榨的局面,網絡主播勞動產品的異己屬性再次被強化。
根據訪談結果和資料顯示,當前的主播市場已趨于飽和,主播行業存在“二八效應”,[27]這就出現了主播需求過剩與市場資源飽和的尷尬局面。數字資本企圖通過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篩選出優質主播勞動力,將“脫穎而出”的幸存者作為自己的主要剝削對象,而對于其余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資本則通過“積少成多”的方式實現利益最大化。在“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下,趨利的資本只會重視對強者的權益保護,而其余“淘汰者”則被無情置于社會風險之中,缺少庇護。
無論是“勝者”還是“輸家”,數字勞動的異化本質都未曾改變,且越是熟練掌握數字勞工規律的人,越能夠在互聯網社會中獲得更高的關注度,進而在“數字等級”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28]最終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不再限于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同階級之間也會產生異化,等級分化下的社會不公平等社會現象將進一步惡化。以創業型全職主播為例,這類主播以直播作為全職工作,受平臺約束指示的程度較高,然而只有少數頭部主播才能真正瓜分主播市場這塊蛋糕,主播收入由低到高的人數呈現“L”型態勢[29],在“流量為王”的時代下,流量曝光資源、受眾關注度都會傾斜于頭部主播,最終主播內部的兩極分化將愈發明顯,這種等級分化仍會進一步造成勞動者的不平等,激化內部矛盾。
(二)權益的流失: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認定爭議
近幾年,有關網絡主播的勞動關系認定案件屢屢發生[2]。由于網絡主播工作存在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這成為網絡主播權益難保障的主要原因,平臺和企業常因此為由拒絕對主播權益作出保障。底部的主播,流動性高,很可能做了一段時間后就不想再做了,所以很多時候都會簽一些比較松散的協議。而這種協議所約定的從屬關系往往在法律上被視為勞務關系或是合作關系,法官在判決相關勞務案件時也常因此否認主播與平臺、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此外,由于《勞動法》存在滯后性和社會兼容性不足等問題,作為新型用工形態的網絡主播并不適用于傳統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譬如網絡主播享有工作時間、地點和內容的自主選擇性,這弱化了傳統勞資關系的從屬屬性與實體屬性;在薪酬分配上,主播與平臺、企業的利益分成形式存在合作性質,因而主播的收入類似于一種合作報酬而非工資。精明的資本往往將法律的漏洞作為剝削的借口,企圖以“合作”的名義壓榨網絡主播,并將主播的法律弱勢(如缺乏相關法律知識、地位上的弱勢等)作為自己的地位強勢,網絡主播的勞動權益也就成為資本“游戲規則”下烏托邦式的假想。
站在平臺角度,隨著大批量主播的涌入,如果要保障每一個主播的權益,這無疑增加了平臺的用工成本,而第三方機構的參與則緩解了尷尬的勞資關系,這也是平臺轉嫁矛盾的策略。但是所謂的第三方機構也只是一個中介角色,他們既脆弱又更怕擔責,因而他們形成了一套迷人的游說式話語來引誘大眾為他們“無償”打工。
(三)沉重的壓力:過度勞動與維權艱難的困境
網絡主播的工作看似光鮮亮麗,但亮麗的背后仍是資本剝削與奴役的結果。隨著勞動者由“單屬性”到“多棲性”的轉變,[29]數字經濟下勞動者的勞動強度不斷提升。一方面,資方與勞動者之間引入網絡技術的變量,其實只是將工作場由現實轉移到線上,勞動者的工作場域被拓寬,在依托網絡技術的虛擬監管下,他們被實時監控。根據筆者的體驗觀察,在主播直播過程中,公會負責人會進入主播直播間查看,平臺也會派遣工作人員進行隨機的“巡查”和“治安”,一旦發現違規行為,主播將獨自承擔責任,因而在平臺和第三方機構的雙重監視下,他們的直播活動受到各種規制和束縛,“謹言慎行”無疑加大了工作的難度。另一方面,對于兼職主播,他們有著隨機的流動性及較弱的資本管制,因而不必承受嚴格的業績標準,而全職主播則因為有著底薪保障而被強加了直播時長、打賞收益等工作要求,為了保證績效的達成,他們往往會采用過度勞動的方式以避免被“裁決”,這也反映了社會競爭的殘酷現實。
在資本的強壓下,當前主播行業內卷化嚴重,過度勞動成為常態,據統計,近84%的主播反映患上了職業病,其中頸椎腰椎問題、聲帶受損等困擾著主播的身體健康;此外,主播作為“公眾人物”,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大眾的矚目,然而當代網民素質良莠不齊,難免會有部分觀眾對主播進行莫須有的人身攻擊,主播作為“普通的人”,其心理也會因此出現不同程度的傷害。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網絡主播身心健康受損背后有著艱難、坎坷的維權之路。
由于網絡主播工作場域的拓展,勞資依附關系形成“中心-散點”結構,網絡主播不再像傳統勞動形式那樣需要在某個固定地點匯集辦公,作為一個群體,他們變得分散化而缺少凝聚力,其勞動成為原子式的勞動,加之他們缺少“集體抗爭的記憶”,與資本的談判經驗尚未成熟,因而主播群體很難形成統一且龐大的規模對資本剝削進行反抗、發聲,孤獨的個體只能任由資本奴役、擺布,網絡主播如何維權問題仍舊是“燙手山芋”。在訪談過程中,發現許多主播都因個體力量甚微而缺少“反抗的精神”,由此可見,分散的勞動結構無形中剝奪了主播集體維權的機會,這亦是數字資本強剝削的一種表現。
四、在逆境中謀生:網絡主播的維權路徑建構
網絡主播雖是數字經濟下的新型用工形態,但在本質上與傳統勞動關系無異,他們并沒有脫離傳統勞動需求者與勞動供給方的結構,且符合現代契約精神。[30]但目前其權益保障還存在用工形式未成體系、法律法規滯后、社會資源缺乏等桎梏。這一系列問題往往依賴于勞動者的團結、企業所有權的改造、民主治理的引入以及基于合作化精神的平臺合作社的創建與運作。[31]對此,社會各界應當重視對于新興職業的權益維護問題,從立法、企業責任及行業資源等方面對網絡主播的權益作出保護。
(一)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勞資雇傭關系的多元劃定
網絡主播勞動關系判定爭議的出現暴露了《勞動法》滯后、僵化等問題。互聯網時代下,新型用工形態不斷涌現,并出現有別于傳統勞工的新特征,打破了過去勞務關系和勞動關系二元對立的局面。從目前有關網絡主播勞動關系判定的案件看出,當前《勞動法》對于勞動關系的認定已不完全適用于數字勞動時代,法官判決往往面臨保證平臺長遠發展與維護勞動者正當權益的博弈。因此本文認為,需要及時更新勞動法的立法理念,在堅持勞動者是弱勢群體的前提下,根據具體場景、考察不同類
型雇員的差異,進行相應的規則設計已是當務之急。[32]這里可以參考國外經驗,例如德國勞動法采取劃分勞動者類別的“三分法”以針對性地判斷勞工與資方的從屬關系;美國則采用泛化認定勞動關系,通過與個案的結合以增強判決靈活性。[33]對此,我國《勞動法》也可嘗試將勞動從屬關系依據關系強弱屬性與工作強度進行多元劃分,如劃分為標準勞動者、非標準勞務者以及勞務者,[34]讓新型勞動形態也可適用于勞動法,避免因處于《勞動法》保護邊緣出現利益保障受限的局面,這也避免了平臺或機構人力成本負擔過重的情況。
針對主播過度勞動方面,有學者指出,我國現行的立法中既未對“過勞”做出明確定義,也未形成相關認定標準,更何況立法對“過勞”進行救濟。[35]基于主播權益在法律層面尚不明確問題,立法部門可以對《勞動基準法》進行增補,在明確勞資雇傭關系的基礎上,完善勞工的工時、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等內容。[36]
(二)平臺責任還是企業責任:主播權益保障的雙向推動
平臺和企業應當聯手保障主播權益,而非相互推諉。于平臺而言,雖然在第三方機構存在下,平臺與勞動方屬于間接依附關系,但是平臺仍應重視主播權益維護,通過限制第三方機構的收益占比、提供主播投訴渠道等方式保障主播權益。平臺還可制定主播直播時間上限,以防主播之間內卷競爭出現過度勞動問題。于第三方機構而言,在與主播勞動合同的簽訂以及勞動關系確認的基礎上,企業應當為網絡主播購買基本的五險一金。此外,企業應合理化設置業績指標和工作強度,所提出的工作要求應與主播實際收入相匹配,充分利用互聯網工作的彈性模式,避免主播連續高強度直播,對于主播熬夜工作等傷身情況給予相應的關懷和補貼,并注意營造公平高效的競爭環境。
值得關注的是,網絡主播往往被視為“青春飯”,面對激烈且殘酷的市場競爭,后期主播是否仍能從事直播行業存在未知性。對此,企業更應承擔責任,通過主播轉型或主播轉崗等方式保證主播依舊能長期在企業中生存。
(三)集體發聲還是獨立維權:創建新型勞工組織
邱林川認為:“互聯網是資本的場域、剝削勞工的場域,也是社會的場域、階級形成和抵抗的場域”。[37]在數字經濟的新形式下,組織新的團體組織來保障不同行業中勞動者的權益是時代所需。隨著工作場域的解放,網絡主播成為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獨立力量,他們難以形成集體規模以對抗資本的過度剝削和壓榨。這時則需要創建專門的勞工組織,以作為中心力量樞紐,打破主播孤立無援的處境,為主播維權發聲。例如,在國外,一些局域聯合甚至跨國聯合的工會組織已經出現,洛杉磯網約車司機組建了“網約車司機聯盟”以抗爭資本。[38]再如國內,常德市的網絡主播協會以聯絡、協調和服務為主要職能為網絡主播服務;吉首市成立的外賣商家協會旨在宣傳行業和法律知識以幫助同行規避風險。各類新勞工組織的成立能在技能提升、信息宣傳、權益保障等方面為數字勞工提供發聲、協調、舉報的途徑,從而減少個體獨立面對風險的無力性。然而,當下我國的這些新型勞工組織并不普及,且現有勞工組織保護工人的方式也略顯過時,因此創建涵蓋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化網絡直播協會,提供主播維權平臺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將權益保障落實到每個主播。
此外,由于網絡的匿名性和隔斷性,同公會或同企業的主播往往無法像傳統職業那樣在現實中見面、交流,即使有線上社群,但是由于公會人員也在場,也很難暢所欲言,進行線上互動。對此,搭建僅服務于主播的網絡渠道十分必要,主播可以在貼吧、超話等專屬平臺進行互動交流,分享直播經驗、講述直播故事,將分散式的主播進行集群駐扎,這種虛擬的“抱團”亦可以強化主播對于自身的職業認同,鞏固主播群體的凝聚力,從而潛移默化地提升主播的反抗意識。
五、結論與討論
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勞動力過剩問題,然而數字資本的剝削邏輯并沒有因為線上用工模式的改變而呈現弱化趨勢,狡猾的資本反而借用數字技術加強了對數字勞動者的奴役和壓榨,權力關系滲透進勞工的用工模式之中,甚至強化為一種更加隱匿和精明的方式。站在《勞動法》角度,數字資本借助網絡主播非傳統工作模式,將網絡主播視為“勞務關系”,即利益分成的合作關系,除直播平臺外,網絡主播自己提供生產資料(也有部分公司會提供直播設備和場地),自由決定直播場所和時間,勞資的從屬性大大縮減,而從屬性是《勞動法》重要的判斷依據,這無疑將網絡主播邊緣化,主播以“合作”的形式接受著平臺或第三方機構的壓迫,勞動關系的模糊認定下主播的權益遭到“去保障化”的風險。換言之,數字平臺經濟下,網絡主播獲取到了一定的工作自由權,自主性大大提升,然而他們也因此付出了失去權益保障的代價。不過,站在平臺角度,若主播都和平臺簽訂勞動合同,難免增加平臺的用工成本和運作難度,因此如何平衡作為主播弱勢方的權益和作為平臺強勢方的壓力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本研究立足于政治經濟學和法學視角,通過對Y平臺的田野調查,結合對相關人員的訪談,發現網絡主播數字勞動背后深層次的資本剝削和壓榨,資本通過各種隱蔽技巧掩蓋剝削事實,否認勞資關系以減少用工成本和責任風險;加之“中心-散點”的權力結構讓主播分散成單一的力量無法抱團,主播的勞工權益游走于法律保護邊緣而更易受到侵犯。基于此,筆者也嘗試提出了網絡主播維權路徑建構的方法,以幫助網絡主播合理維護權益。然而,數字勞動時代下,國家對于各類新生職業的關注度還遠遠不夠,數字勞工的權益保護問題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 考 文 獻〕
[1]張志安,劉黎明.互聯網平臺數字勞動的合法性話語建構研究[J].新聞與寫作,2021(07).
[2]吳寶捷,梁美英. 網絡女主播生存狀態的理性透視[J].當代青年研究,2017(03).
[3][28]李澤誠. 網絡主播勞動權益保障研究[J].理論觀察,2020(06).
[4]騰訊網.《2020年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行業發展報告》發布[EB/OL].[2021-08-05].https://new.qq.com/rain/a/20210518A0FL1J00.
[5]余富強,胡鵬輝.擬真、身體與情感:消費社會中的網絡直播探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8(07).
[6]胡鵬輝,余富強.網絡主播與情感勞動:一項探索性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26(02).
[7]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娛樂直播中女主播的勞動過程研究[J].青年研究,2019(04).
[8]呂鵬.線上情感勞動:短視頻/直播、網絡主播與男性氣質——基于快手的數字民族志研究[J].社會科學,2021(06).
[9]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M].UK:Routledge,2014:44-49.
[10]劉海霞.數字勞動異化——對異化勞動理論的當代闡釋[J].理論月刊,2020(12).
[11]徐婷婷.勞動異化與勞動同意:互聯網數字勞動的價值二重性辨析[J].新聞愛好者,2021(04).
[12][15]吳宏洛,孫璇.當代資本主義數字經濟中的異化勞動問題[J].當代經濟研究,2021(06).
[13]TREBOR SCHOLZ. Digital Labor:The Inte-
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2014(7).
[14]溫旭.數字時代的治理術:從數字勞動到數字生命政治——以內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勞動”為視角[J].新聞界,2021(08).
[16][24]孫蚌珠,石先梅.數字經濟勞資結合形式與勞資關系[J].上海經濟研究,2021(05)4.
[17]丁依然.從“剝削”中突圍:數字勞工研究的現狀、問題和再陌生化[J].新聞界,2021(05).
[18][29]周孟杰,徐生權,吳瑋.網絡里的甘愿勞動:秀場女主播的建制民族志研究[J].新聞與傳播評論,2021,74(03).
[19][23][33][36]朱悅蘅,王凱軍.數字勞工過度勞動的邏輯生成與治理機制[J].社會科學,2021(07).
[20]潘建青.網絡直播用工關系的勞動法思考[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8,32(04).
[21][28]李澤誠.網絡主播勞動權益保障研究[J].理論觀察,2020(06):106109.
[22]吳寶捷,梁美英.網絡女主播生存狀態的理性透視[J].當代青年研究,2017(03).
[24][38]汝緒華,汪懷君.數字資本主義的話語邏輯、意識形態及反思糾偏[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38(02).
[25]艾媒報告中心.直播電商雙月報:行業監管趨嚴,平臺競爭激烈,主播二八效應明顯[EB/OL].[2021-08-05].https://mp.weixin.qq.com/s/E-OXKpr3
TQUylbz_QG8Q.
[26][34]朱陽,黃再勝.數字勞動異化分析與對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9(01).
[27]王立明,邵輝.網絡主播勞動者地位認定的困境、反思和出路[J].時代法學,2018,16(05).
[30]汪穎.網絡平臺與主播間勞動關系認定的困境反思與路徑構建[J].山東工會論壇,2021,27(02).
[31]SCHOLZ TREBOR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J]. 2016.
[32]謝增毅.我國勞動關系法律調整模式的轉變[J].中國社會科學,2017(02).
[35]譚金可.論過度勞動的法律治理[J].法商研究,2017,34(03).
[37]邱林川.告別i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J].社會,2014,34(04).
〔責任編輯:楊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