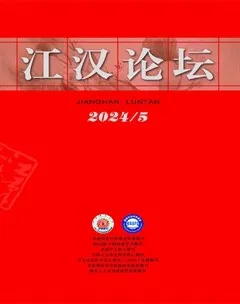紅色大眾美學與民間文藝的淵源關系
摘要:紅色大眾美學是20世紀中國文藝大眾運動的指導方針,它繼承和發展了民間文藝的經驗價值,在內容方面改造了“傳奇”與“復仇”的敘事模式,使其成為了弘揚無產階級革命的正能量,在形式方面則沿襲了民間文藝“看”與“聽”的歷史傳統,進而創建了紅色大眾美學“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文藝樣式。紅色大眾美學的經驗價值,就是通過以改造民間文藝為主,吸納世界先進藝術為輔的運作策略,去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文藝。紅色大眾美學不僅是現代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同時更是傳承無產階級革命價值觀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紅色文藝;大眾美學;民間傳統;歷史淵源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百年文藝大眾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3AZW002)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5-0083-08
傳統民間文藝范疇所說的大眾美學,是通過“通俗性”去體現其“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價值;而紅色文藝的大眾美學,則批判性地借鑒了這一民間文藝的優良傳統。但百年紅色文藝所選擇的大眾化道路,與傳統意義上的“通俗文藝”并不完全相同,它雖然沒有脫“俗”但卻并不“媚俗”;因為在“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理論指導下,它不僅在形式上更能夠體現紅色文藝的“人民性”與“民族性”的藝術特質,而且還在內容上深刻地反映了紅色文藝的“革命性”與“現代性”的思想內涵。即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仍然堅持認為“通俗性”和“民族性”應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正確方向。比如,他在《中國詩的出路》中說中國新詩只能有兩條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1)。毛澤東此番談話,已經把他的文藝思想表達得非常清楚,即社會主義文藝的美學形態,理應是由“民族性”(古典文藝傳統)和“人民性”(民間文藝傳統)相結合所產生的“第三個東西”。而百年紅色文藝的發展道路,恰恰是對這種“大眾美學”的具體實踐。
一、紅色文藝對英雄敘事的經驗借鑒
談及紅色大眾美學的表現特征,“傳奇”敘事自然是一個源自傳統民間藝術的重要現象。“傳奇”敘事之所以能夠“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就在于以“俠”為主的故事情節,經過千百年的歷史流變,早已成為了一種“成年人的童話”(2)。由于人民大眾是古代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無力反抗各種不合理的社會壓迫,因此便通過想象去幻構一些替天行道的“俠”之形象,并在他們身上注入了一種超凡脫俗的神性人格。在古代民間藝術的“傳奇”敘事中,“俠”幾乎都沒有什么具體姓名,人們只能是根據他們的外貌或服飾,去稱其為“虬髯客”(《唐宋傳奇·虬髯客傳》)或“黃衫丈夫”(《唐宋傳奇·霍小玉傳》)等等。正是因為“俠”行走江湖飄忽不定,因此不僅滿足了廣大民眾的“獵奇”心理,同時也寄托著他們渴望得到“俠”之庇護的強烈愿望。所以司馬遷定義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史記·游俠列傳》)
關于“俠”這一概念,王國維曾做過一番考證。他說“俠”始見于唐裴铏所作《傳奇》6卷,后來又經過宋代的《武林舊事》、元代的《錄鬼簿》、明代的《南九宮譜》以及清代的《曲海目》等不斷闡釋,才形成了人們對于“俠”的完整印象。(3)在中國古代文藝里,“俠”的種類十分繁雜,既有“游俠”“義俠”,也有“僧俠”“丐俠”。不過在底層社會中最受歡迎的英雄人物,當然又是那些一身正氣的“義俠”形象了。古代民間藝人想象中的“義俠”形象,他們縱橫江湖鏟除邪惡,以武行俠救世安邦,都具有一種令人敬仰的崇高人格。對于他們這些人而言,“‘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4)。如果僅僅是身懷絕技而沒有救民于水火的俠肝義膽,至多不過是“一介武夫”或“草莽英雄”。綜觀古代文藝作品中的“俠”之形象,在他們身上幾乎都同時具備有“武”與“義”這兩種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武”是“俠”在亂世之中謀求生存的必備條件,不過卻又被封建統治階級視為一種寢食難安的社會隱患。尤其是當“俠”之“武”已發展成為了無所不能的獨家“絕技”時,必然會引起他們在精神上對于“俠”的無比恐懼。因此,儒家文人便對“俠”之形象做了胸懷大志的藝術改造,進而使其走向了“忠君報國”的發展道路。
正是因為“俠”文化在中國民間社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啟蒙精英也一直試圖利用“俠”之精神去實現他們救亡圖存的人文理想。比如在晚清民初的革命浪潮中,革命志士就希望能夠通過重塑“俠”之形象,去提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人格。因此,他們剔除了傳統之“俠”的“忠君”思想,集中去凸顯其“愛國”意識,像秋瑾、徐錫麟等人還身先士卒不懼生死,表現出了一種大義之“俠”的明顯特征。到了五四啟蒙時期,“俠”又被賦予了全新的歷史使命,他們思想自由、人格獨立,“倨傲縱逸,不恤人言,破壞復仇,無所顧忌,而義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5)。如果我們現在重新去反觀歷史,無論魯迅對于“國民性”的批判,還是沈從文對于“湘西人”的贊美,他們都是在以“野性”崇拜去表達復興中華民族的美好愿望。毋庸置疑,具有悠久歷史的“俠”文化傳統,也成為了紅色大眾美學的重要因素。就像王一川指出的那樣,“俠”作為中國似的“卡里斯馬”形象,他們在現代革命中“橫空出世”且大顯神威,構成了20世紀中國小說最為顯著的藝術特色。(6)其實這種觀點,蘇雪林早在40年代就曾提到過,她說中國新文學的最大特點,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它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廿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7)。這充分說明“俠”文化不僅沒有被中國現代社會所消解,反而還在現代社會得到了發揚光大。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指出,盡管“俠”文化在五四文學與左翼文學中都有所表現(如魯迅的《鑄劍》與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但其主觀意圖仍然是在借助“俠”之形象去宣揚個人英雄崇拜,但卻并沒有將“俠”視為人民大眾的集體合力。只有在延安文藝、解放區文藝乃至新中國十七年文藝中,“俠”文化才開始以階級意識去建構其紅色文藝的美學特征,并最終使傳統之“俠”演變成了革命英雄的藝術形象。
百年紅色文藝一直都不乏“俠”之身影,但他們已不再是行走江湖的個人英雄,“俠”之“義”也由傳統的為民除害,轉變成了為全體勞苦大眾謀解放。為了宣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理想,從蘇區文藝、延安文藝、解放區文藝乃至新中國文藝,革命文藝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在運用“俠”之“神性”,去表現革命英雄人物無所不能的“超能力”。比如在柯藍的筆下,民兵英雄“洋鐵捅”彈無虛發,王鐵牛力拔千鈞,李四哥飛墻走壁,都具有超越常人的特異功能(小說《抗日英雄洋鐵桶》)。又如在馬烽、西戎的筆下,武工隊隊員同樣是身懷絕技,無論深入虎穴還是大擺地雷陣,他們都能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沒猶入無人之境,并把日本鬼子打得暈頭轉向(小說《呂梁英雄傳》)。其他作品像《石門陣》(卞之琳)、《周大娘》(崔璇)、《五月之夜》(王林)、《雞毛信》(華山)、《雨來沒有死》(管樺)、《無敵三勇士》(劉白羽)、《新兒女英雄傳》(袁靜、孔厥)、《風云初記》(孫犁)等,也都是在講述一個個革命英雄的傳奇故事。到了社會主義文藝時期,“紅色經典”也借鑒了民間“傳奇”的表現手法。比如,小說《保衛延安》里的連長周大勇,帶頭沖入敵群進行廝殺,“有時候他被煙火吞沒了,眨眼他又出現了”,盡管槍林彈雨但卻毫發無傷,就“連戰士們也覺得自己的連長有點神奇!”又如,小說《林海雪原》中的劉勛蒼,在被“清剿隊”包圍時,他竟能用手中的一根大木棒,就把十幾名荷槍實彈的敵人打得落荒而逃。再如,小說《紅旗譜》里的朱老忠,為了解救被警察鎮壓的示威學生,用三節鞭把一眾警察的槍支都打落在地;嚴江濤則順手甩出一把銅錢,同樣把警察打得“滿面花”。在紅色文藝的“傳奇”敘事中,整個殺敵過程干脆利落絕不拖泥帶水。這種“快節奏”的敘事模式,如同張飛在長坂坡喝退三軍一樣,既可以遮蔽英雄人物身上許多無法去描寫的“神性”行為,又可以最大程度去彰顯傳奇英雄出神入化的“超能力”。不過,“快節奏”在紅色文藝的大眾美學中,已不再是以一炷香為計時單位,而是改用了現代時間單位。舉一個例子,《林海雪原》在描寫“智取威虎山”一戰時,先是把“九群二十七地堡”渲染得神乎其神,可是到了戰斗打響之后,從劉勛蒼沖進“威虎廳”第一梭子彈開始,到所有匪徒們都被押進獄里為止,前后“只用了二十分鐘”。后來在消滅九彪匪徒殘部的戰斗中,更是只用了十八顆地雷和五分鐘時間,須臾之間便徹底消滅了這股頑匪。“快節奏”在革命英雄傳奇的大眾美學中,除了能夠滿足大眾讀者或觀眾的審美心理之外,其在思想內涵方面還有著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即:“我”正“敵”邪、“我”智“敵”愚。就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在紅色大眾美學中,革命英雄并非對傳統之“俠”的簡單模仿,他們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洗禮,才會鍛煉出一種超乎常人的優秀品格。比如,在革命英雄傳奇的故事敘事中,英雄人物都被賦予了明確的政治信仰,進而使傳統之“俠”的“武”與“義”,都在革命英雄人物那里得到了一種現代性的重新釋義。僅以十七年的“紅色經典”為例,革命英雄身上之所以都帶有“俠”的色彩而又不同于傳統之“俠”,并能夠表現出一種所向無敵的巨大能量,就在于他們心中都有著一個“人民本位”的崇高理想。用《保衛延安》里周大勇的話來說,就是“為勞動人民事業打仗,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哪怕明天我就在戰斗中把血流盡,我總認為我選定的事業是偉大的事業”。周大勇的這番話語,生動詮釋了革命英雄與傳統之“俠”的本質區別,即革命英雄不僅具有“武”之外表,同時更具有為天下受苦人謀解放的“義”之品格。正是由于在紅色大眾美學中,既注重表現革命英雄的神勇之力,又注重表現其在政治上的崇高信仰,因此他們的思想覺悟和政治智慧,也都是為常人所不能比擬的。比如梁斌小說《紅旗譜》中的朱老忠,如果沒有接受共產黨人的思想教育,至多不過是魯迅筆下的“庸眾”而已,但他參加革命以后思想境界卻大為提高。尤其是當革命受到了暫時挫折時,是他能挺身而出穩定了局面:“同志們!我們有的是多年的老黨員,共青團員,有的是久經鍛煉的農民積極分子,和封建勢力做過棋逢對手的斗爭。我們為了勞苦大眾的利益,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要離開我們的家,離開我們的妻兒老小,跟隨著黨,跟隨著紅色游擊隊打起游擊戰爭來了。”而沒有文化的“貴他娘”,也因為受朱老忠的思想影響,在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發生沖突時,“想過來,想過去,還是抗日的事業為重”。甚至還能說出一些像“只有打倒那些土豪劣紳們”,全天下的貧苦農民才能翻身得解放的大道理來。由此不難看出,在紅色大眾美學中,剔除了傳統之“俠”的江湖義氣,令其具備了至高無上的革命理想,最終全都成為了中國現代革命的傳播者和實踐者。
我們在探討紅色大眾美學時,也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古代民間傳奇敘事中,“民”是受難者而“俠”是救世主的思維模式,在革命英雄傳奇敘事中也時有顯現。比如在小說《紅旗譜》里,春蘭等一眾婦女被敵人抓進了據點,她在困境中只能暗暗祈禱說:“湘農司令員!睜睜眼睛,看著俺們姊妹們吧!”而賈湘農果然不負重托及時趕到,帶領游擊隊將她們全都解救了出來。因此,春蘭的“期盼”與賈湘農的“解救”,無疑帶有民間傳奇敘事的明顯痕跡。只不過梁斌把古代民間傳奇中的拯救意識,從一種個人行為轉變成了一種政治行為,即革命英雄人物在其實施拯救行為時,總是要向被拯救者說上一句:“我們是黨和毛主席派來的。”這句話語的潛臺詞,就是意在向世人說明這樣一個革命真理:古代之“俠”的“救世意識”,是源自于他們對于“善”與“惡”的自身定義;而革命英雄人物的“救世意識”,則是源自于“領袖”的教誨和“黨”的培養。革命英雄傳奇與民間“俠客”傳奇的思想分野,也恰恰正在于此。
二、紅色文藝對復仇模式的經驗借鑒
民間傳奇敘事中的“復仇”模式,也是紅色大眾美學的一個重要元素。因為古代民間傳奇敘事里的“快意恩仇”,一直都是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故事情節,故而紅色文藝在師承民間藝術傳統的過程中必然也會受其影響。全面考察紅色文藝的百年歷史,我們發現“復仇”這一敘事模式,即便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藝術魅力,“因為沒有比這更容易撰寫而又能吸引讀者的了”(8)。不過紅色文藝中的“復仇”書寫,已經不同于古代民間傳奇中的個人復仇,由于革命已將中國社會分成了“我們”和“他們”兩大階級陣營,故在紅色文藝中“我們”的復仇敘事也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所以從古代“義俠”的替天行道,到革命英雄帶領人民大眾進行階級反抗,民間傳奇的“復仇模式”,也實現了它在功能上的現代轉型。
古代民間傳奇中的“復仇”敘事,既是一種底層社會的情緒發泄,也是一種民間認可的正義行為,所以“有仇不報非君子”,不僅被視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傳統美德,而且還成為了傳奇敘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比如,唐傳奇《謝小娥傳》所講述的,就是一個“俠女”復仇的傳奇故事:謝小娥為父親與丈夫復仇,并在“夢”的啟示下女扮男裝手刃了仇人。對于謝小娥的復仇行為,官府和民間都大為贊賞:“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官府諒解和褒揚謝小娥的復仇行為,是因為它符合儒家宣揚的“忠孝”思想。謝小娥后來“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鄉民同情和認可她的復仇行為,也是因為這種行為完全符合“有仇不報非君子”的民間倫理。《謝小娥傳》通篇都在強調個人復仇的道德合法性,這在古代民間傳奇敘事中是一種最常見的表現手法。然而,若要使這種個人復仇行為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寬容與理解,古代先民還睿智地對“復仇”與“報仇”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嚴格區分。他們認為“報仇”一詞往往是指“私人間互結怨仇,互相爭斗殺傷以圖報復”(9);而“復仇”則超越了“報仇”的思想狹隘性,更能體現民間社會在沒有法律保障下的正義感:“從個體來說,它意味著對個人人格尊嚴的一種維護和伸張方式;從群體上說,它是對危害群體利益、貶損群體信仰的團體或個人實施懲罰的一種社會行為。”(10)如此一來,“復仇”敘事就不僅是在宣揚儒家的“忠孝”思想,同時也是在維護復仇者“士可殺而不可辱”的人格氣節。所以“復仇”敘事,無論復仇者是在為自己還是為他者伸張正義,都在道德層面上表現出了一種責任擔當。這就是為什么到了故事的結尾處,讀者或觀眾全都因沉浸在“善”對“惡”的勝利喜悅中,根本不會對這種殺戮場面產生絲毫的恐懼和憐憫,更談不上對生命尊嚴去做深度思考的重要原因了。“復仇”敘事作為民間傳奇吸引讀者和觀眾眼球的重要手段,在古代小說和戲曲創作中經常出現,即便像“武松殺嫂”“石秀殺嫂”那樣的冷酷場面,也不會有人去譴責他們的行為過于殘忍。我們絕不能將這種“快意恩仇”的復仇行為,簡單地歸結為是古代民眾的思想愚昧,而應將其視為民間社會因得不到人身安全的有效保障,需要通過“復仇”這一形式去發泄自己長期被壓抑的不滿情緒。因此“復仇”敘事既滿足了他們內心世界的“懲惡”要求,又并不違背民間社會的道德倫理,最終形成了一種民間傳奇的美學范式。
紅色大眾美學既然對民間大眾美學具有一種歷史傳承關系,那么它在藝術實踐過程中就不可能缺席“復仇”敘事這一重要因素,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復仇”敘事會在紅色文藝中大量存在,因為在抵御外侮和救亡圖存的時代焦慮中,“復仇”敘事不僅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而且更具有政治上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比如吳伯簫在小說《一壇血》中,便是以“用右膀子給左膀子報仇”的鏗鏘誓言,去表達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復仇意志。這篇作品并沒有直接去描寫槍林彈雨的戰爭場面,而是重在表現中國軍民的心中怒火與復仇信念。日本侵略者對于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廣大讀者和觀眾的心中激發起了一種渴望復仇的強烈信念,因此邵子南在其小說《李勇大擺地雷陣》里,極大地滿足了這種大眾審美的快感心理:
天崩地裂般一聲響,一股藍煙升起,塵土飛揚——雷響了!這下子,紅的白的鬧了一地,好像日本鬼子賣豆花,擔子翻了;長腿,短胳膊,腦袋,爛皮,碎肉,擺了遍地,好像日本鬼子在學《水滸傳》上孫二娘開人肉作坊;軍帽,軍衣,飛上樹梢,槍筒,子彈,擺了一地,好像日本鬼子在開雜貨鋪。——那四山群眾,每天看著險惡的地雷戰,看得發了呆,禁不住的手舞足蹈,喝“好”!叫“妙”!
毋庸置疑,這種帶有夸張性的藝術描寫,其實宣泄的正是一種民族復仇的強烈情緒。由于中華民族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故使紅色文藝中的“復仇”敘事也都被賦予了民族倫理的道義合法性。僅以孫犁的小說《蘆花蕩》為例:作者描寫了一位心地淳樸善良的農村老漢,為了替受傷的“小八路”報仇,把十幾個日本鬼子引到布滿魚鉤的葦塘里,等到日本鬼子全都被鉤住之后,便舉起船篙“狠狠的敲打”他們。對于稍有點歷史常識的人來說,都知道一個農村老漢根本就不可能去對付十幾個日本兵,但孫犁卻將這個故事寫得既浪漫又具有傳奇性,進而給那些在戰爭中飽受苦難的中國讀者帶來了一種心理上的復仇快感。在全面抗戰時期,沒有人會去質疑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一切人間奇跡都有可能發生,任何傳奇似的英雄都有可能出現。因此,紅色文藝中的“復仇”敘事,幾乎全都被人們視為真實事件而備受崇拜和敬仰。換一種方式去理解,紅色文藝恰恰是在借助民間傳奇中的“復仇”文化,大力宣傳了這場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它既凝聚和弘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同時也將個人“復仇”提升到了“保家衛國”的思想高度。故紅色文藝中的“復仇”敘事,反映的正是中華民族不可被征服的神圣尊嚴。
抗日戰爭結束以后,民族“復仇”敘事又被轉換為階級“復仇”敘事。綜觀解放區的文藝創作,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在階級“復仇”的敘事模式中,“善”與“惡”之間那種劍拔弩張的矛盾對立,已經由外族侵略轉變成了民族內部的階級壓迫。“善”代表著全中國的勞苦大眾,而“惡”則代表著地主資產階級。因此,勞苦大眾為了謀解放而同地主資產階級進行殊死搏殺,同樣也被視為具有無可爭議的道義合法性。在解放區文藝的“復仇”敘事中,勞苦大眾全都被描寫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苦大仇深,地主惡霸則都被描寫成兇狠殘忍、巧取豪奪、血債累累。這種階級陣營的涇渭分明,無疑使紅色文藝的“復仇”敘事,都在農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話語中,得到了符合政治倫理的意義闡釋。比如,蕭也牧的小說《貨郎》,就講述了一個貧苦農民的“復仇”故事:主人公“不二價”被地主馬俊義奪走了房產和土地,并被馬俊義派人把他痛打了一頓趕出了村子。從此以后,“不二價”只能靠走街串巷賣點雜貨,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自從“來了共產黨”以后,全村農民都在政治經濟上獲得了翻身解放,“不二價”不僅回到村里參加土改運動,而且還在村民大會上提出了懲治地主馬俊義的三個辦法:先把他吊在樹上一天一夜,再分光他家的土地財產,最后把他趕出村子去。“不二價”提出的這三種懲罰方式,實際上正是地主馬俊義當年整治他所用過的三種手段。從表面觀之,“不二價”的“復仇”行為,帶有民間倫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濃厚色彩,但作者卻站在階級意識的思想高度,將“不二價”的“復仇”描寫成貧苦農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正義行為,以此去彰顯傳統“復仇”敘事的現代價值。在紅色大眾美學觀念中,“復仇”作為一種革命的必要手段,帶有集體主義的明顯傾向性;而個人的“復仇”行為,也因階級斗爭學說的全面介入,被賦予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崇高感。比如在小說《林海雪原》中,當少劍波帶領解放軍戰士趕到杉崗站,看到被土匪洗劫一空的村莊和自己姐姐的遺體時,作者便直接讓他把自己的“家恨”,迅速轉化成了一種階級之“仇”:不僅“小毳毳失去了親愛的媽媽!姐夫失去了賢惠的妻子!我失去了從小撫養我長大成人的慈愛的姐姐!”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則是“黨失去了一個好女兒!群眾失去了他們的好朋友!”這種前期鋪墊,其用意無非是為了要讓少劍波帶領“小分隊”在后續的“剿匪”戰斗中,將“為民除害”以及“手刃仇人”的那種心理快感,都帶有一種不負黨的“囑托”和人民的“期望”的使命意識。
紅色大眾美學的“復仇”敘事,在新中國十七年“紅色經典”中,也是一種講述革命故事的必備手段,并成為了階級斗爭敘事中的常態現象。比如像趙玉林(《暴風驟雨》)、朱老忠(《紅旗譜》)、祝永康(《風雷》)、蕭長春(《艷陽天》)等革命英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有著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過去”。而這種痛苦的“過去”,又被理解為是促使他們參加革命的思想動機。換言之,正是因為擁有這種痛苦的“過去”,才激發了他們參加革命的高度熱情;而他們參加革命的真實目的,也無非是要向地主階級進行復仇。農民階級如果沒有苦難的“過去”,那么紅色文藝的“復仇”敘事也就失去了它在藝術上的審美價值。綜觀十七年“紅色經典”,革命敘事是在以一種全體被壓迫者的階級“復仇”,去向人們展示著一種令人震撼的藝術魅力。
吼聲四起,樓上樓下,還有女牢,像爆發的火山,吼聲連成一片。受盡壓迫和虐待的政治犯,發出了無法壓制的憤怒的吶喊。樓上樓下,每間牢房的人,都異口同聲地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吼。
那春雷一般,萬眾一心的聲浪,一旦升起,怎會被這嗡嗡的蚊蠅的阻擾而停歇?潮水般的聲浪在不知姓名的、重傷的戰友激越的鼓舞下,變得更加高昂豪邁,震撼著魔窟附近的山崗。(羅廣斌、楊益言《紅巖》)
這種革命者群體性的憤怒吶喊,不僅體現了共產黨人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同時也是向一切反動派發出的“復仇”誓言——這種“怒吼”之聲激越而洪亮,并伴隨著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進程,“越來越大,越來越雄壯。人民群眾的洪流,在紅旗的引導下闊步向前”。(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
三、紅色文藝對說書傳統的經驗借鑒
胡適曾說,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真實目的,就是想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11)。后來許多學者都根據這一說法,把“白話文”運動定性為百年中國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歷史開端。比如王瑤先生就曾認為,五四新文學“從根本上講,就是大眾化。提倡大眾化,從‘五四發源。提倡白話文就是提倡大眾化,提倡大眾化就是要更多的人看懂”(12)。其實,這一見解完全經不起推敲。五四新文學雖然推翻了傳統意義上的“貴族文學”, 并希望能使新文學從“廟堂”回歸“廣場”,但是對于那些不識字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文字障礙仍然使他們與新文學無緣。因此,無論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文學都只能是一種“小眾化”的文藝形式,若“要更多的人看懂”新文學,在當時的條件下顯然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國情。對于這一問題,還是瞿秋白看得更為清楚。他說“白話文”是現代“士大夫”的語言專制,“和以前的文言一樣”(13),其功能只不過是“替歐化的紳士換了胃口的魚翅酒席,勞動人民是沒有福氣吃的”。如果不使中國人徹底擺脫文盲狀態,文學終究“和平民群眾沒有關系”(14)。瞿秋白的這種看法,很值得引起我們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紅色大眾美學的價值取向,重點不是去追求文學的“大眾化”,而是去追求文藝的“大眾化”。紅色文藝實現大眾化的發展路徑,就是批判性地借鑒民間說唱藝術的表現形式,并在“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理論指導下,真正做到了“普及性”與“人民性”的完美結合,即:充分考慮到人民大眾對于文藝的接受方式,主要是“看”(戲曲)與“聽”(說書)而并非是“讀”(文學)。因為早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說書”這門民間藝術講述的就是“民眾所喜聽的故事”(15),故“看”與“聽”這種兩種方式,便成為了人民群眾參與文藝活動的主要途徑。所謂“看”,是指他們通過視覺功能,從戲曲、舞蹈等藝術門類中去獲得審美快感;所謂“聽”,則是指他們通過聽覺功能,從“說書”“大鼓詞”等藝術門類中去獲得審美快感。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活躍在“勾欄瓦舍”里的“說書人”,還是活躍在農村鄉鎮中的“說唱者”,他們才是文藝大眾化的具體實踐者。毛澤東就十分欣賞“口述”文藝的美學價值,他語重心長地對“魯藝”文藝工作者說,千萬不要小看了中國農民所具有的藝術天賦,“夏天的晚上,農夫們乘涼,坐在長板凳上,手執大芭蕉扇,講起故事來,他們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他們不用任何典故,講的故事內容卻是那么豐富,言辭又很美麗。這些農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16)。毛澤東說得沒錯,蒲松齡當年在路邊設茶棚,邀請過路農夫“講故事”,最終成就了《聊齋志異》這部不朽名著,便是文壇彌久不衰的一段佳話。學界對于紅色文藝借鑒民間藝術的“看”的功能,已經頗有研究且成果豐富,故本文將重點探討一下紅色文藝的“聽”的功能對于民間藝術的大膽借鑒與師承關系。
在延安和解放區文藝中,“說書”藝術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而“李卜”和“韓起祥”現象,就很能夠說明問題。李卜是一位說唱“眉戶戲”的民間藝人,在陜甘寧邊區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為了爭取他加入“民眾劇團”,以便推動邊區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柯仲平專門殺羊設宴“尊之為師”(17)。李卜也不負重托,在參加了“民眾劇團”之后,親自指導了一部現代眉戶戲《桃花村》,令“民眾劇團”一炮打響、名聲大振。馬健翎的《十二把鐮刀》與“魯藝”的《兄妹開荒》等秧歌劇,李卜也都曾在藝術上給予過指導。韓起祥是由賀敬之在下鄉體驗生活的過程中,從“收容所”里發現的一位盲人“說書人”。他曾回憶說,“聽”了韓起祥表演的說唱節目,內心世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于是,我把他從延安縣政府所在地領到‘魯藝去”(18)。韓起祥加盟“魯藝”,拓寬了專業文藝工作者的民間視野,邊區政府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說書組”,配合他去向廣大農民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從當時農民群眾的反映來看,韓起祥的“說書”藝術的確很受歡迎。每當他帶領“說書組”下鄉演出時,人們都會從四鄉八鄰趕來,聚精會神地“聽”他們“說唱”故事:當他們“說到緊張場面時,一點聲息也沒有,聽眾都靜靜望著他們的嘴,尤其是他那種感染人的神氣更是非常動人,唱到故事人物要哭的時候,他也裝出要哭的樣子,唱到英雄要生氣的時候,他就瞪起了眼挺起了胸膛,張開兩條腿,握著帶力的拳頭,使觀眾看見了這緊張的場面,忘記了他是說書人,好像他就是英雄一樣”(19)。正是因為有韓起祥的示范作用,陜甘寧邊區先后發展了400多位盲人“說書人”(20),他們不辭辛苦地奔走于黃土高坡,成為了革命與農民之間思想溝通的聯系紐帶。而共產黨人也并沒有忘記他們對于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比如韓起祥本人就被推選為第一屆“文代會”的正式代表。
傳統的“說書”藝術,包括“評彈”“說唱”“鼓詞”等形式,通常是以“說唱”相結合的表演方式,去表現底層社會所關注的思想內容。“說書”以“口述”的形式去傳播“故事”的內容,加之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俗語,因而對于那些大字不識的平民百姓來說,聽“說書”是他們欣賞文藝的便捷途徑。正是因為“說書”藝術在民間社會中具有極大的思想影響力,所以“歷代王朝都重視說書演義歷史、講經勸善對于鞏固皇權的作用”(21)。紅色文藝并沒有把“說書”藝術視為封建糟粕,而是對其進行了革命化改造,將新詞語和新思想“放入舊的模式中,新的程式便產生了”(22)。比如,胡考在其小說《陳二石頭》中,就是以“說書人”的口吻,構成了一種“說書人”與“聽眾”之間的對話關系。該作品講述農民陳二石頭,妻女都被日本飛機給炸死了,為了替親人報仇雪恨,他參加了抗日游擊隊。這篇作品的故事內容,其實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作者的敘事風格卻模仿了傳統的“說書”藝術,比如敘事語言明白如話、故事情節線索清晰,特別是在故事的結尾處來上一句“我講完啦,諸位,請你們說好不好,嘿嘿!”(小說原文刊于《文藝戰線》1939年第3期)很符合傳統“說書”藝術的口述性特點。
研究紅色文藝對于民間“說書”藝術的歷史傳承,“趙樹理現象”則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范例。解放區將趙樹理的文學創作視為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發展方向,就在于他那種“講故事”的通俗化方式,帶有“說書”藝術的明顯特征。趙樹理早年一直都生活在農村,他與農民一樣酷愛“小調”“評書”和“戲曲”等民間藝術。他通過對農民文化生活的長期觀察和切身體驗,發現“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和新詩一樣,在農村中根本沒有培活”,廣大農民群眾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新文藝,影響他們精神生活的仍是民間流行的“說書”藝術。(23)因此,他向文藝界大聲呼吁道:“經過‘五四所創之統是寶貴的、是應該繼承的,但為更多數人所熟悉所喜愛之統就不應該繼承嗎?”(24)趙樹理認為民間“說書”藝術在現代社會中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還“遠超過我們的新文藝或改造過的東西,在技術上我們也趕不上舊的”(25)。所以,他決心要一輩子扎根農村社會,永遠做一個為農民群眾所喜愛的“文攤”作家,并以他們所“喜聞樂見”的審美方式,去創作一種屬于農民自己的文學作品——即為學界一致公認的“農民小說”。
但話又說回來,從文學的文字表達特征來看,趙樹理小說的語言和內容雖然都非常的“農民化”,但卻并沒有被農民大眾所關注,其受眾群體仍然是農村社會中的部分“識字人”,對此趙樹理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說“我寫的東西,大部分是想寫給農村中的識字人讀,并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人聽”(26)的。這段話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思想啟示,即:無論趙樹理的小說寫得有多么通俗易懂,“文字”都是隔在他與農民之間無法逾越的一道障礙。故趙樹理將小說寫得口語化與生活化的真實目的,并不是為了要讓農民去“讀”,而是希望農村里的“識字人”,去“介紹給不識字人聽”。由此不難看出,“介紹”與“聽”的傳播方式,才是趙樹理小說與農民大眾的溝通渠道。趙樹理在談論自己的創作經驗時,“聽”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詞。比如他說,“語言是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一是叫人聽得懂,一是要叫人愿意聽”(27)。因此他“在寫《小二黑結婚》時,農民群眾不識字的情況還很普遍,在筆下就不能不考慮他們能不能讀懂、聽懂”(28)。特別是他在同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談話時,無意中又向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重要信息:“從我為農民寫作以來,——我就開始用農民的語言寫作。我用詞是有一定的標準的。我寫一行字,就念給我父母聽,他們是農民,沒有讀過什么書。他們要是聽不懂,我就修改。”(29)既然自己的父母因不識字,只能去“聽”而不是去“讀”他的小說作品,那么其他不識字的農民又怎能“讀得懂”他的小說呢?我當然不否認趙樹理在文學大眾化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像“‘然而聽不慣,咱就寫成‘可是;‘所以生一點,咱就寫成‘因此;不給他們換成順當的字眼兒,他們就不愿意看”(30)。其實,趙樹理在這里還是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邏輯錯誤:既然他把自己作品的“主要讀者對象”定位為“農民”,可是農民不識字又怎么能夠去“看”這些作品呢?就連他自己都明白,農民如果去“聽說書”,他們立刻就能“進入藝術環境”;可是面對兩眼一抹黑的文字作品,無論你寫得多么口語化,他們還是“看不懂”且“不愿意看”的。(31)毋庸置疑,趙樹理小說的文本價值,無非就是一種民間“說書”藝術的“話本”底稿,如果讓農民去“讀”肯定是行不通的,故只有通過農村“識字人”的“介紹”(“讀”或“講”),才能使其與農民之間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所以,他盡量把文字寫得通俗化與生活化,無非是為了“讀”起來能讓那些農民“聽得懂”,并且“聽了一次下次還想來”,絕不能“拿去朗誦,人家一聽就跑了”。而“朗誦”二字則是在暗示趙樹理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像評書這樣受群眾歡迎”(32)。實際上,《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作品之所以能夠得到農民群眾的廣泛認可,農村“識字人”的“介紹”可謂功不可沒。
紅色大眾美學與民間藝術的淵源關系,集中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覺堅守。毛澤東在其一生中,都在提倡以民間形式為基礎去發展民族文藝。比如,1938年他在延安觀看了秦腔《升官圖》等傳統劇目后,便深有感觸地對柯仲平說:“老百姓來的這么多,老年人穿著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劇場擁擠得滿滿的,群眾非常歡迎這種形式。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就是內容太舊了。如果加進抗日內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戲了。”他還強調陜甘寧邊區今后的文藝創作,就是“要搞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形式”。(33)到了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仍然認為搞文藝創作,“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34)。習近平同志更是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他曾一再強調指出,如果“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5)。而這種“民族精神”的歷史傳承,當然更需要紅色大眾美學去發揮其正確的導向性作用。
注釋:
(1) 毛澤東:《中國詩的出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
(2) 魯德才:《歷史中的俠與小說中的俠——論古代文化觀念中武俠性格的變遷》,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王國維文選》,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頁。
(4)(8)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陳平原小說史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9、1052頁。
(5)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頁。
(6) 王一川:《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7) 蘇雪林:《沈從文論》,《沈從文研究資料》(上),花城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48頁。
(9)(10) 陳山:《中國武俠史》,上海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73頁。
(11)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頁。
(12) 王瑤:《趙樹理的文學成就》,陳荒煤等主編:《趙樹理研究文集》 (上),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9頁。
(13) 瞿秋白:《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瞿秋白文集》? (文學編) 第1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465頁。
(14) 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15)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6頁。
(16)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15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第273頁。
(17) 柯仲平:《民眾劇團的成立及初期活動》,《延安文藝檔案·延安戲劇》第4冊,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頁。
(18) 賀敬之:《為人民藝術家立傳》,《農民日報》1988年1月30日。
(19) 通訊員:《山東通訊》,《文藝報》1949年第2期。
(20) 胡孟祥:《韓起祥評傳》,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頁。
(21) 孫曉忠:《改造說書人——1944 年延安鄉村文化的當代意義》,《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
(22)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9頁。
(23) 趙樹理:《藝術與農村》,《趙樹理全集》第3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頁。
(24) 趙樹理:《“普及”工作舊話重提》,《趙樹理全集》第5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25) 趙樹理:《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趙樹理全集》第3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59頁。
(26) 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趙樹理全集》第4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頁。
(27) 趙樹理:《語言小談》,《趙樹理全集》第5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頁。
(28) 趙樹理:《做生活的主人》,《趙樹理全集》第6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頁。
(29) 杰克·貝爾登:《趙樹理》,黃修己編:《趙樹理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30) 趙樹理:《也算經驗》,《趙樹理全集》第3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頁。
(31) 趙樹理:《不要急于寫,不要寫自己不熟悉的》,《趙樹理全集》第6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頁。
(32) 趙樹理:《同工人習作者談寫作》,《趙樹理全集》第5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頁。
(33) 艾克恩:《延安文藝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44頁。
(34) 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49頁。
(35)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 學習出版社2015年版, 第4—5頁。
作者簡介:宋劍華,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廣州,510632。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