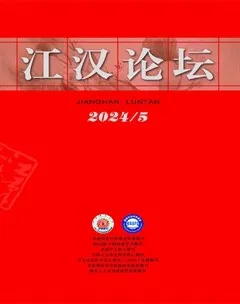楚國(guó)與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
摘要:蜻蜓眼玻璃珠是一類做工精美的飾物,原本出自西方,但通過(guò)中西商貿(mào)往來(lái)很早就傳入到中國(guó),并屢見(jiàn)于諸多楚地出土文物中。通過(guò)考索玻璃珠的傳播路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楚國(guó)與“絲綢之路”的關(guān)系以及楚國(guó)在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人們對(duì)“絲綢之路”的傳統(tǒng)認(rèn)知。蜻蜓眼玻璃珠在楚地的發(fā)現(xiàn)表明,楚國(guó)很早就與西方建立起了某種技術(shù)、文化交流的途徑,抑或已經(jīng)成功開(kāi)辟多條連接域外的“楚國(guó)版絲綢之路”。楚國(guó)在開(kāi)辟“西南西北絲綢之路”過(guò)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促進(jìn)了早期東西方文明之間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為漢代“絲綢之路”的形成作出了重要?dú)v史貢獻(xiàn),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對(duì)蜻蜓眼玻璃珠的傳播途徑及其歷史價(jià)值的研究,對(duì)拓展人們對(duì)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認(rèn)知和拓寬對(duì)早期“絲綢之路”的研究視野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guān)鍵詞:蜻蜓眼玻璃珠;草原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
基金項(xiàng)目:教育部產(chǎn)學(xué)研合作協(xié)同育人項(xiàng)目“基于文化地理學(xué)的文旅資源數(shù)字化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1140017552)
中圖分類號(hào):K203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3-854X(2024)05-0113-08
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麥克尼爾深刻指出,過(guò)去的歷史學(xué)家往往根據(jù)某些“邊界”為各種文明傳統(tǒng)下定義,而低估了各文明超出“邊界”之外的那些貿(mào)易與交流的作用。但各文明及其發(fā)展與它們同其原初社會(huì)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不可分割的,是更大范圍的貿(mào)易和生態(tài)體系的組成部分。各個(gè)文明間的交流和市場(chǎng)交換機(jī)制的形成減少了各文明的孤立性和自足性,將眾多的民族和文化納入不斷變化的市場(chǎng)活動(dòng)的世界體系之中,這種世界體系最初興起時(shí)的作用是邊緣性的,到今天已演變?yōu)榫哂兄行男缘男再|(zhì)。
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歷來(lái)是學(xué)界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早在19世紀(jì)后期,德國(guó)地理學(xué)家李希霍芬就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rèn)為在中國(guó)與中亞、兩河流域、印度之間存在一條交流通道,(1)這條通道正是以古代和中世紀(jì)的絲綢貿(mào)易興盛而得名。(2)文化交流歷來(lái)是雙向的,從考古發(fā)掘所見(jiàn),彼時(shí)東西方商貿(mào)交流并不僅限于絲綢、瓷器等中國(guó)輸入西方的商品,中東、歐洲等地同樣也把他們的商品通過(guò)“絲綢之路”輸入到中國(guó)。以楚地為例,就發(fā)現(xiàn)了不少的玻璃制品,其中又以蜻蜓眼玻璃珠最多,這在學(xué)界引起了廣泛的關(guān)注。張正明、劉玉堂等學(xué)者研究指出,“古代‘蜻蜓眼玻璃珠的分布地帶,大致是從地中海沿岸經(jīng)西亞轉(zhuǎn)南亞和東南亞至東亞”,由此說(shuō)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早在公元前6世紀(jì)的后期就存在了,這條通道謂之‘絲綢之路固可,謂之‘玻璃之路亦可,謂之‘絲綢與玻璃之路則更妥”。(3)王建新教授在2022年湖北考古業(yè)務(wù)成果交流會(huì)上亦提到:早在“張騫通西域前,楚人就開(kāi)通過(guò)一條‘絲路。楚國(guó)在將絲綢‘輸出至海外市場(chǎng)的同時(shí),也從西方引入了‘蜻蜓眼式玻璃珠(亦稱料珠)。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蜻蜓眼一經(jīng)傳入楚國(guó),便迅速被楚人采納,并依托其精湛的工藝技術(shù)進(jìn)行了仿制。無(wú)論是進(jìn)口的‘蜻蜓眼還是本土仿制的‘蜻蜓眼,均在高等級(jí)的楚墓中有所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了其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中的重要地位。”無(wú)獨(dú)有偶,新疆多地也發(fā)現(xiàn)了來(lái)自楚國(guó)的漆器和楚式銅鏡,這些證據(jù)充分表明,新疆地區(qū)應(yīng)是楚人開(kāi)辟“絲路”過(guò)程中的重要中轉(zhuǎn)站之一。(4)由此可知,蜻蜓眼玻璃珠最有可能先從西向東傳入中原,再由北向南流入楚地。與之相印證的是,北方如山西太原的晉國(guó)趙卿墓、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hào)(夫差夫人)墓,南方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及其夫人墓等墓葬都出土了大量的蜻蜓眼玻璃珠,其中曾侯乙墓更是多達(dá)173顆。曾侯乙墓出土的這批玻璃珠雖然仍是以鈉鈣成分為主,但普遍呈現(xiàn)出鈉少鉛多的特點(diǎn),這與西方玻璃珠已經(jīng)頗為不同,因此不排除是利用本地材料仿制的產(chǎn)品。蜻蜓眼玻璃珠主要流行于春秋末至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在黃河中下游以及長(zhǎng)江中游等地均有不少發(fā)現(xiàn),這與楚人的活動(dòng)范圍也基本重合。到了漢代,墓葬中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數(shù)量明顯減少,似乎已不復(fù)流行,僅在川渝、云貴和嶺南等地還有少量發(fā)現(xiàn)。
由此可見(jiàn),楚人很早就與西域、中西亞乃至歐洲文明產(chǎn)生過(guò)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并積極參與了早期“絲綢之路”的開(kāi)拓,對(duì)這一問(wèn)題值得研究者重新加以審視,而楚地出土的大量蜻蜓眼玻璃珠則對(duì)此提供了一個(gè)頗具代表意義的研究案例,通過(guò)考察玻璃珠的傳播路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楚國(guó)“絲綢之路”的形成乃至于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路徑,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huì)刷新人們對(duì)“絲綢之路”的傳統(tǒng)認(rèn)知。
一、東西方蜻蜓眼玻璃珠的異同
所謂“蜻蜓眼”,即是對(duì)西方傳入中國(guó)的一種鑲嵌式玻璃珠的俗稱。其主要特征是在常規(guī)玻璃球體上額外嵌入一層或多層顏色不同的玻璃,以此形成一個(gè)個(gè)凸出表面的“眼睛”圖案,從而達(dá)到裝飾效果。由于造型奇異,又與蜻蜓鼓眼類似,故得名“蜻蜓眼”。(5)
一般認(rèn)為,以蜻蜓眼玻璃珠為代表的玻璃制品最早出自西亞與地中海沿岸,在隨后的民族遷徙與貿(mào)易交換中傳入中國(guó)。(6)至遲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蜻蜓眼玻璃珠就已成為中國(guó)古代貴族墓葬中常見(jiàn)的陪葬品。(7)國(guó)內(nèi)對(duì)這一古代工藝品的研究起始于20世紀(jì)90年代,如安家瑤、后德俊、干福熹等學(xué)者都對(duì)此有十分精深的研究,成就斐然。他們的工作不僅厘清了蜻蜓眼玻璃珠傳入中國(guó)的時(shí)間,還詳細(xì)解析了其制作工藝、玻璃珠材質(zhì)以及傳播路線等問(wèn)題。(8)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進(jìn)一步研究早期東西方的文明交流與互鑒提供了重要線索。(9)
(一)玻璃材質(zhì)的差異
與西方的玻璃制品多為鈉鈣玻璃不同,中國(guó)本土生產(chǎn)的玻璃屬于鉛鋇玻璃,此差異已經(jīng)成為區(qū)別中國(guó)早期玻璃與西方玻璃的一個(gè)重要依據(jù)。(10)推究其原因,或許是與東西方不同的審美喜好相關(guān)。與西方世界普遍喜好貴金屬不同,古代中國(guó)人其實(shí)更鐘情于玉石之美。如王充在《論衡·率性篇》中就提到:“《禹貢》曰‘璆琳瑯玕,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yú)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11)為了獲得接近于玉石的質(zhì)感,中國(guó)本土生產(chǎn)的玻璃制品大多不尚透明。而西方的玻璃制品則極力模仿綠松石或青金石的效果,以鈉鈣玻璃為主,追求更高透明度。由此也就造成了東西方玻璃在材質(zhì)上的明顯差異。值得一提的是,玻璃制造工藝在傳入中國(guó)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中國(guó)本土青銅冶煉工藝和煉丹術(shù)中的技術(shù),使用氧化鉛(紅丹)以及氧化鉀(硝石)作為原料燒制玻璃,提供了當(dāng)時(shí)玻璃制品中鉀硅酸鹽和鉛鋇元素的來(lái)源。(12)這反映了古代中國(guó)藝人對(duì)新技術(shù)的吸收與成功改造。
通過(guò)文獻(xiàn)梳理,并結(jié)合科技考古成果,可以基于材質(zhì)的不同進(jìn)一步判斷蜻蜓眼玻璃珠乃至玻璃傳入中國(guó)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源自西亞、埃及(西方)的蜻蜓眼玻璃珠鈉鈣含量較高,而我國(guó)生產(chǎn)的玻璃珠鉛鋇含量較高,也就是說(shuō),西方的制作材料含有鈉鈣,中國(guó)產(chǎn)的蜻蜓眼制作材料則含鉛鋇。(13)如春秋末至戰(zhàn)國(guó)初,許多這一時(shí)期墓葬出土的玻璃珠就是鈉鈣玻璃材質(zhì),應(yīng)系舶來(lái)品;而到戰(zhàn)國(guó)中晚期,多數(shù)玻璃珠的材質(zhì)已被換成鉛鋇玻璃和鉀鈣玻璃,這意味著楚人在戰(zhàn)國(guó)中期就建立起了較為成熟的玻璃制造手工業(yè)(14),并由此開(kāi)啟了中國(guó)本土化玻璃的生產(chǎn)。再?gòu)某鐾翑?shù)量來(lái)看,鉛鋇玻璃珠主要發(fā)現(xiàn)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以湖北和湖南為中心的楚文化范圍內(nèi),因此不難推斷當(dāng)時(shí)的楚國(guó)應(yīng)是這兩種玻璃的主要制作中心之一。西方蜻蜓眼式玻璃珠通過(guò)一定的路線被引入中國(guó)后,我國(guó)借鑒并吸收了西方技術(shù),創(chuàng)造出了中國(guó)式的蜻蜓眼玻璃珠。從成分上講,中國(guó)蜻蜓眼玻璃珠主要是鉛鋇系統(tǒng)和鉀鈣系統(tǒng),和西亞傳來(lái)的鈉鈣系統(tǒng)不同。
(二)圖案造型與裝飾設(shè)計(jì)
首先,玻璃珠紋飾的交流與互鑒。一般認(rèn)為,古埃及人最早發(fā)明并制造了玻璃珠,其最早的玻璃珠成品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350年之間。而在此后,玻璃制品被法老、貴族等上層社會(huì)廣泛使用于裝飾和葬禮,展現(xiàn)出極高的工藝水平。隨著古埃及王國(guó)版圖的不斷擴(kuò)張,特別是與兩河流域的文化、宗教和貿(mào)易交流,玻璃珠制造技術(shù)逐漸傳播至波斯人和腓尼基人手中。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間的地中海地區(qū)的海路貿(mào)易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今伊朗南部和地中海東岸出土大量公元前5世紀(jì)至公元前3世紀(jì)玻璃珠的重要原因。到了晚期,玻璃珠的制作主要集中在今伊朗吉蘭州、黑海及里海沿岸、地中海東岸等地區(qū)。對(duì)于玻璃珠紋樣的形成,張正明研究指出:“它的裝飾紋樣純屬于地中海風(fēng)格,似乎凝聚著地中海的藍(lán)天白云……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裝飾紋樣的風(fēng)格迥異。”(15)
如前文所述,中國(guó)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就應(yīng)該已經(jīng)具備了較成熟的玻璃制作工藝。蜻蜓眼玻璃珠不僅是其中非常經(jīng)典的一種工藝類型,還結(jié)合了纏芯法和鑲嵌法進(jìn)行制作,(16)外形非常精美。常見(jiàn)的玻璃珠主要有藍(lán)色、綠色以及白色三種玻璃胎,球形表面還鑲嵌有不同顏色的圓環(huán),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工匠們極高的藝術(shù)審美水準(zhǔn)。前文已經(jīng)指出,西方最早傳入中國(guó)的玻璃制品基本以鈉鈣玻璃為主,如在河南淅川徐家?guī)X發(fā)掘的戰(zhàn)國(guó)楚墓就發(fā)現(xiàn)11顆用氧化鈷著色的深藍(lán)色珠眼,是為中國(guó)出土文物中最早使用鈷藍(lán)的案例。(17)至于玻璃珠上的圖案,則是利用著色劑施以層疊上色,使其表面產(chǎn)生一圈圈類似眼紋的白色線條作裝飾,這充分反映了當(dāng)時(shí)藝人們精湛的手工工藝。鉛鋇材料的玻璃珠則是受鈉鈣材質(zhì)的啟發(fā)而發(fā)明制作的,如在戰(zhàn)國(guó)前中期的曲阜魯故城遺址中就發(fā)現(xiàn)了22顆玻璃珠,主要化學(xué)成分為鉛鋇。(18)與前文所述的徐家?guī)X玻璃珠不同的是,魯國(guó)故城玻璃珠無(wú)論在化學(xué)成分還是制作工藝、審美風(fēng)格上都與前者呈現(xiàn)出很多不同之處,但是兩者的蜻蜓眼花紋仍然高度相似,說(shuō)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魯文化與楚文化之間有著比較密切的交流互動(dòng)。
其次,色彩的演變因素。玻璃珠色彩艷麗,色彩對(duì)于玻璃制品非常關(guān)鍵,而色彩與助劑的用量都與燒制的方式有關(guān)。例如,添加適量的銅,玻璃顏色為寶石藍(lán)、淡藍(lán)、深綠、紅或不透光的暗紅;添加鈷后,則其顏色會(huì)變成深藍(lán)色;若其呈現(xiàn)出黃或紫,則須添加錳;添加銻會(huì)出現(xiàn)不透明的黃(淡橘紅)和不透明的白;加入鐵,會(huì)產(chǎn)生淡藍(lán)、深綠、琥珀色或深黑色。因此,在大量實(shí)物中很難找到兩顆完全相同的玻璃珠。(19)根據(jù)趙德云《中國(guó)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中對(duì)中國(guó)考古發(fā)掘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統(tǒng)計(jì)表,可知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玻璃珠的主要出土地點(diǎn)及其色彩紋飾類型。我們知道,西亞伊朗高原地區(qū)的蜻蜓眼的顏色主要以藍(lán)色與白色為主,其蜻蜓眼玻璃珠的裝飾呈現(xiàn)為白、藍(lán)相間同心套圓,與中國(guó)戰(zhàn)國(guó)早期之前的蜻蜓眼接近。從蜻蜓眼的三種樣式可判別為從西亞傳入:第一種裝飾大致為環(huán)紋。代表性楚墓有湖北隨縣擂鼓墩M2,白色環(huán)紋里鑲嵌白色或藍(lán)色寶石;湖北荊州紀(jì)南城M2,表面有點(diǎn),圈狀紋飾;荊州天星觀M2,黃釉彩九個(gè)圓環(huán)等;第二種裝飾為球體均飾凸起的白、藍(lán)色或深綠色的圓圈。代表性楚墓有湖北江陵九店M294,蜻蜓眼出現(xiàn)藍(lán)色或深綠色;長(zhǎng)沙楚墓M1526,胎體綠色,十二蜻蜓眼,分上中下三層排列等。第三種裝飾為六七個(gè)小圓圈組團(tuán)式的排列,代表性的楚墓則為山東曲阜魯故城M52,蜻蜓眼玻璃珠為深藍(lán)色,上飾白色蜻蜓眼紋;湖北江陵九店M124,面飾白、藍(lán)或白、藍(lán)、黃三色圓圈紋。(20)由此,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從西亞傳來(lái)的蜻蜓眼玻璃珠一般色澤為白、藍(lán)、黃、綠,圖案表現(xiàn)形式為圈形或者點(diǎn)與圈結(jié)合。
再次,獨(dú)特的鑲嵌技藝。中國(guó)古代蜻蜓眼玻璃珠也稱為鑲嵌玻璃珠,依據(jù)時(shí)代早晚可分為三期:春秋末戰(zhàn)國(guó)初、戰(zhàn)國(guó)中晚期和西漢時(shí)期。從春秋晚期開(kāi)始,鑲嵌玻璃珠這種工藝品就已經(jīng)在我國(guó)中原地區(qū)出現(xiàn),這一時(shí)期的鑲嵌玻璃珠也有更為豐富華麗的紋飾,比如大圓圈與多個(gè)小圓圈并存的主流設(shè)計(jì)款式等。作為一種可以隨身攜帶的精巧飾物,蜻蜓眼玻璃珠在日常生活中的應(yīng)用可謂十分廣泛,經(jīng)常會(huì)與櫛袋、衣服、家具、金屬飾品及用具進(jìn)行搭配。如河南輝縣固圍村發(fā)現(xiàn)的鎏金鑲玉銀帶鉤,嵌入了由3個(gè)小同心圓組成圖案的玻璃珠。20世紀(jì)90年代末發(fā)掘的新疆扎滾魯克墓地發(fā)現(xiàn)有公元前8世紀(jì)—前1世紀(jì)的藍(lán)白相間蜻蜓眼玻璃珠2串,這和伊朗高原出土的一種鑲嵌玻璃珠非常相似。(21)
這一發(fā)現(xiàn)進(jìn)一步證實(shí),早在公元前10世紀(jì)的中葉,鑲嵌玻璃珠經(jīng)過(guò)后來(lái)的“絲綢之路”從西亞傳入中國(guó)新疆,至春秋末戰(zhàn)國(guó)初在我國(guó)中部地區(qū)出現(xiàn)。通過(guò)考古材料,江陵馬山磚廠二號(hào)楚墓(22)、長(zhǎng)沙楚墓(23)、巴澤雷克凍土墓(24)中出土的四山鏡、鳳紋刺繡、鉀玻璃珠和漆器等典型楚文化遺物,再結(jié)合巴澤雷克文化葬俗葬式、隨葬組合和典型隨葬品,可以發(fā)現(xiàn)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阿爾泰地區(qū)與楚地間也存在著一定的文化聯(lián)系與交流。《湖南出土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學(xué)研究》指出,湖南出土的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240顆蜻蜓眼玻璃珠,經(jīng)過(guò)對(duì)11顆蜻蜓眼玻璃珠的化學(xué)成分分析,發(fā)現(xiàn)有3顆蜻蜓眼玻璃珠屬于泡堿型鈉鈣玻璃,另外1顆扁平蜻蜓眼玻璃珠則為植物灰鈉鈣玻璃,這些玻璃珠均可能來(lái)源于埃及或東地中海地區(qū)。另外,我們還發(fā)現(xiàn)有3顆蜻蜓眼玻璃珠屬于鉛鋇玻璃,另有4顆為鉀鈣玻璃,這些玻璃制品均為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中國(guó)本土典型的玻璃制品,可以判斷為楚國(guó)本地制作。(25)根據(jù)以上論述,玻璃制品傳入我國(guó)的最初起點(diǎn)應(yīng)當(dāng)是今伊朗或地中海地區(qū)。
二、蜻蜓眼玻璃珠的傳播路徑
研究表明,早期東西方之間的商貿(mào)和人員交流其實(shí)出現(xiàn)得很早,不同產(chǎn)地的商品大交換為此提供了可靠物證。正如公元前5世紀(jì)左右,玻璃在中國(guó)的出現(xiàn)與希臘人記錄中國(guó)絲綢的存在,兩者在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幾乎完全吻合。(26)這也就證明了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路徑的客觀存在。從地理上看,中國(guó)西部的高原山地實(shí)際上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把中國(guó)本土與外部世界隔離開(kāi)來(lái)。但中國(guó)絕非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在西北、西南方向上,分別有兩條連接域外的交通要道,構(gòu)成了對(duì)外交往的“絲綢之路”。楚國(guó)雖然深處中國(guó)腹地,但卻并不妨礙楚人積極對(duì)外探索,通過(guò)“絲綢之路”參與東西方之間的物質(zhì)交換、文化交流的活動(dòng)中。因此,蜻蜓眼玻璃珠作為一個(gè)典型實(shí)例,又在“絲綢之路”沿線多有發(fā)現(xiàn),這就為我們深入研究早期交通路線和東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重要線索。
(一)連接楚國(guó)的“西北絲綢之路”
根據(jù)中外史學(xué)家考證,“草原之路”亦即“絲綢之路”的前身,是為當(dāng)時(shí)連接?xùn)|西方交流往來(lái)的主要通道之一。一般認(rèn)為,“草原之路”起自中國(guó)的華北或西北地區(qū),途經(jīng)蒙古高原、準(zhǔn)噶爾盆地和哈薩克草原向西,再沿里海、黑海和多瑙河一線進(jìn)入到歐洲,這條通道幾乎橫跨了整個(gè)歐亞大草原,并有大量的游牧民族活躍其間,通過(guò)牧民長(zhǎng)途遷徙與貿(mào)易交換帶動(dòng)起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相互借鑒。(27)正是在此過(guò)程中,來(lái)自西亞與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制品及其制造工藝漸漸傳入中國(guó)。(28)
其一,從楚國(guó)與西域的交通看。漢代對(duì)西域的解釋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僅僅涵蓋了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周邊區(qū)域;廣義上的西域則包括了整個(gè)天山南北以及自蔥嶺以西的中亞、西亞等地,一直到地中海、印度洋沿岸。20世紀(jì)50年代,在河南洛陽(yáng)發(fā)掘的東周墓葬群的玉器中,根據(jù)檢驗(yàn)有一半左右的玉器制作所用的石材都來(lái)自西域。另外在洛陽(yáng)市東周墓葬群中還發(fā)掘出制作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小玻璃珠,其主要成分屬于鈉鈣玻璃,與我國(guó)主流的鉛鋇玻璃在材質(zhì)上有明顯差異,且其紋飾屬于蜻蜓眼式,與這一時(shí)期我國(guó)流行的蟠璃紋或云紋都有所區(qū)別,而同樣風(fēng)格且制作于同一時(shí)期的蜻蜓眼玻璃珠制品在阿爾泰地區(qū)、黑海北岸及里海地區(qū)也有發(fā)現(xiàn),證明洛陽(yáng)出土的蜻蜓眼式小玻璃珠很有可能就是由這些區(qū)域傳入。而阿爾泰地區(qū)的巴澤雷克墓群中有大量的絲綢織物出土,這些織物也很有可能就是由東周的都城——洛邑所傳出。(29)
根據(jù)宋曉梅的分析,在阿爾泰地區(qū)巴澤雷克6號(hào)墓的山字紋銅鏡是原產(chǎn)于楚地的物品,應(yīng)當(dāng)是先由楚地運(yùn)輸至洛陽(yáng),再以洛陽(yáng)為起點(diǎn)運(yùn)輸?shù)桨柼┑貐^(qū)。(30)王建新教授認(rèn)為,西伯利亞公元前5世紀(jì)的巴澤雷克古墓出土過(guò)絲綢,其紋飾與湖北楚墓出土的鳳鳥(niǎo)紋一模一樣,可以判定是典型的楚國(guó)織錦。這說(shuō)明在春秋中晚期到戰(zhàn)國(guó)初期,中西方之間的物質(zhì)交流就已經(jīng)日漸起步并逐漸繁盛,波斯文化、希臘文化和中國(guó)文化的元素相互交融,而早期中西方之間的物質(zhì)及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就是經(jīng)由北方草原“絲綢之路”進(jìn)行的,其大致路線是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江流域的楚地、黃河流域、太行山、雁門、河套地區(qū)、蒙古高原最終抵達(dá)阿爾泰山及該區(qū)域以北;同時(shí)還向西開(kāi)辟出經(jīng)由南俄草原并抵達(dá)黑海北岸的路徑,可見(jiàn)草原“絲綢之路”具有多個(gè)分支并橫貫歐亞大陸,甚至通向南亞或西亞地區(qū),其對(duì)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都發(fā)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另有研究表明,草原“絲綢之路”在西漢時(shí)期河西走廊開(kāi)辟之前,實(shí)際上承擔(dān)著古代中國(guó)與西域地區(qū)進(jìn)行貨物貿(mào)易和文化交流往來(lái)的使命。西域與中國(guó)地區(qū)蜻蜓眼玻璃珠的出土地點(diǎn),自西向東的主要分布情況如下:伊朗(波斯波利斯遺址)—中亞(費(fèi)爾干納盆地的斯基泰)—新疆(輪臺(tái)窮巴克、且末扎滾魯克等)—甘肅(秦安上袁家、平?jīng)鰪R莊)—山西(長(zhǎng)子牛家坡、長(zhǎng)治分水嶺、太原晉國(guó)趙卿墓等)—河南(固始侯古堆、輝縣固圍、洛陽(yáng)中州路、鄭州二里岡等)—山東(曲阜魯國(guó)故城)—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擂鼓墩、江陵九店等)—湖南(長(zhǎng)沙楚墓等)—廣東(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云南(石寨山古墓)。(31)
絲絹西運(yùn)和玻璃東傳,表明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在古代中國(guó)和今伊朗之間已經(jīng)逐漸形成了一條交通孔道,刻畫了一幅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dòng)圖景。
其二,楚國(guó)絲綢傳播希臘的途徑。絲綢是古代中國(guó)勞動(dòng)人民智慧的結(jié)晶,迄今為止其發(fā)展歷史已有5000多年。國(guó)內(nèi)外一系列歷史文獻(xiàn)表明,早在約公元前1000年的時(shí)候,天山北麓的草原地區(qū)就已經(jīng)引入了中國(guó)內(nèi)地生產(chǎn)的絲綢織物。一些制作于公元前6世紀(jì)至公元前3世紀(jì)的希臘陶器及雕刻上面的彩繪人像表明,當(dāng)時(shí)希臘社會(huì)上層人物穿著一種細(xì)薄透明的高級(jí)衣物,即由源自中國(guó)的絲綢制成。另根據(jù)一些古代傳說(shuō)并結(jié)合出土文物相互印證,《穆天子傳》中的周穆王在晉見(jiàn)西王母之后,就途經(jīng)中亞伊朗高原前往今吉爾吉斯斯坦草原一帶,這也是早在公元前6世紀(jì)時(shí)中西方就已經(jīng)有人員往來(lái)和文化交流的證明。(32)根據(jù)西方文獻(xiàn)記載,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24年期間,希臘國(guó)王亞歷山大曾率大軍入侵印度、伊朗及西亞的部分地區(qū),而一些腓尼基商人也隨著他的軍隊(duì)進(jìn)入亞洲部分地區(qū),并將中國(guó)的絲綢、西亞的珍珠或者印度的寶石銷往歐洲的羅馬、希臘等地,這些貿(mào)易活動(dòng)及人員往來(lái)在客觀上也促進(jìn)了當(dāng)時(shí)楚文化向歐洲大陸的傳播。公元前5世紀(jì),楚地的多種絹制品已經(jīng)大量出口印度并且廣受歡迎,而這一時(shí)期也正是楚國(guó)玻璃制品逐漸流行的時(shí)間段。另外由于印度與西方已經(jīng)有貿(mào)易往來(lái),因此包括楚地在內(nèi)的中國(guó)絲絹制品經(jīng)由印度傳入歐洲國(guó)家,這可能是當(dāng)時(shí)希臘上層人物能夠獲得絲綢制品的重要渠道之一。公元前438—公元前431年,巴特農(nóng)神廟的女神身著長(zhǎng)袍,衣褶雅麗,質(zhì)地柔軟,均系絲織衣料。
其三,楚國(guó)對(duì)“西北絲綢之路”的探索。大量文獻(xiàn)資料顯示,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我國(guó)絲織業(yè)發(fā)展迅速。當(dāng)時(shí),絲織業(yè)最為發(fā)達(dá)的地區(qū)是齊魯和楚國(guó),史有“齊紈魯縞”“冠帶衣履天下”之說(shuō)。但是,考古發(fā)掘出土的這一時(shí)期的絲綢實(shí)物,卻大多見(jiàn)于楚地,尤其以湖南長(zhǎng)沙市郊和湖北荊州最多。(33)在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時(shí)代,長(zhǎng)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幾乎同時(shí)出現(xiàn)了絲綢制造業(yè)的萌芽。根據(jù)歷史記載,中國(guó)最早開(kāi)始種植桑樹(shù)養(yǎng)蠶并制作絲綢織物的時(shí)間是在新石器時(shí)代中期。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和技術(shù)的進(jìn)步,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國(guó)絲綢業(yè)生產(chǎn)已初具規(guī)模,有比較復(fù)雜的手工織機(jī)和高超的織造工藝。1982年,湖北省荊州市馬山一號(hào)楚墓的考古發(fā)掘,印證了楚國(guó)的絲織業(yè)擁有當(dāng)時(shí)世界一流的紡織技術(shù)水平。(34)
楚人對(duì)“西北絲綢之路”是有探索的,戰(zhàn)國(guó)中晚期荊門包山楚墓中出土的人擎燈和江陵望山楚墓人騎駱駝銅燈可為佐證:墓中出土人擎燈2件。燈由燈盤、柱和銅人三部分組成。銅人頭挽右髻,濃眉大眼,直鼻,寬額小嘴,圓頜,耳微外移。(35)柱座上鑄四分蟠螭紋,深衣下擺錯(cuò)紅銅勾連紋。從人物的造型和面相上看應(yīng)該是中原一帶人士。1965年發(fā)掘的江陵望山2號(hào)墓出土人騎駱駝銅燈,由豆形燈與人騎駝形燈座兩部分組成。燈盤較大,平沿稍內(nèi)斂,厚方唇,淺腹,盤內(nèi)中心有一尖形燭針,高1.6厘米;銅人昂首直腰騎坐于駝上,頭部較大,面向正前方,圓胖臉型,鑄有向腦后梳的發(fā)紋,兩手屈肘前伸托住管形銅圈,以承插燈柄,雙腿屈膝彎足貼于駝身兩側(cè);駱駝之頭前伸,弓背垂尾,四足立于長(zhǎng)方形銅板上。(36)根據(jù)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的年代推測(cè)為戰(zhàn)國(guó)中晚期,與荊門包山楚墓為同一時(shí)期。駱駝的出現(xiàn)說(shuō)明楚人探索過(guò)西北沙漠,并在探索西北的同時(shí)也將絲綢帶到了那里。(37)
(二)連接楚國(guó)的“西南絲綢之路”
與“西北絲綢之路”不同,“西南絲綢之路”則連接了長(zhǎng)江中上游地區(qū)與南亞、東南亞地區(qū)。楚國(guó)因?yàn)榈靥庨L(zhǎng)江中游,與西南地區(qū)臨近,所以很可能也通過(guò)“西南絲綢之路”連接域外,這為蜻蜓眼玻璃珠傳入中國(guó)提供了第二條路徑。
其一,從楚與巴蜀、滇黔、兩廣的交通狀況看。早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中國(guó)的四川、重慶等地就與印度存在著貿(mào)易往來(lái)。《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提到:“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lái),言居大夏時(shí),見(jiàn)蜀布、邛竹杖。使問(wèn)所從來(lái),曰:‘從東南身毒國(guó)可數(shù)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gu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guó),患匈奴隔其道;誠(chéng)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wú)害。”(38)據(jù)考證,這個(gè)西域的大夏國(guó)是在今天帕米爾高原以西的阿富汗一帶,天竺也就是中國(guó)古籍對(duì)印度的別稱。這說(shuō)明,蜀地出產(chǎn)的蜀布、邛竹杖等物應(yīng)該是先從中國(guó)四川運(yùn)出至印度,再經(jīng)印度商人轉(zhuǎn)賣至中亞。這一史料無(wú)疑證明了在“西北絲綢之路”外還有一條“西南絲綢之路”的存在。楚地因?yàn)榕R近巴蜀,所以很可能也通過(guò)這條道路進(jìn)行域外交流。一個(gè)比較可靠的例子就是楚國(guó)將領(lǐng)莊入滇。《史記》《漢書(shū)》對(duì)此都有明確記載:楚頃襄王時(shí)曾命將軍莊率部沿著長(zhǎng)江逆流而上,奪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地區(qū)。莊一路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帶),憑借楚軍威勢(shì)征服了周邊的大片土地,后來(lái)因?yàn)榍貒?guó)伐楚,莊無(wú)法返回,遂在滇地稱王,建立滇國(guó)。(39)楚將莊的大軍能夠遠(yuǎn)征千里之外,又有蜀地商品遠(yuǎn)銷天竺,這些史例無(wú)不說(shuō)明楚地與四川、云南乃至印度都有密切聯(lián)系。不僅如此,楚國(guó)的青銅器文化也從兩湖地區(qū)向外擴(kuò)散,并深刻影響到兩廣地區(qū)的青銅器制造,加快其青銅文化發(fā)展。兩廣地區(qū)的某些青銅器物的形制、花紋以及工藝處理雖然具有地域特色,但其技術(shù)手法和工藝形式仍與楚式青銅器有著相似之處。(40)在此基礎(chǔ)上,楚國(guó)極有可能通過(guò)當(dāng)時(shí)生活在嶺南的百越部族與東南亞、南亞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
其二,從楚國(guó)的絲織技術(shù)水平看。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國(guó)雖然經(jīng)常被中原諸國(guó)視為南蠻,但卻是當(dāng)時(shí)非常重要的絲綢主產(chǎn)地之一。從近幾十年的楚地墓葬發(fā)掘所見(jiàn),出土了大量絲織品,如1965年發(fā)掘的江陵望山戰(zhàn)國(guó)楚墓中,就找到了繡有不同花卉紋、動(dòng)物花紋的絹繡和十字菱紋錦繡。(41)1981年江陵九店磚廠楚墓同樣出土了包括絹、紗、錦等在內(nèi)的17件絲織物,織繡圖案多是一鳳三龍或鳳與花卉。此外,像荊州馬山一號(hào)楚墓也發(fā)現(xiàn)了30多件繡有蟠龍飛鳳繡紋、對(duì)鳳對(duì)鳥(niǎo)紋等圖樣的珍貴絲織品。(42)荊門包山楚墓出土絲織物77件,主要的繡紋是一鳳三龍相戲和鳳鳥(niǎo)的圖像。(43)大量絲織品的出土無(wú)疑從一個(gè)側(cè)面展示了楚地絲織業(yè)的繁榮。彼時(shí),因?yàn)閮r(jià)值高昂,絲綢已然成為楚國(guó)經(jīng)濟(jì)的重要支柱之一和楚文化的一大特色。為保障種桑養(yǎng)蠶,吸收先進(jìn)技術(shù),楚國(guó)甚至不惜動(dòng)用武力與鄰國(guó)競(jìng)爭(zhēng)。如《史記·楚世家》載:“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鐘離小童爭(zhēng)桑,兩家交怒相攻”,最后,楚國(guó)滅了卑梁(今安徽鳳陽(yáng)縣東北),吳國(guó)攻占了鐘離(今安徽天長(zhǎng)市西北)。(44)《左傳·成公二年》亦載,楚國(guó)為了獲得魯國(guó)的先進(jìn)絲織技術(shù),直接大軍壓境,動(dòng)用武力威逼魯國(guó),迫使魯國(guó)君主只能獻(xiàn)上百余名絲織技工來(lái)?yè)Q取和平。這些措施大大推進(jìn)了楚國(guó)絲織業(yè)的發(fā)展,使之后來(lái)居上,成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絲綢的核心產(chǎn)區(qū)之一。而在楚地生產(chǎn)的絲綢中,應(yīng)該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流入周邊地區(qū),經(jīng)由商人轉(zhuǎn)手,成為絲綢之路上暢銷的商品。
其三,從楚國(guó)的玻璃制造水平看。楚國(guó)的玻璃制造大約出現(xiàn)于公元前5世紀(jì)左右。仍以蜻蜓眼玻璃珠為例,這一飾物因?yàn)樵煨推娈悾欢攘餍杏诖呵飸?zhàn)國(guó)時(shí)期,常見(jiàn)于貴族墓葬陪葬。如今出土最多的當(dāng)屬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山東、河北、陜西次之,廣東、四川、重慶、甘肅、新疆等地亦有出土。從出土地的分布來(lái)看,楚地當(dāng)是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玻璃器物生產(chǎn)的核心區(qū)域之一。特別是近年來(lái)發(fā)掘的楚墓顯示,進(jìn)入戰(zhàn)國(guó)以后的楚墓往往發(fā)掘出更多玻璃珠,這是一個(gè)非常值得關(guān)注的歷史現(xiàn)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早期的玻璃制造技術(shù)或許已被楚人掌握。楚國(guó)曾是西周的封國(guó)之一,很可能從諸夏那里學(xué)到了以石英砂為主要原料,使用先成型后燒結(jié)的方法產(chǎn)生釉砂,河南淅川縣下寺出土的釉砂就是一個(gè)典型;二是可能來(lái)自西方的大量玻璃制品通過(guò)“玻璃之路”傳入楚國(guó);三是楚人的社會(huì)需求。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禮儀用器和裝飾品是玉,從楚墓發(fā)掘報(bào)告可知玉的資源很少,玉在當(dāng)時(shí)的楚國(guó)非常珍貴。而玻璃能仿制成玉器,同時(shí),玻璃物料比玉器容易獲得,價(jià)格比玉器便宜、色澤鮮艷,因而能夠滿足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裝飾物的追求與喜愛(ài)。
出于對(duì)玉石的喜愛(ài),楚人有意在玻璃中添加入了一些鋇,以達(dá)到仿制效果,并將其與真正的玉石擺放在一起,由此可見(jiàn)楚人對(duì)玻璃制作工藝的重視程度。楚人在這方面的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1)楚人創(chuàng)造了中國(guó)歷史上最早的鉛鋇玻璃,或者說(shuō)鉛鋇體系玻璃;(2)楚人創(chuàng)造了玻璃生產(chǎn)中的模壓工藝。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楚國(guó)具有比較發(fā)達(dá)的青銅鑄造水平,楚人將其應(yīng)用于玻璃制造中,生產(chǎn)出了玻璃璧、玻璃劍首等采用模壓工藝制作的玻璃制品;(3)楚人制造出中國(guó)歷史上最早的平板玻璃制品。從制造工藝上看,楚國(guó)制造的玻璃璧、玻璃劍首等所采用的模壓工藝,為中國(guó)早期平板玻璃的出現(xiàn)起了奠基作用。楚國(guó)發(fā)達(dá)的玻璃制造工藝水平充分表明,楚地應(yīng)該是較早接觸到西方玻璃器物及其制作工藝的區(qū)域之一,這進(jìn)一步印證了楚國(guó)曾積極參與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史實(shí)。
其四,楚國(guó)對(duì)西南絲綢之路的探索。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文化成為長(zhǎng)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qū)的主流文化。春秋時(shí)期,原居住在長(zhǎng)江中游的楚國(guó)積極向北延伸,問(wèn)鼎中原;到了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大力向南發(fā)展,沿湘江南下,同那里的百越文化融合;隨后又向東擴(kuò)展,到達(dá)長(zhǎng)江下游,同那里的吳越文化融合。根據(jù)對(duì)中國(guó)華南、西南地區(qū)乃至南亞、東南亞部分地區(qū)的古墓葬、古遺址的發(fā)掘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諸多楚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往來(lái)的證據(jù)。如《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表明,廣東肇慶市北松嶺山的古墓建成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其中的陪葬品同時(shí)包含了多把楚式青銅劍和一件玻璃珠。此外,在廣東始興的一座春秋后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把楚制青銅劍。(45)另外根據(jù)《云南省楚雄縣萬(wàn)家壩古墓群發(fā)掘簡(jiǎn)報(bào)》中的記載與分析,云南省楚雄市萬(wàn)家壩古墓群的具體修建時(shí)代跨越了春秋中晚期到戰(zhàn)國(guó)初期,其中的22號(hào)墓中也發(fā)現(xiàn)了六棱形淺綠色的玻璃珠,這一出土文物證明了云南地區(qū)與楚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46)肖明華在《云南考古述略》中指出,石寨山古墓出土的葫蘆勺、陶制彈丸,其形制與楚墓中出土的葫蘆勺或鉛質(zhì)彈丸近似。另外在云南發(fā)掘的一些古墓中也發(fā)現(xiàn)了朱底黑花漆器隨葬品,而這類物品在楚墓中比較常見(jiàn)。(47)這些現(xiàn)象都有力地證明了春秋中晚期到戰(zhàn)國(guó)初期,云南地區(qū)很可能是西方文化與楚文化交流的重要驛站。謝崇安《云南石寨山文化與越南東山文化的比較研究》一文認(rèn)為,約在公元前5世紀(jì)至1世紀(jì),云南地區(qū)與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qū),在文化和藝術(shù)方面曾有過(guò)一定程度的交流與碰撞,并且傳至印度及西亞部分地區(qū),這些地區(qū)也出現(xiàn)了工藝及形制類同的漆器及鐵器,尤其是其中的漆器更是集中地體現(xiàn)了楚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風(fēng)格及制造工藝水準(zhǔn)。(48)由此可以看出,在這一時(shí)期,東南亞一帶與印度、西亞及楚國(guó)發(fā)生過(guò)文化接觸交流乃至貿(mào)易往來(lái),因此成為當(dāng)時(shí)西方文化與楚文化交流往來(lái)的重要區(qū)域之一。黃展岳在其所著《兩廣先秦文化》中指出,根據(jù)墓葬出土文物的分析,中原地區(qū)是先秦時(shí)期青銅冶煉業(yè)的發(fā)源地,而楚國(guó)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中轉(zhuǎn)角色。蜻蜓眼式玻璃珠在當(dāng)時(shí)是屬于使用西方工藝制作而成的工藝品,它與楚文化的青銅劍同時(shí)在廣東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墓葬中被發(fā)現(xiàn)這一事實(shí),也是西方文化傳入我國(guó)華南地區(qū)之后與楚文化相融合發(fā)展的有力證據(jù)。
綜上所述,西方的玻璃制品傳入我國(guó)先后途經(jīng)南亞地區(qū)的印度到達(dá)云南地區(qū),再通過(guò)人們的日常生活交往和國(guó)內(nèi)貿(mào)易來(lái)到當(dāng)時(shí)的楚地。這就是“玻璃之路”萌芽時(shí)期的另一條路線,印度及我國(guó)云南等地出土的這一時(shí)期的玻璃制品也證實(shí)了這一判斷。(49)
三、楚國(guó)開(kāi)辟“西南西北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及其意義
楚國(guó)在開(kāi)辟“西南西北絲綢之路”過(guò)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活動(dòng)中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xiàn)。首先,促進(jìn)了中西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西亞的玻璃裝飾珠在春秋末戰(zhàn)國(guó)初,通過(guò)中亞游牧民族作為商品轉(zhuǎn)銷進(jìn)入我國(guó)中原和楚地。戰(zhàn)國(guó)中晚期,隨著玻璃珠制品經(jīng)過(guò)歐亞大陸傳至我國(guó),并且其制作工藝也隨之傳入。我國(guó)在戰(zhàn)國(guó)中晚期時(shí)已經(jīng)把玻璃制品視為玉的一種替代品,對(duì)其仿制并且改良了部分工藝,因此當(dāng)時(shí)我國(guó)的玻璃珠制品雖然外觀近似玉石,但成分區(qū)別則顯而易見(jiàn)。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玻璃已在我國(guó)扎下根來(lái),雖然還不斷受到西方技術(shù)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在戰(zhàn)國(guó)玻璃工藝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玻璃制作工藝和產(chǎn)品。其次,為漢代“絲綢之路”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礎(chǔ)。黃河流域與長(zhǎng)江流域是中華文明主要發(fā)祥地,以玉、漆、絲、瓷等為典型代表的手工業(yè)產(chǎn)品,顯示了古代中華民族高超的手工業(yè)制作工藝水平,也成為中華文明的代表性符號(hào),并使之與世界其他文明相區(qū)別。在科技欠發(fā)達(dá)的古代,陸路交通是古代各民族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lái)的主要途徑。漢代“絲綢之路”的主干線起自洛陽(yáng),經(jīng)過(guò)長(zhǎng)安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帕米爾高原、錫爾河和阿姆河中上游谷地與河中地區(qū)、穆?tīng)柤硬己泳G洲、伊朗高原北部、美索不達(dá)米亞,最后到達(dá)地中海東部。(50)楚國(guó)的早期探索為漢代“絲綢之路”的形成提供了某些經(jīng)驗(yàn),一定程度上為漢代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chǔ)。再次,確立和鞏固了中國(guó)在古代世界先進(jìn)國(guó)家的地位。楚國(guó)在疆域拓展的過(guò)程中,使原先的地緣政治格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使古代中國(guó)境內(nèi)各民族之間的人員往來(lái)與文化交流更加頻繁,推動(dòng)了華夏文明的進(jìn)一步統(tǒng)一。最后,推動(dòng)了楚國(guó)自身的發(fā)展。楚國(guó)在開(kāi)辟“西南西北絲綢之路”的過(guò)程中,不僅促進(jìn)了與外部的交流和合作,也推動(dòng)了自身的經(jīng)濟(jì)、文化和社會(huì)的發(fā)展。楚國(guó)對(duì)“絲綢之路”的探索,使楚國(guó)的貿(mào)易活動(dòng)范圍得到了極大拓展,各種商品和資源的流通更加便捷,為楚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繁榮奠定了基礎(chǔ)。同時(shí),文化交流也為楚國(guó)的文化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過(guò)充分學(xué)習(xí)和吸納外來(lái)元素,使楚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科學(xué)技術(shù)等各個(gè)領(lǐng)域都得到了長(zhǎng)足的進(jìn)步。同時(shí),對(duì)“絲綢之路”的早期探索,也使楚國(guó)的地位得以極大提升,成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南方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
我們還可以站在更寬廣的視角來(lái)考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通過(guò)空間和時(shí)間的跨度將絲綢文化的精髓融入了當(dāng)時(shí)政治、文化、社會(huì)與經(jīng)濟(jì)的各個(gè)層面,絲綢成為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西南絲綢之路”是一條縱貫東西南北的大通道,它是從古至今中國(guó)與南亞、東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一帶的一條重要貿(mào)易通道。“西北絲綢之路”的發(fā)展不僅促進(jìn)了歷史上我國(guó)國(guó)內(nèi)以及對(duì)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對(duì)于文化的交流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西周至戰(zhàn)國(guó)晚期,西方傳入中國(guó)的主要是黃金和銀器,還有玻璃技術(shù)等,而中國(guó)傳入西方的則有絲綢、漆器、金屬制品、龍虎形象、銅鏡、中原文化等。在頻繁的商品和文化交流中,中國(guó)作為古代世界先進(jìn)國(guó)家的地位得以確立和鞏固。
注釋:
(1) 費(fèi)迪南德·馮·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國(guó)旅行日記》,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6年出版,第29—43頁(yè)。
(2)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發(fā)現(xiàn)》,《百科知識(shí)》2014年第16期。
(3) 張正明、劉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 464—466頁(yè)。
(4) М.П.格里亞茲諾夫、О.И.達(dá)維母、К.М.斯卡郎:《阿爾泰巴澤雷克的五座古塚 》,《考古》1960年第7期。
(5)(6)(12)(20)(24)(29)(31)(50) 趙德云:《中國(guó)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學(xué)報(bào)》2012年第2期。另,關(guān)于玻璃珠的形態(tài)與裝飾的相關(guān)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還可以參見(jiàn)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晉國(guó)趙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固始侯古堆一號(hào)墓發(fā)掘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hào)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固始侯古堆一號(hào)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隨縣擂鼓墩一號(hào)墓考古發(fā)掘隊(duì):《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7) 高至喜:《論我國(guó)春秋戰(zhàn)國(guó)的玻璃器及有關(guān)問(wèn)題》,《文物》1985年第12期。
(8) 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論先秦硅酸鹽質(zhì)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術(shù)交流(英文)》,《硅酸鹽學(xué)報(bào)》2013年第41期。
(9) 安家瑤:《玻璃器史話》,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5頁(yè)。
(10)(19) 楊伯達(dá):《西周至南北自制玻璃概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11) 王充著、邱鋒、常孫昊田譯注:《論衡》,中華書(shū)局2024年版,第140頁(yè)。
(13)(15) 張正明:《“蜻蜓眼”玻璃珠傳遞的信息——楚人的開(kāi)放氣度》,《政策》1997年第3期。
(14) 潛偉:《從玻璃技術(shù)與冶金技術(shù)的關(guān)系看中國(guó)古代玻璃的起源》,載《絲綢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5頁(yè)。
(16) 安家瑤:《玻璃器史話》,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8頁(yè)。“纏芯法”是一種在材料科學(xué)、工程技術(shù)以及制造業(yè)中常用的工藝方法,主要用于處理或加工具有芯部結(jié)構(gòu)的材料或組件。該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通過(guò)特定的工藝手段,如纏繞、包裹、填充等,在芯部材料或結(jié)構(gòu)上附加一層或多層外部材料,以改變或增強(qiáng)其原有的物理、化學(xué)或機(jī)械性能。在材料科學(xué)領(lǐng)域,纏芯法可用于提高材料的強(qiáng)度、硬度、耐腐蝕性、隔熱性等多種性能。“鑲嵌法”是一種藝術(shù)或設(shè)計(jì)手法,通常用于裝飾或構(gòu)造物體。這種方法涉及將一種材料嵌入到另一種材料中,以創(chuàng)造出一種獨(dú)特且引人注目的視覺(jué)效果。在藝術(shù)和設(shè)計(jì)領(lǐng)域,鑲嵌法被深入研究,并被視為一種重要的風(fēng)格或技巧。
(17) 干福熹、承煥生、胡永慶等:《河南淅川徐家?guī)X出土中國(guó)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的研究》,《中國(guó)科學(xué)(E輯:技術(shù)科學(xué))》2009年第4期。
(18)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guó)古城》,齊魯書(shū)社1982年版,第178頁(yè)。
(2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hào)墓地發(fā)掘報(bào)告》,《考古學(xué)報(bào)》2003年第1期。
(22) 院文清:《江陵馬山磚廠二號(hào)楚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江漢考古》1987年第3期。
(23) 湖南省博物館:《長(zhǎng)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頁(yè)。
(25) 王宜飛、段曉明、董俊卿等:《湖南出土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學(xué)研究》,《文物保護(hù)與考古科學(xué)》2023年第6期。
(26) 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0頁(yè)。
(27) 張國(guó)剛:《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
(28) 姜義華:《中華文化通志——中國(guó)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yè)。
(30) 宋曉梅:《巴澤雷克墓出土銅鏡新考》, 《洛陽(yáng)——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diǎn)》,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 178—188頁(yè)。
(32) 石云濤:《絲綢之路的起源》,蘭州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62—86頁(yè)。
(33)(34) 陳鯤:《“一帶一路”背景下楚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之路》,《文化產(chǎn)業(yè)》2022年第32期。
(35)(36) 天行健:《奇特靈異楚銅燈》,《今日湖北》2000年第1期。
(37)(43)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duì):《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66頁(yè)。
(38)(39) 司馬遷:《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中華書(shū)局1959年版,第2995—2996、2993頁(yè)。
(40) 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huì)主編、朱學(xué)勤、王麗娜著:《中華文化通志——中國(guó)與歐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頁(yè)。
(41)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編:《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41頁(yè)。
(42) 湖北省荊州地區(qū)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hào)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8頁(yè)。
(44) 司馬遷:《史記》卷40《楚世家》,中華書(shū)局1959年版,第1714頁(yè)。
(45) 徐恒彬:《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文物》1974年第11期。
(46) 云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duì)、四川大學(xué)歷史系:《云南省楚雄縣萬(wàn)家壩古墓群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文物》1978年第10期。
(47) 肖明華:《云南考古述略》,《考古》2001年第12期。
(48) 謝崇安:《云南石寨山文化與越南東山文化的比較研究》,《考古學(xué)集刊》2018年第10期。
(49) 后德俊:《楚國(guó)的礦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頁(yè)。
作者簡(jiǎn)介:陳鯤,湖北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講師,湖北武漢,430062。
(責(zé)任編輯 張衛(wèi)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