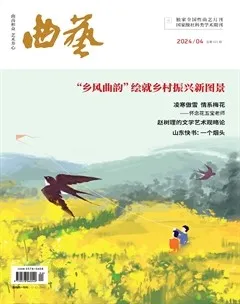凌寒傲雪 情系梅花
佀童強
2024年3月10日原是一個普通的周日,可下午兩點左右,我突然接到了花五寶老師女兒羅香的微信信息—“佀老師您好,老太太上午故去了。”看完這條微信后好久才緩過神來的我隨即以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習慣,在自媒體上發布了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很快微信公眾號“天津廣播”也發布了“痛別——梅花泰斗花五寶逝世”的消息:“天津廣播記者從花五寶老師親屬處獲悉,梅花大鼓前輩花五寶老師3月10日上午10點14分在天津家中安詳離世,享年101歲。”這段文字很快被眾多媒體引用。曲藝的忠實擁躉、曲藝廣播的編輯主持、梅花大鼓傳承者,這三重身份讓我對梅花大鼓有著非同一般的情感。從1998年現場觀看花五寶老師演出到今年,26年間老人家的藝術生平與言傳身教點點滴滴涌上了心頭。

對于北方曲藝來說,1923年是一個重要年份,因為小嵐云、桑紅林、石慧儒、馬滌塵、張伯揚、劉洪元、王殿英、郝艷霞、李國梁等藝術家都是這一年出生的。這一年的農歷五月二十五日,花五寶出生在天津。她本姓龐,很早就被過繼給姑母,也隨姑父改姓張。那個時候“梅花歌后”花四寶也是張家的養女,所以年幼的花五寶和已經名滿津門的花四寶成為了姐妹,并結下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親情。3月10日晚上我去吊唁老人家時聽她的保姆說,老人在臨終前一直在說“我四姐來了,我找我四姐”,可見花四寶在她心中的分量之重。而關于她與花四寶的感情,我們可以從她撰寫的《梅花歌后》中窺其全貌。
我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自幼就聽著收音機中的《每日相聲》《評書連播》等節目長大,十幾歲時又對各種鼓曲藝術產生了濃厚興趣,那個時候天津電臺的《曲苑大觀》節目每天播出,從那里我知道了駱玉笙、小嵐云、石慧儒、王毓寶等一系列鼓曲名家前輩,當然也包括花五寶老師。我記得當時花五寶老師經常帶愛徒楊云、安冰、王瑩等走進直播間和聽眾互動交流,尤其是她與喬月樓老師一起回憶喬清秀的專欄令我感動不已。花五寶老師收王瑩為徒、《梅花歌后》首發儀式、老曲藝家藝術團到臺灣交流演出……這一系列的曲壇佳話、大事也是我通過收音機知道的。
1998年,在知道了天津中華曲苑每天有鼓曲演出后,我的課余時間和零花錢就有了“歸宿”。同年,我國發生全流域型特大洪水。當時正值盛夏,天津曲協和老曲藝家藝術團在中華曲苑舉辦賑災義演,在那次演出中我第一次見到了花五寶老師的廬山真面,還見到了收音機中只聞其聲、未見其人的曲藝前輩張伯揚、闞澤良、喬月樓、郝艷霞、王田霞、王殿英、田立禾、魏文華。行文至此,我的心情依然激動。那一次義演由花五寶老師和她的弟子楊云擔任主持,老人家時年76歲,臺風穩健、衣著得體,聲音依然洪亮,雖然沒聽到她的演唱,但是能一睹斯人風采也令我非常幸福。
第一次在現場聽到的花五寶老師的節目,是她與闞澤良先生對唱的《韓湘子上壽》。老人家一句“到了這一天”“聲振屋瓦、鐵嗓鋼喉”,不僅讓全場掌聲雷動,也讓我對梅花大鼓是“文大鼓”的說法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從那時起只要有她的演出我一定要現場聆聽。藝術的滿足感有了,但疑惑也隨之而生:“這聲音是怎么出來的呢?”多年后這個疑惑終于有了答案。2002年,在花五寶老師學生付向榮的帶領下,我第一次走進老人家的寓所。見到偶像我不免緊張,但花五寶老師很和藹,寒暄過后直奔主題。
“你也會唱梅花大鼓?”“嗯。”“會什么節目?”“《(黛玉)思親》《(寶玉)探病》《王二姐思夫》《(黛玉)悲秋》,這些都是聽會的,沒有老師教。”“你唱一個我聽聽。”
當時我腦子嗡了一下,這是關公面前耍大刀啊!花五寶老師看出了我的緊張:“你唱幾句我聽聽,我給你說說。”花五寶老師的語言和藹真摯,我的緊張情緒消失了,戰戰兢兢唱出了“季秋霜重鴻雁聲……”,唱了幾句實在不能再唱了,因為實在太不好聽,我自己都聽不下去。
花五寶老師看著我說:“挺好,有嗓子,有點緊張。我告訴你,咱們這個梅花大鼓分兩派,一派是‘金派,一派是‘花派,我唱的‘花派以高音為主,‘金派以重低音為主。我小時候也是跟邱玉山師父先學的‘金派,后來跟盧(成科)師父和我四姐學改革后的‘花派。我沒有文化,也不識譜,就是老師教一句我學一句,你剛才唱的吐字不清,我告訴你用拼音唱,字就清楚了。”這段話是我第一次得到藝術家的教導。用拼音唱也是很多前輩名家多年來通過舞臺實踐得來的“金科玉律”,言簡意賅、通俗易懂,但彌足珍貴。從那時起我進一步揣摩梅花大鼓的演唱技法,后隨恩師劉嘉昌先生和周文如老師學唱的時候,二老在教學中也說了同樣的藝術理論。今天看來我是梅花大鼓青年傳承人中的幸運兒,竟得到了“金派”“盧派”(“花派”)兩派前輩的親傳。
從2002年到2024年的22年間,我與老太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了解了她的藝術人生、對梅花大鼓的執著追求和對學生弟子慈母般的呵護。對于她的藝術人生大家可以參閱老太太的專著《情系梅花》,下面我為大家介紹幾件老人家對我講的曲壇軼聞,和老太太演唱梅花大鼓的藝術心得,在紀念的同時,也期望留下第一手口述資料,為后世研究曲藝者作一些貢獻。
一、借鑒“程派”自成一家
熟悉曲藝的朋友都知道,老太太中青年時代演唱風格與晚年的相比有很大不同。中青年時代老太太以典型的“盧派”(“花派”)唱腔與花小寶、花云寶并稱為“梅花三鼎甲”。20世紀80年代之后她大量上演新節目并且在唱腔上大膽革新,形成了高腔聲如裂帛,低音幽咽婉轉、若斷若續的演唱風格。在與老太太聊天的過程中她告訴我,這種唱腔是借鑒了京劇名家李世濟的“程派”唱腔技法之后逐漸形成的,《黛玉思親》中“見黛玉氣息奄奄身體不動”就是典型——“見黛玉”唱完之后要吸足一口氣,然后一口氣緩緩唱出“氣息奄奄”,非常符合《紅樓夢》中對林黛玉病臥瀟湘館時病骨支離的描寫,也為后面賈母探病進行了鋪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以聲傳情、聲情并茂”,老太太每次唱這一句都會獲得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由此可見藝術工作者天賦、技巧、情感三者缺一不可,而老太太都做到了。除此之外,她還向我傳授過《鴻雁捎書》《別紫鵑》《王二姐思夫》等節目的演唱技巧。
二、門墻桃李競相爭艷
老太太少年從藝,青年走紅,1951年成為天津市曲藝工作團元老,1953年成為國營天津市曲藝團的主要演員,1987年又成為天津市藝術咨詢委員會的委員,在諸多身份轉換的過程中她一直沒有離開舞臺和講臺。20世紀50年代,老太太開始在天津群眾藝術館等地輔導業余曲藝演員,1958年天津市曲藝少年訓練隊成立后她又成為專業教師,史玉華的《歐陽海》《繡紅旗》等作品都傾注著她的心血。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老太太培養了籍薇、安穎、楊云這3位梅花大鼓主要傳人。她們最早都不是梅花大鼓專業,籍薇跟小嵐云老師學習京韻大鼓,安穎主攻鐵片大鼓,而楊云是以業余演員的身份從事多項曲藝曲種的演唱。1988年她們同一天拜師,這也是老太太第一次正式收徒。收徒儀式隆重,曲藝界名家悉數到場賀喜。老太太因材施教,悉心傳授,3位后來都成為了天津市曲藝團重要的梅花大鼓傳人,其中籍薇成就最高,現在是國家級非遺項目(梅花大鼓)代表性傳承人,天津市曲協主席,中國曲協第六、七、八屆主席團副主席。
安穎在20世紀80年代初改學梅花大鼓,在老太太、馬滌塵老師等的指導下進步很快。為了使安穎更快上手,老太太親自帶著她演出,師徒對唱過《半屏山》《鴛鴦抗婚》《傻大姐泄機》等曲目。后來安穎獨立演出,雖然嗓音條件與老太太不同,但是尺寸勁頭確實深得真傳,大家可以參考《探晴雯》中“怕別無端分兩地”一句。遺憾的是安穎退休之后幾乎沒有再登臺演出,在此我個人盼望安穎能夠再度出山奉獻自己的藝術。
20世紀80年代楊云與老太太結識。老太太總說她長得像花四寶,還曾經帶著楊云去花四寶故居憑吊,可見對楊云的情有獨鐘。正式收徒之后老太太對楊云嚴格要求、悉心傳藝。除了《老媽上京》等幾段冷活,楊云能唱大多數傳統梅花大鼓曲目,深得老太太藝術三昧。老太太得知楊云能唱京劇青衣之后,把《拷紅》進行大膽革新,融入了京劇唱腔。楊云用青衣唱腔演繹紅娘,而老太太用老旦唱腔演唱崔夫人,革新后的《拷紅》一經上演便轟動曲壇。楊云與老太太的關系情同母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相伴左右、隨同演出,天津電臺還專門制作曲藝專題《瞧這娘兒倆》。老太太每每提到自己的愛徒楊云,臉上都會洋溢出欣慰的笑容。
安冰是1987年老太太親自選定的學生。老太太是中國北方曲藝學校梅花大鼓專業教師,安冰報考后就在她的認真教學下刻苦學習,在學校期間就受到廣大曲藝愛好者的喜愛。老太太認為安冰是個好苗子,所以在安冰臨近畢業的時候告訴她,最好留在學校任教,以繼續傳授梅花大鼓藝術。安冰也不負期望,在畢業后的近30年間培養了眾多的梅花大鼓后學傳人。
安冰是與孿生姐妹趙席佐、趙席佑同時拜老太太為師的。拜師儀式當天馬三立、王毓寶、丁元、劉瑞森、王濟、張昆吾、孫福海等眾多曲藝界同人參加,馬三立先生還發表了熱情的致辭,稱老太太為“五姐”,說“五姐今天收了3個好徒弟,我向她祝賀”,并題詞“五寶梅花大鼓,堪稱碩果僅存,絕妙優雅音韻,曲壇德藝雙馨”。
王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跟隨老弦師謝瑞東學習,后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老太太。老太太發現王瑩的嗓音條件與自己相似,便在收徒之后對她所會的節目二次加工(曲藝界稱為“重新下掛”)。很快王瑩就在天津群眾文化系統舉辦的各種曲藝賽事中摘金奪銀,作品被天津電臺、電視臺錄制播出,還舉辦個人專場,出版個人演唱專輯等。王瑩的藝術成就與老太太的培養密不可分。
楊菲是老太太眾多弟子中年齡最小的,因此在她當初拜師時同行有異議,說楊菲年齡太小。但老太太還是力排眾議,收楊菲為徒。當年老太太親口對我講:“楊菲這個孩子我喜歡,她孝順。當時我的老伴去世的時候,楊菲正在曲校跟我學習,她就在我家門口站著。我問她你為什么站在門口啊,楊菲說我怕您害怕,想陪陪您。這個孩子有心,從來不張揚。我收徒弟就得聽我的,有更多的演員學習咱們的梅花大鼓這是好事,再說楊菲確實是我一字一句教出來的。”楊菲拜在老太太門下后第一次正式亮相于2005年2月24日在天津音樂廳舉辦的“紀念花四寶誕辰九十周年梅花大鼓專場”,師徒兩人演唱了《黛玉思親》。后來楊菲加入北京曲藝團,多年來成績斐然,由此可見老太太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藝術家和教育家。
除了眾多女弟子,老太太門下還有兩位業余的梅花大鼓男弟子,他們分別是來自臺灣的周象耕與天津的退休干部劉文虎。老太太毫無門戶之見,更絕不藏私,除了在天津市曲藝團和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培養專業演員,很多業余演員向其問道求藝,她也是毫無保留。兩位男弟子就是蒙受老太太教誨,于梅花大鼓藝術上頗有造詣的“業余組”代表。劉文虎的拜師儀式是我主持的,當時老人家說,“文虎有嗓子,有文化,他很多節目都是跟我學的,現在他還弄新節目,我鼓勵他。”劉文虎拜師之后推出的梅花大鼓的《劍閣聞鈴》(與郭小霞版本不同)《伯牙摔琴》《琵琶行》等曲目都曾在天津業余曲壇上演。
在眾多正式拜師的弟子之外,天津市曲藝團的張雅琴、王喆、李麗等和女兒羅香也曾得到過老太太的親傳,他們也是梅花大鼓藝術傳承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專場演出名傳四方
在“盧派”(“花派”)梅花大鼓傳承體系中,盧成科先生的弟子以入門先后排序,為花四寶、花五寶、花小寶(史文秀)、花云寶(齊俊英)、周文如、花銀寶、丁慧寶(丁士儒)、花蓮寶(劉淑一)。由于花四寶英年早逝,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花五寶就成為了“盧派”(“花派”)梅花大鼓的第一傳人,也是梅花大鼓藝術生涯最長的一位,在行業內備受尊敬。她將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史,幾乎就是半部天津曲藝史。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她參加了天津各個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曲藝演出,如1957年天津第一屆曲藝雜技會演大會、從1962年開始的歷屆津門曲薈、老曲藝家專場、天津市曲藝團多次團慶、天津市藝術研究所舉辦的梅花大鼓錄音專場等。除此之外,老太太還領銜參與多次梅花大鼓表演專場,見于史料的就有1990年8月17日、18日在天津中華曲苑舉辦的“花派”梅花大鼓展覽演出,2005年2月24日在天津音樂廳舉辦的紀念花四寶誕辰九十周年梅花大鼓專場演出,2011年6月16日在北京舉辦的梅花大鼓專場演出,2015年6月9日慶祝她從藝八十周年的梅花大鼓專場演出等。這些演出她均和弟子學生傾情參加,天津電臺都保留了當時的演出實況錄音。這些專場的成功舉辦,既是文化部門和廣大曲藝愛好者對她藝術成就的肯定,也是她教學成果的集中匯報展示。
四、耄耋之年心系梅花
我從2004年進入天津人民廣播電臺從事曲藝節目的編輯與主持工作,2014年開始在“天津文藝廣播”頻率策劃《曲藝晚霞錄制工程》欄目,并在2014年至2016年集中約請天津、北京的曲藝名家和名票參加錄制,花五寶、王毓寶、王大寶、劉寶光、鐘吉銓、劉嘉昌、朱鳳霞、章學楷、張雅琴、劉志光、張幗英等都積極響應。一晃20年過去了,很多前輩都已作古,這些節目資料就成為了研究他們藝術體系不可多得的珍貴素材,也是后人學習曲藝藝術的參考資料。此處我給大家介紹一段給老太太錄音的幕后花絮。
2015年,老太太當時已經92歲高齡,為了保存資料,我試探性地詢問她的女婿劉志光老師:“老人家能否給我們電臺錄一段資料?”我很快收到了劉老師的肯定答復。欣喜之余,我考慮到老人家年事已高,決定盡量精簡時間,提高錄制的效能,遂邀請老太太和她的女兒羅香共唱一曲。因為老太太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天津人民廣播電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河北人民廣播電臺等眾多電臺錄制過數不勝數的傳統、現代曲目,進入新世紀后又不斷出版音視頻資料,所以我到了老太太家中商量錄制曲目時,與她共同選定了傳統曲目《杏元合番》。該曲目是老太太的代表曲目之一,楊云、安穎、安冰等也都擅長此曲。但老太太親唱的音像資料,當時只有1935年勝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定好曲目后老太太又約請胡子義、孫家俊、劉志光3位組成樂隊進行排練。雖然只是錄音,但老人家仍然以正式登臺演出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2015年6月17日晚,正值盛夏,老太太一身夏季的旗袍,戴著她標志性的白手套和墨鏡,妝容得體、精神矍鑠地來到電臺。老太太先與女兒羅香排練了一遍,到正式錄制的時候忽然跟我說:“一會錄的時候,你替我打鼓吧。”聞聽此言我既激動又緊張,“能為偶像打鼓當然榮耀,但我能勝任嗎?打不好就把老太太的錄音攪了!”我說出了心中的顧慮,老太太說:“你打吧,我現在腿不好,得坐著唱。羅香第一次錄音,我怕她緊張。我聽過你打鼓,打得挺好的,你打吧。”得到了老人家的鼓勵和“授權”后,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與3位樂隊老師順利完成了相應的錄制工作。老太太去世之后,我在節目中制作紀念專題,再次播出這段《杏元合番》。往事涌上心頭,我久久難以平靜。
五、幾代名弦輔佐一生
老太太從藝近一個世紀,把梅花大鼓從大陸唱到臺灣,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促進了海峽兩岸的藝術交流,擴大了梅花大鼓藝術的影響力。她生前不止一次對我講,自身的藝術離不開好樂隊的伴奏。的確如此,筆者在編纂《天津曲藝史》的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史料,并結合天津電臺的錄音記錄單和相關口述,梳理出了為老太太伴奏的弦師的人物譜和時間表。
20世紀40年代初,盧成科先生親自操弦,奠定了花四寶之后老太太在梅花大鼓藝術界中的重要地位。20世紀50年代,換由盧成科先生的親傳弟子謝瑞東、鐘吉瑞和名琴師李默生為老太太伴奏。老太太告訴我,當時她和小彩舞(駱玉笙)用一堂樂隊,除了三弦,胡琴、琵琶都一樣。“謝瑞東和(鐘)吉瑞我們都是從小就在一起,彼此都很熟悉,我的《杜十娘》《傻泄》《合缽恨》《拷紅》等新節目都是他們和我一起排練的。謝瑞東在唱腔設計上給我很大的幫助,后來曲藝團的盲人不能上臺了,他到學員隊教學,我的徒弟史玉華跟他學了很多段子。”
20世紀60年代初謝瑞東不參與伴奏之后,李默生放下琵琶拿起三弦,鐘吉瑞、矯恒謹輪流拉四胡,琵琶手則由當時的學員王福元等擔任。這一時期中國唱片社錄制發行的唱片《繡紅旗》《寶玉探病》《琴挑》和天津電臺錄制的《千里堤送別》《銀環探監》等就是由李默生、鐘吉瑞、矯恒謹、王福元擔任伴奏的。
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20世紀90年代初,老太太在藝術巔峰時期廣收門徒,并不斷整舊創新。她這一時期的伴奏樂隊主要由老弦師馬滌塵先生,還有她的晚輩矯恒謹、馬健、石俊屏、祖金華、王桂玲、黃菊生等組成。這些樂師中,馬滌塵先生是一位改革家,精通北方各個曲種,為老太太的改革創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她的弟子史玉華、安穎、楊云、安冰等也得到過馬滌塵先生的指點。老太太1986年進入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任教,馬滌塵先生又成為了她的好助教,兩人是紅花綠葉、相得益彰。馬滌塵先生去世多年之后老太太還會時常提到這位藝術上的合作伙伴。
馬滌塵先生去世后,劉玉璽、劉志光、胡子義等擔任過花五寶老師的三弦伴奏,鐘吉銓、矯恒謹、孫家俊主要擔任四胡伴奏,劉志光、祖金華等擔任過琵琶伴奏,宋東安擔任過揚琴伴奏,民樂教育家黑連仲擔任過琵琶和大阮的伴奏,這些伴奏名家為老太太70歲之后的藝術成績作出了貢獻。她與闞澤良先生于1996年組織的老曲藝家藝術團成立后推出的一系列對唱節目,都離不開劉玉璽、劉志光、鐘吉銓、矯恒謹、宋東安、黑連仲等的大力支持。
對于和樂隊的合作,老太太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咱們演唱和樂隊是魚和水的關系,必須互相尊重,私底下必須認真排練。人家都知道我脾氣不好,但是在藝術面前人人平等,誰說的對聽誰的,我在藝術上從不自私。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則,在我演唱敘述的時候絕對不能大聲,那樣容易影響我的情緒,也影響觀眾對劇情的了解,因為梅花大鼓有‘三番兒(大段的間奏),在‘三番兒的時候你必須得‘亮范兒,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作品。所以不管是謝瑞東、馬滌塵還是后來的劉志光,他們對我的唱腔特別了解,給我伴奏我唱著特別舒服,尤其是劉志光,他既是我的姑爺又是我的樂隊,我們娘兒倆經常排練。我把我唱腔的小地方都告訴他,我90多歲還能上臺唱,多虧了他的幫助。”
我最后一次與老太太見面是在2023年7月12日,當天是她的百歲壽辰。我帶著賈檸砜、任洽兩位曲藝后學為老人家拜壽,雖然生病,但老太太依然精神矍鑠,看到我的時候還能說出我的名字。當時在場的楊云提議給老太太唱一段節目祝壽,賈、任兩位青年率先演唱了梅花大鼓傳統吉祥曲《指日高升》,老太太聽完后馬上指出“膽大猿猴”的唱腔不對,并親身示范。這種對藝術的嚴謹和熱愛讓在場的所有親友感動不已。最后老人家與我們共同演唱了《十字西廂》,在梅花大鼓旋律中度過了她的百歲壽誕。
斯人已去,心中千言萬語匯成這篇小文,謹表達我對這位世紀老人萬千分之一的懷念和追憶。
(作者:天津海河傳媒中心編導)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