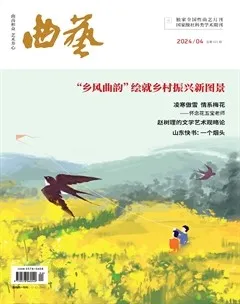趙樹理的文學藝術觀略論
杜學文
趙樹理先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作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曲藝事業最重要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他對曲藝充滿熱情,非常關注,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他關于曲藝的觀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趙樹理的文學成長之路
乘著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東風,一大批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新文學作品蓬勃問世,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趙樹理開始創作的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大批優秀的新文學作家以優秀作品不斷拓展著新文學的影響力。而在蓬勃發展的同時,新文學也面臨著急需解決的“文人圈子”的問題。如果這一問題不能被解決,則新文學的影響力、創造力與生命力都將受到制約。因此,讓文學成為人民的文學而不僅僅是文人的文學既是時代的考驗,也是讓文學真正成為民族的、大眾的文學,真正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接受、喜愛的歷史任務。

趙樹理所在的上黨地區位于太行山深處,山高溝深、交通不便,但存留有豐富的神話傳說、戲曲民樂、宗教禮儀、民間藝術等。它們是當地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僅喜歡這些藝術,同時也是這些藝術的創作者、表演者、參與者。如趙樹理的父親就是當地“八音會”的重要成員。在這樣的環境中,趙樹理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鄉土文化的“小小的創造物”,各種樂器無師自通,吹拉彈唱樣樣能來,并對民間說唱藝術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貼近百姓、貼近生活的表達才能吸引人。在飽受民間傳統文化熏陶后,趙樹理還深刻接受了新文化的浸潤。特別是在長治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讀書期間,他與進步青年王春等往來密切,閱讀了大量的新文學作品,甚至在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時被當局搜捕、驅逐。總的來說,此時趙樹理是以一個新文學青年的形象出現的,作品也有較為鮮明的新文學痕跡,如《悔》《白馬的故事》等小說均是以心理活動為作品的結構線索的。
這些作品并不強調敘述與情節,也不強調人物的行為。趙樹理對人物心理感受的描寫,以及憑這種感受來展開敘述的手法相當熟練,風格與新文學初期的作品非常相近。據此筆者猜測,此時的趙樹理認為,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是具有新意的,是順應時代潮流的。
但是,趙樹理很快就改變了這種寫作手法。他在給老鄉們朗讀新文學作品時,并沒有受到大家的稱贊。他們還是喜歡《七俠五義》之類的“舊”作品。這對趙樹理觸動很大。從此,趙樹理立志不上“文壇”,而是要進“文攤”,寫那些內容進步且被老百姓喜歡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時期內,趙樹理在被抓捕與流浪中徘徊。雖然受到了許多進步人士的幫助,卻在很長時間內沒有穩定的職業,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直至全面抗戰爆發,參加了犧盟會后他才重新找到了方向。這期間,他一直在創作具有通俗風格的作品,如《蟠龍峪》《打卦歌》《有個人》《糊涂縣長》等,大約有數十萬字。他還和王春等組建了通俗化研究會,發表了多篇討論“通俗化”的文章,明確提出“通俗化”不僅僅是抗戰動員的宣傳手段,還要擔負起提高大眾的任務,是文化和大眾之間的橋梁。
就中國新文學而言,抗日戰爭是其蛻變演化的重要社會背景。這一時期,眾多的作家、藝術家投身抗戰,或在前線直接參加戰斗,或到前線慰問采訪。作為敵后抗戰的主戰場,山西匯集了大批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們在山西活動期間創作了大量作品,在風格上都表現出突出的時代特色—關注中國的命運,表現抗日戰爭中英勇殺敵的八路軍,以及開赴前線的將士之戰斗生活。在創作手法上,這些作品更直接、更明曉、更具戰斗性,因而也更具吸引力、號召力。它們集中地顯現出中國新文學的轉變—從接受西方外來手法向本土傳統的回歸。這也為中國新文學進一步實現民族化、大眾化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當時中國文藝的諸多重要問題進行了闡釋,論述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為創作指明了方向。這些論述也從理論上肯定了趙樹理的探索、努力。用趙樹理的話來說,就是“批準”了自己的寫作之路。之后,《小二黑結婚》面世,《李有才板話》《孟祥英翻身》等先后發表。稍后,《白毛女》《兄妹開荒》等也受到了群眾的廣泛喜愛。
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是中國新文學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識之一。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學創作者很少將筆端對準農民,把他們當作被社會尊重并具有自主意識的人物來描寫。即使是魯迅先生,也只是深刻地揭示出他們的麻木和無望。而恰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建設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中,趙樹理發現并塑造了小二黑、小芹,以及李有才等覺醒了的中國農民形象。此后中國文學中覺醒的、成長的農民形象不斷出現。他們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中具有明確自主意識的“中國人”形象。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趙樹理的出現正是他的創作與時代要求,包括社會文化自身演變的契合,是時代造就了他。尤其需要注意趙樹理藝術修養中傳統藝術的作用,正是他自覺地使用包括曲藝在內的優秀傳統藝術的表現手法,才使自己的作品受到了廣泛的歡迎,進而推動了中國新文學向民生化、大眾化的轉化。
二、趙樹理的藝術理念
在趙樹理的創作中可以看到傳統藝術,當然也包括傳統曲藝形式的影響。他使用了曲藝的手法來組織作品、敘述故事,如《李有才板話》便是直接運用了“板話”的形式。《小二黑結婚》雖然是小說,但也明顯受到了評書的影響,或者說借鑒了評書的敘述手法。
評書刻畫人物講究“開臉兒”,創演者要根據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思想面貌,勾畫出他們的相貌特征和氣質風度,給受眾留下鮮明而深刻的印象。而《小二黑結婚》中,思想與行為與常人不同,往往表現出某種滑稽、乖戾特點的“神仙”“二諸葛”與“三仙姑”,美麗、質樸的農村姑娘小芹,以及地痞無賴金旺兄弟,都具有十分明顯的角色特質和性格特征。金旺兄弟對小芹垂涎已久,而小芹對他們并不感冒卻喜歡殺敵英雄、特等射手小二黑,如此形成的矛盾、博弈賦予作品評書“扣子”的特性的同時,也將作品帶入了核心敘述情節。小芹與小二黑被“捉奸”,送到了區里。表面看來,金旺兄弟的圖謀快要得逞了,但也恰在此時,這道“扣子”解開,因為共產黨倡導婚姻自主,打擊惡霸地痞,金旺兄弟反而被區里扣押起來。小二黑與小芹的愛情得到了社會的支持。
整體來說,趙樹理為《小二黑結婚》設計了非常有趣的情節,一波三折、起伏跌宕,拴解“扣子”之間牢牢抓住了受眾的心。從具體描寫來看,作家在刻畫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時使用“擺砌末子”的手法,大量生動準確的細節讓不同的人物形象更為立體、生動。更重要的是,小二黑與小芹的故事符合當時社會條件下人們的價值追求、心理期盼,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與社會的進步,有著鮮明的價值,也符合評書這種曲藝藝術“勸人方”的特質。
總的說來,趙樹理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并借鑒評書、鼓詞等曲藝藝術的創作、表現手法,對新文學進行了積極的革新創造,形成了自身新的、深受民眾喜愛的創作風格。
盡管趙樹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作家,但他并不以“作家”為傲。他更注重的是如何寫出讓老百姓,特別是農民群眾喜歡的作品。他衡量作品的重要標準就是老百姓的滿意度。只要對他們有益,受他們歡迎,趙樹理就可以使用不同的藝術手法來創作,如評書《靈泉洞》、澤州秧歌《開渠》、唱詞《王家坡》、鼓詞《戰斗和生產相結合》等。他創作的高平鼓書《谷子好》在今天仍然深受人們的喜愛,在各種場合被傳唱。
趙樹理之所以投入很大的精力創作曲藝作品,與他的曲藝觀有著根本的聯系。
首先,趙樹理認為曲藝是非常重要的藝術形式。他并不因曲藝短小、面向民眾、形式簡單就輕視,而是將曲藝看作承繼中華文化傳統、具有深厚群眾基礎的“曲高和眾”的高級藝術,其中的唱詞中有中國詩歌的傳統,評書評話則與中國小說的底層邏輯相通。他認為,把曲藝“提高”成西洋的東西,把曲藝“提高”成歌劇,是不對的,曲藝是可以誕生偉大的作品的。“像董解元的《西廂》原本就是唱詞,它的藝術價值是很高的。”
其次,趙樹理認為對曲藝要開展完備的整理、傳承工作,把曲藝遺產中的優秀部分整理出來。他在《運用傳統形式寫現代戲的幾點體會》中比較系統地談了這方面的意見,認為在傳統形式中存在著極具生命力的東西。如設計題材編造故事,目的是突出人物;故事的結構務求集中,在短時間內達到最多的效果;伏筆要伏得穩,伏得正常,自自然然才好等。他認為在曲藝中隱含如此豐富的藝術滋養,可以解決創作中的許多問題。這些論述也可以看作是趙樹理創作經驗的總結。
雖然已經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但趙樹理從來沒有認為自己的創作有什么可以驕傲的。面對曲藝,他仍然認為自己還沒有很好地把握其中的精髓。有些人物沒寫出來;寫舊人舊事得心應手,寫新人新事就不那么生動。他曾說,我寫過一些東西,但每聽一次好的說書,總感覺自己趕不上它。中國的評書藝術,有許多完整的東西、深刻的東西,“我還要全面地學習”,多吸收一些說書、話本的優點。
趙樹理認為文學、電影、戲劇等文藝作品都可以改編為曲藝作品,并積極踐行這一理念。1950年,他就把田間的長詩《趕車傳》改為鼓詞《石不爛趕車》,并在《說說唱唱》上發表。這種改編不是為改而改,而是要提供更多既受老百姓歡迎,又具有新思想、能夠表現新生活的曲藝作品。
趙樹理不僅身體力行改編、創作,還努力為他人的創作提供幫助。作家陳登科的處女作《活人塘》,初稿中有很多錯字和不會寫的字。但趙樹理認為這部作品的基礎非常好,便幫助陳登科修改后發表在《說說唱唱》上。山西的作家秦懷玉創作了《考神婆》,趙樹理幫助他改寫、完善。他還到燕京大學中文系講授說唱文藝課,每次都要請一位著名的曲藝表演藝術家來配合演出,使課堂的理論與表演的實踐生動地結合起來,受到了大家的歡迎。讓更多的人喜歡上了曲藝,有更多的作家愿意為老百姓寫作曲藝,是他最期待的事情。
三、趙樹理對人民的情感
文學藝術是表現人的情感的。作家、藝術家的情感立場對作品至關重要。趙樹理出身于普通農民家庭,經受過被欺壓、被迫害的人生。在他的思想深處,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抵抗,和對社會底層人民的同情、尊重。改變落后黑暗的社會現實,目的是要讓更多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所以他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后,又再次加入共產黨。他知道要改變社會,必須首先改變人,改變人的精神世界。在接受新文化的影響后,趙樹理努力探索、尋找能夠對普通民眾產生積極影響的進步文化創作道路。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至20世紀 30年代,趙樹理一直探求形成大眾喜愛的、具有新的思想內涵的審美形態的有效方法。但這并不容易。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從理論上解決了令趙樹理迷茫的許多問題。心里踏實了,他的創作也呈現出極為旺盛的態勢。不過,他并不是要成為一個“著名”的作家,而是要為老百姓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相較于小說,戲曲是老百姓喜歡的藝術形式,于是他也創作了大量的戲曲作品。戲曲雖好,但畢竟是“大戲”,演出需求相對較高。相較之下,能隨時隨地說說唱唱的曲藝更能滿足老百姓日常的精神需求。一人兩人也可,三人四人也行;可說可唱,可吹可彈;炕角場院不局促,田間地頭也能聚人。曲藝的這種呈現形態是趙樹理重視曲藝,并為中國曲藝事業奔走呼號的重要原因。
人們都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趙樹理創作的視角。他與一般的作家、藝術家不同,不是用“我”來觀察“你”、描摹“你”,而是把“我”當成“你”,寫“咱們”的事。所以他創作的作品中,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他不會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來“教化”或者“啟蒙”別人,只是把新的思想、生活、觀念注入老百姓喜歡看、愿意聽的藝術形式中,使老百姓感到這是自己的藝術,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傳播與時代要求一致的價值、情感和生活方式。這種創作觀能非常充分地反映出趙樹理的情感立場——他不認為自己是“作家”,而認為自己是“鄉親”;他不是寫給與自己不同的“他們”的,而是寫那些與自己一樣的“咱們”的。他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愿望”:到鄉親們中間去。在北京期間,他總是不斷地回到家鄉,以至于終于放棄了北京的工作,捐出了北京的房產,調回山西。這是他內心的選擇,而不是權宜之計。他是那種在北京看到下雨,就會想到地里莊稼不旱了的人,想到農民可以多打糧食的人。與人民群眾在一起,是他的內心必然,是一種“情不自禁”的狀態。所以他強調,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要服務得好,一定要拿起筆來就想到這是為誰寫的,要讓人喜歡,讓人接受。
正是這種“情不自禁”的情感狀態,把趙樹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打成了解不開、扯不爛、剪不斷的“死結”,成就了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家、藝術家、曲藝家。他不僅自己常常到農村去,而且勸女兒趙廣建到農村工作。他不僅在創作的時候會考慮農民群眾的心理愿望,而且在自己的書出版時也會考慮到農民的購買力。他寧愿自己少得版稅,也要讓更多的農民群眾買得起書。他愿意當老百姓的“學生”,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工作、生活中那些積極的東西,包括民間藝術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同時,他也不放棄自己的責任,也要當“先生”,把進步的、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價值觀、生產生活方式,以及藝術表達形式與審美觀等帶給老百姓,通過塑造新的人物、表現新的世界,讓更多的老百姓在欣賞藝術的同時提升自己、改變自己、得到進步。
(作者:山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