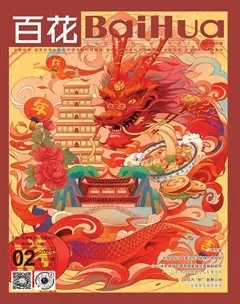陜西關中民居石刻藝術更迭與傳承研究
孫亦凡



摘 要:陜西關中位于黃河流域,素有“八百里秦川”的美譽,是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使關中形成了豐富的傳統民居建筑,也孕育了關中民居特有的建筑文化。民居建筑中的石刻藝術正是在這種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因素影響下形成并發展的。在關中民居院落空間中無不體現著石刻的藝術與語言,本文在關中民居石刻的歷史文化視角下,對石刻的裝飾類型應用與技藝手法進行闡釋,通過了解關中石刻藝術的更迭與演進,實現石刻藝術在當下的保護應用與價值體現。
關鍵詞:關中民居;石刻藝術;裝飾類型;保護傳承
一、關中民居石刻的民俗歷史文化背景
(一)自然環境因素
關中位于陜西省中部,屬暖溫帶半干旱半濕潤氣候,地處亞洲夏季風邊緣,北靠黃土高原南臨秦嶺,是我國南北與東西的地理樞紐,其地層出露齊全,礦產資源豐富,為關中民居建造提供了豐富的原料基礎。關中地區自西向東長約360千米,為西窄東寬近似月牙形的盆形區域。渭河貫穿其中部,將其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受到河流不斷沖刷、地形的高差、泥沙的沉淀等因素影響,關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以河流階地和黃土臺塬為主的地貌特征。渭河兩岸的沖積平原地勢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氣候適宜,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吸引了歷代人口的聚居。隨著時代發展,基于當地居民的世代積累與傳承,關中傳統民居在特有的材質機理下形成了本地特有的風格,民居建筑裝飾構件上也更為變化多樣、風格迥異。以磚石雕刻建筑藝術構件為載體的石刻類型應用也形成了本土獨有的特征。關中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悠久的歷史和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結合民間藝術家和工匠們的聰明才智,為陜西關中傳統的磚石雕刻裝飾圖案以及中國傳統民居雕刻裝飾的蓬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1]
(二)人文歷史因素
距今約20萬年前,關中地區就有人類活動聚居的痕跡,這里擁有眾多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其中在半坡遺址房屋柱腳側部斜置的扁礫石就是柱礎石的原型。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距今約5000~7000年,這說明柱礎的出現至少也有五六千年的歷史。[2]關中自古以來就是富饒之地,“八百里秦川”先后有十三個朝代建都于此,歷史文化底蘊濃厚,影響深遠。
優越的地理條件讓關中地區成為古代的天然糧倉,關中地區借助山川河流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歷史。首先,關中地區利用渭河平原優越的自然條件,形成穩定的農業經濟,發展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并通過其影響力促使文化輻射周邊。關中地區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利用地理區位優勢長期處于安定的自然環境中,民俗藝術中表現出質樸、細膩、儒雅的區域文化特質。其次,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關中是古“絲綢之路”的發源地,這就有了不同地區宗教、習俗、文化的融合,各類文化在本土建筑藝術風格上兼容并進,外域的人物、動物形象出現在雕刻藝術上。再次,不同時期的文化反映在關中石刻藝術表現中,體現了陜西關中地區典型的美學思想,以及深厚、鮮明的地域文化。唐朝以后磚石雕刻逐漸成為民居建筑藝術的主流之一,它的發展規模及趨勢使其技藝愈加完善。明清時期民居建筑石刻工藝更為純熟,以至成為一些大戶人家不惜成本裝點門面的必備之物。最后,關中沉穩的政治環境和民間的粗獷民風互相交融,隨著時代演進與發展,在人們的心里逐漸沉淀,形成關中特定的穩重、豪氣、嚴謹、自由、和諧、剛毅的民居建筑風格,從民居建筑整體到磚石雕鑿細節無不體現著由淳樸到驕奢,到達鼎盛,最終又回歸到淳樸的演變與遞進。
二、關中民居院落石刻裝飾類型與技藝手法
(一)石刻裝飾類型及載體
關中地區石刻藝術既有深遠的文化內涵又具有當地的民族文化認同感,隨著時代不斷發展,石刻裝飾藝術也具備了一套完善的體系。無論是從其表達對象、本土文化及外來文化的多元融入上,還是從題材、造型及技法的純熟程度上,都使關中民居石刻藝術名揚天下。這也形成了以門枕石、柱礎、拴馬樁、上馬石等建筑構件為載體的石刻裝飾藝術。門枕石類型豐富、形態各異,主要在民居建筑中起到驅邪鎮宅的作用。關于門枕石的起源說法不一,根據建筑結構與技術發展的歷史規律,門枕石在脫離了原始穴居以后逐步發展形成,至少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時期就已經出現。[3]門枕石按照民居建筑等級可以大致劃分為門獅、抱鼓石、門墩。它們的造型以及雕花圖案主要象征門第富貴,同時也有吉祥避邪,祈求多子多福、歲歲平安的含義。關中民居多以木柱為主要承重結構,為了防潮其下端往往加設石質柱基,柱基造型豐富、題材廣泛,呈兩至三面,用于門廊或獨立造型表現,外部輪廓用回紋、云紋、卷草等富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石刻紋樣,給人以含蓄內斂、嚴謹莊重的藝術感受,石刻造型形態逼真、生動細膩,獨具藝術表現力(圖1)。關中地區受經濟貿易往來和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許多大戶人家的民居建筑外部常設置拴馬樁以及上馬石,這不僅具有實際作用還象征著宅主的財富與地位,另外,這也被賦予了鎮宅驅邪的意味。關中民居石刻的裝飾造型與紋樣不僅體現了匠人們的智慧以及技藝的高超,還體現了關中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與探索,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活化石”,也是精神文化與物質功能融合的產物,對弘揚和保護本土民居建筑具有歷史性的研究意義。
(二)關中民居石刻的營造技藝手法
關中民居石刻材料就地取材,多運用秦嶺石、青石等石材。關于石刻手法,《營造法式》規定共有四種,即剔地起凸(高浮雕及圓雕)、壓地隱起(淺浮雕)、減地平钑(平面淺浮雕)和素平(平面細琢)。[4]
1.浮雕
浮雕既有繪畫藝術的平面感又具有雕塑的立體感,同時又利用光影,加之工匠高超的匠藝,作品往往精巧靈動、層次感強。此類手法在關中民居中應用廣泛。關中民居建筑中的拴馬樁柱身雕刻、入口照壁的雕花等都運用了浮雕技法,題材豐富,寓意祥瑞(圖2)。
2.線刻
線刻運用以陰陽兩線結合找形的雕刻手法,往往與浮雕聯系緊密,線刻石浮雕也稱“石刻畫”,類似漢畫像石表現手法,在關中最具代表性的拴馬樁、抱鼓石等石刻載體上都有所體現。線刻所呈現出的卷草紋、水云紋、回紋等裝飾紋樣更加突出了石雕作品所要表達的主題,石刻作品生動形象耐人尋味。
3.圓雕
圓雕又稱為“立雕”,通常可分為單體圓雕和復合圓雕兩大類,是一種可以多維度呈現的藝術表達形式。觀者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去欣賞和品鑒石刻作品。關中民居建筑中的圓雕主要應用于某一雕刻作品的局部,如拴馬樁的樁首部分尤為精彩,主要由獅、人、猴或人與動物的混合造型構成,其形態各異、惟妙惟肖,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獅子或馴獅胡人為主的造型(圖3),這也是在拴馬樁表現題材中數量位居前二的造型。其中獅子蜷曲扭動的形態和表情都雕鑿得栩栩如生,人物的體征神態、衣紋服飾等刻畫得細致入微,也凸顯了圓雕更具備細節表現這一特點。
關中民居中的各類石雕構件往往綜合應用了上述多種表現手法,完美呈現所選題材,從而造就關中民居獨特的石刻文化。
三、關中民居石刻藝術的更迭與演進
(一)關中地區自身的文化演進
關中地區的文化建立在當地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秦漢時期大量的陵墓石刻藝術反映出浮雕和線刻技法已發展得十分純熟,不同時期的石刻作品反映了特定時期的生活、社會特征,留下獨特的歷史符號。關中民居石刻藝術以民居建筑構件為基礎,多體現在民居石構件應用方面,其代表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柱礎、門枕石與拴馬樁。建筑石雕的需求為石刻藝術的展現提供了舞臺,典雅細膩的技法表現也反映了關中地區的美學思想,在工匠的手下這些石刻藝術跨越千百年仍生生不息。
民居中柱礎作為最早出現的石刻品,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期,先秦時期大多用鵝卵石作為柱礎;秦代開始已有用整顆石頭作為柱礎,簡單的柱礎做成素面的方形或鼓形;漢代已有類似覆盆、覆斗等樣式的柱礎,但形態仍較簡單;佛教傳入后為關中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在原本的柱礎形態基礎上又增添了人物、獅獸、蓮瓣等形態,既反映了文化的多樣性又展現出石刻技術的進步。柱礎不僅在形態上有所變化,在飾面上關中的匠人還增添了多樣化的題材,如麒麟、人物、蝙蝠,表達了家宅安康、闔家幸福等美好樸素的愿景(圖4)。
關中民居石刻藝術的代表之一便是豐富多樣的門枕石。門枕石原本是古建筑中以支撐院門穩定的支撐結構,在脫離穴居時代后,門枕石便逐步發展形成。民居建筑多因地取材,因此關中民居建筑以木柱為主要支撐,且為保持木材的穩定與防止雨水侵蝕,又多以石制品做基礎。門枕石造型各異,豐富多樣,為關中民居中辟邪鎮宅的象征,不同身份等級的住宅,也能通過門枕石來劃分。關中民居門枕石中抱鼓石缺乏元代的記錄,明代的抱鼓石以元代的造型為基礎,融入自身時代的特征,清代則基本上以繼承明代為主,并融入自身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圖5)。
在三類石刻藝術中拴馬樁是關中獨有的石刻品。目前最早的是陜西關中民俗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拴馬樁,拴馬樁的分布反映了具體時代的社會現狀。關中渭北地區是陜西歷來較為發達的區域,因其與山西、河南兩省相接,大量的商路、貿易都曾匯聚于此。宋代政治中心南移,民間石刻藝術在關中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宋元時期,關中貿易活動頻繁,馬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隨著商業活動的增加,拴馬樁數量隨之上升。受元、清兩個游牧民族的文化影響,拴馬樁石刻藝術也更加被大范圍接受。至民國時期,受工業革命影響,馬匹逐步被汽車取代,拴馬樁石刻藝術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二)外來文化的傳播與浸染
外來文化是在關中文化演變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自漢代絲綢之路起,唐代對外的貿易往來,宋代之后政治中心南移,游牧民族文化大量入侵,關中文化與外來文化無時無刻不在歷史中融合與碰撞。
以陜西最具有代表性與獨特性的拴馬樁為例,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關中地區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與貿易中心,域外文化不斷涌入,它們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拴馬樁中有大量形象以“胡人”為造型,“胡人降獅”造型的拴馬樁說明了游牧民族的精神特點與關中文化的進一步融合,因此形成了獨特的關中石刻藝術。
元代關中地區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各類文化逐漸與關中文化融合并沉淀,在時間催化下,至明清逐漸形成展現于石頭上的雕刻技藝,成為石刻藝術。關中民居中的石刻藝術體現了關中及陜西地區典型的美學,同時又展現出跨越時代民族文化融合的思想。[5]
四、關中民居石刻的保護傳承與應用價值
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傳統民居建筑在城鎮化建設中逐漸消失,民居石刻藝術也隨著建筑構件功能的更迭而逐漸消失。如何在新時代承載和弘揚民居建筑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從當下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視角重新審視關中傳統民居石刻藝術,要如何發掘鄉村的民居建筑文化遺產資源,特別是作為建筑構建的石刻遺存,其存在的原有“土壤”已經發生環境與功能的位移,而新的鄉村民居中建筑院落樣式千篇一律,追其根源無非是文化意識的淡薄與追求效率等利益影響下技藝的缺失。
第一,我們應該實現原有石刻遺跡的在地保護。當下民居建筑中石材已經不再作為民居中重要的建筑構件存在,也不再承擔傳承與寄托傳統文化精神的作用,民居建筑更多的是滿足使用功能需要。對民居石刻遺跡在原有功能位置重建修復,或以陳列的方式展示在鄉村環境中,可以形成新的鄉村公共空間環境。
第二,在快餐式的觀念影響下,民居建筑完全功能化,不再承載地域風格和文化特征,石刻文化功能的轉變勢在必行。鄉村振興帶來的產業結構變化和消費理念的變化,是當下關中民居石刻保護傳承的關鍵要素。我們可以利用關中民居石刻藝術背后的歷史文化與精神價值促進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傳統的民居建筑理念需要更新,石刻藝術所蘊含的精神價值讓我們以新的視角去審視鄉村的發展,發掘出鄉村人居環境中新的物質文化載體。
五、結 語
鄉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不能只是一句口號,也不能單純依靠建造博物館以使其存續。在國家鄉村建設的大背景下,鄉村文化振興、重拾文化自信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環節,需要充分發掘關中民居石刻所蘊含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等來帶動區域內鄉村的人居環境更新。當下,石刻藝術本身已成為文化符號去吸引群眾的支持,推動大眾生成主動保護的意識,促進文化創新,形成文化保護與創新帶領產業發展,產業發展促進文化保護與創新的良性循環。
關中民居石刻是特定地域、特殊環境、極具風格的文化藝術形式,從石刻文化的歷史背后,能看到這片土地上發生的過往,石刻作品所雕刻的不僅僅是單純的形態與奇聞逸事,更是在關中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最樸素的美好向往。時代更迭,關中民居文化不斷受到碰撞,歷經數代傳承逐漸融合,形成這樣獨特的石刻文化,呈現在我們面前。關中民居石刻藝術的探索與應用還在路上,希望本文能成為道路上的基石,為未來的研究提供綿薄之力。
(西安美術學院建筑環境藝術系)
參考文獻
[1] 李媛.關中傳統民居磚石雕刻藝術與內涵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13:17.
[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7-8.
[3] 朱廣宇.中國傳統建筑門窗、隔扇裝飾藝術[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146.
[4] 劉怡燕.開封山陜甘會館建筑裝飾研究[D].鄭州:河南大學,2011:33.
[5] 李琰君.陜西關中傳統民居建筑與居住民俗文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