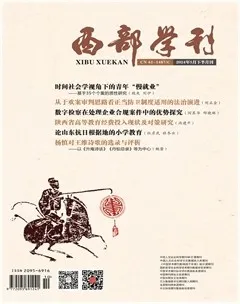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歷史觀的批判及其當(dāng)代價(jià)值
張哲
摘要: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無論是施特勞斯的“普遍信念”、鮑威爾的“自我意識”、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學(xué)”,還是施蒂納的“唯一者”,都局限于黑格爾思辨哲學(xué)與絕對精神之內(nèi),他們對黑格爾哲學(xué)的批判并未超出其哲學(xué)范圍。馬克思通過《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兩部著作徹底清算了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xué)問題,并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xué)。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在當(dāng)代社會(huì)建設(shè)與實(shí)踐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馬克思;青年黑格爾派;歷史觀;當(dāng)代價(jià)值
中圖分類號:B03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10-0145-04
Marxs Criticism of the Young Hegelians View
of Hist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Zhe
(College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The ideas of the young Hegelians, be it Strausss “universal belief”, Powells “self-consciousness”, Feuerbachs “humanism” or Stirners “single person”, are all within Hegel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absolute spirit, and their criticism of Hegels philosophy does not go beyond the scope of his philosophy. Through his works The Holy Family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thoroughly liquidated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Hegel and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establish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s criticism of the young Hegelians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Marx; young Hegelians; view of history; contemporary value
黑格爾主張理性主義,把人類的現(xiàn)實(shí)歷史納入絕對精神之中。青年黑格爾派“青年黑格爾派”:是19世紀(jì)30年代黑格爾哲學(xué)解體過程中產(chǎn)生的激進(jìn)派。亦稱黑格爾左派。活動(dòng)中心在柏林,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參加過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dòng)。意識到了存在的問題,但是他們的批判只停留在宗教方面。所做的批判也未能超越黑格爾的哲學(xué)體系,都是建立在概念、理性、精神及其變種的基礎(chǔ)之上,其錯(cuò)誤就是用錯(cuò)誤的概念代替現(xiàn)實(shí)、用想象肢解歷史,結(jié)果在歷史上陷入了本末倒置的唯心主義泥潭[1]。馬克思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物質(zhì)利益的問題上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產(chǎn)生質(zhì)疑,隨著批判的深入,馬克思逐漸與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yáng)鑣。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宗教史觀的批判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角度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其思想對當(dāng)代中國發(fā)展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史觀
(一)青年黑格爾派的產(chǎn)生與消亡
19世紀(jì)30年代,黑格爾哲學(xué)解體過程中產(chǎn)生了青年黑格爾派,也被稱作激進(jìn)派或黑格爾左派。英國工業(yè)革命至19世紀(jì)40年代基本完成,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機(jī)器制造業(yè)機(jī)械化。法國也幾經(jīng)周折確立了資產(chǎn)階級政治體制。但此時(shí)的德國還以封建貴族勢力為主導(dǎo),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歷程還在艱難地進(jìn)行。德國的哲學(xué)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在政治和經(jīng)濟(jì)上還是十分軟弱。由于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在政治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方面,德國仍承受著封建專制的束縛。1934年,以普魯士為主的各邦結(jié)成德意志關(guān)稅同盟,使經(jīng)濟(jì)得到了快速發(fā)展,也促成了德國的工業(yè)革命。
黑格爾哲學(xué)方法與體系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導(dǎo)致了黑格爾學(xué)派的分裂,被劃分為老年黑格爾派與青年黑格爾派,主要的劃分依據(jù)是對神學(xué)問題的爭論與分歧。青年黑格爾派激烈地反對老年黑格爾派用基督教的正統(tǒng)學(xué)說來解釋黑格爾哲學(xué)的做法,核心成員有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fèi)爾巴哈也曾屬于這一派,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也參加過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dòng)。在哲學(xué)與政治方面,青年黑格爾派整體比老年黑格爾派要更加激進(jìn)和充滿“青年人”的朝氣,批判黑格爾在宗教上的妥協(xié),主張革命和無神論思想。
青年黑格爾派的解體,既由學(xué)派內(nèi)部原因?qū)е拢瑫r(shí)又受到外部環(huán)境的雙重打擊。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爾派以為對黑格爾哲學(xué)進(jìn)行了徹底的批判,但是其實(shí),他們所謂的“批判的批判”并未超過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xué)體系。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仍然是在黑格爾哲學(xué)體系范圍中進(jìn)行的,并沒有打破黑格爾哲學(xué)體系和方法上的固有矛盾。威廉國王堅(jiān)持世襲國家與中世紀(jì)的制度,與青年黑格爾派所倡導(dǎo)的革命和自由相對立,青年黑格爾派受到了阻礙與迫害。青年黑格爾派只停留在理論上的文化批判,并沒有馬克思所倡導(dǎo)的“實(shí)踐”意義,最終只能走向消亡。
(二)青年黑格爾派宗教史觀的發(fā)展
德國當(dāng)時(shí)實(shí)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嚴(yán)重地阻礙了國家的發(fā)展。青年黑格爾派發(fā)現(xiàn)了黑格爾對德國宗教的支持中所透露出的批判態(tài)度,想要通過以宗教批判為中介達(dá)到對德國“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的批判。因此,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展開了長達(dá)十年之久的宗教批判,分別闡釋了自己的宗教批判觀點(diǎn)。
施特勞斯在《耶穌傳》和《基督教教理的發(fā)展歷史及其和現(xiàn)代科學(xué)的斗爭》兩部著作中闡發(fā)了他對宗教批判的兩個(gè)主要觀點(diǎn):“普遍信念”和“思維理性取代神的地位”。施特勞斯在《耶穌傳》一書中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批判方法與文藝復(fù)興以來的“理性主義”的批判傾向,以“矛盾律”和“因果律”兩大規(guī)律為方法對耶穌事跡進(jìn)行求實(shí),發(fā)現(xiàn)這些人們所信仰的耶穌神跡充滿著理性邏輯的矛盾。施特勞斯認(rèn)為神的產(chǎn)生是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在現(xiàn)實(shí)中無法得到解放,就只能寄托于神話與神的救贖,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期望所形成的普遍信念。在他的第二部著作《基督教教理的發(fā)展歷史及其現(xiàn)代科學(xué)的斗爭》中進(jìn)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強(qiáng)調(diào)用理性來改良非理性因素,用無限的取代個(gè)別有限的神的地位,使思維理性成為真神。施特勞斯站在歷史學(xué)家的角度,在歷史事件的分析與考察中對宗教故事進(jìn)行批判,任何超自然的因素都與歷史絕不相容,所以任何宗教的教條都是沒有歷史根基的。施特勞斯的《耶穌傳》開啟了激進(jìn)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運(yùn)動(dòng),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但是,施特勞斯主張的“民族的普遍的信念”還是在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哲學(xué)體系之中,不可避免地忽視了“現(xiàn)實(shí)的個(gè)人”,所倡導(dǎo)的“世俗世界”也不過是缺少人性的“冷漠世界”。
鮑威爾曾反對施特勞斯把宗教理解為群體的無意識的“普遍信念”,鮑威爾認(rèn)為福音書的創(chuàng)作完全是作者本人的主觀思維和意愿,有一定的主觀思維,這些宗教完全就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產(chǎn)物。宗教只是人的意識的分裂,隨著這種分裂的發(fā)展,宗教站在了人類理性的對立面,成為一種與“自我意識”相沖突的力量。但是究其根源,宗教不過是“自我意識”發(fā)展階段的暫時(shí)情況,本身就是“自我意識”的產(chǎn)物。要消除宗教這種與人類理性相對立的形式,就要把它重新納入“自我意識”之中,使它轉(zhuǎn)化為人的“自我意識”的活動(dòng)。鮑威爾用“主體性”消解了宗教的賴以生存的根基,用“自我意識”消解福音書的神圣性。肯定“自我意識”的至高無上與絕對性,把“自我意識”看作是社會(huì)歷史的動(dòng)力,發(fā)展成為無神論主義者。鮑威爾也是在黑格爾“絕對精神”體系之內(nèi),在思辨哲學(xué)的基礎(chǔ)上對宗教神學(xué)進(jìn)行批判。鮑威爾的“自我意識”也絕對不是“現(xiàn)實(shí)中的人”的真正自由,這一點(diǎn)從他的國家觀中有著清晰的體現(xiàn)。并不是人人都擁有“自我意識”的頭腦,只有個(gè)別人才能擁有這種批判的“理性思維”,個(gè)別的“自我意識”也只能在國家中才能得到實(shí)現(xiàn)。即他所說的,“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活動(dòng)之所以一開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實(shí)際成效的,正是因?yàn)樗鼈円鹆巳罕姷年P(guān)懷和喚起了群眾的熱情。”[2]
費(fèi)爾巴哈在宗教的來源和范圍上與施特勞斯和鮑威爾有著不同的認(rèn)識,他深入挖掘了宗教的本質(zhì)。在宗教的來源上,費(fèi)爾巴哈認(rèn)為宗教最開始的對象是自然,人們無法與自然力量相抗衡只能夠依賴自然,想要擺脫這種自然的控制與束縛就只能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之上。宗教的目的就是擺脫這種無力的依賴感,宗教就是在這種矛盾之中演化而來的。他所批判的宗教是所有國家的宗教,不是單指猶太人的宗教,批判的范圍更加廣泛。費(fèi)爾巴哈的一個(gè)重要貢獻(xiàn)在于他把“神本學(xué)”還原于“人本學(xué)”,認(rèn)為福音書所記錄的宗教教理和宗教故事實(shí)際上是人類不斷發(fā)展進(jìn)步的過程。上帝其實(shí)是人自身異化的產(chǎn)物,宗教的神實(shí)際上是被人們賦予的期望。當(dāng)人們無法與自然和苦難抗衡時(shí),就期望神來執(zhí)行人內(nèi)心的法則。神性是人們打破自然對人的限制的心愿,這樣神就變成了現(xiàn)實(shí)的肉體與超越限制的心愿。因此,宗教的本質(zhì)就是人的自我異化,人們對上帝越虔誠越依賴,對自身對現(xiàn)實(shí)的否定越多。費(fèi)爾巴哈提出“類本質(zhì)”的思想,從人自身出發(fā)將理性還原于人,建立一個(gè)充滿愛的聯(lián)合體。把宗教重新收回人自身,人才能夠重新獲得新的解放。他對宗教的揭露與施特勞斯和鮑威爾的批判不同,費(fèi)爾巴哈主張建立一個(gè)充滿愛的宗教,在這里人們被愛包圍,享受著真正的自由與幸福。費(fèi)爾巴哈從愛神者轉(zhuǎn)化為愛人者,確實(shí)是非常大的理論認(rèn)識飛躍。他所主張的類本質(zhì)雖然克服了黑格爾的精神上的抽象,但是在探討歷史時(shí)所謂的“類”仍然是人的共同本質(zhì)的一種抽象,在歷史領(lǐng)域仍然是唯心的。
施蒂納認(rèn)為,從黑格爾到費(fèi)爾巴哈都是用“絕對精神”“理性”的想象來理解歷史,都不能真正地將無神論貫徹到底,他們都用某種超驗(yàn)的事物來替代宗教。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書中提出“現(xiàn)實(shí)的自我”才是唯一者,主張從理性的、超驗(yàn)的精神向個(gè)體自我的還原。值得注意的是施蒂納的“現(xiàn)實(shí)的自我”與馬克思的“現(xiàn)實(shí)的人”有著很大的區(qū)別,馬克思的“現(xiàn)實(shí)的人”指的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以物質(zhì)生產(chǎn)為基礎(chǔ)的有意識的人。而施蒂納所述的“現(xiàn)實(shí)的自我”主要有三個(gè)特性:第一,“獨(dú)自性”,我就是我自己,指我這個(gè)個(gè)體,是根本特性;第二,“所有者”,我自己就是權(quán)力;第三,“唯一者”,我自己就是唯一的自己。從這三個(gè)特性可以看出施蒂納主張個(gè)體的“我”的至高無上性。他把個(gè)體發(fā)展分為三個(gè)階段,兒童階段沒有理性思想,是現(xiàn)實(shí)主義;青年階段追求純粹的理想思想,是理想主義;成年階段思考問題立足于實(shí)際,重視利益,是利己主義。他認(rèn)為利己主義是人的動(dòng)機(jī),給予其極高的地位。主張建立“利己主義聯(lián)盟”從而取代國家等一切共同體,聯(lián)盟與國家不同之處在于聯(lián)盟中個(gè)體自我擁有最高且獨(dú)立的地位,而不用服從于國家的普遍意志。
二、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社會(huì)歷史觀的批判
(一)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關(guān)系
馬克思早在柏林大學(xué)學(xué)習(xí)時(shí)就加入了青年黑格爾派,青年黑格爾派對馬克思早期哲學(xué)的影響非常大。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深受鮑威爾的自我意識的影響。但是他與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秉持的主體與客體對立分離的觀念不同,馬克思主張主體與客體、哲學(xué)與世界的統(tǒng)一。在馬克思進(jìn)入《萊茵報(bào)》工作時(shí),大量接觸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問題,關(guān)心民眾的真實(shí)生活,立志用哲學(xué)變革來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中現(xiàn)實(shí)的人的美好生活與自由追求。這一轉(zhuǎn)變使得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逐漸分裂,他通過對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宗教史觀的批判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
(二)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社會(huì)歷史觀
1.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chuàng)作《神圣家族》,標(biāo)志著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徹底決裂,表明馬克思的哲學(xué)思想已經(jīng)轉(zhuǎn)向唯物主義與社會(huì)主義。第一,馬克思揭露了青年黑格爾派思辨方法的唯心本質(zhì),奠定了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鮑威爾不認(rèn)同蒲魯東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工人帶來了貧困與苦難,工人階級想要獲得自由就需要廢除私有制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工人想要獲得平等和自由只需要把現(xiàn)實(shí)中的不平等情況轉(zhuǎn)化為思維上的平等,即可解決問題。鮑威爾的自我意識是從共同特性中抽離出的絕對本質(zhì),當(dāng)作獨(dú)立于思維主體之外的實(shí)體。青年黑格爾派推崇精神、理智、自我意識,他們的哲學(xué)是思辨唯心主義性質(zhì)的。第二,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英雄史觀,闡述了群眾史觀。鮑威爾輕視人民群眾,認(rèn)為人民群眾無理性且阻礙歷史的進(jìn)步,只有少數(shù)具有批判頭腦的英雄才能夠引領(lǐng)歷史的發(fā)展,群眾也不屬于歷史的范圍。馬克思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對青年黑格爾派進(jìn)行批判,革命成功在于革命符合絕大多數(shù)群眾的利益,才充分喚起了群眾的熱情與支持。歷史的發(fā)展不以個(gè)人的意識為轉(zhuǎn)移,人民群眾才是歷史前進(jìn)的主要推動(dòng)力。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忽視人民群眾,用絕對的“自我意識”創(chuàng)造歷史的觀點(diǎn)。馬克思在這里已經(jīng)認(rèn)識到物質(zhì)利益的重要性,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已經(jīng)萌芽。第三,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社會(huì)歷史動(dòng)力的問題,闡述歷史誕生于物質(zhì)生產(chǎn)。青年黑格爾派繼承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分析路徑,把整個(gè)世界看成“絕對精神”外化發(fā)展的結(jié)果。他們認(rèn)為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的動(dòng)力源于“自我意識”,只有“自我意識”才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決定性力量。他們所認(rèn)為的歷史既不是所處社會(huì)的階段的現(xiàn)實(shí),也不是全人類整體歷史的發(fā)展,而是純粹在思維上發(fā)展變化的歷史,把歷史置于理性領(lǐng)域之內(nèi)。馬克思指出,這種只把歷史置于思想范圍之內(nèi)的闡釋,永遠(yuǎn)無法突破舊世界現(xiàn)實(shí)的秩序。思想要變成現(xiàn)實(shí)就必須由人的實(shí)踐的力量來轉(zhuǎn)化。在某種意義上歷史的發(fā)展也可以被稱為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史。
2.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對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思想、唯心史觀思想、國家觀念展開了批判。
第一,對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觀進(jìn)行批判。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分別對鮑威爾、費(fèi)爾巴哈、施蒂納三人的宗教觀念進(jìn)行批判。馬克思批判鮑威爾空談“自我意識”,企圖用純思想領(lǐng)域?qū)ψ诮膛衼磉_(dá)到政治變革的目的,始終是在黑格爾唯心的思辨范圍之內(nèi),沒有任何的實(shí)際意義與內(nèi)容。鮑威爾把所有運(yùn)動(dòng)都寄托在宗教批判和精神理性之上,是無法實(shí)現(xiàn)人的真正的解放。馬克思指出,費(fèi)爾巴哈的進(jìn)步之處在于突破了以往的唯心主義,但實(shí)際上他的人本主義哲學(xué)仍然是建立在黑格爾的哲學(xué)體系之上。他的哲學(xué)批判的目的僅僅是實(shí)現(xiàn)對宗教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也只停留在“愛”的層面之上,“愛”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絕對力量。他的“人”并沒有處于真實(shí)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僅限于人的“自然性”。費(fèi)爾巴哈的抽象人性論放在社會(huì)歷史領(lǐng)域之中只能走向唯心主義。馬克思批判施蒂納的極端唯心和唯我論,指出他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對人自己以為的所有持否定態(tài)度。施蒂納的“唯一者”也是他自己虛構(gòu)的一種觀念,也是沒有社會(huì)歷史價(jià)值的抽象的個(gè)人。
第二,對青年黑格爾派國家觀的批判。馬克思批判了鮑威爾的“自我意識”主導(dǎo)的國家觀和施蒂納“利己主義”原則的國家觀最終走向虛無的無政府主義。他們的國家觀的目的是實(shí)現(xiàn)自己所處的小資產(chǎn)階級利益,任何的國家和政府都不能與其利益相對立。馬克思指出:“在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下和其他一切時(shí)代一樣,財(cái)產(chǎn)是和一定的條件,首先是同生產(chǎn)力和交往的發(fā)展程度為轉(zhuǎn)移的經(jīng)濟(jì)條件有聯(lián)系的,而這種經(jīng)濟(jì)條件必然會(hu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現(xiàn)出來。”[3]青年黑格爾派的國家觀忽視這種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具有明顯的虛無性和唯心性。
第三,對青年黑格爾派唯心史觀的批判。馬克思通過對青年黑格爾派宗教史觀和國家觀的批判,完成了對青年黑格爾派唯心史觀的批判,并且初步完整地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思想。
三、馬克思社會(huì)歷史觀的當(dāng)代價(jià)值
(一)現(xiàn)實(shí)的個(gè)人和人的解放
馬克思通過對青年黑格爾派抽象的個(gè)人的批判,闡述了“現(xiàn)實(shí)的人”的觀念,他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gè)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gè)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gè)需要確認(rèn)的事實(shí)就是這些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個(gè)人對其他人的自然關(guān)系。”[4]他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又把這種主體性置于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物質(zhì)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中,超越了青年黑格爾派唯心主義的人本學(xué)。此外,馬克思為了實(shí)現(xiàn)人的真正的解放不斷努力奮斗。馬克思提出共產(chǎn)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一種預(yù)設(shè)的價(jià)值目標(biāo),是建立在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之上,這種基礎(chǔ)由人來掌控。因此,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理解和人的解放對我們當(dāng)今社會(huì)建設(shè)仍具有深刻的啟發(fā)意義,在建設(shè)的過程中既要尊重客觀現(xiàn)實(shí),也要充分考慮到人的主體需要。
(二)唯物史觀和重視實(shí)踐
同從前的一切唯心主義把理性當(dāng)作歷史的前提與動(dòng)力不同,馬克思把歷史置于社會(huì)物質(zhì)生產(chǎn)之中,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實(shí)踐的歷史。青年黑格爾派只是在精神理性上“實(shí)踐”,而馬克思把實(shí)踐理解為人的對象化活動(dòng),把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dòng)當(dāng)作實(shí)踐的基礎(chǔ)。這啟示我們,要堅(jiān)持實(shí)踐創(chuàng)新,推動(dòng)全面深化改革。理論只有經(jīng)過實(shí)踐才能得到檢驗(yàn)和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唯有實(shí)干才能興邦。堅(jiān)持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的主體性,堅(jiān)持以人為本,重視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
四、結(jié)束語
通過馬克思早期對青年黑格爾
學(xué)派的批判,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哲學(xué)思想不是固定不變或者一蹴而就。馬克思的哲學(xué)思想也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而發(fā)展形成的。馬克思對前人的繼承與超越對當(dāng)今社會(hu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在學(xué)習(xí)馬克思哲學(xué)思想的過程中,不應(yīng)該僵化地使用它的哲學(xué)理論,而應(yīng)該探尋其思想理論發(fā)展的歷程。只有更加深入地學(xué)習(xí)理解馬克思的哲學(xué)思想,才能深刻地體會(huì)其真正的內(nèi)涵。
參考文獻(xiàn):
[1]徐靖越.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歷史觀變革[D].沈陽:遼寧大學(xué),2019.
[2]黃小琴.青年黑格爾派社會(huì)歷史觀探析[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xué),2009.
[3]陳建宏.《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思想及其價(jià)值意蘊(yùn)[D].重慶:西南大學(xué),2021.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