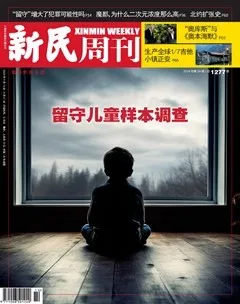瑞典芬蘭與俄羅斯的恩怨情仇

2023年2月15日,俄羅斯圣彼得堡,漁民們聚集在芬蘭灣的冰上捕魚。
隨著芬蘭和瑞典這兩個“中立國家”先后正式加入北約,波羅的海沿岸總計9個國家中,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余8個都是北約成員國。波羅的海事實上已經近乎成為“北約內海”,北約對波羅的海的控制將大大強化。
而俄羅斯不僅與北約直接接壤的陸地邊界一下子增加了約1300公里,位于波羅的海沿岸的兩個重要地區圣彼得堡和飛地加里寧格勒,更幾乎沒有戰略縱深,完全暴露在北約的視野之中,出海口幾乎被“鎖死”。
原本被視為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緩沖區”的芬蘭和瑞典,為什么會改變多年以來的中立和不進行軍事結盟的安全政策,除了國際政治觀察家們分析的北約東擴下的拉攏和俄烏沖突刺激的因素外,回溯兩國的歷史以及與俄羅斯的恩怨情仇,也可從中找到些許端倪和啟示。
瑞典曾是波羅的海霸主
說起瑞典的國家起源,維京海盜時期的故事過于久遠。公元11世紀左右,當海盜時代進入尾聲,而中國中原地帶進入兩宋遼夏金時期的時候,地球另一邊歐洲北方的瑞典才剛剛形成統一獨立國家,而這正是瑞典王國的起點。
在1008年,奧洛夫·舍特康努格成為瑞典第一任基督教國王,他也是第一位領導和管理最初瑞典王國的君主。王國形成之初,瑞典是個由一些獨立性很強的省組成的松散王國。公元1248年,瑞典歷史上較早且較為重要的福爾孔王朝開始,由此瑞典封建化的進程大大加快,國家形態最終于此定型。1155年,芬蘭被并入瑞典國土。
為了對抗強大的漢薩同盟在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勢力,1397年丹麥、挪威、瑞典三國在瑞典東南部的卡爾馬舉行會議,決定成立由丹麥王室主導的卡爾馬聯盟,從此瑞典和挪威臣服于丹麥國王的統治,同時保留了王國的地位。但在聯盟時期瑞典人與丹麥人的沖突不斷發生。1521年,丹麥軍隊鎮壓武裝反抗失敗。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一世再次建立王權,瑞典從聯盟中獨立。
早在16世紀,瑞典就在數次戰爭中擊敗了丹麥和波蘭,成為了北歐軍事霸權。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瑞典加入新教陣營參戰,并派兵深入神圣羅馬帝國腹地。1648年法國與瑞典聯軍最終戰勝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瑞典得到了德意志領土前波美拉尼亞、維斯馬、費爾登和不來梅。三十年戰爭后,瑞典在波羅的海的勢力達到頂峰,成為了北歐及波羅的海霸主,領土包括現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俄羅斯、波蘭和德國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
但瑞典的霸主地位僅維持了50余年。為了奪取可以與西方聯系的波羅的海出海口,彼得大帝領導的俄國與丹麥、波蘭聯手,1700年向霸主瑞典發起了大北方戰爭。1709年,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的軍隊在今烏克蘭境內被沙俄軍隊擊潰,逃至奧斯曼帝國。1721年瑞典戰敗,不僅喪失了波羅的海屬地,北歐霸主的寶座還被俄國掀翻。1808年,瑞典與俄國爆發芬蘭戰爭,瑞典再次戰敗,俄國吞并了瑞典統治下的芬蘭,作為附庸于俄羅斯帝國的芬蘭大公國。
1813年,瑞典加入反法同盟,參加拿破侖戰爭。一年后,丹麥與瑞典簽訂《基爾條約》,丹麥將挪威割讓予瑞典。當時挪威乘機宣布獨立并頒布了憲法。瑞典對其發動戰爭,挪威被迫同意作為一個國家臣服于瑞典國王,結成挪威—瑞典聯盟,直到1905年挪威脫離聯盟獨立。
在從1814年簽訂《基爾條約》至今,瑞典已經中立了210年,避免了卷入任何戰爭與沖突之中。持久的和平穩定帶來了瑞典國內經濟和科技的發展。19世紀末瑞典完成了工業化,開始走上發達國家的道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瑞典也均守中立未參戰。
芬蘭獨立僅百年出頭
在北歐國家里,瑞典、挪威、丹麥、冰島的文化都非常相似,唯獨芬蘭很獨特,被稱為最另類的北歐人。關于芬蘭人的民族起源,史學界仍然存在著爭議。值得一提的是,芬蘭語屬于烏拉爾語系中的芬蘭—烏戈爾語族,和匈牙利語的關系要比其他語言來得更為密切,或許與匈牙利一樣,同樣和古代東方游牧民族有著什么聯系,與瑞典鮮明的維京血統截然不同。
在12世紀中葉,瑞典進攻芬蘭時,芬蘭發展則相對滯后,依然處于原始社會公社時期,完全不是瑞典的對手,最終全境被瑞典吞并。芬蘭人作為北歐唯一的非維京民族,常常被瑞典人歧視為“原始人”,強勢統治了600多年。瑞典則憑借著強大的實力,壟斷了芬蘭的教育和文化權。因此在13世紀之后,瑞典語不僅成為了芬蘭的上層貴族階級所使用的語言,也成為了芬蘭人日常交流所使用的主要語言。至今,瑞典語依然是芬蘭的官方語言之一。
在十六七世紀瑞典奪取北歐霸權,瘋狂對外擴張的年代,芬蘭士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瑞典軍隊一度有三分之一是芬蘭人。但長期的軍事行動也給芬蘭帶來了沉重的賦稅和兵役負擔。芬蘭人民雖然一度起義反抗瑞典統治,但旋即被鎮壓。
在俄國沙皇彼得一世趁此機會,聯合丹麥、波蘭等國對瑞典發起終結其霸權的“大北方戰爭”中,芬蘭正是這場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因為瑞典在這場戰爭以及1808年與俄國爆發的芬蘭戰爭中均告失敗,芬蘭最終成為俄羅斯帝國治下的芬蘭大公國。

上世紀40年代對蘇作戰中的芬蘭軍人。
當時為安撫芬蘭,俄國賦予了芬蘭很大程度的自治權,許諾當地人民仍然享有原有的習俗、宗教、法律等權利。俄國為了進一步削弱瑞典對芬蘭的影響,還鼓勵芬蘭語的復興。在芬蘭上層貴族的推動下,芬蘭開啟了“芬蘭化”的進程,人名和地名紛紛都從瑞典名改到芬蘭名,芬蘭語更是獲得了官方語言的地位。
不過從19世紀末開始,俄國國內政治轉向保守。因為芬蘭擁有獨立的議會和軍隊,俄國認為威脅到了首都圣彼得堡的安全,便取消芬蘭的自治地位,收回芬蘭軍隊,大力推行“俄羅斯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卷入戰爭,俄皇在芬蘭的“俄羅斯化”政策被迫停滯,而芬蘭人也已經不再抱著“順從”的心態依附于帝國的強權。三年后,俄國國內爆發了二月革命,隨后爆發的十月革命徹底推翻俄封建帝制,布爾什維克掌權,并宣告俄國各民族有民族自決的普遍權利,包括完全獨立的權利。嗅到機會的芬蘭議會,當機立斷宣布了芬蘭的獨立,芬蘭人歷史上第一次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雖然芬蘭在十月革命后獲得了獨立地位,不過,當時的芬蘭強敵環伺,形勢并不樂觀,國內不但爆發了內戰,且也與蘇聯因為領土問題發生了武裝沖突。
1939年,兩國經過多次交涉,蘇聯的領土要求始終沒能得到芬蘭的同意,11月底,談判正式宣告破裂,蘇芬戰爭開始,芬蘭人稱之為“冬季戰爭”。 持續了幾個月的戰爭,芬蘭人的抵抗強度超出了蘇聯的想象,雖然蘇聯迫使芬蘭割讓了包括卡累利阿地區和第二大城市維堡在內的約10%的領土,但卻也付出了5.35萬人陣亡、17.6萬人受傷、1.6萬人失蹤的代價。
芬蘭在蘇芬戰爭后強化了與德國的合作關系,并也因此引發了1941年以收復卡累利阿地區等失地為目的的“繼續戰爭”。但隨著德國在二戰中的失利,芬蘭只能于1944年單獨向蘇聯求和。當芬蘭與蘇聯停戰后,芬蘭旋即要求駐扎于國內的德軍離去,但卻遭到了后者的拒絕,于是芬蘭再度對昔日的盟友宣戰,是為“拉普蘭戰爭”。
二戰后,芬蘭雖然沒有直接獲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但仍然通過與西方國家保持經貿來往,讓自己逐步成長為一個工業國。
大國對峙間的平衡術
縱觀瑞典歷史,可以看出在1814年后,隨著俄國、法國、德國的相繼崛起,瑞典已經敏銳地覺察到自己與這些大國的實力已經不在一個維度,雖然俄國國力相較于德法較弱,但由于與俄國勢力范圍直接接壤,瑞典只能保持中立,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哪怕自己與俄國仇怨頗深,瑞典也不輕易選邊站。
也正由于此,二戰時期的瑞典,成為了歐洲極少數幾乎完整保留了其國防力量的國家。二戰后,美國積極采取馬歇爾計劃支持歐洲的戰后重建,致使歐洲大部分飽經戰火的國家不得不依賴于美國的經濟援助,瑞典卻可以進退有據地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立場。
冷戰開始后,夾在北約與華約之間的瑞典,在兩強僵持之時發現自己恰恰是一個分量頗重的砝碼。于是,瑞典接著貫徹自己的一直以來公平外交的理念,對美蘇采取完全一致的態度。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也忌憚若是極力逼迫瑞典站隊可能導致的使其完全歸屬對方的不良后果而對瑞典優容有加,于是冷戰時代的奇觀出現了:瑞典一邊從美國吸收大量尖端科技來發展自身的國內產業,而另一方面則積極與蘇聯進行進出口貿易來賺取外匯支持經濟建設。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當時瑞典還利用其中立身份將自己定位為國際調解人。
冷戰結束時,瑞典再次實現了國力質的飛躍。高新產業位居世界前列,商業貿易與日俱增,作為典范屹立于歐洲。能夠擁有這樣的成就,跟瑞典的中立政策可謂息息相關。
蘇聯解體后,歐洲的東西方力量平衡完全破壞。作為與俄羅斯沒有領土接壤的國家,瑞典已經沒有了巨大的戰略壓力,隨即加入了歐盟。近年來瑞典一反常態,脫離中立政策的原則,反復加強與北約的軍事合作,動輒進行的聯合軍演,已經能夠看出些什么。
至于芬蘭,它保持的中立與瑞典非常不同。1948年4月,芬蘭曾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被看作是芬蘭為了生存和保持國家獨立所采取的務實做法。芬蘭歷史學家邁南德說,如果說瑞典的中立關系到這個國家的身份和意識形態,那么芬蘭保持中立則是為了生存。
二戰后,芬蘭由于特殊的地緣環境,為了避免遭受兩大陣營任何一方的敵視,不偏向美蘇任何一個陣營就顯得尤其必要了,這也顯示出小國在強敵環伺下艱難求生的無奈。從本國的中立政策出發,芬蘭將對蘇友好作為本國中立外交政策的立足點,甚至還允許蘇聯派來的政治人物在芬蘭擔任公職。
1946至1981年巴錫基維和吉科寧兩位總統執政期間,致力于建立與蘇聯之間的互信關系,在此基礎上推進與西方的合作,并成為蘇聯和西方之間的交流門戶。對他們而言,不可忽視的痛苦現實是:芬蘭就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它不能期待從西方盟友那里得到任何幫助;它必須理解蘇聯的想法,向蘇聯證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諾、履行協議,從而獲得蘇聯的信任。
而對蘇聯來說,芬蘭是西方技術的主要來源,也是蘇聯面向西方的主要門戶。
盡管芬蘭在戰后成功游走在兩大陣營之間的灰色地帶,但從政治形態和經貿關系角度來看,芬蘭無疑還是要稍偏向西方陣營一些。隨著蘇聯的解體,芬蘭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大為減少,因此加快了和北約、歐盟的合作進程。
如今,瑞典和芬蘭都改變了中立政策加入了北約,打破了多年來的平衡局面,看似抱上了“大粗腿”,但真的就能如它們設想的那樣獲得更安全的保障嗎?當波羅的海不再平靜,處在北約與俄羅斯對峙的最前沿,這兩個國家的未來命運,不能不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