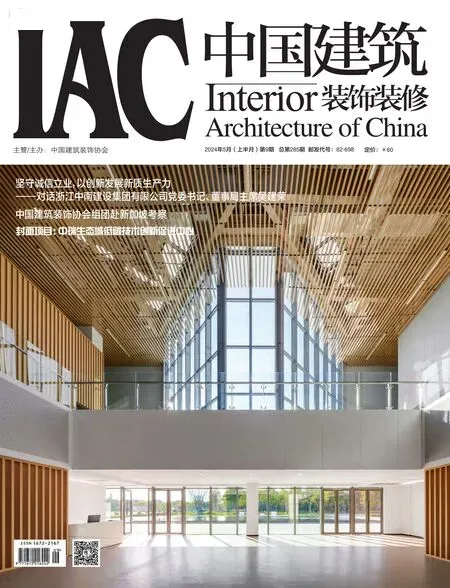更新與傳承:基于城市區(qū)域文化的建筑空間設(shè)計策略
——以云居寺及街巷空間為例
蔡佳霈
1 云居寺概況
云居寺又稱西五臺,原名安慶寺,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門蓮湖路西段南側(cè),東鄰灑金橋,西接明城墻,東西長約500 m。唐代時此地原為長安城內(nèi)太極宮城南墻。云居寺歷來為尼僧道場。《西安府志》記載:“其臺基于唐,創(chuàng)于宋,屢葺于明。由于年代久遠(yuǎn),戰(zhàn)火頻繁,屢毀屢建,究系何代建造,眾說不一[1]。”云居寺與一般佛寺坐北朝南的朝向截然不同,其坐西向東,由山門拾級而上,其中主要殿宇建筑均建于高臺之上,且一臺高于一臺,當(dāng)前由于受現(xiàn)代城市建設(shè)的影響已被分割成3 段,與周邊街區(qū)形成了互有交錯的緊密結(jié)合關(guān)系。
云居寺各日皆有佛事活動,香火旺盛,亦會接待大量香客,同時為西安鼓樂社大型鼓樂演出活動的主要場地。西安鼓樂社于云居寺進(jìn)行的演出是其所參與的各種廟會活動中較為大型的鼓樂演奏活動[2]。期間,鼓樂演奏的地點(diǎn)和時間非常集中,各個樂社要在3 d 之內(nèi)走遍包括云居寺在內(nèi)的分布于西安各街巷內(nèi)的大小廟宇,只要有廟的地方,樂社都要前往并演奏鼓樂曲,這一民俗活動不僅是鼓樂流傳下來的歷史傳統(tǒng),還是民眾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鼓樂能得以世代相傳,與一年一度的廟會活動密不可分[3]。
2 問題分析
云居寺獨(dú)特的空間布局及在今西安城區(qū)中的特殊位置共同造就了目前尷尬而又獨(dú)特的空間格局。而格局的缺損、模糊的軸線是識讀該佛寺建筑群的主要障礙,禮佛儀軌的進(jìn)行及鼓樂演出亦受困于狹小的空間,二者功能沖突時有發(fā)生。其位于居民社區(qū)之中的特殊城市區(qū)位也對佛寺本身更新改造活動形成掣肘。
經(jīng)實(shí)地調(diào)研,筆者總結(jié)出云居寺空間與功能使用問題如下:空間格局缺損,軸線北側(cè)的附屬建筑基本無存;藥師殿與彌勒殿位于一座現(xiàn)代配屬建筑中,空間狹小;降龍觀音殿與大雄寶殿之間之開闊場地鋪裝單一,且缺少綠化;寺中空間利用率較低,仍有部分荒地未加以有效利用;寺院與周邊城市街區(qū)的關(guān)系,多采用圍墻區(qū)隔的硬處理方式,未與周邊社區(qū)、商業(yè)等空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guān)系。整體而言,寺內(nèi)空間利用率低、佛寺功能布局欠佳、建筑軸線模糊、與周邊街區(qū)缺乏互動是目前云居寺區(qū)域存在的主要問題,具體的空間問題描述如下:
1)云居寺院落中部、南側(cè)的問題有以下4 點(diǎn):第1,藥師殿與彌勒殿擠在位于大雄寶殿與降龍觀音殿院落南側(cè)的一座現(xiàn)代配屬建筑中,并無專屬的佛殿建筑。第2,院落北側(cè)閑置場地延伸至大雄寶殿的交界處場地未有效利用,該區(qū)域因堆滿了雜物廢料而成為一處無用區(qū)域,其后的許愿池更是成為香客避之不及的“臭水池”。第3,降龍觀音殿與大雄寶殿之間是一片較為開闊平整的場地,但單一的鋪裝占據(jù)了整個場地,缺少綠化,且整片前段院落完全采用了同一種鋪裝,自山門鋪至五大菩薩殿,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中軸對稱的特點(diǎn)相悖。第4,云居寺北側(cè)即是西安古都大酒店,云居寺與大酒店兩組建筑群之間僅由各自的圍墻做了空間分隔,兩墻之間的間距只有1.5 ~2 m,雖然較為狹窄,但從現(xiàn)場調(diào)研情況來看,當(dāng)?shù)鼐用袷褂迷摰缆奉l率較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其為連接灑金橋和工商家屬院的捷徑。
2)云居寺院落北側(cè)的問題有以下4 點(diǎn):第1,云居寺的整體朝向?yàn)樽飨驏|,主入口與城市主干道路灑金橋由長達(dá)50 m 的窄巷連接,入口極為隱蔽,且路面鋪裝、兩側(cè)墻面質(zhì)量均較差。其中,窄巷南側(cè)為部分居民樓一層商鋪入口,雜物堆放不規(guī)范的問題較為突出。第2,云居寺并沒有固定的法器流通處,當(dāng)香客有禮佛活動需求時,往往無法及時找到所需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香客的活動體驗(yàn)。第3,閑置空地會在春、夏季生長野草,可達(dá)膝蓋高度,行人往往難以直接跨越。降龍觀音殿的最下部臺基與草地之間僅隔0.5 m,難以滿足通行需要。第4,縱觀整個云居寺前段院落,除了主體建筑,附屬建筑較多,但大多數(shù)基本屬于倉儲空間或是僧侶宿舍,并沒有找到衛(wèi)生間等必備空間。
3)云居寺山門區(qū)域的問題有以下4 點(diǎn):第1,云居寺山門入口處經(jīng)常有在此席地而坐或休憩閑談、或向香客乞討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云居寺的對外形象。第2,云居寺山門入口南側(cè)為一處廢品收購處,緊挨山門入口的建筑物長期處于無人使用的狀態(tài),建筑物的門口也常年堆放廢品。第3,云居寺山門北側(cè)為一處小的公共空間,除了滿足一般的通行功能,也經(jīng)常被前來云居寺祭拜的香客用作臨時停放非機(jī)動車輛的場地,但非機(jī)動車的擺放通常沒有秩序,導(dǎo)致該處空間利用不合理。第4,自云居寺東側(cè)主街至山門的東西向窄巷,并未與云居寺中軸線處于同一條線上,且山門建筑樣貌與寺院傳統(tǒng)建筑不符,較為現(xiàn)代。由此可推出,山門的建造應(yīng)晚于其前窄巷的形成時間。囿于既有的城市街巷肌理,山門的位置未能處在寺院中軸線上,與中國傳統(tǒng)寺院建筑布局組織形式相悖。
4)在歷史演變過程中,除物質(zhì)空間外,云居寺與周邊建筑也形成了一種獨(dú)特的建筑風(fēng)貌關(guān)系。出于對建筑遺產(chǎn)及歷史街區(qū)價值的尊重,需要對現(xiàn)存較為復(fù)雜的建筑風(fēng)貌關(guān)系進(jìn)行梳理,更需要對新置入的建筑進(jìn)行風(fēng)貌控制。云居寺前段院落北側(cè)為酒店,南側(cè)為小學(xué),皆屬于大型公共、商業(yè)建筑,而前段院落東側(cè)與后段院落周圍是舊居民樓、居住建筑,建筑類型紛雜,空間體量變化較大,需要從中找尋統(tǒng)一的建筑秩序。
3 策略實(shí)施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提出空間設(shè)計策略:第1,重新定位云居寺與周邊街區(qū)的關(guān)系,從完全封閉的佛教寺院到兼具鼓樂表演功能以及服務(wù)周邊居民的城市公共空間功能的復(fù)合型寺院空間;第2,置入新的功能空間,并重新組織目前較為無序的空間關(guān)系;第3,重塑云居寺的空間格局。更新改造重點(diǎn)區(qū)域示意圖如圖1 所示。在具體操作層面,本文的討論重點(diǎn)為山門區(qū)域、軸線區(qū)域及軸線北側(cè)區(qū)域。

圖1 更新改造重點(diǎn)區(qū)域示意圖(來源:作者自繪)
3.1 山門入口――與社區(qū)居民的積極互動
云居寺的入口空間一側(cè)緊挨著建筑墻體,另一側(cè)與院落圍墻相連,門前有一片約5 m×15 m 的空地。在山門入口處,經(jīng)常能看見老人圍繞入口席地而坐。此外,該區(qū)域的居民也經(jīng)常將非機(jī)動車停放于此。在重新設(shè)計過程中,通過分類與整合,保留了存儲功能的同時,山門區(qū)域以鋪地與標(biāo)高的不同區(qū)分出強(qiáng)化軸線的入口動線,強(qiáng)調(diào)該區(qū)域作為入口空間所起到的重要引導(dǎo)作用。山門區(qū)域更新改造效果如圖2 所示。將山門南側(cè)廢品收購處以及處于廢棄狀態(tài)的臨時建筑拆除,恢復(fù)山門前的院落空間,并結(jié)合云居寺現(xiàn)存歷史建筑特征,提取傳統(tǒng)建筑黃琉璃瓦坡屋面、朱柱梁枋、青磚砌墻等構(gòu)成要素,重構(gòu)山門這一傳統(tǒng)院落中重要的單體建筑形象。由于通往山門的東側(cè)窄巷與兩側(cè)建筑是既有的城市道路、建筑肌理,不宜變更,因此重構(gòu)后的山門仍處于原位置。筆者對寺院中軸線采取與院落其他地面不同鋪裝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因位置偏移而造成的中軸空間錯動的問題。在山門兩側(cè)延續(xù)坡屋頂意象,置入具有遮陽功能的休息區(qū)域,并與車輛停放空間加以區(qū)隔,形成有序的休閑與車輛停放空間。三者在功能上完全區(qū)隔,但在視線乃至具體行為活動方面則形成有機(jī)互動。建筑材料仍以青瓦細(xì)木柱描摹整體形象。

圖2 山門區(qū)域更新改造后效果圖(來源:作者自繪)
3.2 寺院中軸――格局重塑以及功能需求
通過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降龍觀音殿和大雄寶殿之間存在一個平屋頂磚石建筑,建筑內(nèi)部有藥師佛和彌勒佛坐像供香客祭拜,二者之間僅通過一扇隔墻分隔為兩個獨(dú)立的祭拜空間,但空間祭拜方位為南向,作為配殿。這樣的設(shè)置明顯是由于建筑體量不夠造成的。為此,在云居寺中軸線對稱方向設(shè)計了一所佛堂,以解決上述問題,補(bǔ)全中軸對稱的格局。
此外,云居寺沒有固定的法物流通場所,且缺少一個供香客或是其他人員休憩、交流放松的公共空間。因此,在佛堂東側(cè)設(shè)計了以上兩個空間。選擇該處進(jìn)行建設(shè)的原因是與云居寺中軸線另一側(cè)的建筑相呼應(yīng)。
于軸線北側(cè)置入的配屬佛殿建筑及法器流通處建筑組群,在整體格局上作為對南側(cè)既有建筑組群的回應(yīng),在功能上亦為對側(cè)附屬建筑功能的同類擴(kuò)展。整體建筑形象為傳統(tǒng)雙坡屋頂?shù)囊庀螅郧嗤吣局蠢战ㄖ闹黧w形象,內(nèi)外墻體則分別采用夯土與磚砌材質(zhì),以夯土墻體營造靜謐禪意的佛殿空間,青磚外墻則與建筑群的整體風(fēng)貌相呼應(yīng)。佛殿與法器流通處之間圍合出一處庭院空間,作為對寺中稀缺休憩空間的補(bǔ)充。
法器流通房間的東側(cè)是一處小型會議室。筆者調(diào)研時注意到,西安市大多數(shù)鼓樂社多為自發(fā)性組織,平時并無固定的教習(xí)場所,該處空間的布置是借助云居寺作為演出據(jù)點(diǎn)的便利性,為鼓樂社提供一個常駐基地,以滿足其日常訓(xùn)練、教習(xí)、會議等功能需要。會議室以東為衛(wèi)生間,彌補(bǔ)云居寺整個前段院落該類必備功能性空間的缺失。除此之外,本處建筑亦有溝通佛寺內(nèi)外欣賞鼓樂表演的復(fù)合功能,建筑與廊道的設(shè)計是在云居寺北側(cè)院墻的基礎(chǔ)上,劃分為雙墻空間,分別對內(nèi)對外,服務(wù)于居民日常生活和鼓樂演奏兩種情況(圖3)。西安市傳統(tǒng)街巷不僅構(gòu)成城市形態(tài),而且是城市風(fēng)貌的延續(xù)[4]。廊道不僅為附近居民日常使用提供休憩娛樂的空間,還可為鼓樂演奏者提供表演后休整的場所。墻上的展示窗口平時可以為鼓樂演奏提供宣傳平臺。通過對圍合墻體的開洞以及與廊道的有機(jī)組合,實(shí)現(xiàn)佛寺內(nèi)外空間溝通的視覺便利與行為阻隔。在傳統(tǒng)街巷的更新改造過程中,傳統(tǒng)文化不應(yīng)僅作為形式上的元素,更要體現(xiàn)歷史內(nèi)涵[5]。

圖3 北側(cè)附屬建筑佛殿及法器流通處平面圖(來源:作者自繪)
3.3 樹木綠化――寺院中軸的再現(xiàn)
云居寺院落中部的綠化較少,僅大雄寶殿前有少量植被。在對院落進(jìn)行重新設(shè)計的過程中,提升綠化面積,通過植被排列的形制,一定程度強(qiáng)化中軸對稱格局及儀式空間的神圣性。相較于機(jī)械地重建補(bǔ)全空間格局的做法,種植植物這一措施在具體操作層面具有較高的靈活性,且較易適應(yīng)各類復(fù)雜的場地情況。植被的具體類型受當(dāng)?shù)鼐唧w生態(tài)、氣候條件和佛教寓意的制約,不僅要遵循傳統(tǒng)寺院園林的布置理念,還應(yīng)能烘托寺院佛教氛圍。降龍觀音殿前,以觀音竹為主,種植方式為叢植;大雄寶殿前,主要為羅漢松、菩提樹、七葉樹,對植,意在渲染寺院核心空間的莊嚴(yán)肅穆;五大菩薩殿兩側(cè),群植棕櫚、黃葛樹、蒲葵等,兼具教義與修飾環(huán)境的作用。
3.4 古寺風(fēng)貌――建筑材料的選擇
基于設(shè)計的場地與歷史建筑本體在空間層面的緊密聯(lián)系,在設(shè)計時考慮區(qū)域內(nèi)的整體建筑風(fēng)貌,及建筑風(fēng)貌與周邊街區(qū)建筑間的獨(dú)特關(guān)系。雖然云居寺周邊建筑類型多樣紛雜,但仍可找尋相似的構(gòu)筑要素,即大多以青磚與混凝土砌筑,立面呈現(xiàn)灰色、灰白色為主的視覺效果,另外街巷空間以適宜人行尺度為主,緊湊、凝練的空間組織是該片街區(qū)格局的主要特征。因此,材料方面,選用了在工藝、顏色等方面與云居寺的建筑有較高相似的材料,如灰磚、木材等,結(jié)構(gòu)方面借鑒梁上架椽的方式,在佛堂與法器流通處之間建立一個露天的庭院空間,適當(dāng)增加綠化及休憩的空間。建筑布局方面,在有限的場地面積內(nèi)置入多重功能空間,建筑尺度以滿足人的行為需求為主要目標(biāo)。改造后的建筑既達(dá)到補(bǔ)全寺院整體格局的目的,又盡量在外觀效果上隱于場地內(nèi),凸顯云居寺歷史建筑遺產(chǎn)的首要地位。
4 結(jié)語
通過以上設(shè)計實(shí)踐,旨在對云居寺建筑空間設(shè)計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解決。通過保障鼓樂社團(tuán)及香客游人的公共利益,設(shè)計改造最終達(dá)到多方共贏的結(jié)果[6]。單墻與雙墻之變,不僅在物質(zhì)層面增強(qiáng)了空間的豐富性,還以一種獨(dú)特的方式打破了寺院原有封閉的空間環(huán)境,模糊了空間的邊界,促使寺院與社區(qū)的結(jié)合更為緊密,真正融入社區(qū)生活中。而軸線的強(qiáng)化與風(fēng)貌控制則是寺院空間本體的重塑,作為對這一更新改造對象本體的回應(yīng)與尊重,空間的秩序也在這一重塑過程中再次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