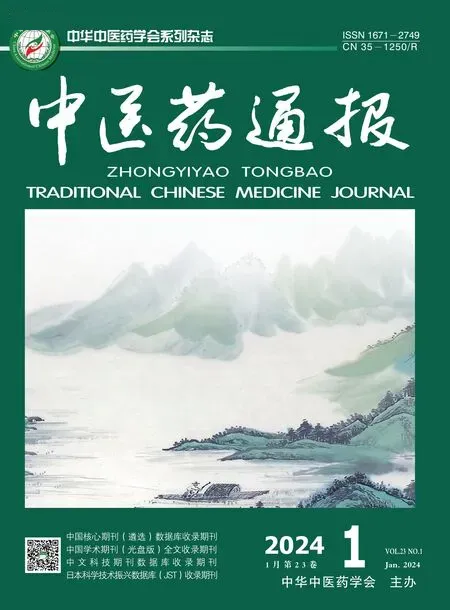《黃帝內經》中“陰陽”理論與唯物辯證法中“矛盾”理論的比較
徐榕浩 楚洪波
唯物辯證法經過長期的研究和發展,其主體內容被概括出了三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質變與量變、否定之否定。其中對立統一即為矛盾,被廣泛運用于解釋世界的一切變化。《黃帝內經》(下文簡稱為《內經》)中的陰陽則是事物或現象之間或內部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的基本屬性,是認識世界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的基本內容被歷代醫家總結為對立制約、互根互用、消長平衡、交感互藏、相互轉化幾個部分。其中對立制約與互根互用被結合起來,成了陰陽的“對立統一”理論,也可以被看作陰陽之間的矛盾,被運用于解釋自然、社會政治及道德倫理。兩個“矛盾”常被模糊等同或是混淆,少有將陰陽之矛盾與唯物辯證法之矛盾細節上的異同進行仔細對比者。雖然部分學者曾對陰陽與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論進行過比較研究,但只有部分研究內容達成了共識,其結論尚不統一,仍然有可補充及商榷之處。為此,筆者從極少被探討的幾個方面(即同一性與斗爭性、普遍性、結果與歸宿三個方面)出發,對《內經》中陰陽的矛盾(下文簡稱為“陰陽”)和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下文簡稱為“矛盾”)進行比較,探討兩個“矛盾”的相關性與差異性。
1 “矛盾”的同一性、斗爭性與“陰陽”的互根互用、對立制約
1.1 同一性與互根互用同一性與斗爭性是唯物辯證法“矛盾”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矛盾的基本哲學范疇。矛盾的同一性或統一性是指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的內在的、有機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體現著對立面相互吸引、相互結合的趨勢[1]230。其同一性使矛盾兩方面聯系與運動有了前提條件,遠離了“形而上學”的束縛。矛盾的同一性不是簡單地將矛盾的兩方面隨意丟進一個統一關系中,而是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包括雙方互相依存、一方的存在和發展必須依靠另一方的存在、雙方相互包含、相互滲透、在一定條件下會向自身的對立面發展。而《內經》中陰陽的互根互用則體現了陰陽雙方互為根本、互以為用的思想。《內經》中有“孤陰不生,孤陽不長”的說法,表明《內經》中陰陽同樣是相伴存在的,沒有單純的陰與陽。王冰在《次注黃帝內經素問》中以“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作了進一步解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闡述了陰陽雙方的發展依賴著其對立面。矛盾兩方面相互包含滲透、相互轉化的特性在《內經》中也同樣有“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與“重陽必陰,重陰必陽”的內容來描述,并據此在臨床實踐中出現了“陽中求陰”“陰中求陽”的治療方法。綜上所述,“陰陽”互根互用所表述的同一性與“矛盾”同一性的豐富內涵幾乎做到了一一對應,因此可以認為二者在同一性上有著同樣的認識。
1.2 斗爭性與對立制約矛盾的對立或斗爭性是指矛盾雙方互相排斥,即互相反對、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屬性,體現著矛盾雙方相互分離的趨勢[1]232。這種趨勢無時無刻不存在于事物之間與事物內部。與同一性一樣,“矛盾”的斗爭性也存在著豐富的內涵。簡單可概括為,事物之間有著激烈的暴力的對抗性斗爭與緩和的非暴力的非對抗性斗爭,事物內部亦是有著激變性及劇烈變化的對抗性斗爭和“相互協調”“自我批評”式的非對抗矛盾。每當斗爭到最后便會推動本矛盾向著下一個矛盾轉變。“陰陽”關于斗爭性的論述多表現在其對立制約的內容中。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謂“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為“制約太過”,“陽虛則陰盛”“陰虛則陽亢”是“制約不及”,從而形成了陰陽失調的病機變化[2];又如《素問·六微旨大論》言“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說明事物內部包含著肯定和否定,即化與變這兩種因素在相互斗爭著[3]。《內經》通過對“陰陽”斗爭性(即陰陽的對立制約)的深刻認識,創新性地在臨床實踐中利用了這一規律,以矛盾某一方的對立面來制約其本身,使其回歸平衡狀態,并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提出“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等觀點,充分說明《內經》對陰陽間的斗爭性有著一定的認識。
相比于“陰陽”對同一性的準確認識,筆者認為其對斗爭性豐富內容的認識是相對不足的。《內經》中把”陰平陽秘“看作理想的狀態,并且多次強調陰陽的平衡才是陰陽正確的關系,這就讓其對斗爭性的觀點看似走向了“形而上學”的方向。《內經》的總體思想中也確實更加強調同一而有些忽略斗爭。眾所周知,“矛盾”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易逝的,而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4]。這就不得不讓人在比較中認為《內經》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矛盾不能調和,斗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有時又主張取消矛盾,反對斗爭[5],這種觀點有部分是正確的,但通過對《內經》進一步的認識,便能得知陰陽無論如何的平衡都沒有哪怕一點靜止的內在因素。《內經》所說的平衡就好比兩個勢均力敵的力士掰手腕,雖然表面上有著紋絲不動、看似靜止的表象,但其斗爭的本質卻是客觀存在的。雖然《內經》并沒有反對斗爭,但其反對所有對抗性斗爭是事實。“陰陽”容不下激變與矛盾雙方的整體轉變。“陰陽”中并沒有真正的對抗性斗爭,即使有也是異常的病理狀態,需要及時矯正。
通過比較,可以得知《內經》“陰陽”對同一性的認識與“矛盾”對同一性的認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前者在斗爭性上并不能涵括后者的豐富內涵。“陰陽”對斗爭性認識的不足將使陰陽作為矛盾的歸宿走上與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完全不同的道路。
2 “矛盾”與“陰陽”存在的普遍性
在“矛盾”理論中普遍性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其是唯物辯證理論中每個矛盾能夠相互聯系,相互變化、發展的理論基礎。《內經》對陰陽學說的闡述中也多次涉及陰陽這對矛盾普遍存在于萬物,在自然世界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兩者的普遍性是否一致主要需看兩個方面。其一,“陰陽”是否如“矛盾”那樣存在于事物的全部階段;其二,“陰陽”普遍性的范疇是否能夠如“矛盾”一樣普遍,這也是存爭議最大的部分。
“矛盾的普遍性,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6]。這是《毛澤東選集》中對矛盾普遍性的高度概括,說明了這種事物處在同一個系統中相互依存、相互統一又相互斗爭、相互排斥的趨勢存在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領域的各個角落,甚至運動與運動趨勢中。“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7]即使是各種復雜矛盾發生著復雜變化時也絕對沒有一瞬間、一剎那的時間是處于無矛盾狀態的。這種時時刻刻統一、時時刻刻斗爭的存在形式也是事物不斷發展、不斷變化的動力源泉。
《內經》中也是如此。首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提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和《素問·生氣通天論》中提到“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據此可以看出《內經》中明確地認為“陰陽”主宰著萬物,是一種規律,是變化的來源,是誕生與消亡的根本。這符合了“矛盾”是發展動力源泉的觀點和存在于事物全部階段的觀點。此外,中國古代哲學對“道”的理解都有著“道”無處不在的理念,《內經》中把“陰陽”看作是天地間的道也可以證明《內經》認為“陰陽”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
其次,《靈樞·陰陽離合論》中還提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這就使“陰陽”的范疇從“天地”“萬物”“生殺”的抽象內 容走向了“一”“二”“三”“十”“百”“千”“萬”這樣的具體內容,最后演化到不可勝數。如此,便與“天地”與“萬物”相對應,確保了其在自然界萬物中存在的“普遍性”。至此,“陰陽”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性有了充分的佐證。
然而,亦有觀點認為,陰陽學說離其更進一步還差在它沒有唯物史觀作為指導和缺乏對意識與物質的正確認識,導致了《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提出:“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征兆也。”這就把陰陽這對矛盾所概括的內容作了近似明確的劃定,給陰陽這對矛盾套上了“具體”的枷鎖,故而在陰陽理論概括事物的規律就有了“有形”的限制:凡為表露于外的、熱的、實的、開放的、無形的、急速的屬于陽性特征;凡為收藏于內的、虛的、晦暗的、屈縮的、有形的、平靜的、遲緩的屬于陰性特征。這使得“陰陽”在離開自然界后用于概括社會、思想、文化、歷史等抽象的運動趨勢產生了局限性,故有“陰陽屬性歸類所依據的是主觀直覺所得材料,本身帶有或然性,未必能恰如其分地真正代表事物運動狀態的特性。陰陽屬性作為運動形式的表述是粗略地。因而牽強附會、發生誤差的事屢見不鮮”之說[8]。例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無產階級于資產階級”等這些在唯物辯證法中經典的矛盾都因為幾乎脫離具體的自然表象而無法用陰陽的矛盾體系來概括。總結這類觀點就是“陰陽范疇和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范疇有著本質的區別,矛盾范疇對于各對立面的性質除了指出它們是對立統一外,不加任何具體限定,而陰陽卻包含著一定的具體內容,對對立雙方的性質作了某種限定和概括,因此,陰陽僅是矛盾中的一類,是矛盾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5]。
對于這樣的觀點也有人以“陰陽并不類似電學中的陰陽那樣‘是矛盾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即物理學上的特定矛盾,而是泛指客觀世界一切對立(即矛盾)而言”[9]的論點來反駁。此觀點把陰陽不看作一種具體矛盾,從而來泛指一切客觀事物,包括非自然的領域與現象的產生、發展和消亡。其將陰陽完全抽象化,只來概括事物兩方面,這種方法雖說可以“解決”陰陽理論上的局限,但卻使得陰陽失去了其豐富的內涵,任何的兩點論都可以套用這種方法來與唯物辯證法保持一致。顯然這是缺少說服力的。
筆者認為陰陽存在的局限是可以克服的。《內經》中把人與自然看作一個整體,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觀念貫穿于《內經》的各個方面。其既有“合于陰陽,調于四時”順應自然的方面,又有“子午流注”“因時制宜”等利用自然規律指導臨床實踐的理論。可見,“陰陽”理論的運用在人體和自然界是統一的。在唯物辯證法觀念中,人類社會屬于自然界,這個社會的范疇包含了階級、文化與歷史。雖然《內經》中“陰陽”對自然界的解釋范疇直接運用到某些方面比較牽強,但《內經》認為人與自然與社會是一個整體,陰陽對人體本身的解釋概括就可以推演到那些不那么“自然”的領域中去。人體中的陽氣(腎陽)起著推動氣血與各項生理功能、主宰生長與發育、鞏固自身抵御外邪的作用;陰氣則有著營養全身、調和制約的功能。生命活動產生的濁以及與陽化生的衛氣所對立的外來病邪也都屬陰的范疇。由此就可以將抽象矛盾的兩個對立面中新事物、歷史前方的、先進的、推動歷史進程的、自身的、激進的、發展的概括為“陽”,將舊事物、落后的、歷史后方的、阻礙歷史進程的、保守的、外部的、循環制約的定義成“陰”。用這樣的方法來看待一些“陰陽”理論之前存在局限的問題,就有克服其局限的可能。例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在歷史前方的和新事物的屬性,故可劃分為“陽”的部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有阻礙歷史進程的因素,故可劃分為“陰”的部分。生產力有著發展的內容,屬陽;生產關系有著調控制約的內容,屬陰……如此也給分析社會各個方面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亦給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提供了新的靈感。
總之,一些觀點在兩者的普遍性比較時,發現了“陰陽”無法概括的范疇,認為“陰陽”出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局限。而筆者嘗試略微延展了《內經》的思想,通過“陰陽”理論中人體-自然-社會三位一體的整體觀念來“以小看大”,用陰陽解釋人體的方法解釋了傳統方式解釋不了的內容。這樣,兩者在普遍性的兩個方面(普遍的范疇與全部的階段)就都達成了一致,進而“陰陽”的普遍性與“矛盾”的普遍性達成了一致。
3 “矛盾”與“陰陽”兩者的結果與歸宿
滅亡是一切事物發展的終點,但不會歸于“寂滅”,這是唯物辯證法中對事物的認識。這種認識來源于其對“矛盾”最終歸宿的觀點,“矛盾”認為雙方力量處在此消彼長的不斷變化中,一旦矛盾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便引起雙方地位的相互轉化,于是新矛盾取代舊矛盾,新事物取代舊事物[1]235。可見,唯物辯證法理論中不存在永恒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會被新的事物所替代,矛盾的一方發生巨大變化后就不是原來的那個統一體了,而是以“揚棄”的方式成為新的統一體。
與“矛盾”不同,從《內經》對“陰陽”的理解來看,陰陽作為一個整體只有兩種結局。其一,外在表現為平衡斗爭的狀態永無止境地進行下去。其二,在陰陽某一方的劇烈變動后失去平衡,統一體徹底崩解,即所謂“陰陽離合,精氣乃絕”。舉例而言,《內經》認為人體的陰陽離散后其統一關系消失,人的生命就此終結,這個對立統一的矛盾就徹底消失了。而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卻認為矛盾運動一旦停止,生命也就結束,死亡隨之而來,但即使有機體生命結束,也不是矛盾運動的終止,因為同化和異化的矛盾運動雖然停止了,而物理與化學的矛盾運動仍繼續進行。《內經》中并沒有如此新矛盾會替代舊矛盾的觀念,而是在解釋人體時,表現為矛盾的徹底消失,其在解釋自然與社會事物時,表現為永遠平衡的斗爭。唯物辯證法的矛盾最終都是要被“解決”的(永恒的矛盾也會在各個階段得到階段的解決),而“陰陽”最終不是僵持就是消失。誠然,《內經》中也有疾病傳變的概念,但這也并不能理解為新矛盾替代舊矛盾。這并沒有一個替代的過程,只是引入了新的因素讓矛盾內部各方面的矛盾變得更加復雜,只是一種“由此傳彼”而非“此消為彼”。兩者在歸宿上出現如此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上文所說陰陽學說對斗爭性的認識較為單一,不承認劇烈斗爭會產生正面變化。“陰陽”在理解事物整體動態發展上出現了“力不能及”的方面。
4 總結
綜上,本文通過對“陰陽”的普遍性與“矛盾”的普遍性進行了比較,探討了兩者所涵蓋事物范疇的關系;通過對比二者對同一性與斗爭性的認識程度,分析了二者對“對立統一”的理解;通過對其歸宿與結局的對照,探尋了兩者對事物發展的判斷。據此可見,陰陽的矛盾與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在以上三個方面都呈現出了部分的高度相同,但卻依然不能說“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學說及規律可以用中國傳統陰陽論加以詮釋和表達”[10]。基于上述比較,筆者將《內經》的思想稍做了延伸,擴充了“陰陽”的普遍性;提出在涵蓋范疇與對“同一性”的認識上二者有著高度相同的認識,在斗爭性認識上“陰陽”有所欠缺,且基于此使二者的歸宿產生了分歧等還有待完善的觀點;同時也提及了一些學界之前的觀點,并且對其表達了贊同或是持保留意見。
通過比較分析可知,雖然陰陽的矛盾蘊含了明確的樸素唯物主義與自發的辯證思想,達到了一定的哲學高度,但其與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相比存在的最大缺陷并不是樸素唯物主義的局限,而是其對斗爭性認識的不足所導致的,故其無法準確把握事物整體的動態發展。陰陽的這種局限使其無法領會新舊事物不斷發展與社會歷史內在更迭的精髓。其在解釋自然變化時陷入了“循環論”與無限的“平衡斗爭”中,因此在面對社會歷史、人文倫理時,雖然可以描述其中的矛盾雙方,卻不能解釋其中的變化。
《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主要用于傳統醫學的理論與實踐,在此范圍內陰陽對世界的理解已經可以應對,但要使陰陽理論能夠在哲學上發揮更大的指導性作用,就需要繼續發展它的理論來克服自身的局限。在歷史上,《內經》之后少有典籍再對陰陽學說作出更進一步的闡述。新時代的背景下,應當充分發掘中國傳統哲學的潛力,在充分認識傳統哲學、了解傳統哲學的優勢與局限的基礎上,對傳統哲學作出新的認識與新的理解,使其有更加寬廣的適用領域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