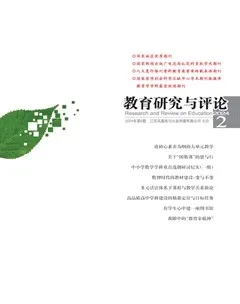我眼中的“教育家精神”
現(xiàn)在大家都在談“教育家精神”。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呢?一下子也說不清,但是一說到“教育家”,似乎總有幾幅畫面在心里揮之不去。
一幅畫面是陶行知先生和孩子們在一起的照片。陶行知先生低眉順目望著孩子們,那種慈愛的神情,讓人動容。在中國要說起“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大概是公認(rèn)的了。但是陶行知先生作為教育家的精神是什么呢?我想,應(yīng)該是對兒童的愛。愛,不是寵溺,不是縱容,愛是赤心待人,成人渡人。
我們對陶行知先生常常有一種斷章取義的理解,似乎陶行知先生只是一個宗教徒式的奉獻(xiàn)主義者:“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實際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首先是致力于解放兒童的教育,是為每一個生命求真爭自由的教育。
他說:“要解放孩子的頭腦、雙手、腳、空間、時間,使他們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從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解放他的頭腦,使他能想;解放他的雙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巴,使他能說;解放他的時間,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會去取得更豐富的學(xué)問;解放他的空間,不把他的功課排滿,不逼迫他趕考,不和家長聯(lián)合起來在功課上夾攻,要給他一些空閑的時間消化所學(xué),并且學(xué)一點他自己渴望學(xué)的學(xué)問,干一點自己高興干的事情。”
他說:“兒童的生活,是一面社會的鏡子。”如果我們現(xiàn)在也用這樣的鏡子去看我們的社會現(xiàn)實,難道不會讓我們這些后來者赧顏嗎?教育不應(yīng)該用來淘汰人,而應(yīng)該造就人;教育不應(yīng)該讓人厭惡這個世界,而應(yīng)該讓人熱愛這個世界;教育更不應(yīng)該讓人有死的決心,而應(yīng)該讓人有生的熱望。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陶行知先生的“愛”,或許才是真正地理解一個教育家的偉大。
說到陶行知先生,很多人都會以為他是一個“泥腿子”教育家。事實上,他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xué),是大哲學(xué)家、大教育家杜威的及門弟子。他的教育著作最大的特點,就是將精深的理論轉(zhuǎn)化為最平實的人人能懂的語言,而不是相反。如果說當(dāng)今需要培植教育家精神,那么不以莫名其妙的概念來唬人,說人人能聽懂的話,大概應(yīng)該是第一步。這是關(guān)于陶行知先生的題外話。
第二幅畫面和梁漱溟先生有關(guān)。當(dāng)時,他正在山東鄒平搞鄉(xiāng)村教育運動,目光炯炯,望之肅然。他在鄉(xiāng)村的教育是伴隨著鄉(xiāng)村的改造一起的,這一點十分重要,也是我以為的教育家精神的第二個重要內(nèi)涵,那就是致力于社會改造的教育變革。教育不應(yīng)該單純地為了順應(yīng)社會,更不應(yīng)該在不好的社會里助紂為虐,而應(yīng)該是指向更好的社會的。
梁漱溟先生說:“今后要設(shè)施(設(shè)法實施——引者注)教育,必先體認(rèn)得社會的出路所在,而把握之以為設(shè)施教育的指針,不要再盲目地辦教育。——這是更要緊的一層。”我以為這是十分剴切的觀點。現(xiàn)在有些人辦教育是缺乏觀照人類發(fā)展的眼光與勇氣的,一味以迎合社會為目的,甚至因為利益和認(rèn)識的問題,誤導(dǎo)社會,從中干名漁利。這樣的教育工作者,被社會捧得再高,離教育家的名號其實還是很遠(yuǎn)。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作品里用了一個詞“Kitsch”,我們翻譯成“媚俗”。我以為,“Kitsch”所指何止媚俗,還有諛權(quán)和逐利,所以“媚俗”這個詞語似乎還不足以表達(dá)這種行為的可惡。如果一個社會的教育陷入“Kitsch”的行為中,并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對于社會非但無益,還是大有害的。不把教育作為社會的附庸,而看作一種引領(lǐng)社會發(fā)展的力量,看準(zhǔn)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方向,就以移山填海的勇氣去做,這才是教育家應(yīng)有的追求。一個社會的教育工作者應(yīng)該眼中有道,手中有術(shù),心中有愛,唯有如此,方能配得上“教育家”的稱號。
說到梁漱溟先生,我們很多人都會以為他的教育追求就是復(fù)興儒學(xué),其實這是大大的誤解。梁漱溟先生不僅精通儒學(xué),而且對于佛學(xué)和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他的教育思想與其說是東方視角,毋寧說是人類眼光。以人類視角看待教育(如果可能,還可以天下視角看待教育),才能夠真正把握教育發(fā)展的方向。
第三幅畫面是胡適先生的。彼時他和蔣介石并排而坐,談笑自若,倜儻瀟灑。相比較而言,作為當(dāng)時的政治首腦,蔣介石反倒顯得拘謹(jǐn)局促。胡適先生說:“只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才能有高價值的創(chuàng)造,而這既是我的希望,也是后世教育者所要努力的方向。”他還說:“我們當(dāng)時曾引杜威先生的話,指出個人主義有兩種:(1) 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它的性質(zhì)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群眾的利益。(2) 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它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dāng)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dāng)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dāng)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jié)果要負(fù)完全責(zé)任……只認(rèn)得真理,不認(rèn)得個人的利害。這后一種就是我們當(dāng)時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教育既然是指向未來的,那么因循守舊、缺乏批判精神的教育,就不足以開創(chuàng)我們的明天。所以,我們的教育就需要培養(yǎng)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現(xiàn)代人,也因乎此,教育者自己就首先必須是這樣的人。
當(dāng)然,我之所以專門提到胡適先生,也是因為他和陶行知、梁漱溟這些教育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埋頭苦干”。站在岸邊指手畫腳的人不少,真正愿意挽起褲腿躬身拉纖的苦力不多。但要想成就中國的教育,成為中國的“教育家”,恐怕就非得要有這樣的“苦力”精神不可的。
今天我們倡導(dǎo)教育家辦學(xué),還應(yīng)該清楚的一點就是我們需要的是“中國的”教育家,要辦的也是中國的教育,中國有很悠久的教育傳統(tǒng),也有具有世界影響的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我所列舉的三位,或者放眼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中有所建樹的大家,無不是中西融通,推陳出新的,但關(guān)鍵在于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顢頇自大,而是真正從教育的本質(zhì)出發(fā)去思考教育,去從事教育實踐。
能以愛心對待每一個學(xué)生,能以改造社會的勇氣和決心去改革教育,能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有學(xué)識,有追求,肯擔(dān)當(dāng),言為士則,行為世范,這大概就是教育家應(yīng)該有的精神了。以這樣的精神去辦學(xué),我們國家教育之強(qiáng)盛當(dāng)可期待。
現(xiàn)在國家強(qiáng)調(diào)“教育強(qiáng)國”,將教育放到了民族復(fù)興的高度去認(rèn)識,這是教育發(fā)展的機(jī)遇,也是教育界同仁當(dāng)仁不讓的責(zé)任。以“教育家精神”來辦學(xué),也自然應(yīng)該是題中之意。然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教育家也不是完全靠培訓(xùn)來培養(yǎng)的,更不能靠名額分配去選拔出來。教育家之形成,一定是依賴良好的教育文化環(huán)境的。
這種文化氛圍中的第一點就是尊重差異、鼓勵發(fā)展。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每個生命也都是在成長中的,那種從一出生就讓孩子進(jìn)入拼殺的“戰(zhàn)場”的文化是培養(yǎng)不出教育家的。
第二,這種文化還應(yīng)該有對兒童成長規(guī)律和教育科學(xué)的敬畏。全社會應(yīng)該有一個共識,就是將教育交給真正懂教育的人去辦。
第三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寬容,要為教育家的形成準(zhǔn)備寬松的思考、研究、實踐的環(huán)境。如果先入為主,將教育工作者的手腳都束縛住了,教育家就很難形成。當(dāng)然,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我們要做的是對生命自由發(fā)展的尊重,對生命成長規(guī)律的尊重,還要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唯其如此,教育才能成為新教育,教育培養(yǎng)出的人才能成為新人。培養(yǎng)教育家的目的并不在名號,而在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于我們的未來。
(鄭朝暉,上海市建平中學(xué),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