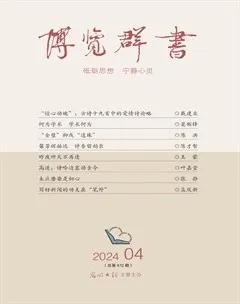徐坤:與時代同行
舒晉瑜
徐坤,1965 年出生于沈陽。文學博士。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小說選刊》雜志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文化名家。已經發表各類文體作品 500多萬字,出版《徐坤文集》8 卷。代表作有《先鋒》《廚房》《狗日的足球》《神圣婚姻》等。曾獲老舍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優秀長篇小說獎、莊重文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以及《人民文學》《小說月報》等文學期刊優秀作品獎。長篇小說《野草根》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07 年十大中文好書”。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德、法、俄、韓、日語、西班牙語。
印象中,徐坤總是笑瞇瞇的,說話不疾不徐,讓人如沐春風。她評價自己年輕時的文章很幼稚,但有激情,敢沖撞,想當前鋒,想射門,有快感;年老時的文章、技術純熟,但倦怠,圍著球門子轉,兜圈子,看熱鬧,就是不往里進球,知道射門以后會有危險后果出來。
文學創作起步時,她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員,短短兩年時間,《白話》《囈語》《先鋒》等中篇小說的問世,使她一度成為文壇熠熠生輝的明星。她研究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犀利地透視世紀末人文精神的衰落,叩問知識分子的靈魂,探尋欲望與掙扎背后的心靈,也溫情款款地書寫親情、友情和愛情。
2022 年底,徐坤出版了長篇小說《神圣婚姻》。這是一部帶有鮮明的徐坤風格的作品。讀完之后,你會覺得,徐坤又回來了,那個寫《廚房》《狗日的足球》的徐坤,那個灑脫智慧的徐坤,給我們講述新時代的北京故事,講得神采飛揚,講得酣暢淋漓。小說探討的主題切近生活肌理,不僅寫出知識分子的堅守,也寫出對市民階層與城市精英、知識分子與海歸青年遭遇的審視。小說融入了她豐富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富有魅力的敘述語言、張弛有度又簡潔凝練的敘事風格。這也是她認真思考、嘔心瀝血打造的一部符合新時代特征的長篇,篇中每個人物小傳,她都寫下了幾萬字的筆記。
她希望充當尋常百姓的代言人,為生民立傳,同時也希望能真實記錄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記錄世事遷徙和風起云涌的變革,以及其中的人心嬗變。
作家王蒙曾稱徐坤“女王朔”
記者:您曾說過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隨社科院同行下鄉鍛煉的那一年,回來就按捺不住地要寫小說。能具體談談是怎樣的影響嗎?
徐坤:20 世紀 90 年代初,我剛畢業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一身學生氣,帶著年輕人成長過程中普遍的叛逆和沖撞精神。80年代的結束和 90 年代的開始,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來說,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剛參加工作不久,我就隨社科院的幾位博士碩士一起到河北農村下放鍛煉一年。遠離城市,客居鄉間,憂思無限,前程渺茫。在鄉下的日子里,我們這群共同繼承著 20世紀80 年代文化精神資源的20來歲的青年學子,經歷淺,想法多,閑暇時喜歡聚在一起喝酒清談,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播放中關村淘回來的各種國外藝術片,在高粱玉米深夜拔節聲中,在驟雨初歇鄉村小道咕吱咕吱的泥濘聲里,凌虛蹈空探討國家前途和知識分子命運,雖難有結論卻興味盎然。回城以后,這個小團體就自動解散,然而,在鄉下探討的問題以及與底層鄉村民眾打交道時的種種沖突和遭際卻一直縈繞我心,揮之不去。終有一天,對世道的焦慮以及對于前程的思索,催使我拿起筆來,寫起了小說——相比起“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做學問方式,激情與義憤噴發的小說更能迅捷表達作者的情緒。
記者:中篇小說《白話》讓您一舉成名,《中國作家》《人民文學》《當代》等刊物幾乎同一時間刊發您的系列小說。您如何評價那一時期的創作風格?
徐坤:在 1993—1994 兩年間,我以《白話》《先鋒》《熱狗》《斯人》《囈語》《鳥糞》《梵歌》等一系列描寫知識分子的小說登上文壇,文化批判的鋒芒畢現,又都是發表在《中國作家》《人民文學》《當代》這三家大刊物上的,立即就引起了讀者和批評家的廣泛關注。年輕時的寫作,十分峻急,仿佛有無數力量催迫,有青春熱情鼓蕩,所有的明天,都是光榮和夢想。仿佛可以乘著文字飛翔,向著歌德《浮士德》中“靈的境界”疾馳。
記者:《先鋒》刊發于 1994 年第 6 期《人民文學》時,評論家李敬澤首先以“歡樂”形容它,說“如果說以艱澀的陌生化表現世界并考驗讀者曾是一種小說時尚,《先鋒》對世界、對讀者卻擺出了親昵無間的姿態”。評論和作品相得益彰,讀來特別過癮。您還記得當時作品發表后的情景嗎?
徐坤:相當激動!接到通知稿子采用后,就天天等著《人民文學》第 6 期出刊。那時我在社科院亞太所工作,住在學院路,總去學院路的五道口新華書店看看雜志到了沒有。前一次去五道口書店還是排隊去買《廢都》。5 月底的一天,終于看到了有賣,只剩下一本了。趕緊買下來,拿起雜志一翻,哇!第 6 期整個卷首語都說的是《先鋒》。激動得我啊,立刻,騎著自行車就直奔了王府井新華書店,因為知道那里的書報雜志到得多。十多公里的路,沒多久就騎到了,也不覺得遠。到了王府井書店,一下子買光了店里的 30 本刊物!那時的雜志是 3塊錢一本,花了我 90塊錢,差不多是一個月的工資。
記者:那時候人們對文學的虔誠和激情,很令人羨慕啊。
徐坤:是的。那期的卷首語,我幾乎是能夠背下來,還曾一筆一畫地抄到了本子上。后來才知,是個跟我一般大的年輕人寫的,叫李敬澤,剛升任了小說組的主任。那是他寫的第一篇卷首語,“《先鋒》是歡樂的;如果以艱澀的陌生化表現世界并考驗讀者曾是一種小說時尚,《先鋒》對世界、對讀者卻擺出了親昵無間的姿態。它強烈的敘述趣味源于和讀者一起開懷笑鬧的自由自在;它花樣百出的戲謔使對方不能板起面孔……”寥寥 600 字,將近 30 年,關于《先鋒》的評論也有千百篇了,我認為沒有一篇能超過它。
記者:王蒙先生說您“雖為女流,堪稱大‘侃。雖然年輕,實為老辣,雖為學人,直把學問玩弄于股掌之上,雖為新秀,寫起來滿不論,掄起來云山霧罩,天昏地暗,如入無人之境”。您是怎樣理解的?
徐坤:那是王蒙老師發表1994 年《讀書》雜志“欲讀書結”專欄上的文章。我理解他的本意,一是震驚,剛進入上世紀 90 年代沒幾天,年輕人寫的東西已經變成這樣后現代了;二是希望文壇多出幾個王朔,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都能夠以年輕的話語,沖撞的身姿,把 90 年代以來的文壇特殊的沉悶的日子捏出個響來;三是希望年輕寫作者除了戲謔、解構、嘲笑外,能不能再穩健莊重些,能有一些建構的思想意見表達。他的話讓我深受教益。從此以后就逐漸收斂起鋒芒,努力在文章中做一些文化建設性的工作。
創作上的拓展和深化
記者:早期的寫作,您以知識分子題材為主,后來您寫《廚房》《狗日的足球》《午夜廣場最后的探戈》《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愛你兩周半》《野草根》等,不斷關注著女性的生存狀況,書寫她們獨特的生命體驗。這種轉變的契機是什么?
徐坤:20 世紀 90 年代初,剛開始寫小說那會,不考慮男女,只是按先賢先哲大師們的樣子,追尋文學審美的傳統精神之路,寫《熱狗》《白話》《先鋒》《鳥糞》,寫我熟悉的知識分子生活,探究人類生存本相,相信能成正果。后來,某一天,女權主義女性主義潮涌來了,急起直落,劈頭蓋臉。忽然知道了原來女性性別是“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告訴我們,子宮的最大副作用,是成為讓婦女受罪的器官。
《廚房》寫于 1997 年,距今已經有 25個年頭過去。依稀能記得,原先想寫的是“男人在女人有目的的調情面前的望而卻步”,寫著寫著,卻不知最后怎么就變成了“沒達到目的的女人,眼淚兮兮拎著一袋廚房垃圾往回走”。之后,《廚房》的主題給批評家演繹成了“女強人想回歸家庭而不得”,所有同情方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午夜廣場最后的探戈》,寫在 2005 年,距今也已經 17年。2005年的夏季,不知在哪家廚房待膩了鉆出來放風的那么一對男女,開始在大庭廣眾之下的居民區的午夜廣場上發飆。他們把社區跳健身舞的街心花園廣場,當成了表演弗拉門戈、拉丁、探戈舞的舞臺,男女每天總是著裝妖艷,嘚瑟大跨度炫技舞步,像兩個正在發情的遺世獨立的斗篷。最后以女方在大庭廣眾之下摔跟頭收場。
記者:您有沒有想過把《廚房》和《午夜廣場最后的探戈》兩篇小說放在一起比較一番?
徐坤:《廚房》和《探戈》兩篇中間跨度有近十年,卻又橫亙了兩個世紀的小說,前后放在一起考察時,連我自己也不禁驚訝,十余年來,竟然用“廚房”和“廣場”兩個喻象,用“拎垃圾”和“摔跟頭”的結局,把女性解放陷入重重失敗之中。小說的結局都不是預設的,而是隨著故事自己形成的。但愿它不是女巫的讖語,而只是性別意識的愚者寓言。
十年一覺女權夢,贏得人前身后名。樂觀一點想,“廚房”和“廣場”的意象,如果真能作為跨世紀中國女性解放的隱喻和象征,二者的場面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不光活動半徑明顯擴大,姿態和步伐也明顯大膽和妖嬈。如果真有女性的所謂“內在”解放和“外在”解放,我真心祝愿二者能夠早一天統一。
《野草根》被評價為女版的《活著》
記者:您的長篇小說《野草根》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07年十大中文小說”,這部作品在文壇獲得諸多好評。
徐坤:當年這部小說被評為“2007 年十大中文小說”,但在今天看來價值也是被低估了。《野草根》堪稱女版的《活著》。小說講述的是三代女人在各種艱苦環境下的堅持與隱忍、不斷與命運抗爭的故事。知青于小頂、于小莊與后代夏小禾三個女人的卓絕成長與紅顏薄命,圍繞她們身邊的男人們的暴戾、頹敗與傾情,構成廣袤東北大地上 40年的最為壯觀的風俗風情畫和最為激越的命運交響曲。
作品的地域背景放到我的出生地東北沈陽,時間跨度則從知青下鄉到當下,筆觸深入底層女性的成長、情感、事業中,而真正的指涉卻是對女性命運的關照。不管命運如何多舛,三代女性始終在生活的夾縫中掙扎奮斗、狂歡跳躍,她們宛如那隨風搖曳的野草,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生生不息,盎然豐沛。
記者:《野草根》以追憶和倒敘的方式講述一個家庭三代女性的故事,折射近半個世紀里女性殘酷的命運。這部作品的創作源于什么?
徐坤:2006 年五一長假,我應邀去參觀沈陽世博園,也順路回家探望父母。回來的路上,堂妹為讓我多觀些風景,特意多繞了些路,將車子一路從棋盤山和東陵山間的森林里穿過,最后竟將車子拐到了東陵山野的墓地上,說這兒離姥姥姥爺的墳不遠了,我領你順道去看看吧。
她的姥姥姥爺也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我們徐家去世的幾個親人都葬于此。這還是我頭一次在這個季節里來掃墓。一見到奶奶那座栽著柏樹的墳我就哭了,淚如泉涌。手撫著墓碑,是熱的,似覺有奶奶的體溫在上面,分別之日竟像昨天!那一刻我真覺得奶奶好像還活著,她知道我們來看她,也能聽到我們在跟她老人家說話。我和小堂妹都是奶奶給一手帶大的,我在奶奶身邊一直長到 15 歲,考進遼寧省實驗中學后才住校離家,對祖母的感情遠勝過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我總是在思鄉的夢里和她老人家頻頻相見……那天的墓地方圓幾十里幾乎沒有人,靜寂無邊。只有隱約的遠山、青蔥的綠草、夏季的風聲和腳下的墳塋與我們為伴。站在芳草萋萋一望無際的墓地,我的心里霎時涌起無盡的惶惑和迷茫,生與死的問題頭一次如此鮮明地涌上心間。
我當時想的問題跟《野草根》書里夏小禾想的并不一樣,我想的竟是:再過幾十年,20 年或者 30 年,我也不過就是回到這里來吧?到時候也埋在這里的祖母和親人們的身邊化作一抔黃土吧!那時候埋葬我的是誰?又會有誰會來掃墓看望? 20 年或者 30年是個很快的時日,倏忽即逝,很快就來。那么,我們如此辛苦地打拼奮斗又有什么意思?活來活去的意義究竟何在?
回北京后,我仍然久久不能平靜。就這樣,原本要做的有關世博園的歡樂文章被擱下了,我開始寫《野草根》,寫生與死,寫底層人民蓬勃的生命力,寫中國人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學中的原動力。
《神圣婚姻》與這個時代
記者:李敬澤以《西游記》中西天取經的降妖除怪作比《神圣婚姻》的敘述,提出“神圣”是一種態度和方法——您其實是在表達一路通關打怪,通往奔赴神圣婚姻的路上?
徐坤:對,《神圣婚姻》這本書的宗旨是,心中有敬畏,人生有修行。我們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在婚姻的相處相守相敬相愛當中,實際上就是不斷修行,走向神圣的過程。面對我們時代各種各樣的選擇和疑難,要在俗世中,在人間,在婚姻中,在多元的價值沖突中去求神圣,從而獲得一份屬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
記者:這部小說是新時代的在場敘事,與時代的連接十分緊密,故事的發生從 2016 年元宵節開始,結束于 2021 年秋天,內容涉及很多時代的熱點和痛點問題,比如買房、假結婚、支教、扶貧等,各種新時代的元素巧妙地融入故事,同時讀起來又非常暢快,能否談談和時代“貼身肉搏”是怎樣的創作狀態?
徐坤:巴爾扎克說,作家要充當時代的“歷史的書記官”,我們的術語說,作家要與時代同行,為生民立傳。我特別希望自己能真實記錄下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趕上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風起云涌,風云際會,這個時代的世事遷徙與人心嬗變都特別有意思,跟以往都不一樣。
現實題材寫好不容易,不是有句話嘛,叫作“畫鬼容易畫人難”。一個作家,與時代“貼身肉搏”,需要膽識,氣度,技巧,需要有對生活機敏的捕捉能力,高度的分析萃取能力,必須抓素材時像記者,追線索時像警察。當然,高高在上、主導一切的仍舊是我們的價值觀。最終必須是由一個強大的價值觀主導作品的走向。
其實我不用刻意去寫新時代,因為我就置身在新時代之中,新時代的風撲面而來,我跟這個時代息息相關,就連呼吸里都滾動著新時代的清香醬香和濃香氣味。新時代同時也會主動找上門來讓我書寫。故事的發生從 2016 年元宵節開始,小說第一章里的一切故事和細節,都是真實的,矛盾沖突就是從這里起來的。緊跟著故事的走向,新時代或說當下的熱點問題緊跟著就來了。買房、假結婚、支教、扶貧等,各種新時代的元素蜂擁而來。但是怎樣編織和處理,還需要技巧。
我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地在北京,實際又超越了北京、跨出了北京,從北京到澳洲,從東北鐵嶺到四川安嶺,幅員遼闊,人物眾多,活動半徑大。小說里的故事都是發生在我身邊的真人真事,有些還是我家族中的事情。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她們在生活中的堅韌和淚水,也看到了他們的奮斗與犧牲。我希望自己能夠充當他們的代言人,與時代同行,為生民立傳。
記者:您一直關注女性生存狀況,書寫她們獨特的生命體驗和生存困境。上次采訪中您提到中國婦女的解放之路,已經從“廚房”寫到了“廣場”,那么下一篇,是否就該是“廟堂”了?《神圣婚姻》讓女性進入廟堂了嗎?
徐坤:是的。這部《神圣婚姻》,我就有意讓女性進入了“廟堂”,讓她們成為新時代的話語中心,能夠充分主宰自己和他人的命運:顧薇薇是律所合伙人,企業技術專利和國際知識產權方面的專家;毛榛是社科院宇宙數字化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分管黨務與人事;樊梨花是世界 500 強企業的董事長,殺伐決斷,雷厲風行。這些女性的獨立和解放,是時代的進步使然,也是中國邁向現代化強國發展進程中的必然。
記者:是什么契機使您開始《神圣婚姻》的寫作?
徐坤:這本《神圣婚姻》的故事早在五六年前就在我腦子里有雛形了,直接導火索或說靈感,就是我家族親人中遭遇的在京假結婚買房事件,親人受到很大傷害。我也感到十分憤懣。我一直想寫出來,但是一直沒有時間寫,也正好借機等待故事發酵,看看生活中真實的事件最后到底是個什么結局。這幾年,我坐在電腦前的時間突然就充盈了。于是才有了大塊時間完成了這部《神圣婚姻》。
記者:為什么叫《神圣婚姻》?其實小說中幾對情人和夫妻的關系在社會價值變化的過程當中都發生了變化,有為兒子在京買房假離婚真結婚的,有被多年男友拋棄的……《神圣婚姻》里的婚姻其實并不神圣,沒有一個人的婚姻是從一而終或完整的。情感變得特別脆弱,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改變了婚姻——您如何理解“神圣”?以“神圣婚姻”為題,是心存敬畏還是某種反諷?
徐坤:《神圣婚姻》書名的緣起,有個從“神圣家族”到“神圣婚姻”的過程。多年前,恰好讀到作家朋友梁鴻寫了《神圣家族》,是寫故鄉梁莊的,我就覺得這個題目太好了,當時就脫口而:我也要寫一個《神圣婚姻》。當時,說這話的時候,也是在一個朋友聚餐的場合,在座的一位批評家朋友聽了,連連稱贊,大呼好好!說這個太牛了!說你要趕緊寫出來!我一聽,更是受了鼓勵,忍不住摩拳擦掌,籌劃著什么時候一鼓作氣寫出來。
當然,我們都知道梁鴻的作品是引用馬恩的經典著作《神圣家族》的名字,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這四個字是具有諷刺的意思,在書中他們闡述了物質生產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思想,批判了鮑威爾及其“神圣家族”伙伴把“精神”和“群眾”絕對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
有了“神圣婚姻”這個想法后,我的故事便找到了切入點,以婚姻為線索編織經緯,形成一道一道的故事,各色人等、各種婚姻形態次第登場,既虐浪笑傲,也正大光明,在聚光燈下開始了表演。而新時代的北京,就是提供給他們表演的最大舞臺。這里的人群來來往往,懷著夢想,懷著意趣,也聚散離合,也飛短流長,更是前赴后繼,更是英勇無畏,在漫長的生命旅途中,在日常煙火和婚姻生活中,開始了探討和追求神圣的過程。
記者:小說中多次出現王蒙及其作品,從一開始的《青春萬歲》到《中華玄機》,為什么選擇王蒙并以這種特定方式走進《神圣婚姻》,您是如何考慮的?
徐坤:為什么會選擇王蒙并以這種特定方式走進《神圣婚姻》?是因為王蒙對于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和心靈影響太大了。他個人的經歷和創作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小說中多次出現王蒙先生及其作品,從一開始,孔令健所長覺得自己是沿著《青春萬歲》結束時,楊薔云、張世群 1953 年在北京郊區畢業告別那會子往前活,走過國家的幾個五年計劃后,終于來到新時代的今天,“十三五”規劃收官和“十四五”規劃開啟;到中間章節,程田田鄉村支教時遇到文旅部下去掛職鍛煉的潘高峰,見他桌上擺著王蒙的當年的新著《中華玄機》;初稿時的結尾,也是讓程田田和潘高峰在天安門廣場看完升旗后,眼望廣場上飛起的白鴿,朗誦起《青春萬歲》的詩句: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寫這本《神圣婚姻》時,我也是想試試,在我自己快要進入老年疲沓時(我今年虛歲 59),還能不能嘹亮高亢地接上一曲新時代的《青春萬歲》?或說是《青春萬歲》的續篇?就從 1953 年楊薔云、張世群他們告別那時候寫起,經歷過孔令健一代研究所的學子,最后定格在更年輕的 90 后一代程田田和潘高峰身上,讓每一時代的文化建設者、時代潮流的舉旗人,都永遠激情燃燒,青春萬歲,永葆赤子之心。
(作者系本刊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