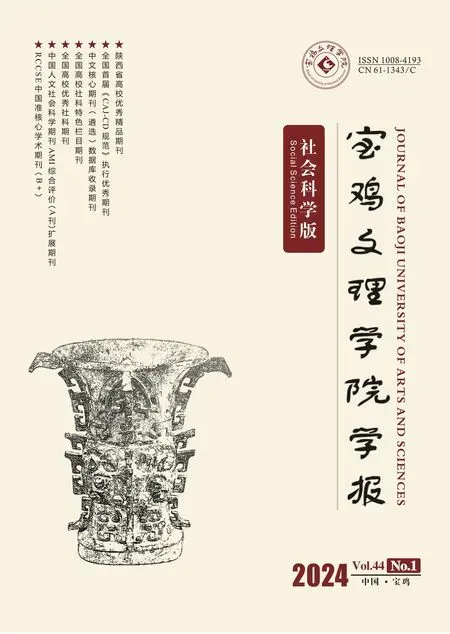社會史視角下書寫考古學史芻議
——從《殷虛發掘員工傳》的史料價值說起
李小東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一、引言
2021年,民國時期殷墟發掘重要參與者石璋如所著《殷虛發掘員工傳》(以下簡稱《員工傳》)出版[1]。是書根據石璋如20世紀30年代的田野手記整理,詳細記載了1928至1937年間,參與15次殷墟發掘的101位民工與46位史語所職員的日常生活與學術事跡。其中,有關101位考古民工的記載,除零星見于《石璋如先生口述歷史》《董作賓先生全集》《徐旭生日記》《夏鼐日記》等史料外,均系珍貴的獨家史料。
考古工作中形成的各類材料,是考古學史的基本史料。然而,目下考古學史成果對《員工傳》的關注相對有限①,該書大量有關考古民工及殷墟發掘期間社會生活的記述,沒有得到充分利用②。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目下考古學史書寫主要基于學科史或學術史視角。學科史視角下,考古學史重在梳理討論考古學自身的理論方法發展史;學術史視角下的考古學史,則主要關注考古學與近代學術發展變化間的互動。因而目前對《員工傳》的利用,主要是梳理該書所載考古學家的學術活動③。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史作為一種新的史學研究領域與視角,開始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社會史注重自下而上地審視歷史發展進程,從社會的細微之處重審宏大敘事。此后,不僅社會史研究本身快速發展,社會史視角亦融合入學術史研究之中。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叢書《史學卷》,即注重“從社會視角觀察,注重學科的發展演化及其與社會的互動”[2]。近年來學界更是開始思考“多維度地研究學術與社會之間的互緣、互動,重視學術史的民間脈絡和變易性”,提出“學術社會史”概念[3]。Trigger在《考古學思想史》中也指出,在書寫考古學史時應注意到,考古學研究受到“考古學家生活和工作的社會情境”的影響[4](P10)。
視角的轉換,往往能夠激活“舊史料”中的“新內容”。社會史視角下,能夠充分發揮《員工傳》有關考古民工及相關記述的史料價值。由是,本文將思考以下三個問題:一是以往考古學史書寫為何基于學科史或學術史視角?二是關注考古民工及其社會生活,從社會史視角出發書寫中國考古學史為何必要、何以可能?三是社會史視角下的考古學史,與學科史、學術史視角下的考古學史有何關系,如何打通兩種不同的考古學史書寫路徑?
二、此前考古學史的書寫成例與初衷
中國考古學史的誕生,正伴隨著現代中國考古學的發軔。由是,1949年前的中國考古學史書寫,事實上是在現代中國考古學尚在起步之時就著手回顧其“歷史”。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1926年梁啟超在《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講演中,首次對“中國考古學”做了歷史回溯。然而,文中所謂的“考古學之過去”,本質上是“金石學之過去”,整篇講演只見北宋歐陽修以降的金石著錄成績,卻幾乎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發掘[5]。當然,這一方面源于梁啟超沒有田野考古經歷,另一方面則應注意到此時中國尚無大規模發掘實踐,僅有安特生仰韶發掘等極少數科學考古活動,中國人掘出的田野第一鏟——李濟的西陰村發掘,只比梁啟超的講演早一周。對于梁啟超的講演,李濟此后在課上不無揶揄地對學生說:“這是中國人的所謂考古學”[6](P171)。換言之,梁啟超所言的考古學,在李濟看來基本與現代考古學無涉。
這一時期還有很多類似的考古學史著述,最著名的當屬衛聚賢的《中國考古小史》和《中國考古學史》。學界一般認為,衛聚賢并不能被視作“考古學家”。雖然他在山西做過發掘,甚至對良渚文化的發現有所貢獻,但他發掘缺乏科學考古的基本要素,所預設的目標也是天馬行空,以至時人為其送上“衛大法師”的雅號[7](P199)。至于其考古學史著述,更接近于擴充梁啟超“金石學著錄成績”,無怪乎李濟在《中國考古小史》序言中為替該書張本,強調考古學存在“舊學根底”,而一筆帶過李素來重視的“自然科學”[8](P119)。
李濟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一文,發表在民國時期發行量最大的通俗刊物《東方雜志》上,這一點暗示李濟撰寫此文時的目標,是向考古學的外行人解釋何為現代考古學。文中,李濟不再將重點放在北宋以降的金石學,而是以“三期論”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破題,回顧了安特生仰韶發掘,以及殷墟發掘、周口店發掘的成績。李濟此文篇幅不算長,更像是中國考古學史漫談。該文之所以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主要因為李濟向公眾介紹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9](P325),借此反觀衛聚賢等人的“考古學史”,則更像是“金石學史”。
民國時期,李濟等考古學家正忙于田野發掘以創立中國考古學,而梁啟超、衛聚賢等學者在中國考古學是什么尚未搞清楚之際就動手做中國考古學史,往往是為了向考古學界之外的讀者介紹何為考古學。基于“正本清源”的中國學術傳統,對中國考古學這一學科的介紹,自然而然地會從“中國考古學史”中帶出。這一點,決定了最初的中國考古學史書寫基本上采取學科史的視角,聚焦考古學科的發生發展。
195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此后田野調查發掘在全國范圍內鋪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考古學由“起步期”邁入“初步發展期”[10](P2-6)。
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內部刊印了學習教材《考古學基礎知識》,其中由徐蘋芳主筆考古學史部分。徐蘋芳在撰文時,部分繼承并創新了梁啟超首開的“北宋以來考古成績”思路,在宋元明清“金石學”之后增補了近代的考古成績。該書的一大創新,是分析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背景,并劃分近代考古學的發展階段[11]。受徐蘋芳此文的影響,此后的中國考古學史書寫基本上形成了一個范式。首先,考古學史往往附屬于《考古學基礎》《考古學理論與實踐》《考古學辭典》等考古學通論性質著述中,作為考古學家向考古學新手學生解釋“何為考古學”的一個時間維度,易言之,書寫考古學史主要旨在厘定考古學科。其次,考古學史的書寫體例大致凝練到三個板塊:一是梳理近代考古學的緣起,如夏鼐在《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中,將五四運動所倡導之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精神、傳統金石學、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視作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背景[12]。二是對近代考古學發展歷程作階段劃分,如張忠培《中國考古學史的幾點認識》以安特生仰韶發掘、梁思永揭示后崗三疊層、蘇秉琦發表《瓦鬲的研究》等,將20世紀中國考古學發展劃出六個時間節點[13]。三是回顧以往考古工作的成績與得失,如王宇信的《近代史學學術成果:考古學》④。
由于此間考古學史書寫著眼于考古學科本身,很容易為外行“看不懂”,甚至在考古學被歸于歷史學科的背景下,一般將考古學史獨立于史學史。進言之,在中國考古學實踐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書寫考古學史,其目的除了廓清何為考古學,更是考古學界內部思考當下考古學學科的發展方向。孫祖初在為陳星燦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所寫的書評中,準確地把握到該書的問題意識,“察古而知今,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尋繹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14]。2021年,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主編的《中國考古學百年史》正式出版,這部集合276位考古學者心血的皇皇巨著,可以說是考古學史研究中學科史取向的集大成者。
當“什么是中國考古學”已經在手鏟與遺址的對話中逐漸清晰,20世紀80年代后,夏鼐與徐蘋芳開啟的“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背景”議題,開始生發出新的研究取向——學術史視角。
張光直在《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的序言中,一口氣提出了八個中國考古學者需要思考的題目,諸如中國文化外來說為什么引起中國學者強烈的反感?1949年以來對中國上古史分期的看法是怎樣來的[15](P3-4)?要回答這些問題,顯然不能僅著眼于回溯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更要探究近代考古學所處的學術背景。這一轉向,被查曉英稱之為考古學史由學科史擴展至學術史[16](P7)。
從考古與近代學術演進史的角度切入,學術史學者嘗試回答以下問題:近代考古學與“古史辨”有何關系,又與傳統金石學有何關系,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如何在近代中國傳播接受。一言以蔽之,考古學在古今中外交織碰撞的近代學術場中處于何種位置,又如何影響近代學術。視角的轉變,使考古學史的書寫主體由考古學家進一步拓展至學術史學者。相關研究的早期代表如俞旦初的《二十世紀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學思想在中國的介紹和影響》、杜正勝的《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沈頌金的《考古學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俞旦初、沈頌金主攻近代學術史,杜正勝在主治上古史外兼及學術史,三人均未受考古學專業教育,亦無考古發掘經歷。學術史學者治考古學史,源于其將考古學視作近代史學學術之一部。這些學者基于學術史視角的研究,展示了一種與此前基于學科史視角所不同的考古學史書寫思路:不再是借“史”來廓清什么是考古學,而是借考古學來審視近代的學術史。此后,羅志田、桑兵、王汎森等知名史家均有論著從考古學的發生發展思考近代學術的演進脈絡。
2010年后,受到Trigger《考古學思想史》的影響,考古學史的學術史研究更突出地關注近代考古學家的學術流派與思想譜系。在此取向下,學術史學者與考古學者“雙向奔赴”,前者不再是看不懂發掘報告的考古門外漢,后者的研究亦不囿于遺址與發掘方法。這一取向下,考古學界的陳洪波、徐堅、孫慶偉,學術史界的查曉英、王興等學者均有相關成果。
總的來看,1949年后中國考古學史書寫視角由學科史拓展到學術史的歷程,正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成熟。也正是因為考古學科自身的成熟,考古學史的關注對象,在李濟、梁思永、夏鼐等科學考古旗幟性人物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擴展到馬衡、衛聚賢等所謂的傳統學者。在近年來考古學的更大繁榮中,有理由將考古民工及其社會生活納入考古學史的書寫視野之中,借以更好地審視近代考古學家開展田野發掘時所處的社會環境。
三、社會史視角下書寫考古學史的必要性、困難與突破口
李永迪在《員工傳》的序言中指出,“考古田野發掘原本仰仗的是當地居民的參與與支持,是一門結合學術象牙塔與民間質樸百姓的草根學科,然而我們習見的是學者爬梳整理的學術成果,鮮有針對參與工作的尋常百姓的著墨。”[1](v)近年來,考古學界對考古學自身天然具有的公共性給予了關注,考古工作的開展必然與公眾、社會高度關聯。王仁湘認為“一切考古活動都可以視為公共考古”[17],曹兵武提出“考古從一啟動實踐就具有了強烈的公共性”[18]。
田野發掘現場既要合理布置探方、揭示文化層,也需要與地方政府接洽、取得土地占有者許可、招雇并組織發掘民工、解決發掘人員的衣食住行,還要盡可能地在與當地民眾的溝通中取得發掘線索、宣傳文物保護知識。由是,考古學史既是考古學科發展史、考古與近代學術演進史,也應包含有社會各界參與考古工作史。近年來已有一些學者注意到近代社會各界對考古工作的參與,初步討論了近代考古學家在發掘前與地方社會圍繞文物歸屬權的交涉,以及發掘結束后文物的展覽⑤。
從社會史視角書寫考古學史,主要有兩個難點。
第一,史料零散。此前研究主要基于《李濟文集》《安陽發掘報告》、史語所檔案等史料,其中有關田野發掘期間社會各界的參與并無系統記述。進而言之,近代社會與考古工作的交叉點之一,正是考古民工。李零在閱讀《員工傳》時注意到考古民工既是來自發掘當地的村民,也是考古工作的參與者[19]。然而,目下僅有《定陵發掘現場指揮白萬玉》等極少數資料對考古民工群體有較多篇幅的記述。
石璋如的《殷虛發掘員工傳》,特別是101位發掘民工的小傳,正是管窺社會參與殷墟發掘,從社會史視角出發書寫考古史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必要重新爬梳原有史料,《石璋如先生口述歷史》《夏鼐日記》《徐旭生日記》《楊鐘健回憶錄》等資料中,均或多或少地提到考古民工及其社會生活。
第二,需進一步凝練問題意識。考古民工及其繁冗的社會生活細節,難以被納入對近代考古學科發生發展,以及考古學與近代學術互動的問題脈絡之中,因而學界多將其視為坊間軼事,寫入面向公眾的科普讀物。譬如《石璋如先生口述歷史》中有關殷墟發掘期間史語所捐資興建洹水學校的記述[20](P120-124),目下僅止于軼聞。由是,如何認識社會參與與考古學史主線間的關系,凝練出社會史視角下考古學史的問題意識,至關重要。
對于從社會史視角出發書寫考古學史,能夠凝練出哪些有價值的問題意識,以下僅就《員工傳》的記述,拋磚引玉地談一些可能的方向。
首先,社會關系研究早為治史者習用,以往考古學史研究主要關注學人間的社會關系。眼光向下,考古發掘民工間亦有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而史語所在組織、管理發掘民工時,對此不但知悉且多有利用。據《員工傳》所載,殷墟發掘主陣地小屯村以何、霍兩家為大姓,何家三兄弟何國楨、何國棟、何國祥皆為史語所招雇的民工,霍家亦以大家長霍鳳東為中心舉家參與發掘[1](P17)。血緣疊加其他因素,又自然形成了發掘民工之中的領導人物。何家老二何國棟最初只是發掘民工,因其手腕不凡,逐漸成為工頭,乃至在辛村發掘時成為總工頭。由于何國棟深受郭寶鈞賞識,逐漸成為河南古跡研究會中“承上接下”的人物,一般人欲拜謁郭寶鈞,必須經過何國棟[1](P9-10)。村民劉廉,系其任小屯村村長的內侄介紹進入發掘團,因而自覺“神氣十足”。劉廉周圍匯聚起一班年輕力壯、“善挖墳墓”的兄弟,而史語所也樂得委劉廉以管理大權[1](P1、3)。
殷墟發掘,先及洹河以南的小屯村,其后逐步延伸到洹河以北的侯家莊、武官村。久而久之,發掘民工以出身洹河南北分為兩派,洹南派以小屯老工人為中心,洹北派則以侯家莊工人為中心。小屯資深工人到洹北參與發掘,是“客卿”,與侯家莊、武官村當地民工間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到了關鍵時刻,方顯小屯“客卿”的重要作用。考古發掘后,需要將土回填,俗稱平坑。平坑無需專業技術,史語所即將平坑包干給侯家莊民工,按日計資。侯家莊發掘工地平坑,實際只需三天,史語所為調動民工的積極性,寬限可五天完成。而侯家莊工人則要求十天,以多得七日工錢,史語所讓步至七天后,侯家莊工人仍不為所動。此時,小屯民工半路殺出,允為七天完成。如是一來,武官村民工為免于一文不得,不得已向史語所方做出讓步[1](P72)。
其次,社會動員是近年來史學研究的一個重點,而考古發掘期間如何刺激發掘民工的積極性,也可以視作某種“學術之于田野”的動員機制。石璋如發現,動員的秘訣之一,是對民工“戴高帽”。發掘時,取土并將之運出是一項耗時費力的工作,而工人們樂于在此間以“打攻擊”的方式自娛。所謂“打攻擊”,即取土工人與挖土工人互相競賽,取土者多取使運土者不堪重負,運土者快運使取土者疲于應付。一番“打攻擊”之下,最積極者被視作“英雄”,而民工一旦得到恭維,發掘進程亦無形加快[1](P81-87)。又如挖掘探坑,原本是嘗試觀察地層的“工具”,但工人們常在攀比中將探坑坑壁鏟得平而再平,如此一來,考古學家對于地層的觀察無疑能夠更清晰[1](P106)。
最后,如果說閱讀史可以視作知識分子中的傳播史,那么發掘民工如何掌握發掘技能,則正是普羅大眾接受新事物的傳播史。針對類型學、地層學等考古方法在近代考古學界的傳播與接受,學界已有相當研究,但對于田野技術如何最終為發掘一線的民工所掌握,則尚有深入考察的空間。
《員工傳》載,除了在發掘時接受考古學家傳授相關技術外,民工原本從事的職業有時也使其掌握相應的發掘技術。小屯村民工劉廉在殷墟發掘停滯期間轉而從事盜墓,待到殷墟發掘復工,劉廉已有辨認土色的經驗。遇見文化層,劉廉即對李濟說:“你看,多大的眼睛珠啊!”[1](P2)眼睛珠系盜墓者術語,指粉碎的土中抱有硬土塊,意即該土非天然土,而是文化層中的文化土。民工王景文原為泥水匠,1931年即參加發掘。王景文的專長是揭露淤土中的遺跡,一般民工遇到夯土包含黃淤土,即挖出淤土保留夯土,而王景文則憑經驗斷定淤土系夯土內所包含物遺跡,必須剝去夯土,露出由淤土填充的器物遺跡[1](P6)。判斷淤土系遺跡很可能來自石璋如等考古學家的點撥,但真正將堅實的夯土從松軟的淤土外剝去,則更多地仰仗其泥水匠技藝。
上述方向,本質上是對“學術與社會互動”論題的進一步延伸。以往對于近代學術與社會的互動,重點關注社會發展大趨勢如何影響學術發展。如從考古民工這一微觀層面來看,學術與社會的互動又含有另一層內容,即考古學、地質學、民族學等受海外影響形成的“田野”學術,如何真正地在中國的“田野”上得到落實。透過《員工傳》的記載可以大致窺見,在考古學家引介海外理論方法、開展考古學本土化的主線之外,尚存在考古民工在一線習得、運用、創新考古技術的“暗流”⑥。
21世紀以來,出版了一系列當代考古學家的各類手記。據筆者粗略統計,自1999年山西省政協文史委編印《山西考古發掘記事》起,截至2023年,已出版各類當代考古學人手記、口述資料50余種。一些資料還形成了系列,如《考古人手記》(共三輯)、《考古學人訪談錄》(目前已出版四輯)。《考古人手記》在約稿之時,注重以考古學家親身經歷,“詳細、生動地敘述發掘的全過程”,“讓讀者知道考古工作者在現場遇到的種種情況”[21](vii)。今后,如從社會史視角審視20世紀后半葉的考古學史,則當代考古學家的田野手記勢必成為重要史料。
四、考古學史書寫中學術史與社會史視角的融合
在梳理考古學史的學科史/學術史與社會史兩種書寫視角的基礎上,有必要思考,討論考古學的學科發展與學術演進,與考察考古學的社會參與間,是否存在某種呼應關系,以使兩種研究最終能夠在某一點上做到會通。翻看《員工傳》,一個有關考古學術的老問題,正有社會史視角下的新生長點。
何日章事件是近代考古學史中的重要公案。1929年殷墟第三次發掘期間,河南圖書館館長兼河南民族博物院負責人何日章,因視殷墟發掘為中央掠奪河南古物,杯葛史語所發掘活動,并在呈準河南省政府后自行開展發掘。何日章強調此舉系保護中州文獻,為爭得輿論制高點,還印發了《發掘安陽殷墟甲骨文之經過》《陳列安陽殷墟甲骨暨器物之感言》兩份傳單。以往被目為守舊派學者的柳詒徵看到傳單后,認為此事本質是中央與地方“政治系統”未能理順,屬于“文化事業之爭執”[22]。對此,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一面認同柳的“確定政治系統論”,一面高擎科學主義大旗,暗示主事者何日章未受現代考古學訓練,其發掘只能是破壞遺跡[23]。最終,在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奔走下,殷墟發掘復工。
論者一般認為,何日章事件的本質是文物歸屬權之爭,并間有史語所科學考古與何日章挖寶式發掘間的分野,何氏的發掘完全基于找甲骨,不作科學記錄,破壞了遺跡的完整性,導致大量非甲骨遺存受到嚴重損壞。相關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史料:最重要的是傅斯年撰寫的《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此外還有《大公報》的報道,《史學雜志》所刊文章,史語所檔案,《傅斯年文集》《傅斯年遺札》《李濟文集》《董作賓先生全集》,以及何日章的《安陽甲骨發掘之回憶》。
研究考古史,最終還是要回到“史”中的田野現場。細思之,無論是河南民族博物院抑或史語所,一旦開啟大規模發掘,都需要招雇小屯當地村民作為民工。《員工傳》中就記錄了一個以往學界在考察何日章與史語所爭端時沒有涉及的“細枝末節”問題:河南民族博物院發掘民工領隊霍全香,是史語所發掘民工領隊何國棟的同村好友。
李濟在多個場合將何日章的發掘視作東施效顰,譬如不知所以然,只簡單模仿史語所,有樣學樣地照相、記錄,但全無系統。然而,透過《員工傳》中有關小屯村村民、發掘民工霍全香的記述,可知此事還有更加具體而微的情景。霍全香與何國棟早年同是古董店學徒,學徒經歷(可能還有盜墓經歷)使兩人都有認土色、剔花土等發掘文物所必需的技能。霍全香被介紹擔任河南民族博物院發掘領隊工人后,何日章以其系小屯本地人,“一切均由他安排”,“以他的意見為依歸”。由是,以往所說的何日章模仿史語所,落實在發掘實操層面,更多是“霍全香們”模仿“何國棟們”。史語所“是有計劃的發掘,開的橫溝、縱溝相互接連,最后連在一起了,叫做大連坑,他們開坑都是用儀器測定的”。何日章一方,在霍全香的指揮下,“學著研究院開坑,研究院開一條縱溝,他也開一條縱溝;研究院開一條橫溝,他也開一條橫溝,最后也有一個大連坑,他們的甲骨大多數出于他們的大連坑內。”霍全香并非發掘外行還有一個例證,1932年殷墟第六、七次發掘期間,霍全香加入史語所的發掘。以石璋如的專業眼光來看,霍全香“拿起抓鉤抓土,拿起小鏟找邊,也真不含糊,的確有兩套。”[1](P90-91)
在模仿史語所開掘探溝一段時間之后,霍“覺得研究院有點迂腐,溝再開的漂亮,不出東西也是枉然,目的是在挖東西而不是開溝,所以后來他們便胡亂挖了”[1](P91)。事實上,如果沒有李濟等考古學家旨在“揭露一切遺跡”的約束,何國棟所領導的史語所民工也很可能走向單純挖寶的“胡亂挖”(正如一些民工在夜間所做)。故此,單考察發掘過程中的技術執行,史語所與河南民族博物院并沒有斷裂性分野,兩方的主要畛域在于發掘主持者有沒有對現代考古學的深入認識:是僅僅挖寶、鑒寶,還是揭露地下一切遺跡。就此,可做一個推論:史語所與何日章兩方的矛盾,從深層來看,不只是何日章在技術上破壞了遺跡,抑或文物歸屬權爭端,更源自傅斯年與李濟反感何日章非科學發掘背后的傳統金石學旨趣——只重視文物本身而對埋藏情況毫不關心。解釋科學考古何以反感金石學,以霍全香的例子來看,僅關注發掘的實際執行不足以說明問題,更要注意到某些思想層面的問題。
由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殷墟發掘的主持者李濟一直對此風波難以釋懷。在1931年發表的《俯身葬》一文中,李濟將有關俯身葬所在文化層的學術討論,引向何日章之業師羅振玉,批評其不知文化層為何物,機械地將殷墟出土物均視作商人遺存。文中,李濟難掩怒火,嘲諷“羅君既以此教人,他的弟子就有服從而無問難的翕然相從;游于羅君之門的若何日章等等諸先生對于殷墟出土的器物也取一種同樣的決然的態度”。“他(指羅振玉)的那種極稀松的大前提作了一班懶學生的保障;依著他的權威,他們居然以為不出門就可考古,不用眼睛就可研究材料;災之棗梨,騰笑外國!”[24](P259-260)事實上,何日章并非全然沒有現代科學意識,在被科學考古學目為“罪人”的同時,何氏也是中國現代圖書文獻分類科學方法的引進者和實踐者。然而,圖書分類畢竟還是書齋之學,相較方法上更接近自然科學的考古學,其科學性相對難以彰顯。
Bahn注意到,在向公眾展示考古成果時,存在“誰來定義呈現給公眾的過去”的問題[25](P93)。同樣,關于何為“現代考古學”,同樣存在“誰來定義”的問題。從《員工傳》所載霍全香的例子來看,如果說安特生、李濟、梁思永等學者從“正面”定義了何為現代的、科學的考古,那么何日章、霍全香事實上從“反面”刺激了傅斯年、李濟等學者進一步加深對現代的、科學的考古的認知。科學考古在近代的流播,既是考古學家引介的結果,也是考古學家與社會各界間碰撞互動的過程。
除《員工傳》外,其他各類考古手記、日記、回憶中,亦記錄有大量兼涉考古學術與社會參與的資料。《石興邦口述考古》中記述,石興邦雖然曾在浙江大學學習人類學,但在1950年參與輝縣發掘時,對于如何辨認土色,仍要向“土夫子”即盜墓者學習。據石興邦回憶,“這批土工,一個個眼力真好”,“挖出的東西,還都能說出點名堂。”[26](P95)現代考古學強調揭露一切遺跡,與旨在挖寶的盜墓有本質區別,但現代考古學在理論方法層面的設計,最終仍要落實在“認土”“找邊”等基本技術層面。當然,“土夫子”對土色的辨認并不完全與現代考古學對文化層的辨認相同。從社會參與考古工作的角度來看,近代考古學的發掘實踐,一方面離不開布設探方、照相、記錄等現代考古技術,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鑒了民間原有的技術。
五、結語
綜上,考古學史的書寫歷程由聚焦考古學科本身開始,此后不斷將視野擴大。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考古學史的問題意識是思考什么是中國的、現代的考古學。20世紀80年代后,考古發掘實踐已足夠多,學術史學者便可以帶著概念清晰的中國現代考古學概念,回溯近代學術場,考察中國考古學的金石學“前身”以及“古史辨”刺激。
到今天,當視野相較學科史為寬的學術史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時,論者似有必要思考,標榜“動手動腳”“走向田野”的近代學術,究竟如何“動手動腳”地走進由普羅大眾所構成的“田野”。如果說田野考古不能重文物而輕地層,那么考古學史的書寫亦應關注近代考古所處的社會歷史“地層”。易言之,社會史視角下書寫考古學史,主張“近代考古學”不僅屬于“考古學”,更屬于“近代”。
此外,書寫社會史視角下的考古學史,也有助于從歷史維度開展公共考古學的理論研究。海外學界關注到,國內近年來在討論公共考古問題時,已將公共考古史作為討論公共考古學的首要任務[27](P51)。公共考古,廣義上即是考古學與社會的多層次互動。社會史視角下的考古學史書寫,可視作考古學史與公共考古學的某種融匯,使公共考古學研究在討論當下如何開展相關實踐的基礎上,通過回溯考古學史,思考中國公共考古的發展歷程并從中汲取經驗。
注釋
① 相關介紹僅見何文競、吳玲《殷墟早年發掘的微歷史——讀〈殷墟發掘員工傳〉》,《中國文物報》2018年10月2日,第7版。
② 目前僅見何凱《考古百年——殷墟考古技師簡史(一)》,《中國文物報》2023年5月19日,第5版;李零《考古筆記》(上冊),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版。
③ 參見吳玲、何文競《考古學的上限與下限》,《大眾考古》,2019年第9期,第28-31頁;何文競、吳玲:《周英學:我國最早的女考古工作者》,《大眾考古》,2017年第9期,第34-36頁;裴世東、陸勤毅《吳金鼎學術人生的塑造與轉向》,《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第67-78頁。
④ 收入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⑤ 見劉承軍、賀輝《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現代考古學規范的建立——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墟發掘為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145-149頁;劉承軍、劉芳《民初中央與地方關系下的學術機構探析——以河南古跡研究會為例》,《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第192-196頁;徐有禮《論殷墟早期發掘中史語所與豫省府間的糾葛——兼及傅斯年、李濟普及科學考古知識的肇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6期,第145-151頁。徐玲《博物館與近代中國公共文化》,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徐堅《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Dashu Qin. Antiquities Market on Archae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ick Merriman. ed. Public Archaeology, Routledge, 2004.
⑥ 徐堅曾注意到“土夫子”在近代考古發掘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但相關討論篇幅有限。見徐堅《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民歌研究暨學術史研討會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