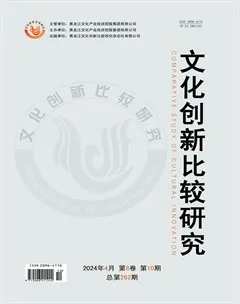“亞文化”傳播對Z世代青年影響的現實審視和探析
齊鵬程 王奇珍 李浩
摘要:Z世代青年參與“亞文化”活動愈發網絡化、游戲化和早熟化,并在演變發展過程中逐漸呈現群體分化、極化的特點。研究發現繁重生活壓力下的自我補償、積極心理暗示下的情感慰藉、強大內生動力下的價值追求,以及相似文化興趣下的流量裂變是催生青年“亞文化”傳播的重要原因。現階段“亞文化”現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增強了青年的個性和熱情,但“飯圈”“佛系”等文化亂象削弱了青年的斗志和骨氣。對此,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涵養校園文化環境、提升青年內生動力、增強歷史認同感和調整文化治理姿態等方面制定對策建議,為青年高質量發展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亞文化;Z世代;虛幻與真相;傳播機制;產生原因;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G122?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4)04(a)-0048-04
A Realistic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ub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 Generation Z-Youth
QI Pengcheng, WANG Qizhen, LI Hao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China)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Generation Z youth in "subcultural" activ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networked, gamified, and precocious, gradually exhib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 differenti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elf compensation under heavy life pressure, emotional comfort unde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ues, value pursuit under stro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flow fission under similar cultural interests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subcultures among young people.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subcultures" has to some extent accelerat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exchange of culture, enhanced the individuality and enthusiasm of young people, but cultural chaos such as fan circles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have weakened their fighting spirit and backbone. In this reg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formul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cultivating the campus cultur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young people, enhancing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identity and adjusting the attitud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ubcultures; Generation Z; Illusion and truth;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Cause of occurrence; Response strategies
“亞文化”作為由主流文化衍生而來具有另類風格和個性特點的附屬文化方式,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變革加速演變、迭代,并在Z世代青年手中創造出許多形形色色、充滿旨趣的文化形態。“亞文化”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青年群體對主流價值導向的認同和傳播,同時也在線上、線下的雙向互動中舒緩了現實生活帶給他們的學業、職場、婚戀、家庭等方面的壓力與焦慮[1]。2022年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數字青年規模達3.24億,占比32%,成為互聯網文化的主力軍。其中玩梗、賣萌、惡搞等具有亞文化典型特征的網絡用語成為當代青年群體交流表達的一種習慣[2]。“恐龍抗狼”“科目三”等網絡熱詞風靡全球,成為主流網絡文化的重要補充,一些主流媒體在公眾號、抖音等渠道也采用類似的表達方式。但從另一角度看,“亞文化”在一些領域發生變質、變味,如“飯圈文化”“次元文化”等在青年群體中造成不良影響[3]。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年是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一個民族的文明素養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準和精神風貌上。”[4]在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時期,相較處于主流地位的社會主流文化,青年“亞文化”憑借其個性化、獨特性的文化心理與行為打破了時空的束縛,從現實與虛擬環境中嵌入青年大眾的日常生活。身處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青年“亞文化”與互聯網媒介之間也表現得更加多樣、動態,如何在規則內理性管控“亞文化”的傳播軌跡和范圍,如何正確引導青年群體規避不同文化間的沖突與矛盾,顯得十分重要[5]。從挖掘青年“亞文化”背后的心理生成機制和價值導向來看,正確厘清青年流行文化的嬗變與沖突等現實問題,能夠有效幫助青年掌握界定自身文化實踐與身份合法性的主動權,從立大志、明大理出發,爭取培育將來成大才、擔大任的時代新人。
1 青年“亞文化”概述
1.1 青年“亞文化”的產生與變遷
“亞文化”的產生是時代進步和社會轉型的歷史縮影,青年“亞文化”的傳播折射出青年群體面對紛擾外部世界的價值選擇,電競手游、街頭嘻哈、“二次元”文化等都體現了相同興趣、共同話題下特定人群的文化偏好[6]。歷經數十年的發展,青年“亞文化”的形態變遷愈發固定并呈現以下四個變化:
一是從反叛對抗到和解共融。從“亞文化”剛開始興起時試圖與社會主流文化分庭抗禮,尋找機會對抗替換,逐漸轉變為與主流文化的和解,形成保留自己特色的“趨主流化”表征。
二是從身份歸屬到興趣圈層。青年“亞文化”經歷了從“憤青”“頑主”等以身份標簽歸屬劃分群體,過渡到以千人千面、百花齊放的興趣標簽自由打造的社群圈層。
三是從松散小眾到大眾聚合。從若干個“非主流”“小眾”的松散小圈子,轉變為呈現“中心—外圍”結構下多元的、有較大群體基數的“亞文化”整合。
四是從價值輸出到情感共鳴。從傳統的單向文化價值輸出逐步發展為以共享性的情感內容、共時性的情感體驗為基礎的雙向情感文化傳遞。
1.2 青年“亞文化”現象產生的原因
1.2.1 身份認同:強大內生動力下的價值追求
在網絡“亞文化”中,青年群體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重點體現在個人身份的認同感高低。在現實社會中,不論個體的能力大小、職位高低、金錢多少,不論曝光在聚光燈下或是處于群體邊緣化狀態,在網絡空間里只要有特殊的技能或特長,部分青年可以獲得與現實身份不相匹配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1.2.2 信息傳播:相似文化興趣下的流量裂變
信息媒介、數據賦能讓身處天南海北但興趣相似的青年個體聯系在一起。“人人自媒體”時代,區別于傳統媒介,“去中心化”的網絡熱詞、流行文學和有趣視頻等都可以隨時生產、發布、傳播,千人千面,迅速走紅并流行于網絡。根據性別、年齡、地域等信息描繪出的個人畫像可以將多元的文化元素進行精準匹配和個性推薦,實現“亞文化”圈層的流量裂變。
1.2.3 現實訴求:繁重生活壓力下的自我補償
伴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競爭加劇等影響,處于“摩天大樓”人口結構的Z世代青年群體在求職就業、婚戀生育、贍養老人等方面承受著來自不同領域的繁重壓力。“佛系”文化、“躺平”主義的出現迎合了部分青年在面對現實與理想差距鴻溝下的訴求,通過娛樂自嘲、行為“擺爛”等來獲取個人對待生活壓迫的內心補償[7]。
1.2.4 情感需要:積極心理暗示下的情感慰藉
“二次元”偶像、“錦鯉”幸運兒等文化現象側面表達出青年群體希望通過支配、主導擬人化的文化對象來獲取情感上的慰藉,希望通過把偶發性、小概率性的事件利用積極的心理暗示來獲得精神上的鼓舞[8]。真實或虛擬的文化載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青年的情感、思想和價值觀念,代表了個人的期望、成長的軌跡、情感的安慰。
2 青年“亞文化”的發展趨勢及傳播影響
2.1 青年“亞文化”的發展趨勢
2.1.1 青年“亞文化”呈現線上線下交融、虛實結合
近年來,動漫、游戲等“二次元”文化在青年“亞文化”圈層里得到廣泛傳播,利用虛擬現實技術,“裸眼”觀賞知音未來的現場演唱會;B站展會嘉年華成為各地UP主為愛“朝圣”的目的地。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網上虛擬偶像走進了現實,受到“后浪”的青睞;另一方面,以現代化的視聽技術為支撐,“宅友”們樂此不疲沉浸在“二次元”構建的虛擬精神家園中,線上線下邊界模糊,虛實相融。
2.1.2 青年“亞文化”的演變呈現出群體分化、極化
“亞文化”的演變過程就是基于每個青年個體針對不同興趣愛好與行為特點的一次群體劃分。相似的人物偏好、相同的價值歸屬、相通的表達互動讓青年個體們在無組織、無意識的高頻活動參與中產生較強的親密感和關聯性。這些不同文化載體間的“小聯盟”不經意間也會引發各種各樣分歧,出現違背綱常的“極化”現象,更有甚者發生激烈的對抗和沖突[9]。
2.2 “亞文化”傳播對Z世代青年的現實影響
2.2.1 “自我”傳播中增強了青年的個性和熱情
青年的流行語言、表情符號、熱詞熱梗等無不彰顯著這一特殊群體張揚的個性和創作熱情。青年個體也皆是“自我”亞文化傳播中的主體力量,看似“叛逆”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繁榮,涌現出“凡爾賽”文學、“遙遙領先”等一批具有時代屬性的文化產品。越來越多的Z時代“科技宅”“潮流人”懷揣著熱情在主流意識形態引領下開創屬于自己一片天地。
2.2.2 “佛系”“躺平”文化削弱了青年的斗志和骨氣
“亞文化”中的許多元素包含了精致享受和拜金消費理念,譏諷“奮斗過時”或者“奮斗無用”的言論。“網紅”“二代”等流量泛濫折射出對于物質享受、利益欲望等虛假“品質”生活的期望。“摸魚”“emo”等否認主體能動意識,體現出逃避社會壓力、得過且過的心理狀態。“佛系”文化削弱了青年的昂揚斗志,“躺平”主義淡化了青年的成長價值[10-11]。
3 突圍:Z世代青年“亞文化”傳播的應對之策
3.1 銳利思想武器,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發揮黨的思想引領作用,以線下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為兩翼,從主流意識形態獲取思想武器,鏟除“亞文化”傳播過程中滋生演化而來的拜金主義、躺平主義、虛無主義,通過正面榜樣學習、典型案例指導,筑牢青年的理想信念根基,將個人價值與社會理想相結合,持續增強青年的底氣、志氣和骨氣。
3.2 推進文化創新,涵養校園文化環境
挖掘新時代、新思想文化內涵,圍繞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主題開展圖文、案例、短視頻等類型的文化產品創作,借助“亞文化”的豐富形式推動主流文化朝著鮮活、生動、有價值的方向發展。“網絡空間并非法外之地”,校園文化中可能會充斥著“亞文化”氣息,需要廉潔自律,應該利用好一切資源壯大網絡育人力量,發揮好教學名師、思政教師、杰出校友等對青年學生的教育引導作用。
3.3 筑牢輿論陣地,提升青年內生動力
筑牢網絡空間中的輿論主陣地,對于引導“亞文化”的正向“發聲”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占領主流媒體輿論陣地,加強網絡輿情監督管理,積極傳遞正能量的文化事件,減少、杜絕“亞文化”傳播中“批紅判白”“斷章取義”現象的發生[12]。青年群體應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尤其是運用好網絡自媒體渠道,敢于主動“亮劍”,繁榮網絡文化空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聲。
3.4 堅定文化自信,增強青年歷史認同感
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堅力量,增強文化自信和歷史認同感是防范錯誤意識形態入侵、把握時代主旋律的價值武器。一方面,厚植家國情懷,從悠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養料,用紅色基因溫潤心靈,用“四史”內涵強健胸襟;另一方面,產生歷史共鳴,堅定和踐行科學唯物歷史觀,站在歷史的深厚基礎上持續提升領悟力、決斷力。
3.5 強調系統整合,調整好文化治理姿態
深刻認識新形勢下不同文化變遷的新理念、新目標、新方式和新手段。以系統整合的觀念,推動“亞文化”在青年群體中有規則、有范圍、有邊界的健康擴張;以“順勢而為”“共榮共建”“未雨綢繆”的治理目標積極引導“亞文化”向主流文化轉變;掌握“亞文化”擴張的流量密碼,包容兼蓄、推陳出新,用知識經濟服務新青年大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給養。
4 結束語
社會變遷、文化隔離、民族差異等是“亞文化”產生與傳播的重要因素,在經歷了與主流文化的反叛弱化、碰撞催化、交融強化等階段,現階段逐漸呈現出主流化轉向之態勢。“亞文化”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市場的繁榮和變革。但不可忽視“亞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文化沖突。要清醒地認識到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建設中,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既要以理性、寬容的態度破除“亞文化”傳播中的保守與封閉,也要學習和融通多元文化里的無限創造活力。完善法律法規,明辨文化是非,確保青年“亞文化”的良性方向,真正匯聚全社會的力量,把規范發展與價值素養培育結合起來,讓青年高質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參考文獻
[1] 汪大本. 網絡青年亞文化的感性化傳播及其引導[J].理論導刊,2023(10):109-114.
[2] 謝加書,張文華. 新階段消極網絡亞文化治理的復雜性論析[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5(4):28-38.
[3] 孫群,王永益.極端“飯圈文化”視域下青年價值觀培育的“難為”與“可為”[J].思想教育研究,2022(7):107-113.
[4] 習近平.習近平關于青少年和共青團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21-22.
[5] 曾昕.情感慰藉、柔性社交、價值變現:青年亞文化視域下的盲盒潮玩[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1):133-141,171-172.
[6] 陳賽金. 近三十年中國網絡青年亞文化變遷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23(3):83-89,99.
[7] 王水雄,周驥騰. 中國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由來、發展與應對[J].中國青年研究,2022(8):28-35.
[8] 楊子強,林澤瑋. 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變遷與治理[J].思想教育研究,2022(2):87-91.
[9] 孟杰. 網絡亞文化對培育青年志氣、骨氣、底氣的影響及應對策略[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2(6):153-159.
[10]付茜茜. 從“內卷”到“躺平”:現代性焦慮與青年亞文化審思[J].青年探索,2022(2):80-90.
[11]曾福文,張莉.增強新時代青年歷史認同的現實審思與有效路徑[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23(11):75-78.
[12]王鷺,陳志勇.社交媒體“擺爛”亞文化的價值流變、行為邏輯與調適政策[J].中國青年研究,2022(11):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