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向的人,青春期總是難過一點兒
閆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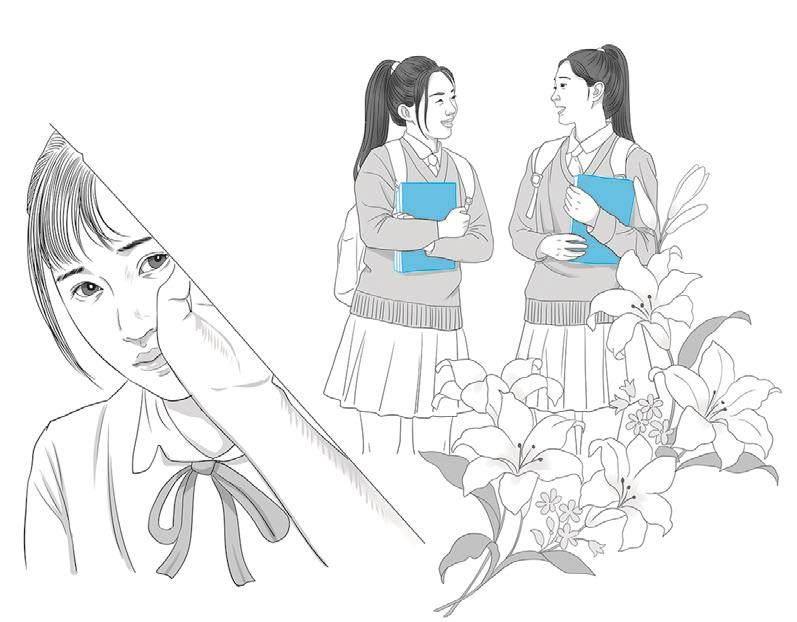
初二那年,我13歲,剛剛進入青春期。我個子不太高,排隊的時候總站在隊尾,這讓堅信我只是晚長的我媽多少有點兒泄氣。她個子很高,年輕時跑過長跑,打過籃球,可我一點兒也不像她。周圍已經不乏亭亭玉立的少女,長長的頭發散發著年輕的光澤,眉眼間透著嬌俏,走起路來也裊裊婷婷的。雖然校服很土,但穿在她們身上還是很熨帖好看。
我悄悄羨慕著那些身姿窈窕的女孩,比如班里那個前額的發辮編得很精致,別著一枚發卡的笑瞇瞇的女孩,比如那個大眼睛扎著粗馬尾說話搖頭晃腦的自信女孩,比如隔壁班那個常穿著牛仔襯衫酷酷的高個子女孩,她們都很好看。更重要的是,她們似乎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常常一群人在一起嘰嘰喳喳地聊天,聊什么并不重要,那種自如的姿態就足以讓我羨慕不已。
這種自卑感還來自一些別的東西。那時班主任不太喜歡我,雖然我的成績很好。班主任創造性地發明了一種“連坐”的制度,座位相鄰的4人為單位結成小組,若小組有一人不交作業或者上課回答不出問題,全組成員放學留下來,罰做值日。
我的同桌是班里倒數第二名,沉默寡言,很少聽見他說話,也從不回答問題。每當他上課被老師點名,我的心便“咯噔”一下,低下頭等待那令人尷尬的沉默,以及老師那句“行了,你坐下吧”。于是,我連著掃了兩個月的地。
不出意外的話,這一年的教室都歸我們4個人打掃。那會兒是放學后掃地,把大家的凳子放到桌子上,拿起笤帚揮舞,教室里彌漫著嗆人的煙塵。我不記得跟我一起打掃的那幾名同學了,只記得灰蒙蒙的天和塵土飛揚的教室。大部分人離開后的教室,有一種恐怖片的感覺。我媽忍無可忍,開家長會時跟班主任提了意見,抱怨我每天回家晚,頭發里都是灰塵,灰頭土臉“像只灰老鼠一樣”,這種“連坐”制度只好結束,恢復了正常的排班值日。班主任那時就覺得我很“多事”吧,而大家都是逆來順受的。
對我而言,更難熬的是休息時間,女生開始扎堆說話、打鬧的時刻,便顯出我的孤寂來。我曾試著去跟一個有氣場的女生表示友好,便提醒她:“包燕燕,你頭發上粘了片草葉,我幫你拿下來吧。”包燕燕瞪了我一眼,沒吭聲。這時另一個女生過來扯她的頭發,大喊:“小包子,你這個壞蛋!”她就喜笑顏開地和對方打鬧成一團。我便縮回我試探的觸角,默默地僵在那里。
有一個周六的早晨,我起晚了,慌慌張張趕到了訓練的體育場,心想一早就點過名了吧?這回又要挨訓了。我找到自己的站位,小聲問旁邊的女生:“點名了嗎?”她搖搖頭。那一次,居然是在訓練結束后點名!膽小的我長舒一口氣,感到非常幸運。
音樂老師站在中心舞臺上,一再拿著擴音器強調說:“參加這樣的大型活動,對我們氣質的培養以及整個人生都有很大的意義!”但活動結束后我感到上當了——什么收獲也沒有,除了臉被曬黑了。可即便如此,當時我也沒有拒絕的權利。當時我相信他們講的那些道理,天真地認為,那特別的意義或許以后會領悟到。
所有的經歷都有其意義吧。比如現在的我,還能記起這件事,就是它的意義。不過,我不擅長說話,也很難在陌生的人群中找到自如感,有輕微的社交恐懼癥,覺得自己不太會被人喜歡,或許就是從那個夏天的操場上開始的吧?
13歲那年我迫切希望快點兒長大,想知道長大后的世界是什么樣的,想要主宰自己的生活。內向的人,青春期總是難過一點兒,還好,之后的我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內向和不自如,長大后才發現,那些光芒和晦暗,可能只是我臆想出來的,在他人的記憶中,我可能也有自己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