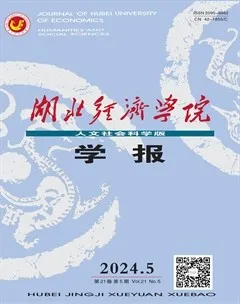土耳其及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的歷程、困境與策略
吳長青 程海燕
摘 要:文章追溯了土耳其及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歷程,分析了困擾土耳其、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本土化過程在觀念和操作兩個層面的困境。文章提出了達成本土化觀念層面共識、穩步解決“三教”問題、充分借助當地華人華僑的影響力三大解決措施,以期對促進中文在世界各國的本土化傳播提供可行性借鑒。
關鍵詞:土耳其;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
基金項目:2022年國際中文教育研究課題“土耳其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策略研究”(22YH03B);2021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研究”專項“土耳其及中亞斯坦五國語言政策研究”(21YDD07)
作者簡介:吳長青(1974- ),男,湖北荊州人,湖北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區域與國別語言政策、語言哲學;程海燕(1982- ),女,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孔子學院。
土耳其共和國是在隕落的奧斯曼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亞歐新興國家,近代經歷了同舊中國類似的被歐洲列強入侵的屈辱歷史。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于1923年,已迎來百年國慶。土耳其99.7%的領土在亞洲,僅有0.3%的領土在歐洲,全國絕大多數民眾信封伊斯蘭教,東部與敘利亞、伊拉克、伊朗、格魯吉亞等國接壤,西部與希臘、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相鄰,土耳其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東西融合的文化特質。由于土耳其多年來加入歐盟的努力一再受挫等歷史雜陳的原因,近十年來對外政策“東方轉向”的趨勢非常明顯:一方面努力與東方國家包括中國交好;另一方面,自俄烏沖突以來,積極利用北約成員國的特殊身份,為沖突雙方竭力斡旋頗受世界的關注。土耳其國際中文教育雖可追溯至土耳其建國初期,但現代意義的中文教育在土耳其立足生根卻發生在近十來年。中亞五國的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直接與中國的新疆接壤,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則是中國連接西亞國家的伊朗,進而連接土耳其和東歐各國的必然陸路通道,中亞五國歷來與中國保持友好。加強對土耳其及中亞五國的語言政策研究,發掘各國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的困境與策略,將為“中國文化走出去”鋪設語言的基石,對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的“民心相通”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土耳其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的歷程
有學者認為“本土化”是英文localization的不同譯釋,也有譯為“在地化”、“當地化”。土耳其1923年建國后,開國元勛凱末爾對現代教育非常重視,力主通過向西方教育學習來逐步實現本國的教育現代化。近100年來,土耳其現代教育體制發生了多次變革,直至2011年頒布的《土耳其教育組織機構與職責相關法》明確了總統負責制下的高等教育委員會與教育部并行的教育運行機制[1],分別負責全國高等學校(非義務教育階段)及高等學校以外(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事務。高等教育委員會下設大學校長聯席會、大學理事會和高等教育監事會,土耳其相關高校開展的國際中文教育事宜就隸屬于大學理事會管理。土耳其教育部則負責高等教育以外事務,在組織層級上分國家、省(市)和縣三級,在教育部的直屬管理機構中亦有專門針對基礎教育中有關國際教育管理的部門。
土耳其在建國初期的20世紀30-40年代就與彼時的國民政府聯系密切,乃至早在1935年即在首都的安卡拉大學設立漢學系,土耳其公立大學漢學系的建立可以算是土耳其中文(漢語)本土化傳播的最早發源地。1971年中土建交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土中關系在波折中向前發展,土耳其國民對中文學習以及對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了解的愿望愈加迫切,土耳其高等院校開始重視中文(漢語)的教學。尤其自2008年土耳其最負盛名的公立中東技術大學設立全國第一所孔子學院(國內合作院校為廈門大學),2013年后相繼成立海峽大學孔子學院(國內合作院校為上海大學)、奧坎大學孔子學院(國內合作院校為北京語言大學)和耶迪特佩大學孔子學院(國內合作院校為南開大學)[2]。據統計(2017年數據),土耳其全國109所公立大學,76所私立大學中的不到20所大學,或設立有漢學系,如:安卡拉大學(Ankara University)、奧坎大學(Okan University)、伊斯坦布爾大學(Istanbul University)、埃爾吉耶斯大學(Erciyes University);或開設了中文課程,如:公立的中東技術大學(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哈捷特帕大學(Hacettepe University)、海峽大學(Bo?azi?i University)、5.19大學(5.19 University)、加濟安泰普大學(Gaziantep University)及私立的比爾坎特大學(Bilkent University)、羌卡雅大學(Cankaya University)、耶迪特佩大學(Yeditepe University)、伊茲密爾經濟大學(Izmir University of Economics)等。
土耳其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歷程的另一條路徑是通過基礎教育。2012年土耳其基礎教育改革明確將義務教育階段由過去的8年制延長到現今的12年制[3],即“4+4+4”各階段均為4年的模式:4年小學教育、4年初等教育、4年中等教育,類似中國基礎教育的小學、初中和高中三個階段。依據土耳其義務教育法,教育部對青少年階段小學和初中的外語課程有嚴格的設限,門檻頗高,在首都安卡拉僅有寥寥幾所小學、初中一貫制的學校開設了中文選修課,如:佳蕾(Jale Tezer Koleji)、奧努爾(Onur Koleji)、阿斯燕(Asiyan Koleji)、歐雅阿肯(Oya Ak?n Y?ld?z Koleji)、白楊溪(Kavakl?dere Ortaokulu)等學校大多是在中東技術大學孔子學院的支持與幫助下開設有中文選修課,這些學校也以此作為招生的亮點,且絕大多數為收費昂貴的私立學校。除與國內相似的高中教育體系分為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之外,與國內不同的是,土耳其的普通高中又分為兩種不同類型。一種是為參加高考準備的常規普通教育型高中(Genel Lisesi),畢業后參加高考進入到大學階段的學習。另一種則是特殊類型的普通高中,其中包括以外語見長的外國語(安納多努)高中(Anadolu Lisesi)、以理科見長的科學高中(Fen Lisesi)、以宗教為特色的宗教高中(Imam-Hatip Lisesi)、以藝術為特色的藝術高中(GüzelSanatlar Lisesi)以及收費高昂的私立高中(Kolej)。據調查,位于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開設有中文課程的高中也并不多見,且全部是以外語見長的安納多努特殊類型的高中,如:阿塔圖爾克高中(Ataturk Anadolu Lisesi)、艾冉哲高中(Ayranc? Anadolu Lisesi)、厄提雷爾職業高中(Etiler Mesleki ve Teknik Anadolu Lisesi)等。相較于土耳其近6萬所中小學校,能開設中文的土耳其中小學可謂滄海之一粟,國際中文基礎教育階段的土耳其本土化可以說仍處于起步階段。
二、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歷程
中亞五國的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進程也基本是通過大學和中小學校兩條路徑來實現的。其中,哈薩克斯坦及吉爾吉斯斯坦基礎較好。哈薩克斯坦高等院校的國際中文教育主要集中于自2007年以來相繼建立在歐亞大學、國立民族大學、阿克托別州諸巴諾夫國立大學、卡拉干達國立技術大學和阿布萊汗國際關系與外國語大學的孔子學院,此外還有6所設立有中文專業的大學、10所設在大學的中文教學中心[4]。吉爾吉斯斯坦則主要集中于自2007年相繼建立在比什凱克大學、國立民族大學、賈拉拉巴德國立大學及奧什國立大學的孔子學院;塔吉克斯坦及烏茲別克斯坦則基礎相對較弱,塔吉克斯坦高等院校的國際中文教育主要集中于自2009年相繼成立的塔吉克斯坦坦國立民族大學和冶金學院的孔子學院,烏茲別克斯坦自2005年建立的塔什干國立東方學院和撒馬爾罕國立外國語學院的孔子學院;位于中亞南部的內陸國家土庫曼斯坦雖是中亞第二大國,但因其永久中立國地位,對外來語言和文化秉持謹慎態度,高校中至今沒有建立孔子學院,僅有4所高校開設有中文專業[5]。
中亞國家國際中文教育在中小學校的起步要比大學更早。早在1959年,彼時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就將第五十九中學及塔什干外語學校作為中文教學的試點[6],現今仍有兩所高中延續中文教學,分別是塔什干國立東方學院附屬高中和塔什干國立師范大學附屬高中;在國際中文教育基礎最好的吉爾吉斯斯坦,盡管全國人口僅600余萬,但國民學習中文的熱情卻非常高,除四所大學合作建立的孔子學院之外,該國的7個州中的5個州及2個市的大部分公立學校都開設了中文選修課,部分學校,如:南部的奧斯曼諾夫中學甚至將中文列為必修課,據2012年數據,在吉爾吉斯境內學習漢語的大、中、小學生就已達到4萬人[7];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在中亞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國旨在培養蘇中外交與經貿交流語言人才,在各地中學也開設有中文課程,如: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國際學校、阿拉木圖市第31中學、184中學等;中文教育在中學基礎同樣較弱的仍是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前者僅有6所中小學校開設有中文選修課,分別是公立的第1語言中學、第2語言中學和第94中學及私立的卡夫拉特中學、杜尚別國際學校和總統中學;直到2016年,土庫曼斯坦時任駐華大使齊娜爾·魯斯塔莫娃曾接受采訪,表達將在中小學階段開設中文作為第二外語,但進展并不順利。
三、土耳其及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面臨的困境
土耳其及中亞五國有非常類似的地理位置,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歷程、態勢也非常接近,歷經數十年尤其自建立孔子學院以來,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無論是大、中、小學校開設中文課程的數量,還是學習中文的絕對人數,在近10年來都有了非常明顯的提升,中國文化在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的傳播正深刻地影響著當地普通民眾對中國的認知。但是,土耳其及中亞國家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的進程與未來雙邊合作前景的預期,及其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國家的身份還遠不匹配。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觀念層面尚未在當地達成完全的共識。其二是國際中文教育深度融入本土化教育體制操作層面仍存有較大困難。
(一)本土化觀念層面的共識難達一致
與世界各國的語言推廣機構,如法語聯盟、歌德學院不同的是,作為國際中文教育的主體,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國家漢辦)及孔子學院總部始終秉持國際中文本土化的理念,主張將國際中文教學與文化推廣植根于所在國家大學并努力與其融為一體,而且這一做法早期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本土化融入效果,優勢也非常明顯,體現在孔子學院中文課程普遍納入到所在高校的課程體系,有明確的課程編碼、課程大綱和考試要求等,與所在學校其他外語類課程渾然一體,中文甚至逐漸成為所在高校除英語之外最受歡迎的第二外語。但伴隨孔子學院通過在承辦高校以外不斷擴大教學范圍,擴大中文學習者受眾數量與規模,這一模式造成的觀念沖突也日漸凸顯。大多承辦高校或明確或含蓄地表明:對孔子學院過多開展所在高校以外的中文教育或文化推廣活動存在不同的聲音,大部分承辦高校都不太鼓勵孔子學院支持私立的教育機構開展中文教學,甚至部分承辦高校表達反對擴大孔子學院的中學教學點。在政府層面,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教育部門對審批新的合作共建孔子學院保持著類似觀念上的警惕。加之基礎教育階段中小學所需的本土化中文師資、本土化中文教材、本土化中文教學法等天然的匱乏,都對國際中文落地土耳其及中亞國家帶來巨大的障礙。即便是在2020年前溯三年,土耳其及中亞五國中小學校中文課程開設的數量及學習人數并未顯著增加,基本應驗了這一判斷。
(二)本土化操作層面的困難
國際中文教育深度融入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本土化教育體制操作層面的困難實際也是中文國際推廣在大多數國家面臨的共性困難,即“教師、教材和教法”的“三教”困難。有學者將本土化大體界定為:教師本土化、教材本土化、教學本土化、教務本土化。參照這一體系,土耳其及中亞五國“三教”的本土化問題非常明顯。以中文教育基礎最好的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和吉爾吉斯斯坦國立民族大學孔子學院為例,該孔子學院有多所附屬孔子課堂和上十個教學點,常年有教師數十名,但其中本土化教師占比不到50%,而其他孔子學院的本土化教師占比要遠低于這個比例,基本是依托中方外派的中文教師及中文教師志愿者。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的本土化中文教材編寫也不盡人意。近年來,盡管各國啟動了基于本國語言或以俄語為對照語言的中文教材的編寫,但總體基本是一般性通用教材,高質量的本土化教材少之又少,這為中文學習者尤其是中文在中亞國家的啟蒙教育增加了難度。此外,由于本土化教師的匱乏,中方選派的教師又以英語為中介語開展教學,加上教師流動頻繁,對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的宗教信仰、風土人情、思維方式等不熟悉等特點,很難開展行之有效、因地制宜的教學方法,從而很難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
四、土耳其及中亞五國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策略
(一)努力達成本土化觀念層面共識
達成本土化觀念層面共識是推動中文國際教育在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發展的前提。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民眾對中文學習持續增長的需求基本面沒有改變。在這一前提下,代表政府的中國駐土耳其及中亞國家使領館與所在國家各部委、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與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承辦孔子學院的雙方高校等都應積極加強溝通,尋求共贏,開展多元層次的交流與合作。除孔子學院層面的語言文化交流之外,雙方還可以就土耳其及中亞國家主要城市“中國文化中心”的建設打開新局面。中國文化中心不但可以承載兩國文化溝通與交流的主要使命,還可以彌補孔子學院無法輻射到的所在國中小學校和私立教育機構的中文教育。此外,孔子學院本身也可以充分利用扎根當地的優勢,主動爭取當地政府主管部門及承辦高校的理解與認可。國際中文教育在中亞國家的本土化過程,根本而言是在順應中國與土耳其及中亞國家關系未來發展趨勢,為本國培養相關語言人才儲備所做的積極努力。
(二)穩步解決“三教”問題
穩步解決“三教”問題是提升中文國際教育在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本土化發展的關鍵。本土中文教師的相對匱乏、通用國際中文教程及普適性的中文教學法的水土不服是制約中文教育在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本土化的主要瓶頸。積極應對并著力解決以上瓶頸,可以考慮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可以通過支持并培育本土教育機構來化解。例如:通過嫁接國內高校與中亞國家具有漢學系但又尚未建立孔子學院高校之間的橋梁,開展本土國際中文教師互派培訓,開展雙方高校中文專業畢業生海外實習等活動,不但可以為土耳其及中亞國家中文教育解決本土化師資問題另辟蹊徑,還可以為所在國高校培養高質量的中文專業畢業生提供可行性幫助。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開展土耳其及中亞國家“三教”問題專項課題研究,總結、深化并夯實國際中文所在國本土化的成果。近年來,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發布了年度研究課題,針對區域與國別國際中文本土化的研究成了熱點之一,這必將對進一步深化土耳其及中亞國家國際中文本土化“三教”問題的研究起到積極推動作用。語合中心甚至還可以分國別發布專項課題研究指南,適度開放所在國本土國際中文教師申報的準入機制,激發本土化中文教師聚焦“三教”問題研究的熱情,并適時轉化為本土中文教師的培養、本土中文教材的編撰、本土中文教學法的實踐。
(三)充分借助當地華人華僑的影響力
充分借助當地華人華僑的影響力是助力中文國際教育在中亞國家本土化發展的重要補充。實踐表明,充分借助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愛國華人華僑的影響力開展相關活動往往事半而功倍。事實上,土耳其及中亞國家本土化中文教師中許多是華人華僑,或因通婚,或因留學而留在了當地,這一群體常年生活在當地,深諳所在國的語言和文化,又普遍對祖國有強烈的歸屬感,更為重要的是,他(她)們的背后是數十上百個與之關聯的所在國的家庭,通過這些家庭良性的輻射效應,在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的民間會逐漸匯聚成一股股“知華”“友華”人士的涓涓細流。
參考文獻:
[1] 劉軍,王亞克.土耳其教育體制與漢語國際教育研究[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9,17(3):62-71.
[2] 劉進,徐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高等教育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以土耳其為例[J].世界教育信息,2019,32(1):34-38.
[3] 程海燕.從土耳其基礎教育階段中文教學現狀看國際中文教育在地化發展策略[J].華中學術,2022,14(2):210-219.
[4] 梁焱,焦健.中亞孔子學院發展現狀、問題與策略研究[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9(2):97-100.
[5] 李琰,聶曦.中亞高校漢語國際教育發展現狀研究[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5):77-84.
[6] 李雅梅.絲綢之路上的漢語驛站——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漢語教學[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5):89-92.
[7] 鄭婕.吉爾吉斯斯坦漢語教育現狀及相關對策[J].民族教育研究,2017,28(3):86-94.